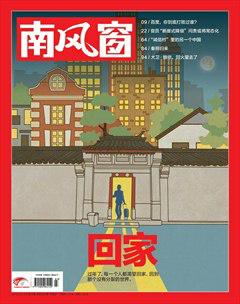百年變遷,中國人“家”安何處?
張墨寧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家庭形態(tài)、家庭觀念隨著社會轉(zhuǎn)型不斷改變,家庭與國家、社會的關(guān)系也幾經(jīng)再造,家庭所承擔功能的嬗變,便是中國人精神空間或拓展或循舊的過程。

著名攝影家海達·莫理循(Morrison ,Hedda)女士于1933年至1946年在北京居住;此間,她拍攝了數(shù)以千計的照片,這些作品系統(tǒng)地呈現(xiàn)出北京市民的家庭生活。
過了農(nóng)歷年,才算是辭舊迎新。大部分中國人的內(nèi)心是以圓滿和團聚作為丈量時間的尺度。短暫而溫情的停頓是為了下一年更有力的前行。或者說,回家即是為了離開。去遠方,這已經(jīng)是今天中國人的主體生活,在一個流變的時代中追逐、給養(yǎng),而回家,反而成了一個詩意的彼岸。
一百年來,中國人的家庭形態(tài)、家庭觀念隨著社會轉(zhuǎn)型不斷改變,家庭與國家、社會的關(guān)系也幾經(jīng)再造,家庭所承擔功能的嬗變,便是中國人精神空間或拓展或循舊的過程。
家庭與社會思潮 ? ?
上世紀初的啟蒙運動中,各派知識分子都認為家庭革命是社會變革的基礎(chǔ)。以“父權(quán)”、“三綱”為核心的傳統(tǒng)家庭是反封建、反專制首先要打破的秩序。家庭革命因而與文學革命一起,成為對中國社會危機和文化危機的先鋒性回應。
較早主張廢除家庭的是康有為,他在《大同書》中倡導男女平等,各自獨立,取消家庭、家族和家產(chǎn),認為孕婦應入胎教院,嬰兒應入育嬰院,長大后依次進入蒙養(yǎng)院和各級學校,病人應入養(yǎng)病院,老人應入養(yǎng)老院。
辛亥革命的輿論家則更為激進,認為中國傳統(tǒng)家庭制度扼殺自由,剝奪人權(quán),踐踏正義,是強權(quán)的根源,是導致“自由死”、“國權(quán)死”、“國民死”的禍端,所以提出了“欲革國命,先革家命”、“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這樣的口號。
到了“五四”時期,《三綱革命》、《家庭革命》之類的文章大量出現(xiàn)。其中,許多無政府主義者認為家庭是萬惡之源,所以主張取消家庭制度。例如劉師培以“申叔”的署名,在《天義報》上發(fā)表的《毀家論》中說:“欲開社會革命之幕者,必自破家始。”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同,當時的民主主義革命派并不主張個體家庭的解體,而是反對封建家長制,倡導家庭革命,建立新型的家庭關(guān)系。陳獨秀等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都曾經(jīng)提出中國傳統(tǒng)家庭制度對個人獨立和個人意志的破壞,主張以“個人本位主義”取代“家族本位主義”。“五四”以來的文學作品比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就對于三、四十年代許多知識青年沖出舊家庭的藩籬,走向革命,起到了啟蒙的作用。
經(jīng)過了這一輪對傳統(tǒng)文化的撻伐,現(xiàn)代的家庭觀念已經(jīng)基本建立。新的社會制度和倫理準則得以形成。隨著家族、宗族這樣的原有基本單位的解體,首先發(fā)生變化的是家庭規(guī)模和結(jié)構(gòu),如果以親屬關(guān)系為標準劃分,家庭結(jié)構(gòu)可以分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聯(lián)合家庭等,“革命”使得相對簡單的核心家庭成為主體,家庭規(guī)模開始縮小。父家長的權(quán)威受到了極大挑戰(zhàn),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開始向更加平等過渡,延伸出的婆媳、兄弟、妯娌關(guān)系也日漸松動。總之,受到政治制度和社會思潮劇變的影響,中國人的家庭觀念以及家庭成員的關(guān)系都開始與傳統(tǒng)儒家社會中的秩序安排相疏離。
另一個家庭受政治思潮和社會運動較深的時期是“文革”。對家長權(quán)威的挑戰(zhàn)和對倫理準則的顛覆以一種非常激烈的方式進行。這一時期的“家庭革命”受到政治滲入的程度更深,家庭的基本聯(lián)系除了親情、血緣之外,還增加了政治立場、政治原則以及階級成分等因素,這些都在挑動家庭成員之間的對立性,從而在心理上重新塑造親緣關(guān)系。
從歷史梳理我們可以看到,家庭革命基本上是圍繞反家長制而進行,從而呼應社會、政治層面的反權(quán)威。中國人開始對家有了更多理想化的追求,家的意義不再僅僅是基于天然聯(lián)系的被動接受和承認,而是要成為個人價值實現(xiàn)的牢固保障,至少也不能成為阻力。期間,《婚姻法》的確立則是一個較大的制度化影響,傳統(tǒng)婚姻模式的顛覆成為家庭變遷的基礎(chǔ)。從上世紀初算起的話,家庭受到政治沖擊的影響是一個漸弱的過程,隨著對傳統(tǒng)文化的重新檢視和復興,家庭的基本秩序和在人的精神層面的作用開始被看重,并且固定下來。此后,雖然受到計劃生育、婚姻法修改這樣一些外在制度的變更,但家庭觀念已經(jīng)很難被沖擊。
家庭社會功能的變化 ? ?
從社會學意義上來說,家庭的基本功能無非是生活保障、社會化、繁衍、經(jīng)濟合作等。但是在不同的階段,每一種功能發(fā)揮的重要程度則不同。新中國成立后,家庭不僅是一個生產(chǎn)單位,而且承擔了部分政治非正式組織的作用,隨著中國經(jīng)濟、社會秩序的正常化確立,后一種功能漸漸消失,而生產(chǎn)單位的功能則越來越強。尤其是在以農(nóng)村為起點的社會改革發(fā)生后,中國家庭的價值體系也進一步世俗化,經(jīng)濟理性開始成為壓倒性的功能。
與以往不同的是,這一次家庭結(jié)構(gòu)和觀念受到的沖擊是來自于社會發(fā)展模式的改變。在農(nóng)村的表現(xiàn)尤為明顯,人們積累財富的方式從農(nóng)業(yè)轉(zhuǎn)向了半工半農(nóng)。由此對鄉(xiāng)土中國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首先表現(xiàn)為子女成年后的分家制,盡管分家制不是近現(xiàn)代才出現(xiàn),但是對剛剛從集體制中脫離的人們來說,盡力甩開負擔、避免平均主義,以小家庭為基本單位去創(chuàng)造財富更符合經(jīng)濟理性和時代趨勢。
在此過程中,父權(quán)自然而然就出現(xiàn)了衰落。至于原因,首先是家族文化的落寞,革命已經(jīng)將宗族制度摧毀,改革開放以來,雖然一些地方的宗族借助舊秩序的消解而重新強化自己的勢力,但是宗族力量普遍是被削弱的,那么家長、族長的權(quán)威性一定也是隨之而減弱。而更為重要的原因是,在以解放和發(fā)展生產(chǎn)力的價值主導下,家長的勞動創(chuàng)造力是一個持續(xù)減退的過程,他們的權(quán)威程度越來越多與創(chuàng)造財富的能力相聯(lián)系。由此導致的最嚴重的結(jié)果就是從80年代開始,分割財產(chǎn)時的齟齬和養(yǎng)老危機成為農(nóng)村家庭的兩大矛盾。尤其是城鎮(zhèn)化發(fā)展加速以來,農(nóng)村的空巢現(xiàn)象已經(jīng)越來越嚴重,年長者的社會屬性幾乎沒有了,完全成了弱勢群體。

1960年代的中國民兵家庭。
家庭實體結(jié)構(gòu)也被肢解。目前,一個大家庭中的青壯年夫婦外出謀生,老人和小孩留守已經(jīng)成為農(nóng)村社會的主要模式,家庭成員的聯(lián)系非常松散。無論從財富創(chuàng)造、生活方式還是精神信仰上,家庭中的第二代已經(jīng)完全成為主要提供者,與傳統(tǒng)社會家庭權(quán)威的代際傳遞速度相比,現(xiàn)在的“交接班”明顯加快。家,對于那些在外面謀生、供養(yǎng)親人的青壯年來說,更多的意義是讓他們的下一代能夠順利成長的地方,他們把更多的夢想和期待放到了異鄉(xiāng),提高家庭的生活質(zhì)量和物質(zhì)水平成為他們最重要的生活目標。
在城市中,空巢現(xiàn)象也非常明顯。尤其是住房商業(yè)化發(fā)展之后,無論是不是獨生子女,尋求獨立的生活空間已經(jīng)成為最基本的成長訴求。子女在同一個城市但與其分開單住的老人,兒女遠在外地老年人獨居的家庭越來越多。有一個變化值得注意,那就是隨著城市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和養(yǎng)老機構(gòu)的發(fā)展,老年人對自己未來歸屬的擔憂似乎沒有以前那么強烈了,如果他們的子女是70后,現(xiàn)在面臨的是下一代教育、事業(yè)上升瓶頸期的壓力,如果是80后、90后,則處在激烈競爭找工作、買房子、找對象的小家庭建立期。因此,老年人對子女的期待變得沒那么多要求了,雙方的感情約束和孝道倫理的綁架都在減少。
社會分化后的“家”
總體來說,以生產(chǎn)和財富積累為主要的家庭形態(tài)是追求小而精的過程,大家庭分化,家庭成員的關(guān)系變得理性、道德感消退。而從2000年開始,隨著財富原始積累期的結(jié)束和社會深層分化的來臨,尤其是上一輪高房價模式的開啟,使得家庭的功能似乎又在發(fā)生新的變化,生產(chǎn)單位的屬性已經(jīng)不是最明顯的特征了,用“共同體”來形容可能更為恰當,社會成本的上升使得家庭成員之間共同承擔風險的能力變得更加重要。
這一階段,家庭的價值上升,原生家庭、新生家庭;核心家庭、聯(lián)合家庭之間是一個重新聚合的過程。由于貧富差距的擴大以及出身在一個人成功的因素中重新占據(jù)重要位置,家庭的資源屬性變得重要,家庭、家族成為人脈和關(guān)系網(wǎng)的天然聯(lián)結(jié),以此為基礎(chǔ),可以建立更大更牢固的網(wǎng)絡,是一個人整合資源最值得信任的依靠。高房價、社會風險和變數(shù)的增大都在促使家庭成員之間成為分攤負擔不可缺少的部分,不但可以共同抵御風險,而且還能幫扶實現(xiàn)買房“融資”等一系列建立小家庭的必備條件。

1933年至1946年,北京市民的家庭生活。

從心理上來說,一個人獨立之后對原生家庭的情感依賴也在增加。競爭壓力和漂泊感讓人們更多從一種穩(wěn)定、輕松而又真誠的關(guān)系中獲取幸福感。而城市化的加速發(fā)展對舊的居住空間和記憶的毀滅則進一步加深了對“故鄉(xiāng)”的眷戀。“家”和“故鄉(xiāng)”有時候更多是一種退舍。
由此所導致的另一重表現(xiàn)是,父母與子女關(guān)系也不同于以往了,財富的重新布局和中產(chǎn)階級的崛起,使得家庭、家長對子女的影響和控制力與日俱增。從上學、工作、婚姻、到帶小孩無所不包。也就是說,家長能夠提供的價值和施加的影響力在增強,家庭成員之間已經(jīng)完全不是上世紀初那樣以個性解放為追求的緊張關(guān)系。
而在今天這樣一個社群化為未來趨勢的時代中,新的變化又在醞釀。在趣味、生活態(tài)度、主張這些變得越來越重要的精神需求中,家庭的影響力是極其微弱的。年輕人已經(jīng)很難保持以家庭作為自己的情感動力,而更多是從朋友、以共同興趣為紐帶的人際交往中獲取。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在未來,或許家庭不在是一個深沉的、詩意的心靈歸屬,而是與個體、社群相差無幾的單元,并不會有特殊意義。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么我們今天對“家”的精神依歸顯得更加稀缺而珍貴,更應該抓住這或許是“最后的”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