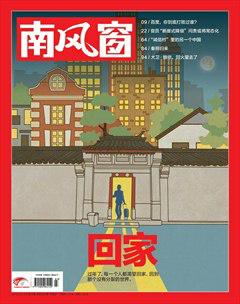中產做創投,如何破解“業余化”?
譚保羅
中產做創投,如何破解“業余化”?
“一起開工”社區由一間舊廠房改造而成,別具一格的設計風格和開放式的辦公空間吸引了超過13個常駐創業團隊和眾多年輕創客會員加入。



2016一個打趣的說法是,中國的90后年輕人之中,一半在創業,另一半在做創投。
這顯然夸張,但創投熱的確是中國經濟時下的一個獨特景象。數據顯示,在深圳這樣的“創業熱土”,投資機構的數量甚至在3年時間內翻了10倍。
對普通中國人而言,能快速實現財富增值的投資,一是債權投資,二是股權投資。前者主要通過購買信托計劃或者參與P2P來進行,而后者則是通過買二級市場股票,或做創投來投資一級市場。當下,前景不明的股市正讓越來越多的人卻步,那么投資一級市場是否是一條新路?
不過,在創投熱之下,一個悖論也不容忽視。一方面,創投機構LP的“門檻”不低,普通的中產者難以企及,這意味著他們會失去投資的“權利”。另一方面,監管“門檻”也是基于普通人風險承受能力不強,投資專業技能不夠的原因而設定。
在這種局面下,如何破解這個悖論?顯然,創投機構和律師們有的是解決方案。
天使投資人
中國的有錢人總是多得超過窮人的想象,窮人在思考如何賺錢,而有錢人則在尋找如何“錢生錢”。
2016年的第二個周末,前Intel工程師王大慶從江蘇趕到深圳一個名為“前創匯·創投天使匯”的論壇,并上演了他的“個人秀”。
他的目的是要融資。作為一家創業企業江蘇博悅物聯網技術公司的負責人,他希望通過一場“路演”吸引投資人。這些投資,可能來自于機構投資人,也可能來自于臺下的數百位“有錢”的個人投資者。
博悅公司的業務是智能家居,其“產品”之一是一款可移動的智能家電開關。“路演”臺上,王大慶拿著這款新產品,向聽眾介紹它的“緣起”。
王大慶說,自己曾是Intel公司的產品經理,曾在上海參與過衛星定位系統的研發。但他認為,衛星定位產品的市場太小,并不足以彰顯自己在商業上的雄心。所以,他選擇了創業。
在他的描述中,這家公司的未來藍圖是,攫取智能家居不可限量的“大蛋糕”,同時提供一整套社區服務的體系。主要市場是未來的中國一二線城市,而產品“切入點”正是他手中這款開關。
一般的家庭裝修,業主和施工隊之間存在太大的信息不對稱,這使得業主經常被施工隊要高價。特別是電路系統,施工隊可能故意增加施工復雜性,以提高造價。
通過這款智能開關,則可以簡化電路系統,在原有系統上實現新電器控制的“零增加成本”,從而改善裝修中業主長期的“弱勢地位”。
“市場是巨大的,比我之前做衛星大得多。”王大慶介紹,公司的目標是在2016年實現收入過千萬,同時在新三板掛牌。本次融資,只計劃出售10%的股份,融資額為800萬元人民幣。資金用途是補充凈資本和做市場拓展。
他介紹完畢之后,臺下十余名“專家評委”開始了輪番轟炸。“你憑什么估值這么高?”“你的注冊資本是實繳嗎?”這些問題主要來自于法律、會計和經營策略等方面。
除了王大慶,還有另外幾名創業者上臺“路演”,流程和王大慶一樣,先是展示和演講,隨后是專家挑戰和觀眾提問。總體而言,這場“前創匯”創業者路演的模式和流程,和目前中國流行的電視真人選秀節目如出一轍。
一位參會的聽眾對《南風窗》記者說,“買房子的一次性投入太大,深圳的房子又漲了,現在不是投資良機。”她是一位家庭婦女,先生是一位成功的職業人士,她說股市不好,理財產品的收益也越來越低,所以想做股權投資。
幾位創業者的“路演”剛一結束,立刻就有人圍攏上去,他們被稱為是“潛在的天使投資人”。他們問東問西,拋出一些專業或者不專業的問題。不過,創業者是否通過一次“路演”就融到資,這是個未知數。因為,深圳有錢人的理財和算計水準可能并不低于他們。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找錢”的創業者的確來對了地方。
一項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深圳有各類股權投資基金企業達3.87萬家,注冊資本2.27萬億元。深圳已成為全國創投機構數量最多、管理資本總額最多的地區之一。
2012年,深圳市金融辦負責人曾透露過另一組數據:截至2012年10月30日,深圳市股權投資基金企業累計達到3890家,注冊資本1750億元。
如果沒有統計口徑的差異,那么縱向對比可以看出,深圳的股權投資基金在3年時間內已經翻了10倍。多位深圳創投界的人士對《南風窗》記者表示,這個數字還會增長,一是深圳的“高凈值人群”太多了,二是全國的創投資金都在流向深圳。
資金門檻
在所謂“全民創業、萬眾創新”的潮流之下,創投機構方興未艾,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為創投機構的LP(有限合伙人),從其中分羹一杯。
“前創匯”創始合伙人、深圳凱摩創投董事長何曉霖對《南風窗》記者說,此前,中國高凈值人群參與股權投資主要是通過成為創投機構的LP來實現的。但按照我國監管法規,成為LP的門檻極高,一般人達不到這個門檻。
按照2014年8月21日起施行的《私募投資基金監督管理暫行辦法》(下稱《私募基金辦法》),私募基金的合格投資者的資金門檻為:投資于單只私募基金的金額不低于 100 萬,同時還要是符合下列相關標準的單位和個人:(一)凈資產不低于 1000 萬元的單位;(二)金融資產不低于 300 萬元或最近三年個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50 萬元的個人。
《私募基金辦法》特別強調,“金融資產”包括銀行存款、股票、債券、基金份額、資產管理計劃、銀行理財產品、信托計劃、保險產品、期貨權益等。換言之,作為中國家庭主要資產配置的房產不在其中。
《私募基金辦法》由證監會頒布,而另一個同樣規范股權投資的《產業投資基金管理暫行辦法》(下稱《產業基金辦法》)則由發改委頒布。所謂私募基金和產業投資基金,其實并無嚴格區分。
在業界,一種區分是,私募基金更多是指投資于二級市場股票的基金,而產業基金則傾向于上市前的企業股權。另一種是,它們都可以投資未上市企業,但私募更類似于投資早期的VC,而產業基金更類似于投資成熟期的PE。但兩類區分都并不嚴格,業界經常混用。
一般而言,后者門檻比前者要高。根據《產業基金辦法》,發起人的資金門檻要求為:法人作為發起人,除產業基金管理公司和產業基金管理合伙公司外,每個發起人的實收資本不少于2億元;自然人作為發起人,每個發起人的個人凈資產不少于100萬元。
此外,發起人須具備3年以上產業投資或相關業務經驗,在提出申請前3年內持續保護良好財務狀況,未受到過有關主管機關或者司法機構的重大處罰。
《產業基金辦法》的另一規定意味著除發起人外,其他投資人的門檻同樣不低。其要求,投資者數目不得多于200人。但又規定了產業基金擬募集規模不低于1億元。這意味著每位投資者至少投入50萬現金,對普通家庭而言這不是小數。
在成為機構投資者的LP之外,監管對“天使投資人”并未設定門檻。何為“天使投資人”?實際上,在監管口徑中,并無“天使投資人”這一投資人種類的嚴格定義。某種程度上講,這是一個民間約定俗成的說法。它指的是,投資于企業萌芽期,投資金額比VC還要小的投資人。
這個邏輯就好比,我國的金融法規規定企業之間不能直接借貸,但不禁止個人之間的借貸行為。因此,就產生了基于互聯網的P2P小額借貸熱潮。同樣,法規設定了成為私募基金和產業基金的LP的門檻,但并不禁止個人參股投資企業,所以便有了“天使投資人”的大眾化。
不過,一個簡單的邏輯是,私募基金和產業基金之所以存在,在于投資者并無專業投資知識,因此需要專業人員,即GP(一般合伙人)來管理基金。那么,人人都希望做天使投資人的創投狂潮,是否意味著投資者巨大的風險呢?
破解業余化
近年來,由于創投行業激烈競爭,好項目越來越難找,一家好項目,出現十多家投資基金搶投的局面早已司空見慣。因此,資本選擇目標逐漸向前端即初創期的企業轉移,但這也意味著越是初創,風險越大,對投資的專業能力要求越高。
此前,由于好項目的競爭激烈,創投機構在獲取項目方面開拓了兩個新途徑。一是科技園孵化器或者產業基地,直接面對大批創業者,在早期介入。第二種模式是產業集團投資,這以BAT三巨頭的投資模式為典型,即順藤摸瓜,投資產業鏈上有戰略價值的優質企業。
現在,第三種方式開始成為潮流,即形成創投的網絡化。通過穿透機構的合作形成一個信息網絡,使得每一個機構都成為一個項目端口,實現了優質項目在網絡內的共享。這種模式改變了以前一家創投機構的“單打獨斗”的局面,是投資機構的抱團作戰。
何曉霖對《南風窗》記者分析,普通人成為天使投資人,這是投資機會,但業余投資者畢竟專業知識不足。目前,“前創匯”的模式是,業余投資者加入這個創投機構的項目共享網絡,在專業創投機構投資之后進行“跟投”。
何曉霖表示,可以“跟投”的項目都已經過專業投資機構的項目質量初選,風險相對較低。此外,因為這是一種“集體投資”,每位天使投資人的單獨投資金額相對較小,這也意味著風險就小。
不過,投資分散化是否會觸及法律對公司股東人數的限制?我國《公司法》就明確規定,股份有限公司股東人數應在2人以上、200人以下。此外,《證券法》也規定,向特定對象發行證券累計超過200人的視為公開發行,未經依法核準,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公開發行證券。換言之,不經批準,不得發行超過200人。
監管的“200人”限制,既是基于公司未上市公司“人合性”的考慮,也是為了在中國并不完善的信用體系之下,防止不規范集資事件的發生。
但考慮到中國金融環境和投資者個人財富的積累,監管在這方面已經有所松動。2013年實施的《非上市公眾公司監督管理辦法》規定,股東人數超過200人的企業可納入非上市公眾公司管理。此后,一系列文件出臺,逐漸明確了超200人的公司的的監管方式和流程。
按照監管要求,股東超200人的公司,可在獲得證監會前置行政許可后,申請公開發行股份并在交易所上市、在新三板掛牌公開轉讓。其中,新三板掛牌方面,對這類公司有著更為寬松的限制。《南風窗》記者從深圳創投界了解到,希望吸引這類小而散的天使投資的企業,多數都劍指新三板。
上個世紀90年代,美國的兩位年輕人找到了“天使投資人”、Sun公司聯合創始人安迪·貝托爾斯海姆(Andy Bechtolsheim),告訴他要做搜索引擎。貝托爾斯海姆聽得一頭霧水,不過他說:盡管聽不懂你們的商業模式,但我還是先給你們一張支票,半年后再告訴我你們在做什么。
于是,貝托爾斯海姆開出的10萬美元支票,成了Google公司的首筆天使投資。貝托爾斯海姆也成了世界上最幸運的天使投資人之一。那么,在中國人的全民創投熱潮中,是否也會有如此幸運的投資人呢?沒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