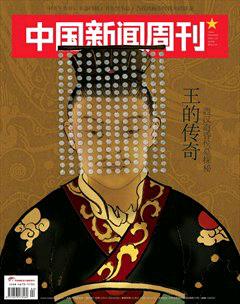當(dāng)單身罪不可赦
像所有反烏托邦作品一樣,這部《龍蝦》注定是一則寓言。某種程度上說,它特別適合中國(guó)觀眾,因?yàn)樵谶@個(gè)國(guó)度里,單身幾乎已經(jīng)被“定罪”,被歧視,被打入另冊(cè)。在這里,單身似乎是一種殘缺。《狗牙》的導(dǎo)演歐格斯·蘭斯莫斯把這種“單身罪責(zé)”的景觀推向了極致。
所有單身的人都被集中在一座酒店內(nèi),限時(shí)找到配偶,如果失敗,他們將變成一種動(dòng)物,在森林中被這些單身者獵捕,生死由命。單身者每獵捕一頭“動(dòng)物”就能延續(xù)自己作為“人”的時(shí)限一天,如果屢不得手,他們也終將被送入森林。
像所有反烏托邦的典型設(shè)定一樣,在一群順從者之外,注定還有一群反叛者,他們拒絕在戴罪之身和成為動(dòng)物之間做出抉擇,他們?cè)谏掷镉?xùn)練自己,抵抗外部。這樣一來(lái),有趣的對(duì)比就產(chǎn)生了,理論上講,那群反叛者應(yīng)該是“自由”的象征,他們反抗一種強(qiáng)加的生活方式上的暴力,但其實(shí),他們并不是自由的。這個(gè)群體中不允許有性和愛的關(guān)系存在。這是另一種殘酷。他們看似與敵人斗爭(zhēng),但本質(zhì)上已經(jīng)成為了和敵人一樣的人。
科林·法瑞爾曾在神劇《真探》第二季中扮演了一個(gè)隨時(shí)都處在崩潰邊緣的警察。這一次,作為男主角,境遇更加悲慘,這個(gè)挺著啤酒肚,戴著近視鏡的中年男人,成為了單身罪人中的一員,但他最終逃離了那座酒店,去往反叛者的陣營(yíng),但又因?yàn)榕c一位反叛者相愛,而再次逃亡。相愛的本質(zhì)是一種自由的選擇,當(dāng)任何強(qiáng)力所附加,都是對(duì)于自由的破壞,強(qiáng)迫人們配對(duì)如此,強(qiáng)迫人們不能相愛同樣如此。
《龍蝦》向人們展示了兩種被禁錮的可能,“森林”和“酒店”兩個(gè)殘酷的意象告訴人們,只要有強(qiáng)迫,無(wú)論打著愛意還是自由的旗號(hào),最終都會(huì)變成對(duì)人性的囚禁。在那座必須配對(duì)的監(jiān)獄般的酒店里,人們表演著各種乖張與謊言。而諷刺的是,在那個(gè)世界里,說謊是違法的,人們不能假裝般配地結(jié)合以逃過劫難,還必須證明兩人真的登對(duì),但問題在于,在外力脅迫下,怎么可能有真正的情感?當(dāng)反叛者沖入酒店經(jīng)理的房間,強(qiáng)迫夫妻兩人抉擇誰(shuí)生誰(shuí)死的時(shí)候,經(jīng)理的丈夫向她扣動(dòng)了扳機(jī),而他們每天都在宣講夫妻恩愛的真意。那把槍沒有子彈,但空槍的脆響卻洞穿了彼此之間的一個(gè)巨大的謊言。而在另外一邊,那個(gè)反對(duì)者的陣營(yíng)里,謊言也仍然同樣流行。相愛的男女必須發(fā)明一套秘密手語(yǔ),在眾人的耳目下,悄悄傳遞愛意,那種壓抑與酒店里其實(shí)毫無(wú)差池。乃至于最終,那場(chǎng)秘密的愛情敗露之后,反叛者的頭目不惜弄瞎了女人的眼睛。

電影《龍蝦》劇照
當(dāng)彼此相愛與享受孤獨(dú)都不能名正言順地進(jìn)行,自由的根基就已經(jīng)被挖斷了。
近年來(lái),反烏托邦題材確實(shí)很熱,但是大多都將這個(gè)黑暗的題材童稚化了,基本上演變成借由反烏托邦的殼子講述青春愛情故事,無(wú)論《饑餓游戲》還是《分歧者》都是如此。而這部電影與那些商業(yè)化的主流大片顯然有著不同的野心,它向標(biāo)準(zhǔn)的反烏托邦題材回溯。
希臘導(dǎo)演歐格斯·蘭斯莫斯對(duì)于權(quán)力對(duì)人的傷害這樣的題材,一直情有獨(dú)鐘,用寓言講述這一切是他迷戀的闡述方式。這部電影的優(yōu)點(diǎn)和缺點(diǎn)都十分明顯,或者,換個(gè)說法,導(dǎo)演就是想用這樣明確的方式,不折衷的方式講述這一切。《龍蝦》有著標(biāo)志性的、頗具壓迫感的配樂,和機(jī)械的、講述歷史故事式的念白,這一切都讓它變得更接近一部純粹的寓言而非一部電影。也正因?yàn)槿绱耍@得有些沉悶。
但影片的最后有一個(gè)漂亮的開放結(jié)局,男女主角逃離了酒店也逃離了森林,回到城市,他們坐在咖啡館里,男人決定扎瞎自己,以便變得和女人再度“般配”。他們明明相愛,但卻仍然固執(zhí)地認(rèn)為需要尋找一個(gè)能說服自己的共同點(diǎn),來(lái)印證這種相愛的合法性。他們看似逃離了奴役,但實(shí)則仍然禁錮著自己。但是,直到最后,我們也不知道,在洗手間里躊躇的男人,是否真的對(duì)自己下了手。女人無(wú)所適從地坐在咖啡館里,窗外陽(yáng)光燦爛。人們必須成雙成對(duì)地走過,但恩愛的面具之后一定都是一顆顆冷若冰霜的心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