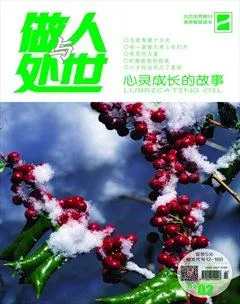青春之約
鄭旭
“我用十年青春赴你之約。”有人用這句話宣誓愛情,而我想用這句話去分走父親肩上的巨大壓力。
我靜靜地回想,思緒停在了身處南方城市的那段時間。這個南方的城市竟下起了大雪,農民喜上眉梢,感嘆著瑞雪兆豐年。一切想象是美好的,可在大雪落下的路上卻傳來陣陣罵聲。一個中年男子騎著破舊的電動三輪車,在寒風里瑟瑟發抖,他伸手拉了拉破舊的棉襖,試圖讓可恨的寒風少進去點。終于騎到了家,他一下子從三輪車上滑落下來,揉了揉腳,半走半跳地進了屋,臉凍得發紫。他用力地把腳挪進了妻子送上的熱水里,等著腳恢復暖意。他笑著看看自己的兩個孩子,兩個窩在被窩里看電視傻笑的孩子。

其中一個就是我,那時我還太小。父親在一個冬季里,只有三四天沒有出去工作,還是因為大雪封路。直到現在,當別人問起父親時,我都會很驕傲地說:“我爸是白手起家的。”父親在一座大城市做生意失敗后,欠了一屁股債,不得已回老家賣房賣地還清了債款。那時我五歲,姐九歲,父親也三十大幾了,卻一文不名。不甘失敗的他揣著僅存的積蓄,其實不過幾千元錢,到了這座南方的城市。只是10年而已,從徒步、自行車、摩托車到現在的大貨車,從十幾平方米的出租房到現在一百多平方米的溫馨居所,父親,竟付出了這么多,只是兒時的我都沒注意到罷了。
2011年,我在小升初考試中名落孫山,父親發了大火,我被流放到了異地,一所管教嚴格的寄宿中學。是的,被流放,至少那時的我是這樣認為的。到了寄宿中學,我仍不肯學習,直到那一個電話。初中以前,印象中的父親一直是盛氣凌人的,他可以做到當我考試失敗時,在飯桌上憤怒地將筷子擲向我的頭。那時,我固執地認為父親太冷血,太野蠻,卻從未想到父親竟會有軟弱的時候。
那天,我從老師手中接過電話,靠近耳朵的前一秒還以為是毫不留情的訓斥。結果父親帶著哭腔叫了一聲我的名字,那一刻仿佛五雷轟頂,我一下子癱坐在了凳子上。父親像是傾訴一般跟我說著,仍帶著哭腔。他訴說著生意上的不如意,與母親之間因生意上的分歧而產生矛盾、離婚,還有我的不省心不用功。一字一句,卻這般沉重。最后,父親只是囑咐了一句:“稍微認真些吧。”晚上,我躺在床上呆滯地看著天花板,一夜未睡,越發地難受,直到一個人不爭氣地淚濕眼眶。天明,透過鏡子看著這張與父親相似的臉,這才明白,父親也只是一個普通人。每日心安理得地花父親的錢,揮霍自己的青春,還傻傻地對自己說:“你還小,父親那么厲害,不在乎多玩幾年的。”可不知不覺,父親的皺紋越來越多了。當我開始意識到這點時,我長大了。
青春是把刀子,割去了我年幼的發絲,帶走了青澀和年少輕狂。父親,我用十年青春赴你之約,父親請早一些,更早一些地讓我分走你肩上的壓力。求您,您的孩子懇求您,老得慢些吧!
指導教師 ?黃忠
(編輯/張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