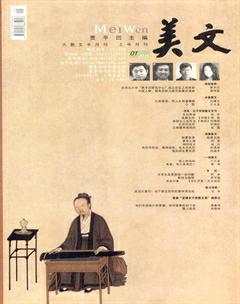波斯女性
[伊朗] 納莉
一
“女人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杰作。”蕭伯納的這句名言可謂是最能說明女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價值。
經(jīng)過九年多在中國的生活,我覺得中國或者至少北京是一個“母系社會”。每當(dāng)我的朋友們或者同胞們問我對中國男女之間關(guān)系的看法如何時,我都會毫無疑問地給他們講一個永遠(yuǎn)不會從我腦海里抹去的記憶。剛來中國那段時間,有一天,我和我的伊朗朋友一起去逛北京的王府井。我們一邊觀賞周圍的商場與百貨大樓,一邊往位于這條大街上的清真寺走,但當(dāng)我們發(fā)現(xiàn)走在我們面前的一對年輕男女時,就突然停住了:可能是女孩累了,男的很自然地蹲在那位女孩面前,背起她就接著往前走,女孩還在他背上撒嬌。這一幕讓我和我的朋友大吃一驚,但周圍好像除了我倆相互議論之外,其他人都沒有感到任何意外,甚至習(xí)以為常,熟視無睹。我倆吃驚的原因是,如果在伊朗一個男的這樣做的話別人肯定會叫他“zanzalil”,這相當(dāng)于中文的“妻管嚴(yán)”,而這樣的綽號會給男人帶來某種恥辱感。盡管目前隨著伊朗女性恢復(fù)了她們該有的社會地位和真實(shí)權(quán)利,“zanzalil”這個詞已慢慢失去了它的貶義色彩,有時反而會把它當(dāng)一種玩笑給大家?guī)砜鞓罚诖篑R路上男人背自己的老婆或女朋友,對我們伊朗人來說仍然是一種不可思議的行為。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有趣的中國文化現(xiàn)象表明他們的“母系社會”,那就是男人提著女人的包。我敢說任何人即使在中國時間很短的人也肯定會遇到過這一幕。我剛來中國的時候還不太了解中國人的文化風(fēng)格,那個時候我以為中國男人喜歡買女士包、用女士包,或者在中國包不分男女,后來才明白男人為女人拎包是對女性的一種尊重和幫助。
我的中國朋友們也很好奇地想知道在我的國家女人的地位與權(quán)利如何,在伊朗男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娶四個老婆等類似的問題。這些問題促使我不能只根據(jù)自己的經(jīng)驗(yàn)來回答,我必須做一個較為全面地了解和思考,我想通過這篇文章向中國朋友介紹我了解和思考的結(jié)論。
在我看來,學(xué)習(xí)一個國家的文學(xué)是了解那個國家文化的最好的辦法之一,因?yàn)橐粋€國家的文學(xué)可以反映那個國家的社會條件和文化狀況,我們通過學(xué)習(xí)文學(xué)也可以了解到一個國家的人民在一個固定的時期內(nèi)有怎樣的文化習(xí)俗和思維。伊朗是一個有著悠久歷史和豐富文明的國家,它在歷史上有過各種各樣的變化,因此婦女的社會地位也根據(jù)這些變化而改變,其中的一種變化就是伊斯蘭教的到來。
二
伊朗人在公元651年波斯薩珊王朝被阿拉伯人推翻之前,承繼瑣羅亞斯德的學(xué)說,也就是說信拜火教。波斯文學(xué)在伊斯蘭教進(jìn)入到伊朗之前的歷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那個時期的文獻(xiàn)以口頭與書面兩種形式存在。學(xué)者認(rèn)為這段時期的史詩文學(xué)是以口頭形式流傳,而收集到的書面形式的文獻(xiàn)大部分是基督教、拜火教、摩尼教、佛教等宗教的經(jīng)典。由于缺少關(guān)于女性地位在伊斯蘭教進(jìn)入到伊朗之前波斯文學(xué)的相關(guān)參考文獻(xiàn),因此我們沒法得到更多相關(guān)的信息,但通過閱讀世界上最富有的文學(xué)之一波斯經(jīng)典文學(xué)之后,看到了一些史詩與浪漫的故事,女人在那些作品中充當(dāng)著相當(dāng)積極的角色。這些婦女的性格與地位表明古代波斯時期的伊朗人對婦女的看法。阿拉伯人入侵伊朗之后伊朗人就開始逐漸加入到伊斯蘭教。
伊朗人完全信伊斯蘭教有一個漫長的過程。雖然伊斯蘭教的經(jīng)典《古蘭經(jīng)》以及先知和伊瑪目們的圣訓(xùn),對波斯文學(xué)產(chǎn)生了很大而不可否認(rèn)的影響,但是伊朗人還是保護(hù)了自己的文明和文化習(xí)俗,也就是說伊朗人雖然變成了穆斯林,但是他們的文化并沒有完全阿拉伯化。伊朗人進(jìn)入到伊斯蘭教之后,伊朗就成為一個獨(dú)特而與別人不同的伊斯蘭國家,最后還給全世界介紹了一種新層面上的伊斯蘭教。伊朗被阿拉伯人統(tǒng)治的時候,偉大的波斯詩人“菲爾多西”在保護(hù)波斯語和波斯文學(xué)應(yīng)對阿拉伯人的侵略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他的書《王書》(又譯《列王紀(jì)》)是伊朗文學(xué)中最偉大的民族史詩之一,在波斯文學(xué)經(jīng)典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女性在伊朗文學(xué)經(jīng)典中扮演著多重角色。有的時候是情侶,有的時候是情郎,有的時候是愛人,而有的時候是母親,有的時候是奉獻(xiàn)和虔誠的象征,有的時候代表明智的政治家和愛國的人物,而在另一個地方卻有惡意和狡猾的角色。在伊朗經(jīng)典文學(xué)的作品當(dāng)中,女性的智慧以各種形式表現(xiàn)了出來,其中的一種是當(dāng)女人遇到男人的表白與求婚時,能夠想出最適當(dāng)而聰明的措施,既能保護(hù)自己又能達(dá)到保護(hù)其他人甚至整個族群的目的,從而達(dá)到最恰當(dāng)?shù)哪繕?biāo)。菲爾多西《王書》里蘇赫拉布對克勞達(dá)法理德的失敗愛情故事就是其中的例子之一。
故事是這樣的。蘇赫拉布裝備了一個龐大的軍隊(duì)從圖蘭出發(fā)去打擊伊朗。伊朗軍隊(duì)那邊有一位勇敢的戰(zhàn)士走進(jìn)戰(zhàn)場,跟蘇赫拉布開始決戰(zhàn)。他們之間爆發(fā)了相當(dāng)艱苦的戰(zhàn)斗,因?yàn)樗麄z都很強(qiáng),但最后還是蘇赫拉布贏了。蘇赫拉布用劍把對方的鋼盔掀掉之后大吃一驚,沒想到快要被他打敗的那位勇敢、頑強(qiáng)而技藝高超的戰(zhàn)士竟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克勞達(dá)法理德。蘇赫拉布把克勞達(dá)法理德與其他伊朗的軍隊(duì)俘獲后,包圍在一個堡壘里。最后又把克勞達(dá)法理德投放在監(jiān)獄里,但蘇赫拉布在心里愛上了克勞達(dá)法理德。最后蘇赫拉布向她表白,希望克勞達(dá)法理德嫁給他。克勞達(dá)法理德是一個既聰明又愛國的人,自己想一想,蘇赫拉布是敵人,所以根本就不能跟這樣的人結(jié)婚。但是,她利用了這個機(jī)會,對蘇赫拉布說同意跟他結(jié)婚。這樣,蘇赫拉布釋放了所有的伊朗戰(zhàn)俘,而克勞達(dá)法理德也跟隨他們一起逃走。她的這個做法就證明了她作為一個女人真是一個精明的政治家和戰(zhàn)略家,可以使用“美人計”。總的來說,隸屬和服從在伊朗人的文化當(dāng)中始終是一個好妻子的優(yōu)秀品質(zhì)。菲爾多西也認(rèn)為最好的女人就是讓自己的丈夫?qū)λ指吲d又滿意。
三
伊朗歷史上影響到婦女地位和作用的另外一個主要改變就是立憲革命。伊朗人認(rèn)識了歐美與其他國家之后,發(fā)現(xiàn)自己在經(jīng)濟(jì)和政治方面的落后點(diǎn),并認(rèn)為國家的基本問題在于沒有一個根本大法以及專制獨(dú)裁政府的存在。立憲革命的學(xué)者們與知識分子認(rèn)為,必須喚起民眾,讓民眾明白社會要進(jìn)步就必須向古老守舊的傳統(tǒng)開戰(zhàn),必須給新的風(fēng)尚打開道路。立憲文學(xué)即是針對古代文學(xué)而形成的,因此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內(nèi)容上都打破了傳統(tǒng)。1905年,當(dāng)時的波斯國王穆扎法·厄丁宣布了實(shí)行憲法,并于次年10月7日,首次召開立憲會議。1925年卡扎爾王朝由伊朗議院投票被推翻,并推選雷扎·可汗為巴列維王朝之家的第一個國王。雷扎·可汗在1934年6月2日訪問了土耳其之后,深受阿塔圖爾克西方化政策的影響。他看到土耳其婦女已經(jīng)變得如此開放,使他深思自己國家的婦女情況如何。回到伊朗之后,有一天,他對自己的部長們說道:“我去土耳其之后親眼看到了那邊的婦女已經(jīng)把頭巾摘了下來并進(jìn)入到社會的各個方面,跟男人一樣工作,我就開始討厭我們國家所有戴頭巾的婦女。我覺得頭巾和面紗是人民進(jìn)步和發(fā)展的對立物,就相當(dāng)于一個膿腫,必須把它毀掉!”隨后,雷扎·可汗在1936年1月8日批準(zhǔn)了一項(xiàng)伊朗婦女禁止戴頭巾、面紗或者長黑紗的禁令。
然而,雷扎·可汗的做法失敗了。他的最大錯誤就在強(qiáng)迫女人移除頭巾,在突然間奪取了婦女的選擇權(quán)。而阿塔圖爾克在這方面則是精心策劃過的,他鼓勵女人自選移除面紗和頭巾,所以土耳其婦女戴不戴頭巾是自愿的。雷扎·可汗并沒有任何計劃,而是通過此法律規(guī)定嚴(yán)重壓制有不同意見的老百姓或神職人員。雖然雷扎·可汗的這種做法是對伊朗婦女解放采取的步驟,是希望伊朗婦女能更自由地參與到社會各界的活動中,但是,由于當(dāng)時伊朗人民對“自由”這個概念并沒有正確的理解,政府也沒用更好的措施和手段讓人們了解什么叫“自由”,什么叫“發(fā)展”,這種不尊重人民的宗教信仰和思想的做法,導(dǎo)致了一些年紀(jì)比較大的老人還有一些宗教信仰比較深的傳統(tǒng)女人,感覺自己就像強(qiáng)迫被脫光衣服,只好困坐家中不敢出門。而另有一部分女人,因錯誤地理解“自由”的意思,認(rèn)為“自由”就是不戴頭巾,以至于她們在社會上做出一些不道德的事情,帶來社會上大面積地墮落。
社會上發(fā)生的各種變化、活動與革命,會反映在文學(xué)作品中,而在一個文學(xué)作品尤其是小說中會有很多虛構(gòu),而這些虛構(gòu)也會反過來影響社會變革。在立憲革命時期,伊朗的詩人和作家們的思想也在發(fā)生變革,這直接導(dǎo)致了直接關(guān)注社會問題的波斯現(xiàn)代小說的產(chǎn)生。有關(guān)女性,這時期的作家們更關(guān)注的是妓院里的女人。在他們的作品當(dāng)中女人通常大部分都是衣衫襤褸的,被淹沒在污穢中,并從事一些低級的工作。如果在他們的故事當(dāng)中偶爾出現(xiàn)其他身份的女人們,則要么出現(xiàn)的時間太短暫,根本給讀者留不下任何印象,要么就是她們的角色太暗淡了,讀者根本覺不到她們的存在。立憲革命后,最具代表性的一部關(guān)于女性問題的小說是《阿湖夫人的丈夫》,作者是阿里·穆罕默德·阿富汗尼。這部小說描述了一個伊朗家庭在1935年至1942年之間七年的不穩(wěn)定而充滿困難的生活情境。這部小說出版兩年后,也就是在1962年,被評為年度最佳小說。該書也是波斯文學(xué)中很有價值的一部小說,它是一部伊朗女人的悲劇。作者以“阿湖夫人”為代表,通過描寫伊朗婦女的艱難困苦,來反對一夫多妻制,這在當(dāng)時是伊朗社會制度最根本的問題,并且作者在該書的各個部分都呼吁伊朗婦女應(yīng)該取得已失去的權(quán)利。這部小說的故事富有表現(xiàn)力地描述了伊朗老百姓的生活狀況,并細(xì)致刻畫了當(dāng)時經(jīng)濟(jì)、政治與社會結(jié)構(gòu)的各種細(xì)節(jié)。
四
伊朗的另外一個大事件就是伊朗伊斯蘭革命和兩伊戰(zhàn)爭。在巴列維王朝的統(tǒng)治下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差距擴(kuò)大了,引起社會局勢緊張。在此期間,伊朗伊斯蘭革命的領(lǐng)袖霍梅尼認(rèn)為君主政體是一種充滿“傲慢”的傳統(tǒng)禮儀,是從多神教時代繼承給我們的,必須被推翻。就這樣,伊朗伊斯蘭革命在1979年取得了勝利。伊朗伊斯蘭革命勝利不久伊拉克軍隊(duì)入侵了伊朗,發(fā)生了兩伊戰(zhàn)爭。伊朗人勇敢地與侵略者作戰(zhàn),表現(xiàn)在波斯文學(xué)尤其是在詩歌和小說上,開啟了一個新的境界,并造成了新的話題、主題,甚至產(chǎn)生了“熱詞”。伊朗人民在八年時間內(nèi)英勇抵抗了侵略者,導(dǎo)致在文學(xué)上創(chuàng)作了新的“戰(zhàn)爭文學(xué)”。在戰(zhàn)爭期間內(nèi),女人也跟男人一樣走進(jìn)了戰(zhàn)場,并在那段時間的文學(xué)里明顯出現(xiàn)了女性角色。從這個時期的小說文學(xué)里女性的角色能夠看到,伊朗女人在社會的各個方面,在戰(zhàn)場上面對敵人也好,在戰(zhàn)線的背后供給用品或者照顧傷員也好,都顯示了強(qiáng)烈而自覺的存在。
再靠近伊朗文學(xué)一點(diǎn),我們會遇到一些女作家。她們作為女性作家從女人的角度來寫關(guān)于女人生活的故事。佐婭·皮爾扎德、莫奈·拉瓦尼·波爾、莎哈儂什·帕西·波爾等是伊斯蘭革命后的幾位女作家。在她們作品當(dāng)中女人不再是“有罪的”“敗壞的因素”,不再是“不幸的”或“依賴的”的人物,而是解放了的女性。
總而言之,縱觀伊斯蘭革命前的文獻(xiàn),女性作家的數(shù)量稀少,大部分是男性。在他們作品當(dāng)中女人的角色并不重要和突出,女人作為“女仆”“女奴”或“小三”受到各種精神和心理上的壓迫,很多“惡詞”都濫用在女性身上。伊斯蘭革命后,女性的地位在伊朗當(dāng)代文學(xué)中達(dá)到了一個新高度,至少不再被認(rèn)為“女人身負(fù)罪孽”。事實(shí)上,今天的伊朗女人,在文學(xué)作品中已被描寫得有身份、有自信、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