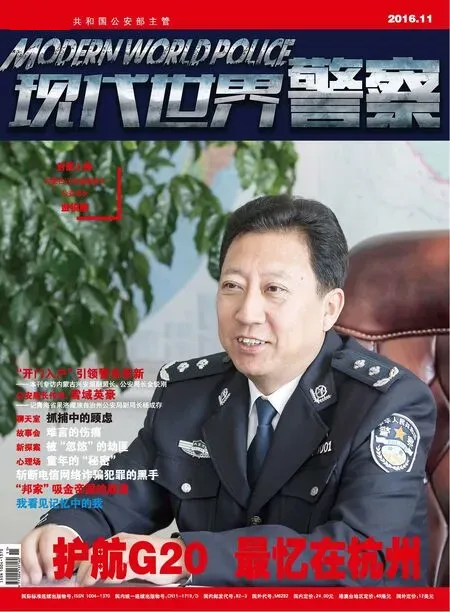背負虛無的十字架,尋找救贖之路
文/賀子鈺
背負虛無的十字架,尋找救贖之路
文/賀子鈺
所謂的罪與罰,究竟本質為何?是讓犯人聽到自己的死刑宣判而感到解脫,還是讓他重返自由社會,但用盡一生贖罪?
上面這句話是東野圭吾在他的一本書——《虛無的十字架》中拋出來的問題。這本書的創作靈感據說是來源于一起震驚整個日本的入室殺人案(即福田孝行殺人案),一名剛滿18歲的少年殺害了一對母女,并且進行奸尸的嚴重罪案。在這起案件的審理過程中,盡管人權律師大聲疾呼槍下留人,但日本輿論卻“一面倒”地支持被害人家屬。經過九年纏訟,少年終于被判死刑。這起案件到了后期已經超出了一場單純兇殺案的審判,反而演變成一次對死刑存廢問題的爭論。東野圭吾也由此構思出了這部小說。
作為日本推理小說社會派的代表人物,東野圭吾的小說有別于傳統的“本格派”與“變格派”在案件推理上的側重,而是著重于對人性與社會現象的深入發掘,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物命運發展中設置各種懸念,并結合這些社會元素去探究犯罪背后隱藏的社會原因。因此在他的筆下法律一直是充滿矛盾的存在。
東野圭吾通過小說主人公中原道正的眼睛與經歷見證了兩種對待生命的不同態度:
年輕的仁科史也與女友井口紗織因為一時沖動,還在學生時期就有了孩子,缺乏正確引導的他們親手殺害了自己的親生骨肉。一段青梅竹馬的純真戀情也因此變成了不堪回首的噩夢。對史也和紗織而言,對幼時殘忍無知的悔恨慢慢在內心發酵,壓得他們無法喘息。成年后良心的杖責也一直鞭撻著他們,活著的每一天都如同身處煉獄,生命中也再無快樂。
紗織認為自己如同老鼠般卑劣,并患上了偷竊成癮的毛病,她在內心深處認為,被世人所唾棄,就是對自己最好的懲罰。史也背負著這具沉重的十字架不斷地尋求彌補自己罪行的方法,成年后他選擇成為一名兒科醫生,每天都在不遺余力地拯救著那些瀕臨死亡的小生命,后來更救下了一位因受騙而試圖自殺的孕婦,并承擔起了照顧她和孩子的責任。或許在他看來,對這對母子的持續付出會讓他備受煎熬的內心稍微好過一些。
而對于另一位殺人犯蛭川和男來說,不管是他自己的生命還是別人的生命或許都如草芥般無足輕重。他因為殺害了中原道正八歲的女兒而被判處死刑,在得知自己的判決結果后他反而有一種身心放松的感覺,甚至放棄了上訴,原因竟然是“太麻煩了,懶得再上訴”。從這句話就能看出他對自己的生命已經不再執著,并且直到這時,他也沒有對自己的罪行進行過真正的反省。
從他們身上,我們可以鮮明地看到兩種對待生命的態度。史也身上我們能看到一個犯錯年輕人的悔改之心,以及后來他對生命的敬畏與尊重。而在蛭川身上我們只能看到一個對生活失去熱情,對生命漠不關心的虛無主義者。
再回頭想想,對于我們大部分人來說,在對待一個犯了重罪的人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把他們關進監獄或者剝奪其性命,大部分的人認為這樣就算對某些人犯下的罪行進行了懲戒,以為這樣就能以儆效尤,使其他人不敢越雷池半步,但事情是否真的如世人所想的那么輕易呢?或許并不是這樣。
如果是對于一個心存良知的人而言,哪怕極偶然的一次作惡,都會在其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陰影,哪怕沒有死刑,道德良知的譴責也會讓他們終生背負著一具沉重的十字架。而對于那些窮兇極惡的罪犯來說,死刑未必就能達到我們所期望看到的效果。
所以,歷年來無數的人提出要廢除死刑,當然原因并不僅僅只是上述說的這些,但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幾點,即人權天賦、死刑錯用、不穩定性(死刑的有無與一個國家的謀殺案數量并沒有一定的聯系)、增加了不合適的赦免所帶來的惡性影響。或許在很多人看來,冤假錯案中死刑的錯用是死刑廢止運動中最有力的聲音,但我的看法卻稍有不同。舉個例子:在事件A中,犯人被判了死刑;在事件B中,犯人也被判了死刑。但這卻是完全不一樣的兩起事件,加害人與受害人及其家屬也完全不一樣。但最后結果卻全都用死刑給結束了,這不得不說是死刑的一個缺憾。
在寫這篇文章時我查閱了不少有關書籍,甚至也差點兒被死刑廢止論所說服,但是細思之后我依然覺得這些并不能真正成為廢止死刑的充分理由。
這就涉及幾個問題,其中之一便是“公正”。“公正”這個詞最早在《慎子》中出現。慎到在書中提出:“故蓍龜所以立公識也,權衡所以立公正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審也,法制禮藉所以立公義也。”
在《史記·高祖本紀》中也記載了劉邦“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這也是一種比較樸素的“公正觀”。后來唐太宗也把“以公平為規矩,以仁義為準繩”作為在整個司法系統以及選官、擇官中的標準。
由此可看出,在中國自古以來“公正”這種觀念就已深入人心,不管是在行政管理上還是在社會生活上。
“公正”也正是現代法律價值的核心。而死刑的廢止卻恰恰違背了法律的“公正”這一重要原則。對于這點我想引用一段《虛無的十字架》中的原話,因為我無法再找到更深刻的話來代替下面這段描述:
請想象一下,自己的家人被殺,要經過怎樣的痛苦才能接受這個事實。就算犯人死了,被害人也不會醒來,但遺族要求什么才好呢?之所以請求死刑,是因為除此之外沒有任何其他手段能讓遺族感到慰藉。
就算是下達了死刑判決,那也不意味著遺族就勝利了。他們什么都沒有得到,只不過是經歷了一些必要的手續罷了。即便是最后執行死刑也是一樣的。這都不能改變犯罪者奪去了自己心愛的人的事實,心中的傷痛也不能痊愈。有人會說,既然這樣的話,沒有死刑不也沒關系嗎?并不是這樣。如果犯人還活著,那么遺族就會想:“為什么他會活著?他有什么權利活著?”這樣的疑問最終會腐蝕遺族的內心。有人提意見說,可以廢除死刑,改為終身刑期。這些人完全沒有理解身為遺族的心情。如果實施了無期徒刑,那犯人還是活在世上的。在這個世界的某個地方,每天吃飯、聊天,說不定還有那么一兩個興趣。不停止這種現象,遺族就會一直痛苦到死。對于遺族來說,犯人只能用死來“謝罪”。這樣,遺族才能越過悲傷的節點。然而,即便是跨過了節點,遺族也不能忘記這一路走來的痛苦。他們全然不知,自己以后要怎么辦,走到哪里才能重新得到幸福。如果連允許家屬走向未來的機會都奪取了的話,那么遺族要怎么辦才好?所謂的死刑廢止,也就是這樣的東西了。
就像上面所說,死刑雖然無法讓被害人再死而復生,但卻給了被害人的家屬一個繼續活下去并走向未來的機會。
書中的這段描述讓我想起了福田孝行殺人案中受害者家屬本村洋在得知殺人犯僅需在監獄待七八年就會被釋放后,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對司法很絕望。原來司法保護的是加害人的權益,司法重視的是加害人的人權。被害者的人權在哪兒?被害家屬的權益在哪兒?如果司法的判決就是這樣,那不如現在就把犯人放出來好了,我會親手殺了他!”
其實本村洋的這種復仇心態也是公正思想的一種體現。倘若對于社會中存在的那些非正義行為不進行遏制和懲處,那么部分本來具有正義愿望的人就很可能開始效仿這種行為,從而可能造成大量非正義行為的發生。
而且,刑罰存在的一部分意義也是為了避免私人的力量對罪犯進行報復而采取的一種公眾處罰方式。如果把死刑取消,謀殺等重罪或許會更加肆無忌憚發生,而私刑和私力報復也會隨之泛濫。
當然,基于“公正論”下的死刑也是有其局限性的,因為公正論過分強調犯罪和刑罰兩者的等同性,這就必然導致我之前所提出的質疑,即異罪同罰。但是隨著社會發展,相信人們道德觀中的公正觀及其刑罰觀會變得日趨理性,豐富的物質財富以及民智的逐漸開化或許會讓更多的人去認真思考生命的意義,刑罰的嚴厲程度可能也會逐漸減輕,這應該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種表現吧。
對于死刑存廢這個問題,或許正如孟德斯鳩所言:當人們對失去安逸生活的恐懼大于失去生命,那么死刑就應該廢除;而當人們對失去生命的恐懼大于失去安逸的生活,那么,就不應該廢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