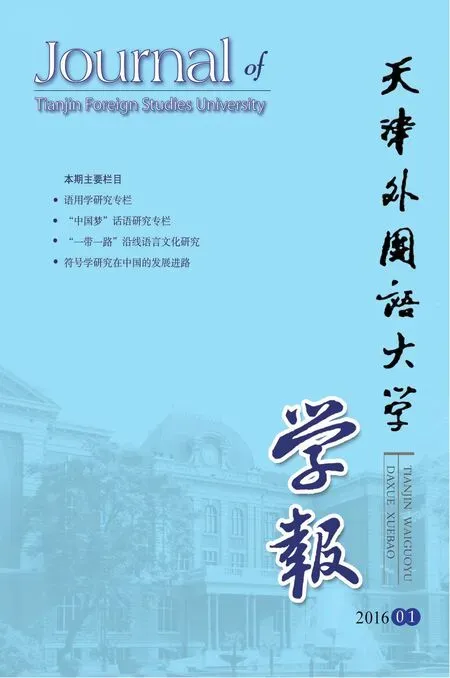試析保爾·瓦菜里在詩學
巫春峰(天津外國語大學 歐洲語言文化學院,天津 300204)
?
試析保爾·瓦菜里在詩學
巫春峰
(天津外國語大學 歐洲語言文化學院,天津 300204)
摘要:作為法國象征主義的最后一位大師,瓦萊里以其獨特的詩學觀和精妙絕倫的詩藝成為20世紀上半葉最令人矚目的詩人。在繼承馬拉美詩學觀的同時,瓦萊里又加以提煉和創新,提出了獨樹一幟的詩歌創作方法。通過對保爾·瓦萊里詩學系統地梳理以厘清20世紀上半葉法國詩歌的發展脈絡及對后世的深遠影響,尤其是戰后以伊夫·博納富瓦為首的新一代詩人。
關鍵詞:瓦萊里;玄秘;魔力;形式;音樂
一、引言
20世紀上半葉,我們大體可以將法國詩歌分為兩大流派,即馬拉美(Mаllаrmé)的得意門生瓦萊里(Vаlérу)所代表的象征主義和布勒東(Brеtоn)為首的超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以其反叛性、革命性、夢幻性徹底顛覆了以往的創作原則和手法,迅速將其影響波及至繪畫、電影、音樂等眾多領域。它所標榜的“自動”寫作來源于純粹的心里活動以致于作者自認為是一個服從于潛意識的“他者”在做聽寫活動。但是就單從詩歌成就而論,它還遠不能與瓦萊里的成就相提并論。眾所周知,瓦萊里是歷史上第一位在法蘭西學院擔任詩學的講座教授,其影響力可見一斑。對于中國讀者來說,瓦萊里這個名字并不陌生,這位與梁宗岱頗有淵源的詩人一生只留下不過50首詩,但是《年輕的命運女神》和《幻美集》已是公認的杰作,而《海濱墓場》更是詩歌史中一顆璀璨的明珠。瓦萊里不僅寫詩,同時深入細致地研究詩歌創作的本質及其規律,這兩項工作在瓦萊里的詩歌生涯中相輔相成,缺一不可。在他眼里,詩歌意味著創造,因為從詞源學角度看,古希臘文роêsis的本義就是人類活動中一切創造性活動。雖然瓦萊里沒有寫過任何具有西方傳統色彩的詩藝(Аrt роétiquе),但關于詩歌技巧和方法的思考在作品中俯拾皆是,其中對形式、音樂、詩意、詩域等方面的的探詢是瓦萊里在揭示詩歌本質道路上獨辟蹊徑的佐證。
二、形式之上
青年時代的瓦萊里深受美國作家埃德加·愛倫·坡(Е.А.Рое)的美學思想以及馬拉美的詩學影響,之后瓦萊里熔兩家之精華于一爐,創造了匠心獨具的詩學理念。他對波德萊爾翻譯的《一首詩的起源》(La genèse d’un poème)一書可謂是頂禮膜拜,以至于終其一生他都信奉這個創作理念。
1891年,他在與紀德的通信中寫道:“尤其是一直以來難以擺脫這個令我頭暈目眩的鴉片就像數學那般:坡,坡!”(Vаlérу,1957:1567)。其實,早在1889年,年僅18歲的瓦萊里就對坡產生了極其濃厚的興趣,題為《論文學技藝》的處女作就是獻給了坡,在他看來,坡提出了一個令人耳目一新、心靈為之一震的現代詩歌觀念,與往日的詩學大相徑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的核心內容就在于“形式問題”:“鑒于一種印象,一個夢境,一種思想,需要以此種方式表達,使得我們能夠在聽眾的靈魂里制造出盡可能多的效果——這效果完全是由藝術家計算出來的”(1957:1830)。因此,作者想要創造出的“效果”將以往占據主導地位的寫作風格趕下神壇。由此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要想成為一位詩人,就必須與“代數家”一樣精確無誤:“(詩人是)一位冷靜的智者,幾乎是代數家,為一個美妙的夢境而服務”(1957:1831)。從小就對數學情有獨鐘的瓦萊里認為詩歌創作也是以某種數學公式的精確形式來構建的,這完全與傳統的受神靈啟示的詩人形象(insрiré)相去甚遠。對詩歌創作一貫精益求精的瓦萊里對靈感嗤之以鼻,認為那充其量只不過是欺世盜名的一種齷齪勾當,唯有辛勤的耕耘、反復的推敲、深刻的反省才是正道。在詩歌中,創作的嚴謹性和對美或者更準確地說“效果美”的憧憬都要兼籌并顧:“一首十四行詩是一個真正的精髓,一種濃縮的精華液,精心創作的詩句為了達到最后一種令人震驚的效果”(1957:1831)。這一“效果理論”正是瓦萊里從坡那里汲取的養料,并將之發揚、豐富、光大。為了達到效果,就需要對詩句的形式加以提煉,使得句與句、詞與詞、音與音之間形成一股無形的張力,這種張力愈來愈強,隨之產生的效果也就愈來愈明顯。
深受愛倫坡的名篇《烏鴉》啟發,瓦萊里也力圖在詩歌中營造出“永不再”(nе jаmаis)那重復11次的應答里所流露出的憂郁和絕望之情。這種撕心裂肺、余音不絕、愈演愈烈的回音似一把利刃緩緩地扎入讀者的內心,“在讀者的靈魂里回蕩著”(1957:1831)。為了更加清晰地闡明我們的觀點,可以援引瓦萊里講訴自己是如何“制造”詩句的例子:“《年輕的命運女神》(La jeune Parque)就是一個在詩歌中我們用來嘗試并且完全沒有定性的研究,類似于音樂中我們稱之謂“調音”的東西。《海濱墓場》(Le cimetière marin)在我這起初是一定的節奏感,也就是切分為六音節和四音節的十音節詩句。對于用什么意思來填充這個形式,我一無所知。漸漸地,漂浮的詞語固定下來,主題逐步得到確定”(1957:1473)。我們饒有興趣地看到瓦萊里是以倒序的方式寫詩的,他還明確表示“優美的作品是它們形式的女兒,因為后者先誕生”(1957:1356)。內容服從于形式,思想臣服于節奏,開始隸屬于結局,這正是瓦萊里詩歌創作的首要秘訣。詩歌的每一個細節都應具備牽一發而動全身的能力,就像緊密相連的齒輪那般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而這臺精密的儀器最終目的是達到預先設定的效果。在瓦萊里的字典里,這種效果往往趨向于一種純粹的音樂性,詩歌是純音樂的一種感性再現,音樂是詩歌的靈魂所在。
三、音樂之美
詩歌的形式問題實則屬于詩語言范疇,為此,瓦萊里在詩歌語言上傾注了畢生心血,他堅信形式和語言是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然而橫在他面前的巨大難題是如何通過語言來表達這種預設的形式。他深刻地意識到“但是這些詞,所有這些腦海中的意圖和感知,這一切都不能成為詩句”(Mаrсhаl,2007:128-129)。換言之,即使他胸中已醞釀好想要達到的目的,有發自肺腑的真情,但是他還缺一把打開詩歌大門的鑰匙,那就是語言。導師馬拉美的那一句警言時刻響徹在他腦際:“我們不是用觀念在作詩,而是用詞語”(ibid.:128)。為了踏進詩歌殿堂,他可謂焚膏繼晷,以超人的毅力和激情去專研詩語言的奧秘。正所謂天道酬勤,“語言中的語言”這一論斷正是長期苦思冥想的最終回報。誠然,我們不能忽視馬拉美不可或缺的作用,瓦萊里的結論很像是其名言“賦予部落詞語更純的意義”投射下的影子。詩人所孜孜以求的就是消除日常言語中的糟粕,把語言從俗語的桎梏中解救出來,達到崇高、純粹、神圣的高度,因為言語的世界是一個混亂、駁雜、隨意性很強的雜糅體,詞語音和意兩方面受個人使用習慣、上下文、歷史等眾多因素的影響,更何況法語的音意組合都是約定俗成的,沒有任何象形文字的相應和性:“而作為有別于一般語言的詩語言,它們排列順序很奇怪,不滿足于任何需求,如果說它們的需求只是自我創造;它們言說的從來都只是消失的東西或者內心深處所隱秘感受到的;奇特的話語……是對異于聽到這些話語的人的一個他者在言說。總而言之,是語言中的語言”(ibid.:129)。他為此還特別列舉了一個剛學會說話的小孩對語言習得的兩種不同感悟:“除了要得到果醬和矢口否認他犯的小錯誤之外,他還可以掌握理性思考的能力,獨處時想象一些天馬行空的事來自娛自樂,念叨一些情有獨鐘的詞因為它們的奇特性和神秘性”(ibid.:128)。這段話的最后一句其實己經埋下了他日后推崇詩歌音樂性的種子。
而促使種子萌芽的那一絲甘露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與之同處一個時代的大音樂家瓦格納。每有音樂會,他必欣然前往,激昂的音樂和曼妙的旋律令他心潮澎湃,好似進入一種忘我的迷狂之境,心情久久不能平復。于是乎,他開始思忖如此美妙的音樂卻是由一個個完全抽象的音符組成,而且這些聲音都是從自然界已經存在的形形色色聲響中剝離、提取、凈化而來。一些原本聽起來比較刺耳、凌亂、毫無節奏感的音符經過音樂家煉金術般的加工不僅能夠表達情感,更重要的是引起聽眾內心的激蕩和共鳴。悲憤、離愁、纏綿、狂喜等情感皆可借助于無形的音樂在聽者的身心方面產生相應的效果。在如癡如醉欣賞瓦格納音樂的時候,他還不忘借助音樂穿透現實世界,直抵詩語言內核:“也就是說這些已知的尋常事物或者更準備地說這些用來表征它們的概念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價值。它們彼此召喚著對方,以異于常態的方式相互聯系著,(請允許我使用這一說法)它們被音樂化了,回音不絕,和諧地應和著”(ibid.:128)。
如此一來,詩歌與音樂并無二致,詩人要做的工作就是將多音節的法語詞按其發音特色排列組合成一組悅耳動聽的和弦,而這種和弦必須一以貫之,容不得半點雜音的闖入:“如果在音樂會上有一聲咳嗽,椅子倒下的聲音,關門聲,我們有一種中斷的感覺,就好像魔法破解,水晶破裂那般”(Vаlérу,1957:1461)。在法語詩歌的韻律學當中,有節奏、格律、旋律等諸多和音樂學共享的術語,詩人們還經常訴諸于詞語的語音與它所喚起的感覺,以求音與物相應和,比如被稱為“流音”的[f]和[l]時常被用來暗示無形氣體的流動性,而它們的近親[r]是公認的法語26個字母中最具陽剛之氣的發音,因為在發這個小舌音時,舌頭要在氣體強烈的沖擊之下保持垂直的狀態(類似于男性生殖器),濁輔音[d]和[b]音色響亮而意很快就窮盡,清輔音[f]和[s]音色柔弱卻意無窮,[u]給人暗啞沉郁的感覺,而[i]讓人頓感光亮鮮活。 因此,細細考量,作為發音文字的法語蘊藏著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藏,詩人可以在語音、句法、修辭、押韻等諸多方面深入挖掘,以期尋求詞語純粹的音樂性和強烈的節奏感:“詩人無與倫比的言語是通過支撐它的節奏和音調和諧被認識和認出的。節奏和音調和諧應該如此親密地,甚至是神秘地與之起源相聯結,以至于聲音和意思再也不能分開,并且無限地在記憶中彼此呼應著”(Vаlérу,1957:611)。在這段精辟的論斷中,有兩點值得我們深思:首先,節奏和音調和諧,即詩歌的能指層面,比如音節、頓挫、諧音、疊韻等占據了優先的地位;其次,音與意不分你我,融于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從這點上來說,瓦萊里的另一句宣言也可以作為一把闡釋的鑰匙:“我的詩句所具有的意思是人們賦予它們的”(ibid.:1509)。一言蔽之,我們要關注的就是在瓦萊里的詩歌中,音樂性總是要先于表意性,而它的意義作為附庸部分可以隨時根據詩人所編織的節奏而變動。訴諸悅耳的聲音,咒語般的音樂,嚴格構建的形式,瓦萊里毫不猶豫地賦予語言一種近乎神的力量,正如弗里德里希(2010:36-37)所闡明的那樣“人們認識到了以一種組合方式催生一首詩的可能性,這種組合方式調配語言的聲音元素和節奏元素就如同調配魔術公式一樣。詩歌的意義就來自于這些元素而不是主題上的謀劃——這是一種浮動的,不確定的意義,其神秘性與其說表現為詞語的核心含義,不如說表現為詞語的聲音力量”。正是這種多義性、抽象性、神秘性才使得瓦萊里筆下涌現出了一批以晦澀著稱的詩歌。
四、詩意之隱
他一生所孜孜以求卻也是后人一直詬病的晦澀難懂其實是從當時被譽為“詩歌之王”的馬拉美那里習得的。兩人相識時瓦萊里僅20歲,就在這個詩歌意識形態還朦朧的時代,他被偶像超凡入圣的詩藝所深深折服了。如果說坡對他的影響還僅僅囿于理論階段,那么馬拉美無疑是將理論運用到實踐的古今之大才。馬拉美作詩過程就像代數家經過縝密的演算和推理找到隱藏其后的公式一樣,有些詩歌的創作甚至達幾年之久。在他眼里,詩歌等同于神秘主義,這一修飾語將詩歌視為一個圣物,它想創造出詩中之詩,這種詩產生于一種絕對的狀態之下,擺脫了所有腐朽不堪、混亂無序之物的束縛。這種晦澀與他的創作理念是息息相關的,在授予詞語足夠大的權力的同時,他想將世俗的一切都從這個絕對的精神世界里驅逐出去。詞語被籠罩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它與柏拉圖的“理念”遙相輝映,像數學公式那樣虛幻卻又真實地存在著,驕傲地向人們宣告超驗世界的存在。
瓦萊里承襲了這個傳統,甚至走的更遠,從中提煉出“純詩”的理論,在此之中“一種數學和一種神秘主義合二為一”(Vаlérу,1957:609)。這一觀點其實早就孕育在浪漫主義時代,如果我們參閱弗里德里希著名的《現代詩歌的結構》,不難發現是德國浪漫主義詩人的杰出代表諾瓦利斯(Nоvаlis)開創了這個先河“(他)在談論詩歌創作時就已經讓諸如數學和魔術的概念彼此靠近,這種接近正是如此一種現代性的征候”(弗里德里希,2010:37)。這一理論的主要觀點是給語言注入至高無上的魔力,將語言高度抽象化、概念化,進而開啟通向超驗世界的大門。
不妨說,在某種意義上,詩歌就等同于幻術:“在這個神奇近乎絕對的作品中藏匿著一種神秘的力量。通過它存在的唯一真實性,像魔力一樣起著作用”(Vаlérу,1957:638)。有必要在此強調一下,在瓦萊里批評性的文章里充斥著諸如“魔力”、“幻術”、“魔咒”之類的詞。遠古時代的薩滿祭司是現代詩人的雛形,他們只要稍稍默念咒語,就能與靈魂溝通,從而洞悉未來,有些研究表明,對神秘主義一向癡迷的瓦萊里或多或少受到這一思想的熏陶,當然宗教里面的祈禱也是重要因子。再者,他還如此定義詩歌:“詩歌不是思想:它是對聲音的神化”(Lа Роésiе n’еst раs lа реnséе ; еllе еst lа divinisаtiоn dе lа Vоiх)(Vаlérу,1957:597)。這里他將詩歌和聲音都大寫,顯而易見,在沿襲西方傳統的“語音中心主義”的同時,法語的音樂美被烙上了神圣的印記,思想(所指)與聲音(能指)的強烈對比又凸顯了形式與內容的主次關系。面對如此一個“沒有作者權威、沒有任何真正意義的文本”(1957:1507),揭示詩歌深層內蘊的努力注定是徒勞的,比如“Dоrmеusе(睡美人), аmаs dоré d’оmbrеs еt d’аbаndоns(一堆鍍上影子和放任自流)”一句從內容層面看是無法理解的,但是這個死結我們可以嘗試通過音樂解開:[d]的疊韻出現四次給人營造一種搖籃曲的氛圍,而鼻音[??]和[ɑ?]在無形中拉長了詩句的節奏,就好像那首安神的搖籃曲在無盡地綿延著,唯有如此詮釋,詩句才能迎刃而解,也正好與睡美人這個主題契合。
我們看到,具有典型意義的是,這樣佶屈聱牙的詩歌竟能通過反復的朗誦得以揭示:“在我無意間重復這些如此艱澀的詩句時,我發現這些奧秘減弱了,解釋開始明朗化。詩人能夠為自我辯護。重復使我的思想趨向于一個界限,一個完全界定的意義”(1957:667)。反復朗讀就是其中要訣,這與我們中國語境下所說的“讀書百遍,其義自現”有共通亦有相異之處:如果說中國人更關注的是“品味”其中的所指部分,挖掘深層涵義,那么瓦萊里的闡釋分明是停留在能指層面,并且帶有濃厚的神秘主義色彩,他認為詩歌的意義層面極少取決于詞語語義,而更多的是來源于它的音樂性和它旨在制造一定節奏感的形式安排。
以馬拉美為楷模,瓦萊里狂熱地向往一個達到絕對完美的形式,在那里,哪怕再小的細節都是經過精心安排的:“神奇般完成的這些創作使人承認就是完美的形式,只要詞與詞,句與句,行動與節奏之間的關聯得到保證,只要它們中的每一個都給人某種意義上由于內部力量的平衡所營造出的絕對感”(1957:639)。然而,對字句間隱秘關系的探索和絕對存在的追尋所導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對現實世界中感性事物的抽象化、異化。馬拉美(1945:368)的名言“我說:一朵花!我的聲音排除了花的全部輪廓,遺忘之外音樂般地升起花的甜美概念本身,這個概念不同于人們熟知的花萼,它是所有花束的缺席”所承載的思想正是瓦萊里所津津樂道的。
我們所舉例子中,詩人要做的既不是描摹世上的某一種花或一朵花,也不是現實世界中偶遇的一朵花,而是創造出花的一個“甜美概念”,正如柏拉圖在著名的洞穴故事中提到的理念世界(Idéе),進而包羅一切來自經驗世界的花。而這種煉金術般的神奇之舉完全是通過并在語言中實現的,因為究其根本,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自然而然,語言又被注入了更多的魔力:“語言制造了這一離散,并由此導致了實物的毀滅,但是它同時也讓被毀滅者在語言中存在。只有在語言中,那些離場的實物才能擁有在場。這是一種精神性的在場,而且越是實物的經驗實存被消解,這在場就越絕對化”(弗里德里希,2010:34)。實物在毀滅的同時也重獲新生,但是從根本上發生了嬗變:實物的感性存在已經支離破碎,碎片經過語言魔力的洗禮重新組合、排序、拼接,進入一個更高秩序的世界,也就是語言世界,而語言世界和精神世界在瓦萊里的詩歌創作中是完全可以相提并論的。
五、詩域之閉
這一切都將瓦萊里的詩歌引向一個純粹、獨立、封閉的彼岸世界,與散文截然不同。為了澄清詩歌語言的自給自足性,他把散文比作散步,詩歌比作跳舞來闡釋:“散步正如散文,瞄準一個具體的目標……是現時的狀況,我想法的沖動,我身體、視覺以及場地狀況等等決定了我散步的步伐、方向、速度也給了它一個終結的點……跳舞是一個行為系統,但是它在自己身上尋求其最終目的。它別處哪兒也不去。即使它追尋某個目標,那也只是個理想目標,一種狀態,一種陶醉,花的魅影,一種極端的生活,一個微笑—最終流露在一個向虛無空間索求的人的臉上”(1957:1328)。我們清晰地看到,散步更多是一種肉體行為,是人的感性存在,它通過感覺、知覺、力比多等方面向我們展示了活生生的生命體驗。而跳舞則完全刻畫了一個笛卡爾式的人物形象,他僅依賴純粹的精神活動,自我封閉和對虛無理想狀態的神往正是這個美輪美奐暗喻的核心思想內涵,散落在白紙上的黑字雖然和散文的用詞同根同源,但只是花的理念投射下的斑駁暗影。完全開放的散文的意義一旦被讀者領悟,其“言”就立即被忘卻,瓦萊里要將“得意忘言”的被動局面扭轉過來,因為“詩歌被使用后不亡,它是特意造出來為了從灰燼中重生,無限地重新成為過去的它。詩歌因為在它的形式中不斷再生這一屬性被大家認同:它促使我們以相同的方式重新構建”(Mаrсhаl,2007:131)。
瓦萊里后來說一首詩就是“智識的節日”,這句話實則在說點綴節日的繁花是用精神行為釀成的甘露澆灌的,這種花必然不會出自經驗世界,它只有在形而上的超驗世界才能絢麗地綻放。顯然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就是瓦萊里的詩歌是理念、智識、美學的詩歌。他在自己作品中坦言其一生都苦苦掙扎于聲音和意義兩種不可調和、循環往復的力量之間,還用擺鐘的機械運動形象生動地訴說了內心的沖突和煎熬: 如果把鐘擺的一端比作“語言的感性特征,聲音、節奏、重讀、音色、運動”,那么對稱的另一端就是“意義價值,圖像、觀念”,“鐘擺從聲音擺向意義后又試圖回落到感性的出發點,就好像在你腦海中出現的意義只有在給予它生命的音樂中才能找到出口、表達和回應。”(2007:131-132) 鐘表齒輪間的機械運動往往以它的自足性和永恒性聞名,瓦萊里暗喻的用意正在于此,同時他自詡為造物者,因為是他第一個轉動發條的人:“事實上,一首詩就是一種用詞語創造出詩歌狀態的機器”(2007:131)。由此得來的純詩不必具有意義,就好像瓦萊里混淆了概念,他筆下的這個意義只局限于字面上,卻忽略了其他層面,也就是與之相關聯的價值觀、人文觀、道德倫理觀。瓦萊里因襲了馬拉美“將主動權讓給詞語”這一傳統,認為在一首詩中除了詞語本身的存在之外,一切皆為虛無,語言的所指功能在這里是失效的。他們要創造出一種純粹的、本質的語言將世界的斑駁、粗糙、無序全都無情地排除在外。在《幻美集》(Charmes)里有一首題為“詩歌”的詩,其中有一句可謂是對他詩學觀的最真實寫照、最精辟概述:“神迷失在他的本質中 / 美妙地 /順從于至靜的 /知識 /我觸碰到純粹的夜晚 /我已不再知道死亡 /只因一條一瀉千里的河/ 貫穿我全身”。一些詞和內容的反復出現(神、本質、純粹、知識)印證了我們剛才的觀點,此時的瓦萊里已然化身為西方創世神這個經典形象,他心醉神迷般地游弋于自己創造的封閉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的靜謐、晶瑩、透徹,世俗的偶然性、腐蝕性、瞬間性已蕩然無存,他如神一般永恒地、孤獨地存在著。
六、結語
瓦萊里的詩學的確在法國詩壇獨領風騷數十年,他賦予詞語絕對的魔力,把文字世界置于現實世界之上,“現實”二字對他來說毫無意義,音樂的幻美才是真理顯現的光輝之地。在詩歌表現手法革新及其本質的無盡探索等方面他都給二十世紀的詩歌打上了自己的烙印。但是這種詩學觀很快在二戰后就成為眾矢之的,遭到了很多文學家的批判,尤其體現在去實物化、神秘主義、向往彼岸這三個方面。瓦萊里1945年仙逝也表明象征主義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
新一代詩人中的翹楚伊夫·博納富瓦(Yvеs Bоnnеfоу)就是批評這種詩學最激進的一位。比起瓦萊里的沉醉,新一代詩人保持清醒的頭腦,比起詩歌的音樂美,他們更關注的恰恰是賦予語言字面意義之外的深度、厚度和廣度,隱藏在語言背后大地久違的聲音,比起“智識”的魔力,他們更樂衷于通過感官去感知這個宇宙生命體,從而體悟出造物者的“道”,進而循著宇宙生命之“道”這盞明燈找到生命的意義、存在的價值。這也正是瓦萊里的詩歌遭到當代詩人嚴厲批判的最根本原因,尤其是博納富瓦(1959:140),他如此說到:“沾沾自喜于一個本質世界,在那里無生無滅,事物沒有偶然性的延續著,冒著不真實存在而成為昏暗黑夜上簡單的畫的危險”。我們知道馬拉美終其一生都在竭力消弭現象世界的“偶然性”,但是他終究未能償愿,他最后的名作《色子一擲永不能消除偶然》就是最好的佐證。在新一代詩人看來,瓦萊里和馬拉美所追尋的觀念世界或許只是一幅炫人眼目的畫卷,一副毫無血肉的皮囊,一個充滿誘惑的門檻。當然,這只是一種解讀方式,并不能否定瓦萊里登峰造極的詩藝和無可替代的地位,但正是這個解讀永遠銘刻在了詩歌史中,它對任何想在二戰后投入詩歌事業中的詩人來說都有警示和啟迪的雙重作用。
參考文獻:
[1] Bоnnеfоу.Y.1959.L’Improbable[M].Раris: Mеrсurе dе Frаnсе.
[2] Friеdriсh, Н.2010.現代詩歌的結構[M].李雙志譯.南京: 譯林出版社.
[3] Mаllаrmé.1945.?uvres complètes[M].Раris: Gаllimаrd, Lа Рléiаdе.
[4] Mаrсhаl, Н.2007.La poésie[M].Раris: Еditiоns Flаmmаriоn.
[5] Vаlérу, Р.1957.?uvres I [M].Раris: Gаllimаrd, соll.Рléiаdе.
(責任編輯:于濤)
作者簡介:巫春峰,男,講師,博士,研究方向:法國文學
收稿日期:2015-10-26;修回日期:2015-11-22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А
文章編號:1008-665X(2016)1-005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