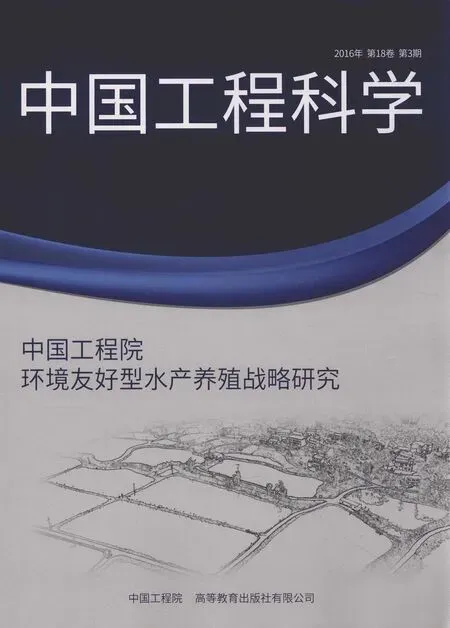海水養殖容量評估方法及在養殖管理上的應用
張繼紅,藺凡,方建光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海洋漁業科學與食物產出過程功能實驗室,山東青島266071)
海水養殖容量評估方法及在養殖管理上的應用
張繼紅,藺凡,方建光
(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青島海洋科學與技術國家實驗室,海洋漁業科學與食物產出過程功能實驗室,山東青島266071)
隨著海水養殖規模的增大,超負荷養殖使得養殖水環境遭到嚴重破壞,病害加劇,危及養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亟待加強養殖容量研究,建立科學的適應性管理對策。本文綜述了國內外有關海水網箱、貝類、藻類等養殖容量研究進展、存在的問題。指出了容量評估的關鍵技術,主要包括:生態容量評估的指標體系、養殖生物個體生長數值模型、水動力過程與生態模型的耦合。分析了養殖容量研究在指導養殖密度調整、優化養殖布局、拓展養殖空間以及構建新型養殖模式中的作用。對于未來開展養殖容量研究提出了三點建議:建立養殖水域的容量評估制度、設立近海養殖結構與養殖容量評估的長期監測實驗站、設立養殖容量研究和布局與結構調整專項,以建立生態系統水平的養殖管理策略。
海水養殖;容量;管理;模型
DOI 10.15302/J-SSCAE-2016.03.014
一、前言
2014年我國海水養殖產量達1.812 65×107t,產值達2 815.47億元,在保障我國蛋白食物供給以及經濟發展中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中國漁業統計年鑒,2015)。但是,隨著海水養殖規模的增大,超負荷養殖,使得養殖自身污染嚴重,生態環境受到破壞,養殖生物病害加劇,危及養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亟待加強養殖容量研究,建立科學的、適應性管理對策,以保障養殖產業的高效、可持續發展。
容量的概念:該概念來自于種群生態學的Logistic方程,dN/dt=r×N×(K–N)/K,其中,N代表種群大小;t為時間;r為種群的瞬時增長率,表示該物種的潛在增殖能力;K為環境容量。種群密度與增長率之間存在反饋機制,即密度制約作用。當N=K時,增長率(dN/dt)為零,種群數量保持穩定,達到環境容量。可見,在特定的環境條件下,種群的數量不能無限制地增加。養殖容量的概念,從最初的關注最大養殖產量向最大可持續產量轉變,從關注經濟效益向生態效益轉變[1~3],養殖容量的基本內涵:特定水域單位水體養殖生物在不危害生態環境、能夠保持生態系統相對穩定、符合可持續產出的最大產量。
二、我國海水養殖容量研究進展
不同養殖種類養殖容量的限制因子不同,容量評估的切入點就會不同。按照投餌情況,可以分為投餌型(如網箱養殖)和非投餌型(濾食性貝類、大型藻類等)兩大類。投餌型養殖因污染物排放量較大,主要將與污染物密切相關的環境指標作為容量評估的限制因子,非投餌型養殖以天然餌料及營養物質為主,主要考慮食物或者營養限制。
(一)海水網箱養殖容量研究
網箱養殖產生的殘餌、魚類排泄、代謝產生的顆粒和溶解態物質,會對養殖區域水質和底質環境產生壓力,因此,網箱養殖容量評估主要將環境對養殖產生負荷的承載情況作為限制因子,也稱為環境容量。網箱魚類養殖容量方法有實地調查估算法[4],顆粒有機碳沉積通量估算法[5],數值模型估算法[6]。限制性指標有底質硫化物含量[4],水體中無機氮濃度[6],水體中氮、磷濃度[7]。
(二)海水濾食性貝類養殖容量研究
方建光等[8]在20世紀90年代率先開展了濾食性貝類養殖容量研究。濾食性貝類以浮游植物等顆粒有機物為餌料,養殖容量與生態系統的功能如初級生產力、浮游植物現存量及懸浮顆粒有機物的濃度等密切相關。食物通常為貝類養殖容量的限制指標。養殖容量評估方法包括營養動態模型、能量/餌料收支模型、食物限制因子指標法、生態數值模型法等。研究的種類有筏式養殖的櫛孔扇貝,長牡蠣,馬氏珠母貝,灘涂及底播養殖的菲律賓蛤仔、文蛤、蝦夷扇貝。研究的海域有山東的桑溝灣、膠州灣、乳山口灣,遼寧獐子島,江蘇如東,廈門大嶝島海域及同安灣等[9~12]。關于生態容量的研究甚少,處于起步階段[13]。
(三)大型藻類養殖容量研究
關于大型藻類養殖容量的研究較少[8,14,15],評估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以氮、磷為限制指標的營養物質供需平衡法;另一種是耦合水動力模型的生態動力模型法。
(四)綜合養殖系統的養殖容量評估研究進展
Ge等[16]以浮游植物為指標,采用數值模型的方法評估了桑溝灣筏式貝類(櫛孔扇貝、長牡蠣)與海帶的綜合養殖容量,給出了貝藻適宜的養殖比例。徐姍楠等[17]利用ECOPATH軟件,構建了灘涂紅樹林種植–養殖耦合系統的生態通道模型,分析了耦合系統的能量流動和系統特征,并估算了該系統的養殖容量。
三、國外海水養殖容量研究進展
Inglis等[18]對貝類養殖的容量進行了劃分,分為自然容量、養殖容量、生態容量和社會容量。建立了評估生態容量DEPOMOD模型[19]和基于生物量平衡原理的ECOPATH模型[20]。目前已建立多種評估養殖容量的技術方法和模型,從簡單的指標法,發展到一維、二維的數值模型,進而發展為包括水動力學的三維模型,還建立了多營養層次綜合養殖
容量評估模型[21~24]。
挪威建立了基于網箱和貝類養殖容量的管理決策支撐工具AkvaVis,有效地限制養殖環境的惡化和病害的發生,保證了三文魚、貽貝養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AkvaVis開辟了在水產養殖決策支持系統中應用虛擬技術的新方法。它可以幫助管理者、決策者非常直觀地綜合利用地理信息系統、鑒別任務,制定決策。既可以考慮養殖場的養殖容量、養殖活動對環境的壓力,又可以考慮養殖場的最優布局,同時,盡量少地受原始數據、模型模擬等復雜過程的影響。
四、海水養殖容量評估的關鍵技術
(一)養殖容量評估的指標體系
在關注養殖產量的同時,尚需關注養殖對環境的影響以及經濟因素,如規格與價格的關系等。其中,確定養殖活動對生態系統影響程度和生態系統彈性的確定是養殖容量評估的核心。不僅需要加強養殖與生態環境相互作用機理研究,從生態系統水平上闡釋養殖對生態環境的壓力,而且有必要與生態系統健康評價相結合,有助于基于生態系統水平的漁業管理模式的建立。
(二)養殖生物個體生長數值模型
養殖生物是養殖容量評估的主體,個體生長數值模型是養殖容量評估模型的關鍵子模型,決定了容量評估的正確性和準確性。常用的有基于特定生長和動態能量收支原理的個體生長數值模型。
(三)水動力過程與生態模型的耦合
水流作為養殖過程中代謝原料和產物的載體,其交換過程對于海域內營養物質的輸運和補充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以精細過程觀測為基礎,以數值模型為手段,將物理過程與生物模型進行耦合是養殖容量評估的關鍵技術。
五、我國海水養殖容量評估存在的問題
(一)評估方法與技術問題
我國養殖容量研究開展得較晚,評價方法和理論基礎研究都相對薄弱,尚未形成有自主知識產權且較為完善的容量評估數值模型,尤其在與水動力過程的耦合上相對不足。在養殖貝類的生態容量評估指標方面,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缺少科學的量化指標。
(二)數據的積累不足
因為區域環境的特色,限制容量的因子往往不同。而且,養殖容量受環境、社會、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的影響,會因養殖種類、方式、養殖技術以及管理水平的提高而改變。我國海域廣闊,跨越北溫帶–熱帶,受全球氣候變化和人類活動多重壓力影響,生態環境復雜多變。另外,海水養殖面積大,養殖種類、方式繁多。因此,不僅需要養殖海域的物理、化學、生物等方面的環境參數的長期調查,而且需要加強對養殖結構、養殖生產要素以及養殖生物的生理生態指標的系統研究和數據積累。
(三)養殖產業問題及需求
近年來,隨著養殖規模和養殖強度的不斷擴大,淺海養殖空間有限,加之沿岸水域的環境污染、病害暴發等危及海水養殖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究其原因,與養殖品種單一,密度過大,比例失調,布局盲目,以及養殖生產管理不規范、不科學有關。我國養殖種類、方式和模式多樣,并且海域地理環境復雜,跨越溫帶、亞熱帶、熱帶海域,所以,亟需加強海水養殖容量評估體系和制度的研究,建立科學的管理規范以保障海水養殖高效、可持續發展。
六、容量評估技術在養殖管理上應用的保障措施
海水養殖已成為我國沿海的重要產業,隨著養殖密度和規模的增大,養殖對于近海及河口生態系統的影響日益增大。在2016年的全國漁業漁政工作會議上,將“加快轉方式調結構,促進漁業轉型升級”作為“十三五”全國漁業發展的宗旨,其中,尤其強調了以“提質增效、減量增收、綠色發展、富裕漁民”為未來漁業發展的目標。如何調整結構?根據什么來減量還能增收?另外,在近海可利用空間幾近飽和的情況下,拓展深遠海空間是未來海水養殖發展的方向。新空間、新模式的拓展迫切需要規劃、選址的科學指導。養殖容量評估是制定
現代水產養殖發展規劃的基礎,也是保證水產養殖可持續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免受破壞的前提。以養殖容量為基礎,科學安排海域的養殖規模、密度,進行總量控制及成本核算,以及進行確定適宜的放養和采捕規格,形成科學的管理策略。以養殖容量為基礎,以高效、可持續產出為核心,科學地控制養殖密度和規模、優化養殖結構和布局,構建經濟效益高、生態環境友好的養殖模式[25]。因此,提出了容量評估技術在養殖管理上應用的保障措施。
(一)建立養殖容量評估制度
容量評估應納入政府的公益性和強制性工作范疇,形成制度化。并且以此來確定養殖密度和布局,發放養殖許可證、水域使用證,加強違規處罰措施的力度。建立容量評估制度,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1. 資金保障
容量評估和宏觀管理規劃是公益性的政府行為。養殖者或者企業缺乏評估技術和資金,難以具體實施,因此容量評估應納入政府強制性工作范疇,并形成制度化。容量評估的保障資金可以從收繳的養殖水域使用費中安排一定的資金。
2. 技術保障
容量評估是需要多學科交叉的復雜技術工程。對于特定養殖區域,容量不僅與養殖種類、方式有關,而且與養殖系統的物理、化學、生物因子有關,甚至受政治經濟文化因素的影響。因此,容量評估需要經過專業培訓的、同時了解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的專業人員才能勝任。另外,容量評估需要有長期的、全面的理化生物以及養殖活動等方面的數據作為支撐。
建議建立穩定、有能力、有意愿長期堅持從事基礎監測事業的科研隊伍,針對養殖主產區和主要養殖品種,按照科學、標準的監測方法進行監測、樣品采集、分析和數據交匯,建立覆蓋我國海域養殖主產區物理水文、水化學、生物學長序列、多點位大數據庫,輔以數據挖掘和機制研究,明晰我們主產區主要養殖品種、養殖容量的動態變化特征,為我國養殖海域布局、可持續養殖管理策略的制定提供基礎數據支撐。以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所屬研究所為中心,利用省級研究所和地方研究所的地理位置優勢和基層實踐優勢,5~10年內形成黃渤海、東海、南海監測中心,建立涵蓋筏式養殖、底播增殖、灘涂養殖、網箱養殖等典型養殖方式的長期監測實驗站和掛靠省級以上科研院所的省級容量評估中心。各省所轄海域的容量評估工作可以委托省級評估中心來實施,逐步形成以省及自治區為單位的養殖水域容量評估制度。
3. 行政保障
國家行政機關如相應的管理委員會及地方政府以容量評估結果為指導,確定養殖密度和布局,發放養殖許可證,從宏觀上控制海水養殖規模,制定相應的違規處罰措施。另外,養殖海域的選址作為發展海水養殖的首要環節,應在容量評估結果的基礎上,結合海洋功能區劃現狀、當地漁業結構、資源狀況、航運交通等多種要素進行綜合論證。因此,建立養殖水域的容量評估制度,科學地調整養殖許可證和水域使用許可證的發放管理制度,應為制定水產養殖發展規劃的重要內容,并建立相應的實施和監督體系,以便確保水產養殖業規范化和標準化地發展[25]。
4. 政策保障
政府加強宏觀調控,以生態系統養殖理論為基礎,制定養殖管理以及海洋生態系統保護的行動準則,為各級政府和漁業漁政部門建立容量評估制度提供政治決策依據,全面推進水產養殖業執法與監管。
(二)設立養殖容量研究和布局與結構調整專項
目前,評估容量的方法主要有經驗研究法、能量/餌料平衡模型、生態動力學模型法等,各有利弊。缺乏完善的、通用的容量評估技術方法。不同生態系統間差異較大,難以進行比較研究。針對目前我國養殖容量評估存在的基礎理論和技術的薄弱環節,以生態系統健康、高效、可持續發展為核心目標,建立耦合動力過程的養殖生態容量、環境容量評估數值模型,將生態容量與生態系統健康評價有機地結合,促進生態容量評估技術、指標和模型的發展,為養殖水域的容量評估制度的科學有效實施提供技術保障[9]。依據養殖容量評估結果,結合各地資源條件、產業狀況和經濟水平,按照“主體功能突出、布局結構優化、統籌協調發展”的方針,積極推進現代漁業生產主導區、生態建設區和功能
拓展區建設,加快海水養殖業發展方式轉變、結構調整和區域拓展。
[1] 唐啟升. 關于容納量的研究[J]. 海洋水產研究, 1996, 17(2): 1–5. Tang Q S.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and its study [J]. Mar Fish Res. 1996; 17(2): 1–5.
[2] 董雙林, 李德尚.論海水養殖的養殖容量[J]. 青島海洋大學學報, 1998, 28 (2): 253–259. Dong S L, Li D S.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mariculture [J]. J Ocean Univ Qingdao. 1998; 28(2): 253–259.
[3] 楊紅生, 張福綏. 淺海筏式養殖系統貝類養殖容量研究進展[J].水產學報, 1999, 23 (1): 84–91. Yang H S, Zhang F S. Advances of studies on carrying cafacity of shallow sea for filter-feeding bivalve raft culture [J]. Fish Sci. 1999; 23 (1): 84–91.
[4] 杜琦,張皓. 三都灣網箱魚類養殖容量的估算[J]. 福建水產, 2010, 4: 1–6. Du Q, Zhang H. Estimation on the cage culture capacity of fishes of Sandu Bay [J]. J Fujian Fish. 2010; 4: 1–6.
[5] 黃洪輝,林欽,賈曉平,等. 海水魚類網箱養殖場有機污染季節動態與養殖容量限制關系[J] . 集美大學學報, 2003, 8(2): 101–105. Huang H H, Lin Q, Jia X P.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asonal dynamic of organic pollution and carrying capacity limit in marine net cage fish farm [J]. J Jimei Univ (Nat Sci). 2003; 8(2): 101–105.
[6] 姚煒民, 周燕, 沙偉, 等. 應用數值模擬方法計算小尺度海域養殖容量[J]. 海洋通報, 2010, 29(4): 432–438. Yao W M, Zhou Y, Sha W, et al. Application of numerical value simulation in estimat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smal1-scale sea area [J]. Mar Sci Bull. 2010; 29(4): 432–438.
[7] Cai H W, SunY L. Management of marine cage aquaculture—an environmental carrying capacity method based on dry matter conversion rate [J]. Enviro Sci Pol Res. 2007; 14(7): 463–469.
[8] 方建光, 孫慧玲, 匡世煥, 等.桑溝灣海帶養殖容量的研究[J]. 海洋水產研究, 1996, 17(2): 7–16. Fang J G, Sun H L, Kuang S H. et al. Assess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Sanggou Bay for culture of kelp Laminaria J Aponica [J]. Mar Fish Res. 1996; 17(2): 7–16.
[9] 張繼紅, 方建光, 王巍. 淺海養殖濾食性貝類生態容量的研究進展[J].中國水產科學, 2009, 16(4): 626–632. Zhang J H, Fang J G, Wang W. Progress in studies on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mariculture for filterfeeding shellfish [J]. J Fish Sci Chin, 2009; 16(4): 626–632.
[10] 朱春華, 申玉春, 謝恩義, 等. 湛江流沙灣馬氏珠母貝的養殖容量[J]. 熱帶海洋學報, 2011, 30(3): 76–81. Zhu C H, Shen Y C, Xie E Y, et al. Aquaculture carrying capacity of Pinctada martensii in Liusha Bay of Zhanjiang [J]. J Tro Oceanogra. 2011; 30(3): 76–81.
[11] 陳辰. 乳山海域長牡蠣養殖環境與養殖容量研究[D]. 青島: 中國海洋大學 (碩士學位論文), 2012. Chen C. Studies on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and carrying capacity of Pacific oyster farming sites in Rushan [D]. Qingdao: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Master's thesis); 2012.
[12] 劉學海, 王宗靈, 張明亮, 等. 基于生態模型估算膠州灣菲律賓蛤仔養殖容量[J]. 水產科學, 2015, 34(12): 733–740. Liu X H, Wang Z L, Zhang M L, et al. Carrying capacity of manila clam Ruditapes philippinarum in Jiaozhou Bay estimated by an ecosystem model [J]. Fish Sci. 2015; 34(12): 733–740.
[13] 張繼紅, 方建光, 王詩歡. 大連獐子島海域蝦夷扇貝養殖容量[J]. 水產學報, 2008, 32(2): 236–241. Zhang J H, Fang J G, Wang S H. Carrying capacity of Pationpecten yessoensis in Zhangzidao Island, China [J]. J Fish Chin. 2008; 32(2): 236–241.
[14] 盧振彬, 方民杰, 杜琦. 廈門大嶝島海域紫菜、海帶養殖容量研究[J]. 南方水產, 2007, 3(4): 52–59. Lu Z B, Fang M J, Du Q. Carrying capacity of Porphyra and Laminaria in Dadeng Island sea area of Xiamen [J]. S Chin Fish Sci. 2007; 3(4): 52–59.
[15] 史潔, 魏皓, 趙亮, 等. 桑溝灣多元養殖生態模型研究: III海帶養殖容量的數值研究[J]. 漁業科學進展, 2010, 31(4): 31–43. Shi J, Wei H, Zhao L, et al. Study on ecosystem model of multispecies culture in Sanggou Bay: III numerical study on the kelp culture carrying capacity [J]. Pro Fish Sci. 2010; 31(4): 31–43.
[16] Ge C Z , Fang J G. Reponse of phytoplangkton to multispecies mariculture: a case study on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shellfish in the Sanggou Bay in China [J]. Acta Oceanologica Sinica. 2008; 27: 102–112.
[17] 徐姍楠, 陳作志, 鄭杏文, 等. 紅樹林種植–養殖耦合系統的養殖生態容量[J]. 中國水產科學 2010, 17(3): 393–403. Xu S N, Chen Z Z, Zheng X W, et al. Assessment of ecological carrying capacity of interidal mangrove planting-aquaculture ecological coupling system [J]. J Fish Sci Chin. 2010; 17(3): 393–403.
[18] Inglis G J, Hayden B J, Ross A H. An overview of factors affecting the carrying capacity of coastal embayments for mussel culture [R]. NIWA, Christchurch; 2000.
[19] Henderson A, Gamito S, Karakassis I, et al. Use of hydrodynamic and benthic models for managing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marine aquaculture [J]. J Appl Ichthyol. 2001; (17): 163–172.
[20] Christensen V, Pauly D. ECOPATH II—a software for balancing steady-state ecosystem models and calculating network characteristics [J]. Ecol Model. 1992; 61(3–4): 169–185.
[21] Duarte P, Meneses R, Hawkins A J S, et al. Mathematical modelling to assess the carrying capacity for multi-species culture within coastal waters [J]. Ecol Model. 2003; 168: 109–143.
[22] Nunes J P, Ferreira J G, Gazeau F, et al. A model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shellfish polyculture in coastal bays [J]. Aquaculture. 2003; 219: 257–277.
[23] Dowd M. A bio-physical coastal ecosystem model for assessing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marine bivalve aquaculture [J]. Ecol Model. 2005; 183: 323–346.
[24] Ren J S, Stenton-Dozey J, Plew D R, et al. An ecosystem model for optimizing production in integrated multitrophic aquaculture systems [J]. Ecolog Model. 2012; 246: 34–46.
[25] 唐啟升, 丁曉明, 劉世祿, 等.我國水產養殖業綠色、可持續發展保障措施與政策建議[J]. 中國漁業經濟, 2014, 32(2): 5–11. Tang Q S, Ding X M, Liu S L, et al. Stragegy and task for gree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quaculture [J]. Chin Fish Econ. 2014; 32(2): 5–11.
Carrying Capacity Assessment and Its Application in Mariculture Management
Zhang Jihong, Lin Fan, Fang Jianguang
(Function Laboratory for Marine Fisheries Science and Food Production Processes, Qingdao National Laboratory for Mar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ellow Sea Fisheries Research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Qingdao 266071, Shandong, China)
With the growing scale of the mariculture industry, the problem of storage overcapacity in aquaculture has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aquatic environment and the aggravated the dangers of disease, which have hur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in the long term. So it is urgent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carrying capacity and to set up the scientific and adaptive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progress of research and existing problems relating to the mariculture industry's carrying capacity for cage, shellfish, macroalgae, etc; it also points out the key technologies behind capacity evaluation, including the index system of ecological capacity assessment, the numerical model of individual growth of cultured organisms, the coupling of hydrodynamic processes and ecological model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role of carrying capacity in determining the current population density of maricultural farms and optimizing the layout of the mariculture operations, expanding the maricultural farming space and building a new mode of maricultural farming. And then, this paper advanced three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a capacity evaluation system in aquaculture water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monitoring experimental station of the offshore aquaculture structure, culture capacity assessment, setting up research initiatives for aquaculture capacity research, and identifying the layout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for establishing a ecosystem management strategy.
mariculture; carrying capacity; management; model
S967
A
2016-04-20;
2016-05-16
張繼紅,中國水產科學研究院黃海水產研究所,研究員,研究方向為海洋健康養殖模式與技術研究;E-mail: zhangjh@ysfri.ac.cn
中國工程院重點咨詢項目“現代海水養殖新技術、新方式和新空間發展戰略研究”(2015-XZ-30)
本刊網址:www.enginsci.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