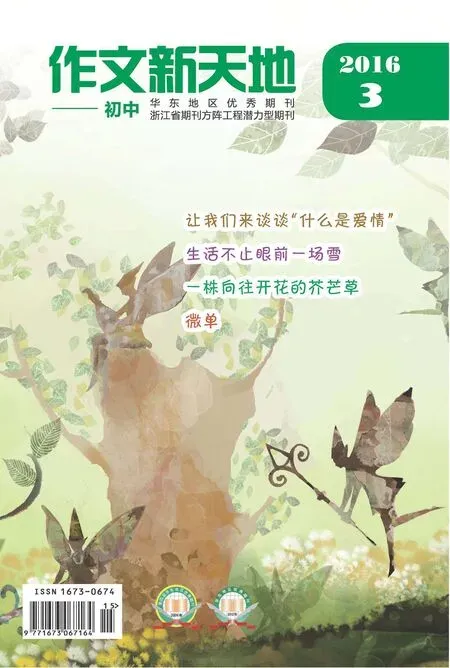七歲上學堂,九歲做“老師”
七歲上學堂,九歲做“老師”
◎王向陽


“小呀么小二郎,背著那書包上學堂。不怕太陽曬,也不怕那風雨狂。只怕先生罵我懶呀,沒有學問(啰)無顏見爹娘。(朗里格朗里呀朗格里格朗),沒有學問(啰)無顏見爹娘。”一九七五年九月,雖然千般不情愿,我這個無拘無束慣了的“小二郎”,也只有背起書包,乖乖地上學堂——浙江省浦江縣前店聯校。
記得在小學《語文》第一冊里,有一篇叫作《階級斗爭永不忘》的課文,使我終身難忘,至今能夠一字不漏地把它背誦出來:“爺爺七歲去討飯,爸爸七歲去逃荒。今年我又七歲了,高高興興把學上。”朗朗上口,容易背誦,容易理解。
先從修辭上來講,該文運用的是對比手法,“爺爺”和“爸爸”生活在舊社會,他們的命運不是討飯,就是逃荒,無比悲慘,而“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能夠背著書包上學堂,該是多么的幸福啊,自然而然地得出“新舊社會兩重天”的結論;而從音韻上來講,四句順口溜,第二句的末一字“荒”和第四句的末一字“上”押韻,都是“ang”韻,而第一句的末一字“飯”,雖然是前鼻音“an”,跟后鼻音“ang”不同,但南方人的普通話不太標準,往往分不清前鼻音與后鼻音,所以從寬泛的角度來看,也是押韻的,念起來就更朗朗上口了;再從語言上來講,四句二十八個字,沒有一個生僻字,“爺爺”“爸爸”“我”和“討飯”“逃荒”“上學”都是具象的,而非抽象的,明白如話。
在小學《語文》第一冊里,記得還有這樣一些課文:“學習張思德,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寫的是在延安燒炭時犧牲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學習白求恩”,寫的是不遠萬里從加拿大來到中國參加抗日戰爭的國際主義戰士白求恩大夫;“生的偉大,死的光榮”,寫的是堅貞不屈、死在敵人鍘刀下的十四歲女英雄劉胡蘭;“天上星,亮晶晶,我在大橋望北京,望到北京天安門,毛主席是我們的大救星”,寫的是杭州錢塘江大橋的守橋戰士蔡永祥烈士。這樣的內容安排,切合當時的形勢,可見編輯的良苦用心。
此外,語文課本里也充滿了學農支農的“泥土味”。記得第四課是農村常用詞:“水稻、棉花、花生、油菜”等。還有一課是《顆粒歸倉》:“稻子熟,一片黃,貧下中農秋收忙。紅小兵,拾稻穗,要教顆粒全歸倉。”第二十課的題目叫作《五七道路寬又廣》,畫面上是一個小孩子拎著籃子拾牛糞,為生產隊積肥,記得其中的兩句是“紅小兵,積肥忙”。所謂的“五七道路”,現在已經很陌生了,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澤東主席所作的《五七指示》,大意是:人民解放軍應該是一個大學校,要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工人、農民、學生也要這樣做。后來,便有了著名的“五七干校”。到了三年級以后,每冊課本后面附有一張非常實用的《農村常用詞表》,我從那里知道“耘田”等農村常用詞匯,受益匪淺。每年到了春夏之交,農民忙于收割麥子,播種早稻,學校里專門為此放一個星期的“農忙假”,讓學生回家幫助父母干農活,可見對務農的重視程度。這符合“學生也要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既要學文,也要學農、學工、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的最高指示。
我上語文課的最大興趣,在于背書。記得當時年紀小,記性好,過目成誦。有一天,同桌的留級生神秘兮兮地拿著課本向我炫耀,我看他每課課文的題目邊上多了一顆用紅墨水畫的五角星,很是羨慕,問了半天,他才得意地告訴我,那是語文老師畫的,因為他把課文背誦了。背課文可以得五角星?那不是小菜一碟嗎?我跟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樣,從此就纏著當時教我語文的方球琳老師背課文,跟同學們比一比,誰得的五角星多。后來,因為好勝心切,連沒有上的課文,我都預先背熟了,想背給方老師聽,結果挨了她的一頓批評。

至于當時的算術課,無非是十以內的加減乘除法,對我來說簡直是小菜一碟。因為我從小喜歡玩牌,點數的計算早已了然于胸。當時的算術課,也要貫徹“以階級斗爭為綱”的路線。記得教數學的王興育老師經常給我們出類似的題目:“解放前,農民張大爺租了地主的4畝土地,每畝產量300斤,其中250斤要交給地主。張大爺辛苦一年,只能得到多少糧食?”答案很簡單:(300-250)×4=200斤。800斤交租了,200斤留給自己,由此可見,農民受到了地主殘酷的剝削。
一九七七年上半年,我念小學二年級下學期,已經認了幾個字,便現炒現賣,稀里糊涂當起了“小老師”。我的學生不是別人,而是生我養我的姆媽。
當時,姆媽作為生產隊里的婦女隊長,當選為“貧下中農代表”,出席浦江縣貧下中農代表大會。作為一個農村婦女,能夠參加縣里的會議,自然是無上的光榮。會議開了三天,進場時會場兩邊還有人夾道歡迎。姆媽住在浦江縣府塔山招待所,吃的菜有三樣——魚凍、豬肉和青菜豆腐,因為一字不識,只能做點點人頭、領領饅頭的工作。
也難怪,姆媽從小沒有正式上過一天學,只在十五六歲的時候,讀過幾天夜校,認得的幾個字早已還給先生了。連外公、外婆都識字,當時目不識丁的姆媽痛下決心,要我教她識字。我二話沒說,一口應承,似乎從小就有“好為人師”的嫌疑。
我這個“小老師”當時到底教給姆媽這個“學生”幾個字,已經模糊了,似乎最初是“低語”二字,因為當時有一種練習本叫作“低語簿”,或許是“低年級語文練習簿”的意思吧。盡管姆媽這次有感而發,決心很大,但不久還是無疾而終。到底是我教得太差,還是她缺乏耐心,我記不得了,也不重要了。
作家小檔案

王向陽,男,1968年生,浙江浦江人,文學碩士,主任記者。愛好古典詩詞、傳統戲曲和鄉土散文,現為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中華詩詞學會會員、中國散文學會會員、浙江省作家協會會員、浙江省散文學會理事。著有散文集《戲劇的鐘擺》《六零后記憶》《最喜小兒無賴 一位六〇后的成長史》《梨園趣聞錄》和《鄉愁中國》。
給同學們的一句話:
咬住一事,鍥而不舍,堅持十年,必有所成。
給同學們推薦的書:
《約翰·克里斯朵夫》
責任編輯:陳玉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