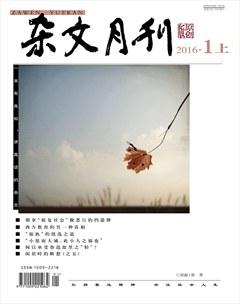偏愛《賈母的月亮》
2016-02-11 16:20:59李志遠
雜文月刊 2016年1期
李志遠
2015年第11期(上)《雜文月刊》佳作連連,但我偏愛鄧迎雪的《賈母的月亮》。
就此文而言,有故事、有形象、有情感,因此更貼近雜文的文學特質,也更使人喜聞樂見。賈母看到“月上中天,皎潔如銀”,說“如此好明月,不可不聞笛”,卻又囑咐下人“音樂不可過多,要那吹笛的遠遠的吹起來就夠”——幾句話,便使賈母的“文藝范兒”活靈活現,躍然紙上。從賈母繼而寫到陸游賞梅賦詩、張岱流傳至今的小品文《湖心亭看雪》、王子猷的任性風雅,讀者像是聽了一串小故事,生發出對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諸多美感。
當然,在追美的同時,也不忘排除丑的路障——敘罷賈母賞月,接著議論:今天看到美麗圓月,很可能多是“拿手機拍照”,“然后發到微信朋友圈分享”,“賞月”也就完成了。說完陸游雪中賞梅,筆鋒一轉,竟將自己的先生也擺了進去,“但他不愿在姹紫嫣紅的花前留影,問之為何,他答‘我一個大老爺們在花前照什么呢?”到文尾,針對當今生活步伐“變得匆匆又匆匆”說:“在我們忙碌的生活里,保留一些賈母那樣的小清新小文藝,陸游、張岱那樣熱愛自然萬物的癡心,也許我們的世界會變得更細膩、美好,一賞久違的詩情畫意”。仿佛拉家常,讓讀者易于接受。雷長風對林永芳的雜文有句評語:“誰說雜文只能尖銳凌厲?平和善意的真摯文字最能綿里藏針,有理有據的溫婉表達絲毫不減觸動心靈的力量。”應當說,這話對于隨筆式雜文《賈母的月亮》同樣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