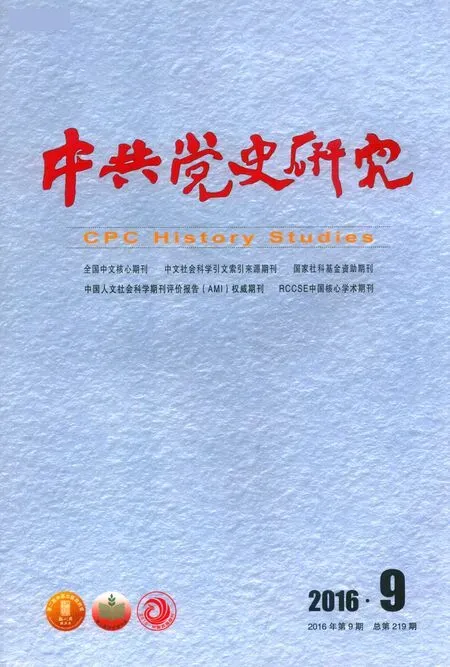中國改革的是哪個蘇聯模式——中國、蘇東改革研究中一個應當注意的問題
鄭 謙
·專題研究·
中國改革的是哪個蘇聯模式
——中國、蘇東改革研究中一個應當注意的問題
鄭 謙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蘇聯逐漸出現了一個有別于原斯大林模式的蘇聯模式。雖然兩者尚無根本區別,但它們的差異也是不應忽視的。1956年前后,與蘇東等國相同,中國一開始就把斯大林模式確定為改革對象,但不久便因失誤走上了維護這種模式的道路,與蘇聯東歐等國拉開了距離。1978年后,當中國再次開始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后,很快就走到了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的前列,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與此同時蘇東等國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在取得一定進展后陷入停滯,直至引發蘇東劇變。社會主義各國改革的艱難揭示了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深層次特征,以及落后國家以社會主義方式實現現代化的一些規律。
斯大林模式;蘇聯模式;蘇東改革;中國改革
一般認為,蘇聯模式是1956年后中國改革的對象,但這種說法還欠準確。廣義的蘇聯模式包括了俄國十月革命至1991年蘇聯解體74年發展道路的框架與特征,如從戰時共產主義到新經濟政策,從斯大林模式再到對這種模式進行改革的蘇聯模式,等等。而狹義上的蘇聯模式則是在這一整體過程中以鮮明特征區別于其他階段的某一特殊階段。本文從狹義上把它區分為1953年前的斯大林模式和此后處于曲折改革中的蘇聯模式。盡管兩者可統稱為蘇聯模式,但其內在的區別也是明顯的。雖然中國從1956年起就明確地把斯大林模式確定為改革對象,但不久就因失誤走上了維護斯大林模式的道路,與同時進行改革的蘇聯東歐等國拉開了距離。1978年后中國走上了正確地改革斯大林模式的道路,并很快超越了其他長期陷于停滯、反復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初步建立起嶄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從狹義上準確地區分兩種蘇聯模式,有利于弄清中國改革的起點、對象及由此決定的種種特點。
一、 從改革到停滯:蘇東國家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1.赫魯曉夫時代的改革
斯大林在領導蘇聯革命、建設和反法西斯戰爭中作出了卓越貢獻,但因在理論和實踐方面一些嚴重失誤,他逝世前蘇聯社會已積累了許多嚴重矛盾,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弊端已比較突出。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已經是蘇聯黨的當務之急。蘇共新一代領導人對這種模式的反思和改革,并不始于1956年蘇共二十大,而是在斯大林去世后便展開了。在政治上,1953年3月,即他去世當月,蘇共就開始著手解決黨政最高權力過分集中在個人手中的問題,使新任命的部長會議主席不再擔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決定按黨章規定定期舉行中央全會,使中央委員會成為經常起作用的機關,恢復集體領導,解決舊體制黨政不分、高度集權的問題,改善黨內生活;改革干部管理體制,實行干部任期制和輪換制,取消或縮小特權制度,等等。當年6月,《真理報》發表文章,提出反對個人崇拜問題,7月蘇共中央全會討論了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此后的兩年多時間里,蘇聯理論界陸續發表文章、講話,批判個人崇拜,揭露斯大林的錯誤。與此同時,開始大規模地平反冤假錯案,強調恢復和健全法制,改組了國家安全機關,把它置于黨的各級領導之下。*參見〔蘇〕羅伊·A.麥德維杰夫等著,鄒子嬰等譯:《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6頁;王正泉主編:《從列寧到戈爾巴喬夫:蘇聯政治體制的演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第218—219頁。
在經濟上,自1953年9月蘇共中央全會起,開始改變經濟發展次序,強調發展農業、住房建設、輕工業和消費品的生產,注重物質利益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為解決經濟上高度集權問題,調整經濟體制,下放管理權限,擴大企業管理權限,減少下達給企業的指令性計劃指標。1954年8月蘇聯部長會議通過決議減少了52%的國家指令性計劃,擴大了企業在計劃、財務、勞動工資待遇方面的自主權。與此同時,進一步調整農業政策,鼓勵農民發展自留地、自留畜,提高農副產品收購價格,努力改變農業長期落后的局面。
在國際上,改變了斯大林時代與西方僵硬對峙的方針,努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強調兩種制度共存,提出用和平手段解決爭端,建議召開世界普遍裁軍會議等,擴大與西方的經濟聯系,加強國際合作,等等。在國際共運內部,1953年6月即主動恢復同南斯拉夫的外交關系,承認社會主義的不同具體形式應由各國人民自己解決,實際上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社會主義模式的多樣化,等等。*參見劉新宜:《社會主義國家演化簡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第167—170頁。
經過近3年思想準備和政策調整,1956年2月蘇共召開了在歷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把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推向高潮。二十大的主要內容有三項:一是對國際政治和國際共運提出了一系列新觀點,如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雖然必須對帝國主義發動戰爭保持警惕,但也要看到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將會越來越多樣化,不一定必然同國內戰爭聯系在一起,等等。二是在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提出在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同時,實現農業的迅速發展,加快技術進步和消費品生產速度;在生產管理中貫徹個人物質利益原則,提高蘇聯人民物質福利和文化水平;重視介紹西方發達國家工農業發展成就。三是批判斯大林個人崇拜的錯誤,進一步解放思想。
蘇共二十大既凸顯了時代發展的迫切要求,又反映了時代的局限性,表現出明顯的兩重性:一方面它在一些重要方面提出了改革斯大林模式的任務,解放了思想,沖破了教條主義的嚴重束縛,為社會主義國家根據本國實際探索建設道路創造了有利條件。中國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全面探索自己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另一方面,從總體上看,它所提出的發展戰略和改革目標仍帶有傳統模式的濃厚色彩;在分析斯大林晚年錯誤時,側重于個人因素,未觸及黨的領導體制等深層問題。此外,它對斯大林錯誤的批評方式也很不妥當,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國際上引起了嚴重的后果。
一個往往被忽視的重要問題是,以1953年為界,隨著蘇共改革的開始,原有的斯大林模式已逐漸不再完整,實際上已經出現了兩個雖然基本框架一致但又有所區別的、沒有清晰界線的“蘇聯模式”:一個是終止于1953年的蘇聯模式,即未經改革的斯大林模式;一個是1953年后即處于曲折改革進程中的蘇聯模式——盡管改革一直未能取得實質性突破。有學者把它稱為“后斯大林模式”。把這兩者、兩個階段加以區分是必要的。這不僅涉及對赫魯曉夫及其之后蘇聯改革的評價,而且涉及對中國改革起點、特征的認識。在這個問題上,應防止兩種傾向:一種是夸大蘇聯改革的意義,低估了此后斯大林模式的影響、作用;另一種是貶低蘇聯改革的作用和意義,認為50年代后的蘇聯模式還是原來的那個斯大林模式。
蘇共二十大后,蘇聯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在曲折中又有所發展。在農業方面,擴大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的生產自主權,推廣小組包工獎勵制度,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放寬對農民經營個人副業的限制、貫徹物質利益原則,改革勞動報酬制度,等等。在工業管理體制方面,繼續克服經濟體制高度集中的弊病,調動地方積極性,從1957年起開始把工業和建筑業的領導重心由中央轉移到地方,取消大部分中央部委的直接領導,由按部門管理改為按地區管理。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新綱領和決議提出了以擴大企業權限、加強經濟刺激、充分利用商品貨幣關系和經濟杠桿,加強以經濟核算為中心的比較完整的改革思路和方向,使改革從主要是調整“條條”“塊塊”關系發展到改變經濟運行機制等更深的層次。與此同時,在政治領域的改革也取得一些進展。
1962年赫魯曉夫支持了由著名經濟學家利別爾曼《計劃·利潤·獎金》一文引發的大討論,提出要用經濟手段即利潤、獎金、價格等手段,代替行政手段來刺激生產,提高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發揮企業經營主動性,克服平均主義,改進計劃工作,實際上提出了社會主義條件下計劃與市場的關系問題。從1964年初開始,在赫魯曉夫的支持下,若干企業進行以利別爾曼建議為核心的試驗,把經濟改革推向高潮。雖然這次討論和試驗不久便因赫魯曉夫下臺而中斷,但為1965年后柯西金全面推行“新經濟體制”試驗作了輿論和理論上的準備,對東歐國家20世紀60年代相繼進行的經濟體制改革產生重要影響。這些改革雖然未能從總體上觸及原有的經濟體制,但卻是社會主義第二次改革浪潮中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大事件。*國內外一些學者提出,20世紀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過三次經濟改革浪潮;第一次發生在五六十年代。這次改革發端于南斯拉夫,蘇聯、匈牙利、波蘭、中國等也隨后卷入其中,其核心是反思斯大林模式的弊端,開始嘗試改革本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第二次發生在六七十年代,主要有蘇聯、東歐等國家參與,其結果是一部分國家的經濟改革發生了部分退卻或受到遏制。第三次出現在80年代,蘇聯、東歐國家采取了激進的政治經濟改革,而以中國為代表的一些國家則采取了漸進式改革的模式。參見〔法〕貝爾納·夏旺斯:《東方的經濟改革——從50年代到90年代》,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波〕W.布魯斯著,鄭秉文等譯:《社會主義的所有制與政治體制》,華夏出版社,1987年。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曾大力介紹利別爾曼的經濟思想,但一直受到冷遇,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為“中國的利別爾曼”。
“赫魯曉夫執政的年代,是蘇聯進行了真正的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時期。盡管這些改革充滿矛盾,而且畢竟是有限的,但在實際上,蘇聯社會生活的每一領域無不受到1953年至1964年這段時期變革的影響。”*斯蒂芬·科恩語,轉引自〔蘇〕羅伊·A·麥德維杰夫等著,鄒子嬰等譯:《赫魯曉夫的執政年代》,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頁。赫魯曉夫是個充滿矛盾的人物,他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績,但又存在嚴重的不足,如改革缺乏理論準備,措施凌亂多變,出臺倉促,缺乏總體設計和慎重考慮,隨意性大,改革措施首尾不一,往往半途而廢或淺嘗輒止,進一步退兩步,往往流于一般號召。特別是在改革取得一些成績而自己又大權在握時,便又重蹈舊模式覆轍。如1957年11月他在慶祝十月革命40周年大會上提出:“今后十五年內不僅趕上而且超過美國”的目標,重犯急躁冒進、急于求成的通病。他過高估計蘇聯社會主義發展程度,在1961年二十二大上認為蘇聯已建成社會主義,進入全面開展共產主義建設的階段,并以此為基礎提出諸如“全民國家”“全民黨”之類口號,似乎蘇聯不久便要進入共產主義了。在農業取得一些成就時又提出求高、求快、求純的目標,由改革初期鼓勵農民發展自留地和個人副業,變為后期減少自留地、限制個人副業,急于向公有制高級形式過渡。在批判了斯大林大權獨攬后,1958年赫魯曉夫又以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身份兼任部長會議主席,此后又大搞個人專權,壓制黨內民主,對特權階層、官僚主義妥協。在文化政策、知識分子政策上,很快從“解凍”走向收緊和壓制,挫傷了知識分子積極性。改革——冒進——倒退——再改革的循環成為蘇聯社會常態。
在國際事務和外交方面,赫魯曉夫更是重復了斯大林時代的許多錯誤。如對中國和東歐社會主義諸國搞大國沙文主義,要求這些國家服從蘇聯的指揮棒和戰略利益,遇有不服從者便批判、圍攻甚至中斷援助。在緩和國際關系的同時,又希望由美蘇兩大國共同主宰世界。凡此種種,正如毛澤東所說,赫魯曉夫“批評了斯大林,現在他又在搞斯大林的東西”*《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93頁。。
從總體上看,赫魯曉夫的改革是不成功的,但它是當代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斯大林模式漫長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是改革的有益嘗試,帶有社會主義國家早期改革的通病。他同時兼有舊體制的產物與舊體制的改革者、“體制病”患者與“體制病”改革者這樣的雙重身份,是一個迫切希望改革斯大林模式的斯大林主義者。但當人們指責他的失誤時也應看到,他未解決的那些問題在之后的幾十年間又解決了多少?他的錯誤在此后幾十年間還被多少后繼者一再重復?所以,對他的批評不應停留在個人因素的層次上,而應看到這正是斯大林模式固有的“體制病”的外在的、人格化的表現。赫魯曉夫的境遇說明,當代社會主義的改革充滿了艱難曲折,不是一個人、一代人、一次沖擊就可以順利完成的。
2.勃列日涅夫時期的改革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臺后,首先開始著手糾正赫魯曉夫改革失誤帶來的一些混亂,進行一系列理論、政策調整。比較突出的就有糾正了赫魯曉夫超越階段的錯誤,以“建設發達社會主義”的概念取代了以往“全面開展共產主義建設”的提法,等等。另一方面,在以往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改革,如在工業中推行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減少國家指令性計劃;加強經濟核算和經濟刺激;提高農產品收購價格,取消對家庭和個人副業的過多限制,大力增加農業投資;加快農業機械化、集約化,等等。上述一系列調整和改革,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從總的方面看,仍未從根本上擺脫斯大林模式的束縛,在計劃經濟、單一所有制、商品經濟、市場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等方面仍裹足不前,未取得實質性進展。1972年底的蘇共中央全會批評了柯西金的新經濟體制,并要求警惕“市場社會主義”。
隨著政治地位的穩固、蘇聯國力的增強和國際地位的提高,勃列日涅夫又重蹈赫魯曉夫覆轍,重犯“體制病”。個人專權,權力高度集中,*1977年勃列日涅夫又以總書記身份兼任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個人崇拜盛行,黨政不分,以黨代政,任人唯親,高層領導年齡老化,干部領導職務終身制、國家機關機構臃腫,安于現狀、因循守舊的官僚主義充斥,教條空談盛行,自我感覺良好,不斷擴大并穩定的特權階層反對任何改變現狀的改革,僵化保守趨勢日益嚴重,改革逐漸趨于停滯,經濟發展速度放緩。到勃列日涅夫晚年,蘇聯已從穩定走向全面停滯,改革效率遞減。改革的停滯造成一系列嚴重政治、經濟后果,持不同政見者、“雙面人”大量出現。
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為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大搞軍備競賽,對外推行霸權主義,四處用兵,使其背上了沉重的軍費包袱。在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上,繼續赫魯曉夫后期的反華路線,加強對中國的軍事威脅;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壓制東歐各國的改革。
從1953年斯大林去世到1986年戈爾巴喬夫上臺,在30多年的時間里,蘇聯的改革起起伏伏,曲曲折折,始終未能取得實質性進展。改革的停滯與“空轉”,使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發展,導致整個社會改革呼聲的不斷激進化,是導致1989年蘇東劇變的基本原因之一。
3.東歐等國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
戰后,社會主義超出了蘇聯疆域,成為一個陣營。在冷戰初起的背景下,在蘇聯強勢推動下,東歐各國絕大多數開始全盤接受斯大林模式,并在實際上接受蘇共的領導。日趨嚴峻的冷戰形勢為蘇聯強制推行傳統模式提供了豐厚的土壤,限制了東歐各國探索適合自己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可能性。“東歐斯大林主義的主要特征是對蘇聯模式的模仿和無條件地服從莫斯科的指示”,它的“任何改革都要首先由莫斯科來推動”*〔英〕本·福凱斯著,張金鑒譯:《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第115頁。。沒有選擇的自由,只有統一和服從,這是1953年前多數東歐各國突出的特點。
因歷史與地緣等各方面的差異,東歐多數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一般都高于十月革命時的蘇俄,加之民族關系方面錯綜復雜的矛盾,斯大林模式在東歐諸國的推行往往是比較勉強的,一些國家從一開始就有所抵制。南斯拉夫在1950年就開始了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波蘭、匈牙利等國照搬斯大林模式并因蘇聯對它們內政、外交的各種干預,政治、經濟上的矛盾日漸突出,工人罷工、農民學生鬧事等不斷發生,嚴重地束縛著社會主義的發展。一場深刻的改革已經呼之欲出。
1953年后的幾年間,在蘇聯改革的影響下,“解凍”浪潮也席卷東歐各國,推動他們程度不同地進行了一些被稱作“新方針”的改革。例如:放慢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的速度,改變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鼓勵發展私人農業,允許農民退出集體農莊,強調發展輕工業,改善人民生活水平,重視黨的集體領導,強調社會主義建設要從本國實際出發,放寬文化政策,發展黨內外民主,等等。這些“新方針”不久就因受到黨內保守勢力的抵制而步履蹣跚。改革的遲緩和反復激化了積累已久的各種矛盾,直至釀成1956年諸如波匈事件那樣的嚴重后果。
對國際共運和社會主義各國來說,1956年是開始大規模地對斯大林模式進行改革的一年,堪稱是一個不平凡的轉折年頭。 “從1956年起,把各共產黨同蘇聯連在一起作為它們唯一營養來源的那條臍帶斷了。各黨于是開始了制訂自己對共產主義理論與實踐的態度。”*喬·烏爾班主編,石益仁譯:《歐洲共產主義》,新華出版社,1980年,第9頁。“人們不再談論有什么獨一無二的領導了,相反,人們在談論由于走不同道路而取得的進展。”“蘇聯的模式不能、也不應當再是什么必須遵循的模式了。”蘇共二十大在各社會主義國家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在東歐,有人稱它是“一塊引發山崩地裂的大石頭”。人們逐漸開始接受了這樣一個現實,取代資本主義現代化模式的并非只有斯大林式的社會主義一種*這是意大利共產黨總書記陶里亞蒂在蘇共二十大結束后第二天發表的談話中所指出的。參見〔意〕貝爾納多·瓦利著, 張慧德譯:《歐洲共產主義的由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第148頁。。此后,社會主義各國雖然在總體上還受到斯大林模式的巨大影響,但畢竟開始了從一種模式到多種模式的過渡。如果說1945年二戰結束實現了社會主義從一國到多國的轉變的話,那么,1956年則可以說是實現了社會主義改革從一國到多國的轉變。改革的浪潮第一次席卷了多數社會主義國家,此即戰后社會主義史上第一次改革浪潮。
在這次改革浪潮中,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先后提出反對照搬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即斯大林模式),強調從本國特點出發,探索適合本國特點的社會主義道路。1956年前后,波蘭一些經濟學家已提出引進自由的、市場決定的價格體系,要求分權和指令性計劃相結合,引進西方投資和恢復私人企業,中央計劃要通過市場機制和直接工業民主來實施,*參見《東歐共產主義的興衰》,第140、148頁。等等。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在平反冤假錯案的同時,恢復和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重開民主化進程并開始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和集體領導;調整農業政策,實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按照自愿方式重新進行合作化;要求在實現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原則的同時,必須實行經濟的分散領導,發揮企業、國營農場等獨立經營管理經濟的作用;建議實行較大程度的放權,并在更大程度上依靠經濟管理手段,等等。
在20世紀60年代前期東歐等國出現的第二次改革浪潮中,多數國家又開始謹慎地醞釀和進行一些經濟體制改革。1964年10月捷共中央公布了以解決黨政企不分、讓企業成為按經濟規律活動的主體、提高獎金和利潤等的刺激作用為主要內容的《關于完善國民經濟計劃管理的原則草案》。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會通過了《捷克斯洛伐克通向社會主義的道路》的改革綱領,希望賦予社會主義發展以新的形式,堅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與此同時,匈牙利、波蘭、民主德國、保加利亞等國也進行了內容大體一致但程度有所不同的改革,并都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因傳統觀念的嚴重束縛、蘇聯的干預、國際上各種因素的制約以及領導者的失誤,這些改革大多不久便陷于停滯,改革效益開始大幅度遞減,各種社會矛盾又開始不斷積累。
縱觀近40年來蘇聯、東歐等國改革,可以得出幾個結論:(1)不論過程如何曲折、反復甚至倒退,就其基本線索來看,都是把對斯大林模式作為改革的對象,改革的基本內容、過程也大多類似。(2)改革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取得了一些成功,到20世紀80年代末,1953年前的蘇聯模式(即斯大林模式)在一些重要方面已經有所改觀。(3)但就這一模式的一些基本方面(如計劃經濟、單一公有制、高度集中、排斥市場、黨政不分、高度集權、缺乏民主等)來說,改革仍然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
二、從改革到回歸:中國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1953年至1976年)
新中國成立頭三年,在新民主主義建國理論的指導下,中共全面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大綱。在經濟上,實行混合經濟,在優先發展國營經濟的基礎上,實行公私兼顧、勞資兩利、城鄉互助、內外交流的政策。在國營經濟的領導下,多種經濟成分并存、計劃與市場并存、多種分配形式和積累形式并存,共同繁榮。與此同時,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政治、文化綱領。從這些方面來看,它與列寧新經濟政策和他1921年后有關過渡時期的理論有不少相近之處,*新經濟政策的重要內容是強調發展商品經濟,用商品交易代替產品分配并允許多種經濟成分存在,利用資本主義文明成果建設社會主義,等等;1921年后,列寧更多地強調越是落后國家,過渡時期越長。受斯大林模式的影響較小。三年經濟恢復和社會改造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豐富了落后國家通過特殊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理論,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內容上都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
1953年至1976年間,中國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從總體上看表現為從全盤接受——開始改革并取得一些積極成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回歸舊模式——把舊模式的一些弊端推向極端。20多年時間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53年至1956年,從全盤接受到開始改革斯大林模式。
從1953年起,根據變化了的國內外形勢的迫切需要,按照斯大林模式和當時對社會主義的理解,中共中央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由實施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轉向全面學習斯大林模式。在經濟建設上,采取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在政治上和社會改造方面,實行用國家資本主義形式與和平贖買政策改造資本主義工商業,用逐步過渡的形式改造農業和個體手工業;在所有制結構方面,按照斯大林模式的標準,消滅資本主義和農業、手工業中的個體生產,實行單一社會主義公有制,限制商品經濟作用的范圍和深度。這就是當時所說:過渡時期總路線就是解決所有制的問題,*《毛澤東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1頁。“使資本主義絕種,使小生產絕種”*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第351頁。,“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惟一的經濟基礎”*逄先知等主編;《毛澤東傳》(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第267頁。。現在來看,這些當時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廣泛流行的斯大林模式的基本觀點,有很大的局限性*參見《毛澤東傳》(上),第267頁。。
可以說,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正是從全面仿效斯大林模式開始起步的。特別應當注意的是,當時這種模式在蘇聯、東歐等國已經成為改革對象。與40年代末東歐各國往往是被動地接受斯大林模式不同,中國更多的是主動地、全面地、真誠地接受。從當時中國國情出發,這種模仿、接受是必要的,其主要原因在于當時中國面臨的嚴峻國際形勢,以及一些基本國情更接近20年代至30年代的蘇聯。在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我國在很短的時間里初步奠定了工業化的基礎,實現了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
從模式選擇的角度看,如果說前三年接近列寧新經濟政策的話,那么從1953年起則主要是以斯大林模式為基本依據和標準的。在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同時,中共中央號召“要在全國范圍內掀起學習蘇聯的高潮”*毛澤東語,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第45—46頁。。這種情況的出現一是因為蘇聯工業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二是毛澤東當時和后來曾多次談到的:“因為我們不懂,完全沒有經驗,橫直自己不曉得,只好搬。”*《毛澤東傳(1949—1976)》(上),第791頁。在經濟建設特別是重工業方面,“幾乎一切都抄蘇聯,自己的創造性很少”。“缺乏創造性,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參見《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05頁。
但也應看到,由于中共豐富的革命經驗及旺盛的創造力,近四年中,盡管基本上主要是仿效斯大林模式,但在某些內容和形式上也有一些鮮明的中國特色,特別是在三大改造方面和政治體制建設方面。幾年后,毛澤東甚至說基本上照抄蘇聯的辦法,總覺得不滿意,心情不舒暢*《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17頁。。
這種轟轟烈烈地基本上全盤接受斯大林模式的局面很快發生變化。1953年中國開始大規模計劃經濟建設后,立即從自身的經驗中對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弊端有了切身感受。另一方面,蘇共從1953年起不斷發展起來的對斯大林錯誤的批評、反思也漸漸引起了中共的注意。*如1954年4月中國駐蘇使館給中央的報告中指出:一年來蘇聯宣傳中對斯大林的提法有了一些改變,主要是改變了對他功績提得過高的偏向,如此等等。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239頁。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1956年前后,即蘇共二十大前后和中共八大前后,中國開始了由“以蘇為師”到“以蘇為鑒”的深刻轉變,從全面學習到醞釀對斯大林模式改革、探索自己的建設道路。這離1953年正式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還不到4年時間。
這種轉變在蘇共二十大前后出現了一個高潮。毛澤東多次贊揚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評,說它“打破了神化主義,揭開了蓋子,這是一種解放,是一場‘解放戰爭’,大家都敢講話了,使人能想問題了”*《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27頁。;“感謝赫魯曉夫揭開了蓋子”*毛澤東對《若干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批語和修改(1956年4月2日、4日)。,說明“蘇聯、蘇共、斯大林并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這就破除了迷信”,“有利于反對教條主義”*吳冷西:《憶毛主席》,新華出版社,1995年,第4、6頁。。搞社會主義建設不一定完全按照蘇聯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據本國的具體情況,提出適合本國情況的方針和政策。
毛澤東在他的名篇《論十大關系》的開頭就提出:“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過去我們就是鑒于他們的經驗教訓,少走了一些彎路,現在當然更要引以為戒。”*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全文貫穿著以蘇聯經驗教訓為借鑒探索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精神。他號召全黨 “我們學習蘇聯,要包括研究它的錯誤”,“把蘇聯走過的彎路避開”,“應當爭取這個可能”*毛澤東:《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注意,這里所說的蘇聯經驗教訓也就是斯大林模式的經驗教訓。)他要求全黨不要再認為蘇聯所做的一切都是絕對真理,而應該更好地考慮中國的問題。“中國和蘇聯兩個國家都叫社會主義,有不同沒有?是有的。”他指出:現在我們有了自己的初步實踐,又有了蘇聯的經驗和教訓,應當更加強調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在結合上下功夫。“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吳冷西:《十年論戰》(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9年,第23頁。與此同時,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等黨中央領導集體成員也提出了許多類似思想。經過對斯大林模式的初步反思,“走自己的路”的思想在黨內外引起了廣泛的共鳴與呼應,成為全黨的共識。
在以上認識的基礎上,以中共八大的召開和《論十大關系》《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重要歷史文獻的發表為標志,中國開始了對斯大林模式的最初改革。全黨解放思想,意氣風發,進行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的探索,尋找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毛澤東后來曾多次說過,前幾年經濟建設主要是學習外國經驗,1956年《論十大關系》,開始提出自己的建設路線,有我們自己的一套內容*參見胡繩主編:《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第438頁。。
八大前后,中共在發展經濟、政治、文化、科學等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觀點和方針,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例如,在經濟建設方面,針對蘇聯片面強調重工業,忽視輕工業、農業的積弊,提出要正確處理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系,*參見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在發展重工業同時,更多地發展農業、輕工業*參見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針對蘇聯中央集權過多的問題,提出應當在鞏固中央統一領導的前提下,擴大一點地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不能像蘇聯那樣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點機動權也沒有;*參見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為糾正經濟建設中盲目“冒進” 的傾向,確定既反保守又反冒進的方針;為解決三大改造中要求過急、形式過于簡單劃一等問題,提出進一步調整經濟關系的“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方針,提出“可以消滅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的新思路;通過改進工業、商業、財政管理體制的決定,探索改進經濟管理的方針政策。在發展科學技術和文化藝術方面,提出“雙百”方針,強調知識分子中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在政治方面,指出國內主要矛盾已不再是階級斗爭,要求全黨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強調擴大人民民主、建立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在處理國際關系方面,堅持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的外交方針;在黨的建設方面,強調加強執政黨建設、發展黨內民主,反對個人崇拜,等等。這些都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良好開端。
由于時代的局限,剛剛開始的改革還不可能觸及斯大林模式的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往往只是在其基本框架內進行一些局部的、修補性的、淺層次的調整,即“原則和蘇聯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毛澤東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369頁。。正是這些局限,潛伏著此后改革發生反復的可能。
另一方面,與這種正確或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勢并存的,還有一種不那么正確的發展趨勢。例如,毛澤東雖然肯定了蘇共二十大對斯大林的批評,但又很快把這種批評等同于“全盤否定”。他還認為,二十大提出可以通過議會道路去取得政權,這就是說“各國可以不學十月革命了。這個門一開,列寧主義就基本上丟掉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類似的觀點(包括和平共處等)毛澤東以后還曾多次提及*例如1960年5月他說蘇共二十大就是和平過渡、反斯大林兩條,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4卷,2013年,第405頁。。現在看來,這些觀點確實是有些簡單化了。
在分析波匈事件的原因時,毛澤東一方面正確地指出波匈事件的發生就是照搬蘇聯模式的結果*《毛澤東文集》第7卷,第64頁。,另一方面,他又越來越多地傾向于認為這些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這一下暴露出來了”*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東歐一些國家的基本問題就是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沒有搞掉,沒有在階級斗爭中訓練無產階級”,“不依靠群眾進行階級斗爭,不分清敵我,這很危險”*毛澤東:《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在他看來,二戰后蘇聯、東歐一些國家的黨,不講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不講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結果出了個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他還批評:“東歐土改后沒有趁熱打鐵,實行集體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批注和講話》,1997年,第874頁。,如此等等。現在看來,波匈事件的發生,肯定有反革命和西方反共勢力的作用,但這不是主要原因。說東歐沒有趁熱打鐵搞集體化,實際上正是他們糾正強行推廣斯大林模式的正確舉措。*20世紀40年代末,東歐一些國家不顧本國實際強制推行斯大林模式搞集體化,造成農業滯后和農民不滿。在50年代初改革斯大林模式時,東歐諸國都把縮小集體化規模、鼓勵農民個體經營當成重要任務之一。對波匈事件等這些片面總結,成為1957年“反右”斗爭誘因之一。
對1953年至1956年中國發展的觀察,應注意兩條線索的發展、交織:一條是以全盤接受斯大林模式取代了新民主主義建國綱領的實踐;一條是幾乎在接受斯大林模式的同時,就開始了對它的改革。在50年代初社會主義國家第一次改革浪潮中,一度有一個良好的開端,在一些重要方面站到了社會主義各國改革的前列。
第二階段:1957年至1966年,逐步從改革斯大林模式轉向維護斯大林模式,批判蘇東等國的改革。
1.不成功的政治改革
八大后的一段時間里,在中共八大路線的指引下,對斯大林模式的突破、改革基本上在政治和經濟兩個主要方面展開。但很快,這個探索便出現了嚴重失誤,逐漸走偏了方向。失誤從1957年開始,首先出現在政治領域,這就是反右派斗爭嚴重擴大化。幾年之后,這次嚴重失誤被當成對斯大林模式的成功突破。
在社會主義社會階級斗爭問題上,斯大林在不同時期講過不同的話,出現過較大反復,往往處于一種矛盾的狀態中。1934年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七次代表大會上宣布,蘇聯國內不再存在敵對階級。在基本上完成農業集體化后,他又宣布蘇聯“已經不存在彼此對抗的階級”,“沒有階級沖突”*轉引自《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1963年9月13日)。。1936年的蘇聯憲法也確認了這一點。但他在1937年和1938年又犯了肅反擴大化的嚴重錯誤,并提出:“我們的進展越大,勝利愈多,被擊潰了的剝削階級也會愈加兇惡,他們愈要采用更尖銳的斗爭形式,他們愈要危害蘇維埃國家”*《斯大林文選》上冊,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129頁。。
八大前后,毛澤東曾幾次講過:斯大林時期,階級沒有了,社會已進入沒有階級的社會,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631、633頁。。他多次批評斯大林一方面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還存在矛盾和階級斗爭,一方面在宣布蘇聯消滅階級、進入社會主義后,思想仍停留在舊社會的時代,“還要繼續進行階級斗爭”,認為“這就是錯誤的根源”*《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2卷,第631頁。。在中共八大上,中央鄭重地宣布階級斗爭不再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全黨、全國的工作重心應轉向經濟建設。可以肯定地說,如果在政治方面的改革能沿著這個正確方向走下去,大的曲折完全能夠避免。
但僅僅一年,因1957年的反右派斗爭的嚴重擴大化,中共輕率地放棄了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論斷,重新把階級斗爭確定為社會主義時期的主要矛盾,1957年因此成為從改革斯大林模式到維護斯大林模式的轉折點。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又進一步把階級斗爭引向黨內高層。這種處理黨內分歧的方法基本上重復了斯大林當年的做法。1962年,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反復提出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問題;強調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這兩個階級、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于“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后來這個論斷被稱作黨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踐”,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確定為黨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基本路線。*參見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2卷下冊,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10—711頁。確立了這條“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基本路線后,自1963年起,階級斗爭擴大化的錯誤通過“四清”、“五反”、意識形態領域里的批判以及中蘇大論戰等形式,在經濟、政治、文化等領域不斷發展,直到發動“文化大革命”。
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的發展,毛澤東又反過來批評斯大林的錯誤在于過早宣布蘇聯消滅了剝削階級,不承認社會主義存在階級斗爭,沒有搞好階級斗爭,“不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群眾進行反對資本主義勢力的斗爭”*《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載于《關于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論戰》,人民出版社,1965年,第462頁。。1964年開展“四清”運動時,他又表示:“斯大林是長期抹煞社會矛盾,反對講社會有矛盾,總是強調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一致的。我們就鑒于這個教訓,公開發動群眾來認識這個問題。”*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第361頁。這就是說,斯大林的錯誤不是在階級消滅后還要進行階級斗爭,而是沒有繼續進行階級斗爭,因而導致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集團”的出現和資本主義的復辟。顯然,諸如此類的說法已經完全改變了八大前后的相關認識。1975年底,毛澤東更是提出,階級斗爭是綱,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這個問題上犯了大錯誤”*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 ,第621頁。。按照當時流行的說法,“文化大革命”就是對斯大林晚年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中存在階級斗爭錯誤的糾正,亦即從政治方面對斯大林模式的突破和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一個觀點是:“斯大林搞了幾十年,并沒有解決這個斗爭問題。毛主席及時提出了這個問題,要我們來解決,是我們的幸運”。 參見林彪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6年10月25日。。顯然,循著這個方向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是錯誤的,是從更“左”的方面發展了斯大林的錯誤。
2.經濟改革的曲折
歷史上成功改革的基本條件之一,是政治改革與經濟改革的同步、協調。隨著階級斗爭擴大化的發展,經濟建設、改革失去了政治方面的必要保證,很快出現重大失誤。
1956年后黨內逐漸發展起一種認識,即在社會主義國家建設中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方法,一種是相信群眾,發動群眾,突出政治和精神的力量,以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方式實現建設又多又快地發展;一種是脫離群眾、不發動群眾、不注意突出政治、只靠專家和行政命令因而速度不快的方法*參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900頁。。 毛澤東曾說:“1956年提出‘十大關系’,提出多快好省,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的兩種方法的問題,這是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形成的開始,到1958年正式形成了社會主義建設的總路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890頁。認為《論十大關系》就是同蘇聯比,看能否比它更快更好。*參見《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353頁。由于缺乏經驗和忽視經濟規律,特別是1957年后黨內外民主受到嚴重削弱,改革很快走入歧途。1958年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不論是在工業化速度還是在農業集體化程度上都超出了傳統模式,當時都被認為是突破斯大林模式的創新和發展。從形式上看,“大躍進”等大膽實驗的確不同于斯大林模式*鄧小平說: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這不是搬用別國模式的問題”。《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37頁。,但卻往往是更為簡單地照搬經典作家19世紀對未來社會的一些設想及戰爭年代的經驗,甚至是從中國古代社會汲取建設未來社會的靈感,把斯大林模式中高速工業化、全盤集體化、平均主義等推向極端。它不僅在許多方面違背了八大精神,也是從傳統模式基礎上的倒退。
3.調整中的改革及反復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立刻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為糾正錯誤,戰勝困難,從1960年冬季開始,在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下中共開始了卓有成效的三年調整。調整從農業、工業等領域開始,不久就擴展到政治、文化、思想、教育等方面,并立即取得明顯成效。1958年以來急于求成、急躁冒進的錯誤得到不同程度的糾正,工農業生產秩序得到一定恢復,政治空氣有所緩和,人民生活水平開始有所改善。特別應當注意的是,經濟、政治調整中的許多思想、政策、措施,不僅已超出了對一些極端做法的糾正,而且已經順理成章地深入到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提出了一些同60年代初處于第二次改革浪潮中的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相同或相近的思想、政策、方針。例如:搞活農村經濟、停止農村和商業中的集體經濟向全民所有制的過渡,反對平均主義,重視物質利益原則,給企業一定的自主權,加強企業內部核算和管理,注重發揮價值規律的作用和搞活商品流通,尊重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的作用,重視科學技術的作用,給受到錯誤政治打擊的人員甄別平反,恢復黨內外民主,緩和階級斗爭,等等。實際上,調整在一定程度上恢復和發展了八大的建設和改革思路,是一種特殊形式的改革,在內容上順應了社會主義各國改革浪潮的基本方向。但是,由于調整是在肯定“三面紅旗”的前提下、在因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致使黨內外民主受到嚴重削弱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它越是深入進行,就越是加深了同當時尚未受到根本觸動的“左”的指導思想的矛盾,接近了糾“左”的極限。1962年八屆十中全會“重提階級斗爭”,就是對深入調整中一些重要思想、重大措施某種程度上的否定,也是對當時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些改革方針、實踐的否定,實際上就是對斯大林模式弊端的維護和發展。例如,八屆十中全會對“單干風”的批判,其衡量的主要標準顯然是斯大林模式的全盤集體化;斷言“城鄉資本主義的猖狂進攻”顯然是對搞活商品經濟的憂慮;對“三和一少”的批評實際上反映了斯大林“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總危機的進一步加深”及“世界革命”等思想,如此等等。
1962年后,經濟方面的調整繼續進行,并于1965年基本完成。與此同時,在政治生活領域,以階級斗爭擴大化為核心的“左”的錯誤卻在不斷發展,并逐漸在黨內占據了主導地位。又由于對當代社會主義改革的陌生,中共在一些重要問題上越來越多地站到了維護斯大林模式甚至其弊端的立場上,對當時蘇聯東歐一些國家的改革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抵觸以至反對。
1959年毛澤東讀蘇聯修訂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時,就認為這本教科書刪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的東西,增加了蘇共二十大不少壞東西,是一個很大的退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713頁。。實際上,這本教科書雖然反映了初步改革斯大林模式時理論上的一些新成果,改正了傳統模式的一些缺點,但其基本框架和主要觀點仍然停留在斯大林《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的水平上。毛澤東的批評在一些方面反映了他對改革斯大林模式的抵觸。
1958年后逐漸發展起來的中蘇兩黨的爭論,到60年代上半期發展為舉世矚目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論戰前期,當雙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諸如對斯大林評價問題、時代主題、戰爭與和平、和平過渡、議會道路、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問題、全民國家、全民黨等一系列國際共運重大問題上時,中國黨曾經有不少正確的觀點和精彩的論述,但也表現出明顯的局限性、片面性。如對蘇共等緩和國際局勢、防止核戰爭、爭取和平發展、同西方發展經濟聯系、爭取限制軍備競賽和裁減軍備、簽訂關于不擴散和禁止核武器試驗的協定、改革傳統模式等努力等采取了批評或否定的態度。到論戰后期,當分歧和爭論逐漸擴展到社會主義建設和國內政策方面時,中國方面的錯誤成為主要方面。這樣,國內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不斷發展和國際大論戰不斷升級相輔相成,更難以糾正。例如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就有回應蘇共二十二大“全民國家”“全民黨”的背景*《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128頁。;1963年發展起來的社教運動就有“防止像蘇聯那樣出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的考慮;1965年《二十三條》中提出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概念,以及此后頻繁出現的“要警惕中央出修正主義”“警惕睡在我們身邊的赫魯曉夫”等,更是十分牽強地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主線把中蘇兩國的現實聯系起來,強有力地推動著國內“左”的錯誤的發展。
在國內外雙重因素的作用下,一種不符合中國國情和當代社會主義改革潮流、比斯大林模式更“左”的模式的輪廓逐漸清晰起來。如1963年至1964年中國相繼發出的“九評”等文章中,把單一公有制結構和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等同于社會主義;把在一定范圍內允許私人資本和私人企業的存在和發展當成發展資本主義;把重視利潤、價格、市場調節、物質利益等經濟手段、縮小計劃調節范圍、開展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貿易等當作修正主義;把階級斗爭當成社會主義的主要矛盾和發展動力;重新把知識分子定性為資產階級一部分;把個人集權當成是馬克思主義,把反對個人迷信說成是違反列寧關于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相互關系學說、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參見人民日報編輯部、紅旗雜志編輯部:《關于斯大林問題》,《人民日報》1963年9月13日。;把緩和國際形勢的努力當作投降主義,如此等等。在這種比傳統模式更極端的標準觀照之下,不斷加深了對資本主義復辟的警惕和憂慮。1966年6月,毛澤東曾說全世界一百多個黨都變修了,不信馬列了。作出這一判斷的依據正是在相當程度上把傳統模式或比它更為極端的模式當成評判姓“社”姓“資”的標準,而把對中國調整中出現的改革以及當時社會主義國家改革中出現的一些理念、措施當成“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這實際上就是維護和強化斯大林模式。“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中國強調‘社會主義建設共同規律’,實際上是強化斯大林模式”*《閻明復回憶錄》(二),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907、909頁。。 這些都為“文化大革命”的產生做了理論、思想、政治方面的準備。
1957年至1966年十年間,從滿懷信心地解放思想、改革斯大林模式(即1953年前的蘇聯模式)出發,結果卻走向維護斯大林模式甚至使其向更僵化、極端化、激進化的方向發展,在政治、經濟、政治體制等諸多方面違背或部分違背了中共八大路線,與當時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興起的改革潮流漸行漸遠。
4.十年改革探索中取得的積極成果
十年中,雖然從總的方面看,“‘左’的思想開始抬頭,逐漸占了上風”*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02頁。,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走偏了方向,但在黨的指導思想和實踐中也存在著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發展趨向,在改革中取得了的一些明顯的積極成果。例如:
在1956年改革之初及1958年糾“左”中形成的一些正確和比較正確的理論觀點和方針政策。例如,八大前后形成的一些正確的認識,1958年至1959年間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平均主義、急于過渡、否定商品經濟等“左”的思潮、實踐的批評與糾正;毛澤東等領導人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等等。
三年調整時期中央領導集體在糾“左”過程中提出的一系列正確的思想、政策。如果說八大前后中共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思路、實踐在當代社會主義第一次改革浪潮中處于前列,那么,60年代初調整中許多重要觀點、政策則完全可以與世界范圍內社會主義第二次改革浪潮媲美。
強調和發揮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體性、創造性。由于中共自身的革命傳統和豐富實踐,又鑒于“斯大林后來不那么靠群眾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學會編:《毛澤東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第900頁。,毛澤東特別強調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相信群眾、依靠群眾、充分發揮人民群眾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主動性、創造性,重視發揮先進思想和政治教育的作用,警惕和反對特權階層,等等。
堅持獨立自主的建設道路。赫魯曉夫剛上臺時對中國、中共的態度還是友好的,“改變了斯大林時期很多侵犯中國利益的做法”*《閻明復回憶錄》(二),第890頁。,但當他鞏固了自己的地位后便故態復萌,重犯斯大林大黨、大國沙文主義的錯誤,50年代蘇聯駐中國經濟總顧問伊萬·瓦西里耶維奇·阿爾希波夫在回顧這段歷史時說:赫魯曉夫認為蘇聯在一些方面都是“領導”國家,而中國則是“被領導”的國家,他個人決定并支持挑起公開論戰,并把分歧擴大到國際論壇和報刊上,對中國施加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壓力,以迫使中國領導接受蘇聯的觀念和觀點。事實證明,蘇聯自1960年起對中國所奉行的方針整個是錯誤的。*參見《閻明復回憶錄》(二),第893頁。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對這種沙文主義行為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十年中,盡管在改革斯大林模式中走偏了方向,但就反對赫魯曉夫大黨、大國沙文主義和霸權主義而進行的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來說,就反對蘇共一些重大錯誤來說,就擺脫對蘇聯模式的依賴和捍衛獨立自主、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來說,都是應當充分肯定的,都是改革歷程中值得大書特書的一筆,具有深遠意義。從長時段來看,它不僅使中國徹底擺脫了蘇聯的控制,為中國謀求獨立于蘇、美之外的國際戰略地位創造了有利條件,也減輕了一些希望擺脫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壓力,打破了蘇聯在國際共運中的一統天下的局面,客觀上促進了世界多元化發展趨勢。如果沒有這種斗爭,失去了獨立自主的地位,成為蘇聯模式的追隨者和衛星國,那么1989年蘇東劇變時中國的處境會艱難得多。
第三階段:1966年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中“左”的錯誤被推向極端,在一些主要方面發展了斯大林模式的弊端和斯大林的錯誤,全面否定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
“文化大革命”是長期“左”的錯誤發展到極端的結果,是改革斯大林模式走入歧途并把這種模式的弊端發展到極端的產物,也是把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當成“修正主義”加以否定的結果。雖然“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論和實踐沒有多少直接來自傳統模式,但傳統模式卻包含了可能產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些主要基因。例如:在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問題上、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關系問題上、高度個人集權、缺乏黨內外民主、輕視法制和法律、對計劃經濟和單一公有制的迷信、輕視商品經濟和價值規律、否定市場經濟與私有經濟以及體制結構上的種種弊端,等等。這些基因并不必然產生“文化大革命”,但它如與另外一些因素結合,則有可能導致“文化大革命”的產生。
“文化大革命”早已不滿足于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和超越,它追求的是更為宏大和長遠的目標。按照當時的說法,它的發生是系統地總結了中國無產階級專政和俄國十月革命以來國際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特別是總結了蘇聯資本主義全面復辟的嚴重教訓,完整地、徹底地解決了在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進行革命、防止資本主義復辟這一個當代最重大的課題,這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無產階級專政學說劃時代的偉大發展”*《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1967年11月6日。;其基本經驗“反映了無產階級專政建立以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歷史階段中階級斗爭的普遍規律”*《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1967年11月6日。;“這是一個最重要的標志,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在20世紀初葉,馬克思主義發展到了列寧主義的階段。現時代,又發展到了毛澤東思想的階段”。*參見《紅旗》雜志、《人民日報》編輯部:《偉大的歷史文件》,1967年5月18日。它使中國這個“世界革命的中心,變得更加鞏固、更加強大了”*《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編輯部社論:《沿著十月社會主義革命開辟的道路前進》,1967年11月6日。。
“文化大革命”中,除了對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共八大前后和調整時期一些正確和比較正確的思想、政策進行全面批判外,對當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也采取了全面否定的態度。其中,對蘇聯改革的批判顯得尤為典型。例如:
赫魯曉夫上臺后不久,在工業部門進行了所謂的“經濟改革”。這一“改革”的實質,就是廢除適應于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的某些經營、管理方針,代之以資本主義的經營、管理方針,把利潤原則作為一切經濟活動的指導原則,使追求利潤成為生產的最終目的。早在1955年,赫魯曉夫集團就作出了“擴大企業經理職權”“擴大廠長權限”等決議。在1956年2月舉行的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叫嚷“必須徹底實行”“個人物質鼓勵原則”。1961年12月蘇共二十二大通過的《蘇共綱領》和赫魯曉夫的報告,強調要“加強物質刺激形式”,對經濟工作進行“盧布監督”,“提高贏利率”“應當成為蘇聯企業活動的法律”,要“給予企業以更多的可能性來支配利潤”,等等。1962年9月,蘇聯《真理報》拋出了蘇聯御用經濟學家利別爾曼兩篇鼓吹“利潤掛帥”的文章,鼓吹利潤應當成為衡量企業效率的最后的總尺度。赫魯曉夫親自出馬加以肯定和推廣。勃列日涅夫上臺以后,繼承赫魯曉夫“經濟改革”的衣缽,于1965年明令推行以利潤為核心的“新經濟體制”,并制定了具體貫徹“新體制”的《關于完善計劃工作,加強工業生產經濟刺激》的決議和所謂《社會主義國營生產企業條例》,從立法上進一步肯定了在工業中業已復辟了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參見《人民日報》1975年6月6日。此外,還把在中國熱心介紹利別爾曼經濟學思想的經濟學家孫冶方說成是“妄圖把赫魯曉夫復辟資本主義經濟的一整套做法搬到中國來”*參見《社會主義建設與經濟學領域中的階級斗爭—批判孫冶方的修正主義經濟理論》,《紅旗》1970年第2期 ;《粉碎孫冶方復辟資本主義的反革命綱領》,《人民日報》1966年8月14日。。
“蘇修集團的所謂‘新體制’的中心,就是以各種措施鼓勵企業追逐利潤,依靠物質刺激推動生產。它擴大企業經營的自主權,大力推行按市場行情調節生產的制度,擴大企業負責人對職工的招收、解雇和獎懲的權力。這一系列措施,就把全民所有制的社會主義企業變成為資本主義企業,以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代替了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蘇修集團推行“新經濟政策”惡果累累》,《人民日報》1967年11月8日。“‘完全經濟核算制’是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復辟資本主義的工具”,“反映了官僚壟斷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是實行資本主義的利潤原則”,“是蘇修官僚壟斷資產階級對蘇聯勞動人民的一種剝削制度”。*《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18—223頁。
此外,對蘇聯強調按價值規律組織生產、重視知識分子作用、在企業中強調發揮技術人員作用、發展個人農副業、鼓勵集貿市場貿易、實行五天工作制、對西方國家開放、對美國緩和等也進行了批判,甚至連在美國發廣告介紹蘇聯旅游資源招徠西方游客也被說成是賣國,如此等等。
盡管在“文化大革命”中“左”的指導思想占據了主導地位,但黨內正確的發展趨勢并未中斷。這突出地表現在1972年和1975年周恩來、鄧小平在毛澤東的支持下進行的兩次著名整頓中。整頓中,周恩來、鄧小平在初步穩定形勢的基礎上,要求企業加強經濟核算,抓好企業管理、重視物質利益、鼓勵農村發展多種經營和落實按勞分配政策、強調“科學技術叫生產力,科技人員就是勞動者”、發展對外貿易、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利用資本主義國家的商品交易和期貨市場,等等。這些整頓思想和措施,都包含有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內容,都為后來的改革準備了必要條件。
從表面上看,50年代初至1976年間,中蘇兩國在改革斯大林模式過程中走上了十分不同的道路,一個是維護斯大林模式,一個進行了一些淺層次的、局部的改革后便止步不前,最終以失敗告終。雖然雙方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和尖銳的對立,但雙方在一些基本方面卻是一致或十分相近的,即都未觸及斯大林模式的一些基本內容和結構,有的還有所發展。例如:在時代問題上,在計劃經濟和所有制問題上,在處理條條、塊塊、集中、分權關系問題上,在對待私營、個體經濟問題上,在物質利益問題上,在高度集中的政治體制問題上,在對待個人崇拜問題上,在社會主義民主問題上,在社會主義階段商品經濟、價值規律問題上,在急于過渡、低估社會主義歷史階段的長期性、曲折性問題上,在對當代資本主義的認識問題上,在堅決否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問題上,等等。當中國黨尖銳指責蘇共“全民國家”“全民黨”是右傾機會主義時,殊不知蘇共這些提法正是基于“二十年內建成共產主義”的發展目標,是急于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產物,根本不是什么“右”,而是“左”。正如有論者指出的那樣:“ 蘇聯方面是‘左’,我們是極左”*《閻明復回憶錄》(二),第909頁。。又如在大論戰中,我們一方面反對蘇共自封為中心,但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自稱“世界革命中心”;一方面批評蘇共搞以我劃線,強加于人,另一方面我們又把不同意自己觀點的黨一律戴上“修正主義”的帽子,認為全世界一百多個黨都變修了*參見《閻明復回憶錄》(二),第905頁。,如此等等。不論是蘇共還是中共,在這點上都未走出斯大林在國際共運中“以我為中心”的老路。在激烈爭論的表象之下,竟然是一些十分接近的基本觀念和思維方式!
三、改革斯大林模式難在何處
從50年代初起,全世界十多個社會主義國家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經歷了許多曲折,取得了一些成就,付出了許多代價。但直到70年代末,不但沒有一個取得成功,反而出現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大分裂以至蘇東劇變。這樣的結果是開始改革時人們始料不及的。改革斯大林模式如此艱難坎坷,原因何在?
盡管斯大林模式自產生以來一直毀譽參半,蘇東劇變后對它的詆毀更是失去了節制,但經過反復的“重評”“再評”后,越來越多的人還是傾向于承認,雖然它存在巨大的缺陷和歷史局限性,但它的產生、存在自有其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它是落后的東方大國以社會主義方式實現現代化過程中一種難以替代的選擇,曾有力地推動了歷史的發展。它的弊端有個人方面的因素,但更多的顯然應該用歷史條件來解釋。它之所以引起經久不息的爭議,正在于它是正確與錯誤、必然性與局限性、有效性(適應性)與強迫性甚至嚴重迫害的統一體,“非此即彼”的思維方式在它面前只能窘態百出。對它的科學態度不是拋棄而是“揚棄”。斯大林模式包含了眾多內容和層次,其中有些內容應當隨著時代發展而被淘汰,有些內容卻只能靠改革不斷發展。它的一些核心部分如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的基本制度,是必須堅持的,放棄了這些基本內容也就無所謂社會主義和社會主義改革。1989年蘇東劇變后的改制易幟便是如此。但是,這些核心必須隨著時代發展而不斷發展、改革和升級。不論是黨的領導,還是社會主義制度,如不能與時俱進地、實質性地充實社會主義民主等內容,便也無所謂堅持。
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困境,可以用以下原因解釋:
第一,斯大林模式的基本內容包括指令性計劃經濟、單一公有制以及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體制三個方面,三者互為條件,高度匹配。改革這種三位一體的整體結構的難度在于,單從哪方面改革都不可能成功。一位俄羅斯學者說,斯大林模式是一部設計十分精巧的機器,對其每一部分的觸動都會引起整個系統的強烈反應。
第二,一些過時的傳統觀念和頑固的教條主義及其造成的普遍思想僵化,是改革斯大林模式的嚴重障礙。時代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巨變,卻硬要現實服從幾十年甚至上百年前經典作家的某些具體結論,把能否從本本出發作為評判“政治正確”的標準。20世紀60年代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論戰中,雙方唇槍舌劍,尖銳對立,但在照搬“本本”以證明自己正統地位這點上卻高度一致。沒有對教條主義實質性的突破,任何改革都沒有成功希望。20世紀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改革中就提出“制定捷克斯洛伐克改革模式的基本先決條件是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非教條化”*陸南泉:《勃列日涅夫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緣何停滯不前》,《蘇聯真相》(中),新華出版社,2010年, 第851頁。。1976年后中國的改革若不是以空前力度和范圍的思想解放運動為前提和開端,也斷無成功的可能。
第三,政府主導的制度變遷難以避免地會成為權力尋租的土壤,高度集中的體制結構必然形成的“官本位”與之高度契合,盤根錯節的利益集團和特權階層本能地阻礙著任何實質性的改革。
第四,模式本身的封閉性使人們難以感覺到落后的危機與改革的迫切性。20世紀80年代初谷牧受中央委派出國考察回來后感嘆:出去后才知道世界變化之大,而我們的經濟學知識還是50年代初蘇聯列昂節夫教科書上那些“老概念”。
第五,缺乏對當代社會主義多樣性的深刻認識,都熱心為國際共運制定“總路線”,自封核心,感覺良好,如此等等。幾十年過去了,現在的人們恐怕都接受了這樣一個現實,科學社會主義不只有一種模式,社會主義也不只有科學社會主義一種模式。全球化時代的社會主義應是開放的、多樣化的實踐和運動。
還有一些深層的原因更需要歷史辯證法光芒的燭照,即改革的困境,恰恰來自斯大林模式在某些特殊條件下的有效性、適應性——盡管它同時具有明顯的弊端或“副作用”。例如:
——對于具有長期封建專制歷史而缺乏民主傳統,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水平低下的東方大國,這種模式是有效的甚至是必需的,表現出明顯的時空適應性。反之,它對民主傳統越強、經濟越發達的國家越不適應。*參見項佐濤:《如何看待蘇聯和東歐國家去斯大林模式的改革》,陸南泉等主編:《蘇聯真相——對101個重要問題的思考》(中),新華出版社,2010年,第818頁。有蘇聯學者指出:“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斯大林比號召人們學習經商和進行有盈利工作的列寧更能贏得大多數黨內積極分子、大多數新的蘇維埃知識分子的喜歡。”*轉引自陸南泉等主編《蘇聯興亡史論》,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36頁。這反映了斯大林模式對當時落后的社會經濟現實的適應性。
——落后東方大國現代化初期啟動趕超戰略時,必須依靠強大的政黨導向、國家力量、廣泛的政治動員和權威的、高度集中的領導核心。國家越落后,國土面積越大,越需要強調權力集中和政府權威以保護經濟迅速曾長。只要實行趕超戰略,只要重工業優先,只要弱化了價值規律和市場的作用(這是實行趕超戰略的條件),斯大林模式就表現出很強的適應性,就會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出現。反之,對那些經濟社會已經比較發展、市場關系比較活躍的中小國家,其適應性則比較低。這就是說,這種模式往往與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成反比,它對經濟社會發展程度比較高的國家的適應性比較低;反之則比較高。就一個國家來說,在其發展初期適應性比較強;反之,則明顯降低,弊端明顯增加,改革的任務更突出。斯大林模式的這些特征決定了對它的改革,一般只能出現在社會主義已經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并與原有模式發生矛盾時。這種矛盾越發展,改革的要求越強烈,出現得越早。蘇聯改革是在十月革命后近40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近20年后出現的。東歐各國,特別是那些革命前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沙俄、自然稟賦、經濟社會結構與蘇聯差異較大的國家,從一開始就感到蘇聯模式的束縛,50年代后矛盾更為突出。“1955年至1956年間,舊的和過時的管理體制所造成的惡果已經看得很明顯,并且具有相當嚴重的程度了……這些惡果在某些生產部門內甚至已達到了災難性的程度。”*1957年2月波蘭部長會議主席彼·雅羅謝維奇在波蘭黨中央宣傳員訓練班上的講話。轉引自《十年后的評說》,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第267頁。蘇聯東歐國家率先興起的改革,正是這種矛盾的反映和結果。也就是說,由于發展程度較高,蘇東等國改革的條件顯然較我國更為成熟。
——在受到外敵嚴重威脅或國內政治經濟形勢嚴峻時,其適應性、有效性比較強。斯大林“作為一個面臨戰爭的國家領袖在帶領國家走向工業社會方面做出了正確選擇……他是確保國家邁入工業社會體系的維護者,是一個瀕臨戰爭的國家的領袖”*轉引自徐艷玲主編《科學社會主義學》,第149頁。。斯大林模式正是這種環境的產物。離開了這種背景,任何評價都是不公道的。
——在戰后恢復、經濟危機等某些特殊歷史時期,斯大林模式中一些基本要素也是有效的。中國抗戰勝利前后,在戰后恢復和建國問題上,民盟及重慶國民黨資源委員會中那些具有西方留學背景的知識分子,就提出政治上學英美的自由主義,經濟上學蘇聯的計劃經濟,認為在經濟方面蘇聯做得比英美好。“蘇聯1917年的革命和蘇聯將近30年在這方面的努力,成績特別多”*啟良:《20世紀中國思想史》,花城出版社,2009年, 第217頁。。二戰后歐洲一些國家在恢復時期也開始強調加強政府管制和國家對經濟的計劃。甚至美國資本主義政客陣營中一位死硬派人士哈里曼在1946年也表示:如今民眾對“計劃”一類字眼再也不會感到畏懼,國家一定要有計劃。法國經濟自由主義擁護者莫內成為法國計劃經濟的熱情支持者。自由市場經濟學家羅賓斯(與哈耶克一起在倫敦經濟學院主持講座)搖身一變成為英國戰時半社會主義式經濟制度的領導人物。除聯邦德國外,大戰后的各國政府紛紛走上改革之路。美國有羅斯福主義者,西歐的各原交戰國則是一片由社會主義主導或傾向社會民主路線的新氣象……*參見〔英〕霍姆斯鮑姆著,馬凡等譯:《極端的年代》,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09、425頁。諸如此類變化的原因顯然不是對斯大林模式意識形態的認同,而是看中了它在戰后恢復時的效率。
凡此種種說明一個問題,改革的困境正在于斯大林模式是一個十分復雜的、有效性(適應性)和弊端并存的矛盾統一體。只看到或強調哪個側面都是不科學的。還應強調,對這種模式的全面評價,沒有長時段的歷史視野也是不可能的。這種模式的基本特征是某些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只要這些條件存在,它的適應性也會重復出現,當然,也會有相應的弊端伴隨。這與現代西方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市場至上與政府主導、自由放任與政府管制等周期性交替出現有些相像。歷史上沒有全優的選擇,只有權衡利弊的智慧。
以上所列斯大林模式的一些特征,有益于解釋中國改革的曲折與成功。中國是在剛剛按照斯大林模式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剛剛進入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時進入改革時代的。由于經濟社會水平發展遠低于蘇聯東歐等國,傳統模式的弊端在中國暴露得還不充分,所造成的矛盾也不及蘇聯東歐那樣尖銳。這種低水平的發展造成兩方面的后果:一是改革的難度要大于蘇東等國,二是傳統模式對中國的適應性、有效性也明顯多于蘇東等國。換言之,由于一種歷史形成的“時間差”,全面、深刻改革的條件還不成熟。
當時,中國面臨著獨特的雙重轉型局面:一是工作中心由革命轉向全面的社會主義建設,二是從照搬斯大林模式到改革斯大林模式,探索自己的發展道路。雙重轉型既給我們解放思想、實現歷史性跨越提供了歷史機遇,又因“模式真空”(傳統模式已經開始過時,新模式還在襁褓中)增加了模式選擇的難度。“模式真空”的困境又為一些歷史、文化傳統的影響保留甚至拓展了空間,以致出現了人民公社化運動中的“吃飯不要錢”之類的實驗。就當時中國社會發展程度來看,雖然可以提出一些初步的、淺層次改革思想,但卻還不足以深刻地理解處于較高發展程度上的蘇聯東歐等國正在進行的改革實踐,反而容易把它們當作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
例如,在剛剛建立起高度集中統一的計劃經濟時,讓人們深刻認識其局限性;讓剛剛經過三大改造高潮、建立起單一公有制的人們,去重視一定數量的個體或私人經濟對社會主義的必要補充作用,以及市場經濟的一定積極作用;讓那些沒有經歷過商品經濟相當發展階段,只是從書本上學到一些經典作家有關社會主義應當取消商品生產知識的人們,去深刻認識大力發展商品經濟對社會主義的意義……在當時的條件下,往往不具備現實可能性。雖然也有少數人覺察到傳統模式的某些缺陷,但畢竟還不成熟和牢固,更不可能成為黨內認識的主流。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及傳統文化的作用突出出來,干擾了探索、改革的正確方向,使中國在20年時間里走上了維護舊模式甚至發展其弊端的道路。
但是,到70年代末,事情又發生了出乎人們意料的轉變。在經歷了勃列日涅夫保守主義所造成的改革低潮之后,在80年代興起的第三次改革浪潮中,蘇東等國因改革的長期反復、停滯積累了大量矛盾,很快走向激進和失控,最終導致80年代末紛紛以失敗告終。而中國在結束“文化大革命”后開始的漸進式改革,借助“后發優勢”一躍而居世界前列。不僅很快超越了斯大林模式和蘇東等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進行的一些改革,而且在90年代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這是社會主義發展史上一個劃時代的成就。經過20多年的曲折,改革斯大林模式的艱辛探索終于漸入佳境,得到豐厚的回報。
如何解釋這種趕超式的發展呢?
第一,20多年“左”的錯誤并沒有動搖中共的領導地位,它不僅依靠自己的力量糾正了錯誤,而且成為中國改革開放的堅強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領導核心,中國的成功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的。中共對斯大林模式特征、內涵的把握是比較深刻、全面的,在改革時沒有對它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而是區分了它的不同層次和不同方面,堅持了其正確的、長久起作用的核心內容,如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當然是在改革和完善基礎上的堅持和發展。這與蘇東等國截然不同。
第二,嚴重的“左”的錯誤是一柄雙刃劍,不僅阻礙了中國的改革,也從“左”的方面動搖了斯大林模式的穩定性,從反面孕育了某種“后發優勢”, 為成功的改革準備了條件。傳統模式的三個基本要素(計劃經濟、單一公有制及高度集中的政治、經濟和意識形態體制)曾被認為是改革的主要難點,而這三者(不論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方面)都因連續的政治運動和經濟波動而失去了原有完整性、穩定性和權威性,從而為改革提供了較多的空間和回旋余地。例如,在計劃經濟方面,由于經濟運行頻頻受到政治運動干擾,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在中國已程度不同地變形,它已不再是單純的計劃經濟,而是一種帶有濃厚“運動經濟”“戰備經濟”或“政治掛帥經濟”色彩的經濟,遠沒有蘇聯計劃經濟那樣嚴格、剛性和僵化,相應地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又例如,由于農業生產力水平長期偏低及自然災害的影響,為生存計,廣大農民不斷自發地公開或半公開地搞起了包產到戶等形式的責任制,雖屢禁而不止。諸如此類的行為不能不使單一公有制大打折扣。在意識形態方面,長期的“左”的錯誤及其造成的嚴重后果,為人們充分認識其原因、實質提供了有利條件。感情上的厭惡和理性的思考使群眾形成了廣泛的改革共識,積蓄了巨大的改革能量。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那樣極端的“左”的錯誤更是引發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浪潮,形成了某種“鐘擺效應”和物極必反式的反彈,為中國改革奠定了堅實的思想基礎。總之,雖然1976年前對斯大林模式的改革雖然沒有成功,雖然1976年時中國的模式比1956年后的蘇聯模式更為陳舊,但另一方面也使其沒有固化,不論在經濟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制度化程度都比較低,沒有蘇聯那樣僵化,存在著巨大的制度改善空間和潛力。
第三,20多年的探索從正反兩面積累了改革斯大林模式的經驗教訓,如中共八大前后的探索,60年代初的全面調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鄧小平領導的兩次整頓,黨內外一些改革先驅如陳云、張聞天、孫冶方、顧準等對社會主義經濟規律的探索和對國外改革經驗的介紹,都為改革準備了寶貴的思想基礎。用更廣闊的眼光看,蘇東等國的失敗和中國的曲折等多方面的“試錯”,已大大縮小了我們選擇的范圍。
第四,1978年后中共對一些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經驗教訓廣泛、深入地學習、比較,使中國改革一開始就有了較高的起點。有成功的經驗可資借鑒,有成熟的理論可供參考,一些改革重點、難點在其他國家已爭論多年,一批涉及社會主義改革的經典著作在國內風靡一時。中國人如饑似渴地學習,大大縮短了探索、趕超的時間。此外,當時世界經濟、政治形勢也為中國集中發展經濟提供了一定空間,有利于中國從國外大量引進各種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
第五,由毛澤東那一代領導人歷盡艱辛地打造出來的中國獨立自主的國際地位,使中國改革得到了一段比較適宜的國際空間。
國內外往往有學者把成功的中國改革稱之為“謎”。把中國改革的起點、對象進一步精確化,搞清“我們從哪里來”,似乎是解開這個“謎”的一條途徑。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 北京 100080)
(責任編輯 薛 承)
Which Soviet Model Is the Object of Chinese Reform ——An Issu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in Chinese Reform and the Reform of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Zheng Qian
After Stalin’s death in 1953, the Soviet model different to the original Stalin mode began to appear in the Soviet Union. Although the two modes were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their differences could not be ignored. From 1956 to 1976, the object of Chinese reform was mainly the Stalin mode. Although the reform was once on the wrong direction, but it prepared the conditions for the successful reform after 1978. At the same time, the reform of Stalin mode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other countries was at a standstill after they made certain progress until the trigger of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 upheaval.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countries reveals some deep-seat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talin mode, and the basic law of backward countries realizing modernization in the way of socialism.
D232;K27
A
1003-3815(2016)-09-0026-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