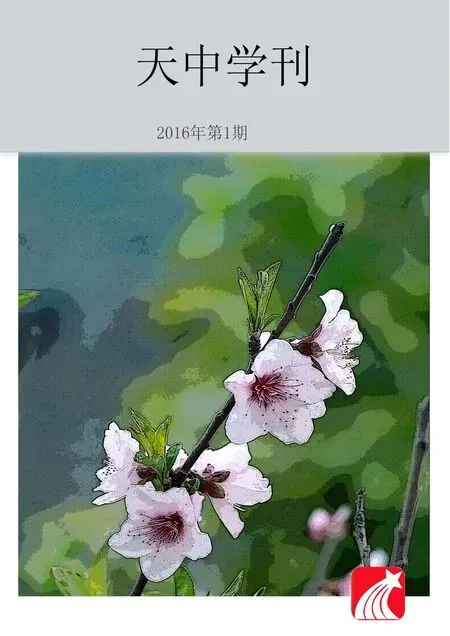周作人對陶淵明詩文的接受
劉中文(蘇州市職業大學 教育與人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104)
?
周作人對陶淵明詩文的接受
劉中文
(蘇州市職業大學 教育與人文學院,江蘇 蘇州 215104)
摘 要:周作人崇拜陶淵明,他在著作中不斷征引和評價陶淵明及其作品。他認為,陶詩意誠而辭達,陶文則思想寬博,文辭恬淡,陶淵明是“獨一無二的圣手”。周作人在解讀陶淵明詩文或論證陶淵明的觀點時,常把顏之推、韓愈分別作為正反兩種論據進行對比論證,以此深刻詮釋自己的人本主義文學價值觀。與此同時,周作人在獄中思陶、詠陶,從陶淵明那里汲取了生存智慧,安頓了心靈,洞開了心路。
關鍵詞:周作人;陶淵明詩文;陶學
“中國第一流的文學家”[1]6周作人,其文學創作汲取了陶淵明文學作品的菁華,尤其是他平生著力創作的小品文,風格沖淡平實,深得陶淵明文學創作的精髓。筆者依據《周作人散文全集》《知堂回憶錄》《知堂雜詩鈔》《老虎橋雜詩》《周作人詩全編箋注》《過去的生命》等文獻統計,從1919到1965 的46年間,周作人有67篇散文、17首詩歌共84篇作品言及陶淵明及其作品。這些涉陶作品或自白崇陶心理,或評論陶公其人,或引述陶公詩文為證,或評陟陶公詩文,或集陶句為詩,或詩中化用陶句,或引陶事以發議論,或臚列所存諸種陶集,等等。共引用或化用了陶淵明的29篇詩歌和7篇辭賦與散文,使用頻次近70次。出現頻率較高的依次是《歸去來兮辭》《飲酒》諸篇、《讀〈山海經〉》諸篇、《責子》《擬挽歌詩》《神釋》等。此外,周作人還引用了陶公“攢眉而去”蓮社、遣仆力助子、“我醉欲眠卿可去”等陶事。
周作人曾經坦言,“鄙人固是真心愛好陶公詩文”[2]23/九①,“我平常喜歡陶淵明的詩,因此恍然大悟,這并非因為他的隱逸或是慷慨,實際是為的他的詩說理能說得那么好,正是獨一無二的圣手,至少我的佩服他的原因是大半由于此的”[2]288/十。黃子云《野鴻詩的》曰:“古來稱詩圣者,唯陶、杜二公而已。”[3]862潘德輿《養一齋詩話》曰:“兩漢以后,必求詩圣,得四人焉:子建……陶公……太白……子美……”[4]2046周作人亦不吝把“詩圣”之美譽奉與陶公,且認為陶公是“獨一無二”之“圣”,這不僅體現了周作人的詩史觀念,也足以見得作為中國文學典范的陶公詩文在周作人心中的地位與分量。
一、傾心陶公詩文
對于陶詩,周作人總是掩飾不住內心的情感:“現在似乎未便以老年自居,但總之已過了中年……陶詩讀了也總是喜歡”[2]649/七,“即最所喜歡的陶詩亦一篇都背不完全也”[2]167/八,“我平時很喜歡陶淵明的詩”[2]17/九,“我喜歡讀陶淵明詩,有許多篇都很喜歡。”[2]803/十二清人胡式鈺論詩道:“吾于詩人無不好,尤好淵明詩。吾于詩人詩各有好有不好,有好無不好惟淵明詩。”[5]周作人認為胡氏此論“能說得出愛陶詩者的整個心情也”[2]69/七。在周作人看來,陶詩的價值突出體現在“意誠”和“辭達”兩方面。
意誠即為情真。情是周作人衡量文學的首要條件。他認為“天下事物總不外一情字。作文亦然,不情之創論,雖有理可據,終覺殺風景”[2]167/七。所以每賞陶詩,周作人總是著眼于陶詩之“情”:“其《歸園田居》云:‘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神釋》云:‘應盡便須盡,無復更多慮。’在《擬挽歌辭》中則云:‘欲語口無音,欲視眼無光。昔在高堂寢,今宿荒草鄉。’陶公于生死豈尚有迷戀,其如此說于文詞上固亦大有情致。但以生前的感覺推想死后況味,正亦人情之常,出于自然者也。”[2]288/六談及生死,陶公曠達超脫又有些許悲涼,情致自然而發之于內心,真切感人。“‘向來相送人,各自還其家。親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此并非單是曠達語,實乃善言世情……陶公此語與‘日暮狐貍眠冢上,夜闌兒女笑燈前’的感情不大相同,他似沒有什么對于人家的不滿意,只是平實地說這一種情形,是自然的人情,卻也稍感寂寥,此是其佳處也。”[2]306/七陶公之詩,情感往往既出己心,又合世情,不怨天,不尤人,平和中正,恰如其分,故稱佳作。陶淵明《雜詩十二首》之六曰:“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6]299周作人認為陶公“這種經驗大抵各人都曾有過,只是沒有人寫出來,而且說的這么親切。”[2]384/九正是因陶公道常人所未道,又道人之常情和人性之真,才讓已是花甲之年的周作人為情所動,心有戚戚。
《論語·衛靈公》:“子曰‘辭達而已矣’。”[7]170周作人認為:“陶詩大概真有其好處,由我個人看來,當由于意誠而辭達乎。”[2]17/九陶詩不僅理趣豐饒,而且明白曉暢、生動透徹,恰得詩詠之妙。周作人這樣解讀陶詩:“三國以后的文人里我所喜歡的有陶淵明與顏之推兩位先生……這是以科學常識為本,加上明凈的感情和清澈的理智,調和成功的一種人生觀,以此為志,言志固佳,以此為道,載道亦復何礙。”[2]122?123/六所謂的“科學常識”亦即自然之理、倫常之情,這是載道無礙(辭達)的前提,而“明凈的情感”和“清澈的理智”則是辭達的兩個條件。陶詩具備了辭達的三要素,所以周作人倍加推崇。
周作人《再談文》說:“司空表圣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一境,固然稍嫌玄虛,但陶淵明詩亦云‘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可知這是實在有的,不過在我們凡人少遇見這些經驗而已。”[2]623/六比較而言,司空圖載道之辭玄虛而不“達”,陶公之語則“是實在有的”,是以“科學常識為本”的,所以陶詩理更切、意更深、味更永。這也是周作人將陶公“榮木,念將老也。日月推遷,已復九夏,總角聞道,白首無成”之語“借來當作我的懺悔之詞”的原因[2]105/六。周作人《志摩紀念》說:“文章的理想境我想應該是禪,是個不立文字,以心傳心的境界,有如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或者一聲‘且道’,如棒敲頭,夯地一下頓然明了,才是正理,此外都不是路。”[2]815/五這一觀點是對嚴羽以禪論詩的回歸。在周作人心中,陶公的人與詩都達到了這種境界,史書云,陶淵明對蓮社之招攢眉而去,“我讀了卻很喜歡,覺得甚能寫出陶公的神氣。”[2]94/七“陶淵明《飲酒》詩中云:‘汲汲魯中叟,彌逢使其淳。鳳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這彌逢二字實在說得極好,別無褒貶的意味,卻把孔氏之儒的精神全表白出來了。”[2]697/七無須言語,一“攢眉”而心神畢見。未落言筌,然理趣明晰透徹。
陳繹曾《詩譜》曰:“(陶詩)情真景真,事真意真。”[8]630其“真”是以道家哲學的“自然”觀為底蘊的。而周作人關乎文學的理論基點即是“真”。他說:“藝術以求誠為歸,故所有自白,皆抒寫本心,毫不粉飾……對于世間,揭發隱伏,亦無諱忌。”[2]431/十四而且“文學作品……只須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2]104/二周作人所提倡的“誠”與“真”,雖然也受到道家自然觀的影響,但更深層的動因卻是人道主義思想。他提倡“人的文學”的旨歸在于“提倡一點人道主義思想”[2]86/二,“用這人道主義為本,對于人生諸問題,加以記錄研究的文字,便謂之人的文學。”[2]88/二而他所倡揚的“平民文學”,同樣也是“以真摯的文體,記真摯的思想與事實”[2]104/二。可以說,人道主義是周作人人本主義文學價值觀的哲學根基。“人是一種生物……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2]86/二“人的文學”的原則是對人的生活的真實記錄,亦即“尚真”,這是周作人美學觀的基石。“尚真”的美學觀不僅體現于他對陶淵明及其作品的推崇中,也體現于他對王充、李贄、俞正燮、金圣嘆等性情真率、反叛傳統的文化名人的推崇與贊美中,同樣也體現于對明代“獨抒性靈”的公安派、“幽深孤峭”的竟陵派、“率真直露”的小品文等反對復古、反對道統、倡揚自立的文學思想或理論的深刻接受中。
周作人在1925年11月的《〈雨天的書〉序二》中表達了懺悔與渴望:“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國外文學才有此種作品……像我這種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定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愿望……田園詩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難所,但這個我近來也有點疏遠了。”[2]346/四五四運動過后的20世紀20年代中期,周作人的創作重心轉向小品文創作,風格由前期的“奔競躁進”逐漸轉向安詳沉著、恬淡閑適、平和沖淡了,這使他對陶淵明的散文和辭賦更加情有獨鐘。
周作人評陶文為“文不多而均極佳”[2]194/九,原因在于“朱子說陶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2]536/六。可以說,陶淵明自然恬淡的散文與辭賦是周作人小品文風格形成的藝術淵源。周作人服膺道:“我們寫文章決不能有陶公這種本領,那么結果只好自己警惕,不要多發議論,還是寫些有事有人的文章好,雖然這事也并不容易。”[2]288/十閱讀周作人的全部作品后會發現,周作人崇陶的深度完全不減白樂天和蘇東坡,周作人同樣從陶淵明那里汲取了很多的人生的藝術與文學的生命。周作人討論陶淵明的散文時常將陶淵明與顏之推和韓愈并提,形成立與破并舉、褒與貶同存的特點。
所謂立與褒,即在欣賞陶淵明的同時,周作人也推崇顏之推。他最推崇陶淵明與顏之推的散文,雖認為顏不及陶,然還是常將二人并稱:“漢魏六朝的文字中我所喜歡的也有若干,大都不是正宗的一派,文章不太是做作……如陶淵明顏之推等都是好的。”[2]429/九“從前看過的書,后來還想拿出來看,反復讀了不厭的實在很少,大概只有《詩經》,其中也以《國風》為主,《陶淵明集》和《顏氏家訓》而已。”[2]304/九“《家訓》末后《終制》一篇是古今難得的好文章,看徹生死,故其意思平實,而文辭亦簡要和易,其無甚新奇處正是最不可及處。陶淵明的《自祭文》與《擬挽歌辭》可與相比,或高曠過之。陶公無論矣,顏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卻難找得出來。”[2]271?272/六“陶集中《與子儼等疏》實是一篇好文章,讀下去只恨其短,假如陶公肯寫得長一點,成一兩卷的書,那么這一定大有可觀,《顏氏家訓》當不能專美了……我只因為他散文又寫得那么好,所以不免起了貪心,很想多得一點看看,乃有此妄念耳。”[2]45/七眾所周知,陶淵明雖然生活在南方,然而他的文風卻未染彩麗竟繁、綺靡浮艷的南朝詩風,以至于得不到劉勰等人的認可。陶文的風格自然平淡而又含蓄蘊藉,可謂之文質半取。《顏氏家訓》文風平易樸實而情理兼致,文質彬彬,亦可為合南北文風之優長。周作人推崇二賢的正是這種自然恬淡、簡要和易、含蓄蘊藉的文風。依據龔斌《陶淵明集校箋》統計,陶淵明的散文有11篇、辭賦有3篇,周作人“恨其短”“貪心”“妄念”的心曲自白,樸實感人,道出了對陶淵明散文的深深熱愛、癡迷與珍視。
所謂破與貶,即是論陶的同時否定韓愈。“抑韓”現象在周作人的作品中非常明顯。歸納起來,周作人的觀點大致有二。
其一,韓愈人性虛偽,為人無品。周作人在《談韓退之與桐城派》中對韓愈的評價直言不諱,他說:“我對于韓退之整個的覺得不喜歡,識器文章都無可取,他可以算是古今讀書人的模型,而中國的事情有許多卻就壞在這般讀書人手里。他們只會作文章,談道統,虛驕頑固,而又鄙陋勢利,雖然不能成大奸雄鬧大亂子,而營營擾擾最是害事。講到韓文我壓根兒不能懂得他的好處……不但論品概退之不及陶公,便是文章也何嘗有一篇可以與《孟嘉傳》相比。朱子說陶淵明詩平淡出于自然,我想其文正亦如此。”[2]535/六周作人對韓愈的剖析比較深刻,并以陶淵明的散文作品為參照評騭韓文。韓文沒有陶文的自然與平淡,即所謂“虛驕”——虛偽傲慢,從而對韓愈的人與文作了雙重否定,他在《〈醉余隨筆〉》提出“(韓愈)達固不是諸葛一流,窮也不是陶一路也”[2]648/六。元人吳澄《陶淵明集補注序》列屈原、張良、諸葛亮、陶淵明為“四君子”,認為四賢皆“明君臣之義”[9]卷廿一。對周作人而言,孔明與陶潛是人格完美的化身,是人生的偶像。相形之下,韓愈人品的根本缺陷在于虛偽和勢利,“他是封建文人的代表,熱衷躁進,頑固誕妄而膽小,干謁宰相,以勢利教兒子,滿口禮教,因諫佛骨謫官,立即上疏哀鳴,登山怕下不來,嚎哭寫遺囑,這些行動正好配上那么的外表”[2]448/十。應該說,周作人的這些觀點犀利透徹,入木三分,剝落了韓愈儒家衛道士的外衣。
舒蕪在1982年給陳邇冬《韓愈詩選》作序時,對韓詩予以深刻而全面的剖析,同時對韓愈其人評論道:“通觀韓愈這個人,盡管是博學高才的大文學家,但是氣質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就是躁急褊狹,無容人之度。他在仕途上,又特別熱衷利祿,無恬退之心。他在詩篇中,經常貶低朋友,好為人師,攘斥異端,自居正學,就是褊狹的表現。他在詩中,一再公開地以富貴利祿教子,在兒子面前吹噓自己的交游如何光顯,就是熱衷的表現。二者結合起來,更是利祿情深,恩仇念重,互為因果,愈扇愈烈。誰妨害了他的功名富貴,誰不尊敬他的學問文章,他對誰就會恨之入骨,永世不忘……五四運動以來,科學和民主的觀念深入人心,于是,中國古代大作家當中,韓愈成了最不受歡迎的一個,這就是因為他的作品中流露出來的氣質和精神狀態上的庸俗性,總帶有獨斷和專制主義的味道。”[10]17?19舒蕪的論述不僅繼承并發展了周作人的觀點,同時也從時代文化角度剖析了韓愈被抑的原因。
其二,韓文道統說教,貽害后世。周作人一生著力于小品文的創作,對于文學史上處于至尊地位的古文則多予不滿和排斥,個中原因難以排除他對韓愈的態度因素。他在1944年所寫的《文學史的教訓》中,用史學視野來審視韓文,提出了驚世駭俗的觀點:
而中國則至唐朝韓退之出,也同樣的發生一種變動,史稱其文起八代之衰,實則正統的思想與正宗的文章合而定于一尊,至少散文上受其束縛直至于今未能解脫,其為害于中國者實深且遠矣……完全是爛八股腔調,讀之欲嘔,八代的駢文里何嘗有這樣的爛污泥……將這樣的思想文章作為后人模范,這以后的十代里盛行時文的古文,既無意思,亦缺情趣,只是瑯瑯的好念,如唱皮黃而已,追究其這個責任來,我們對于韓退之實在不能寬恕……中國散文則自韓退之被定為道與文之正統以后,也就漸以墮落。[2]429?430/九
在周作人的文學史觀中,陶淵明與韓愈是一真一偽、一平一矯、一實一虛的截然對立的兩極,周作人對“古文”“韓愈”這兩個詞十分敏感,稍一觸及便意氣澎湃、怒火中燒、慷慨陳詞,大有罄竹難書之勢。他在20世紀50年代的文章中論道:
我們假如以韓愈為例,他的散文無論哪一篇,現在拿出來恐怕都已沒有一顧的價值(這也因為是本來沒有價值)……韓愈的那篇《原道》,即使不提他那封建思想,單看文章也就夠惡劣的……完全是濫八股調,讀了要覺得惡心。[2]2?3/十二
我找壞文章,在他的那里找代表,這即是《古文觀止》里人人必讀的那兩篇,《原道》與《送孟東野序》。《原道》是講道統的八股……《送孟東野序》……話都說得前后不兜頭。音韻鏗鏘,意思胡涂矛盾,這是古文的特色,上邊兩篇是最道地的。古文多壞,而古文的正宗為韓氏,此又是韓氏的代表作,可以夠得上稱為標準的壞文章了吧。[2]448?449/十
對周作人來說,真的是“談韓色變”,其“抑韓”之詞無以復加了,字里行間,我們鮮明地感受到周作人對韓愈散文的痛恨與厭惡,原因在于韓愈散文的道統說教、八股濫調以及文中所滲透出的虛偽與狂妄的品性。周作人在《不寫說理文》中將韓愈散文的這些特點概括為“韓氣”與“煤氣”,并認為這即是所謂的“文學史的教訓”。正是這樣的教訓,周作人才提倡“不寫說理文”,而且在批判韓愈的同時,提出要像陶淵明一樣“不要多發議論,還是寫些有事有人的文章好”[2]288/十。
推究起來,“抑韓”的原因在于周作人的骨子里。其一,離經叛道的文學思想。對于儒家,周作人思想上是“叛道”,文學上則是“離經”。他否定儒家的經典:“我到十三歲的年底,讀完了《孟》《論》《詩》《易》及《書經》的一部分。‘經’可以算讀得也不少了,雖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總不會寫,也看不懂書,至于禮教的精義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話,以前所讀之經于我毫無益處……因此我覺得那些主張讀經救國的人真是無謂極了……總之就是這么一回事,毫無用處,也不見得有損,或者只耗費若干的光陰罷了。”[2]768/四有如中古時期的嵇康,在儒家思想作為官方意識的文化背景下,周作人此論甘冒不韙,其毀圣叛道之論實質上是對儒家文學思想的宣戰。他否定任何以儒家道統自居的作家,韓愈便首當其沖成為儒家的擋箭牌。也正是內心深處對儒家大逆不道價值取向,他才把王充、李贄、俞正燮推尊為“中國思想界之三盞燈火”[2]195/九。其二,尚真惡偽的美學觀。周作人尚真,反對并痛惡虛假的文學:“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無論他是舊是新,都是一樣的無價值;這便因為他沒有真實的個性。”[2]289/二尚真自然惡偽,周作人批判的目標直指那些以儒家后學自居的道學家:“道學派的批評家大抵是色厲內荏的神經變質者,所以他們的話都是虛偽的,它們唯一的用處只是證明它們的主人是偽善者罷了。”[2]322/三“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豈知這正是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2]346/四毫無疑問,以叛逆思想和挑戰權威為主導的價值取向,直接形成了他的這種嫉“偽”如仇的審美取向,這正是他貶斥韓愈及其作品的“底火”。
周作人追求藝術化的生活,他的活法是調和了儒、道、釋、仙諸家后的淡泊超達、平和中正,然而,對于文學他卻不然。人本主義文學價值觀的內核即是“真”——本真的人性和真實的生活,這使得周作人在文學上求真求實、愛憎分明、正色凜然,甚至嫉“偽”如仇。也是因為有陶淵明這樣的文學偶像深固內心,所以他對韓愈的貶斥便不遺余力了。
二、思考陶學問題
雖然周作人對陶淵明未作專門研究,但他的陶淵明批評同樣以“立破并舉”的方式闡述了對陶淵明及其作品的深刻體悟和獨到見解。
周作人在多篇文章中認為,陶淵明看徹生死、高曠超達,在中國文化史上無出其右者。通過對陶作的文本深入剖析,周作人認為,陶公《自祭文》《擬挽歌辭》《歸園田居》《神釋》等“并非單是曠達語,實乃善言世情”[2]306/七,而且“此所謂閑適亦即是大幽默也”[2]351/七,陶淵明不戀生、不畏死,是心靈的解放,“此等難事惟有賢達能做得到”[2]351/七。陶公對生死的超曠,遠逾那終日參禪看話、貌似超脫的和尚,這也是陶公對蓮社攢眉而去的深層原因。
最能體現周作人學術見解的是他對陶淵明的“反批評”,這體現于陶學的三個問題上。
第一,反駁鐘嶸“陶淵明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的觀點。周作人認為“陶淵明古來都當他作隱逸詩人,這是皮相之見,其實他是很積極的”[2]70/十三。支撐這一觀點的論據是陶詩《讀山海經》諸篇。他認為,《讀山海經》中對精衛、刑天、夸父等神話人物的歌詠,聲調都比較激越,表現了“勇往直前的精神”[2]71/十三,尤其是陶公對夸父“功竟在身后”的頌贊“已超越了文人學士的范圍”[2]71/十三,詮釋了中國文化的核心精神——自強不息,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證明陶淵明的人生是積極的,并非是消極的隱逸。
第二,反駁唐人“陶淵明忠于晉室”的觀點。沈約《宋書·隱逸傳》記:“(潛)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11]2289但并沒有明確提出陶淵明忠于晉室的觀點。唐開元時期文選學家劉良認為:“潛詩晉所作者皆題年號,入宋所作者但題甲子而已。意者恥事二姓,故以異之。”[12]其后,顏真卿《詠陶淵明》詩以題詩庚子為據[13]1583,在陶淵明接受史上第一次以詩的形式提出了影響頗為深遠的“陶淵明忠于晉室”的觀點。周作人認為,“俗儒辯甲子,曲說徒瞢騰”[14]45,把陶淵明看作“一姓之忠臣”是“令人悶損”的錯誤觀點[2]521/六。他說:“他(陶淵明)有一肚子理想,卻看得社會渾濁無可實施,便只安分去做個農工,不再來多管。”[2]521?522/六雖然時世處“江河日下之勢”而莫可挽救,但陶淵明還是“能自振作”[2]730/六。由于沒有提供足夠的論據,周作人的反駁顯得勉強而無力。
第三,反駁杜甫。陶公教子是陶淵明研究中的突出問題,杜甫《遣興五首》之三曰:“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達生豈是足,默識蓋不早。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15]563認為陶公掛懷于子之賢愚,故未能達“道”。杜甫的觀點招來了后世的批評。比較而言,周作人的批評雖委婉卻不留情面:“對于此詩(陶公《責子》詩),古來有好些人有所批評,其中唯黃山谷跋語說得最好,‘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觀也。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嘆見于詩耳,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這里的所謂俗人之中,卻有一個杜子美,這很有點兒奇怪。杜詩《遣興》之三是說陶公的,末二句云:‘有子賢與愚,何其掛懷抱。’陶詩題目雖是責子,似乎是很嚴肅的東西,其實內容是很詼諧的,其第五聯最是明了,如果十三歲的小孩真是連六與七還不懂,那么這是道地的白癡,豈止不肖而已。”[2]803?804/十二在《關于教子法》一文中,周作人也談及陶公教子問題,他引述陶公《與子儼等疏》、蕭統《陶淵明傳》、《南史·隱逸傳》、黃庭堅《書陶淵明責子詩后》和俞正燮《癸巳存稿》等相關材料來證明“陶公善解子意”的觀點。他的《兒童雜事詩·陶淵明一》最能概括他對陶公教子問題的理解,詩曰:“但覓栗梨殊可念,不好紙筆亦尋常。陶公出語慈祥甚,責子詩成進一觴。”[16]67可以說,周作人對這個問題,引證豐贍,論析透徹,對杜甫的反駁情理俱合,令人信服。
三、獄中陶詠
崇陶,幾乎是大多數中國士人的心靈訴求,這便形成了貫穿中國文學史的擬陶、和陶現象。出于深刻的崇陶心理和對陶詩的篤愛,周作人也不由自主地詠陶。其陶詠詩歌計數十七首①,有詠陶、集陶句、用陶句陶事三類。
第一類詠陶三首,除上文引述的《兒童雜事詩·陶淵明一》外,還有《兒童雜事詩·陶淵明二》《丁亥暑中雜詩·陶淵明》。如“離家三月旋歸去,三徑如何便就荒。稚子候門倏不見,菊花叢里捉迷藏。”(《兒童雜事詩·陶淵明二》)[16]67這首詩立足陶公彭澤歸來作賦事,化用《歸去來兮辭》“三徑就荒”“稚子候門”以及“陶菊”意蘊;“如何”一詞,語氣反詰,強化了“歸去來”的信心與決心;尾二句獨具匠心,再現了稚子的淘淘童趣和陶公歸家后的天倫之樂,旨在推崇陶淵明回歸自然的價值取向。此詩風格詼諧幽默,止庵先生評為“甚是生趣盎然,有如天籟”(《關于〈老虎橋雜詩〉》)[14]iv。
宋書傳隱逸,首著陶淵明。名文歸去來,所志在躬耕。
本來隱逸士,非不重功名。時艱力不屬,脫然謝簪纓。
人不可無勢,桓溫語足征。孟嘉亦豪杰,尺寸無所憑。
偃蹇居掾屬,徒為螻蟻輕。五斗悔折腰,此意通彌甥。
細讀孟君傳,可以知此情。俗儒辯甲子,曲說徒瞢騰。[14]45
止庵先生認為這首詩風格“古樸渾厚、率直懇切”[14]iii,且以理論思辨見長,剖析陶淵明與其外公孟嘉的文化淵源關系。前半部分挖掘陶淵明歸來躬耕的深層原因——時艱,著力詠嘆陶公脫然謝簪纓的英明之舉。后半部分從陶公所著《孟府君傳》記載的孟嘉軼事入手,表達對桓溫之輩的輕蔑,論證孟嘉的“豪杰”品性,得出了陶公性情源出于孟嘉——即外公與彌甥文化同源的結論。周作人還認為,陶淵明本無意棄劉宋而隱居,怎奈“時艱”而不得已,所以唐以來“入宋但題甲子,恥事二姓”的觀點曲解了陶公,實在令人困頓悶損。
第二類集陶句詩共二首,均出其組詩《題畫絕句》中。《題畫絕句》共五十九首,止庵先生考證,其中“前五十四首,寫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之間”[17]257。如“凄厲歲云暮,園林獨余情。翳翳經夕雪,寒花徒自榮。”[16]86這是第一首集陶句詩。四句詩依次出于陶詩《詠貧士七首·其二》《悲從弟仲德》《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九日閑居》。詩人將梅花和水仙與陶公所歌詠的貧士、菊花相模擬,贊美其傲雪斗寒、堅貞不屈、超拔塵俗的品性,看得出,周作人諳熟陶詩,亦深得中國古典詩歌“香草美人”之法。又如“戶庭無塵雜,夏木獨森疏。白日掩荊扉,時還讀我書。”[16]86這是第二首集陶句詩。四句詩依次出于陶詩《歸園田居五首·其一》《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于規林二首·其一》《歸園田居五首·其二》《讀山海經十三首·其一》。詩歌借陶詩抒寫自己平靜而無奈的“且作浮屠學閉關”[16]23的生活狀態,表達對陶淵明歸隱后的自由、恬淡、寧靜的生活的企慕。
第三類用陶句陶事詩較多,計有《苦茶庵打油詩》之六、七,《往昔》之《李白》,《題畫五言絕句》之《籬邊菊花》《山水桃花》《菊花下有雞啄蝴蝶》《墨菊旁有棘枝》《菊花》《野菊與雞》,《丁亥暑中雜詩》之《女兒國》《夸父》《乞食》,共12首。這類詩或詠物,或抒懷,或詠史,或借陶言事,或依陶立意,詠及了陶淵明《乞食》《讀〈山海經〉·其五》《九日閑居》《桃花源記并詩》《飲酒·結廬在人境》《飲酒·秋菊有佳色》《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歸去來兮辭》《讀〈山海經〉·其九》等詩以及沈約《宋書·隱逸傳》所載陶公“我醉欲眠,卿可去”的軼事,全方位地表達了崇陶情懷。而在這類詩中,詠菊詩就有五篇之多,均出于《題畫五言絕句》中。
持醪嘆靡由,秋華浸盈把。陶令不歸來,寂寞東籬下。(《籬邊菊花》)[16]86
閑坐東籬下,獨酌不成醉。回首看雞蟲,領略蒙莊意。(《菊花下有雞啄蝴蝶》)[16]87
何時去東籬,寂寞伍荊棘。傲霜徒自榮,黯然無顏色。(《墨菊旁有棘枝》)[16]89
秋菊有佳色,籬邊徒自榮。獨慚蒿艾輩,廢疾起蒼生。(《菊花》)[16]89
寒花正自榮,家禽相向語。似告三徑翁,如何不歸去。(《野菊與雞》)[16]95
這5篇詩作,以《籬邊菊花》最為代表。此詩從陶詩《九日閑居》中化出,尾二句為題旨,人亦菊,菊亦人,陶令與籬菊默契相知,頌贊陶公如籬菊般高潔、堅貞、拔俗的人格。詩人歌頌陶公,亦不無自況之意。必須強調的是,周作人的17首陶詠除《苦茶庵打油詩》之六、七,《往昔》之《李白》3首詩外,余者都是在南京老虎橋監獄中所作。從1945年12月6日被捕羈押在北平炮局胡同的陸軍監獄,到1949年1月26日被釋放而走出南京老虎橋監獄的三年多歲月,周作人是一個地道的囚徒。然而,從周作人的17首陶詠詩作中,我們卻絲毫察覺不到作者身陷囹圄的困境,更感受不到他對生活的絕望、對衰病的痛苦、對命運的怨怒。相反,我們從詩中體悟到了童趣、幽默、冷峻、縝密、豁達、樂觀、淡定、超然……陶淵明高遠博大的胸襟和擺落塵俗、超脫生死的智慧,安頓了獄中的周作人,也洞開了他未來的心路,陶淵明真正成了他生命中的寶貴精神財富。周作人獄中思陶、詠陶,這種現象在陶淵明接受史上是絕無僅有的特例,是帶有悲劇色彩的陶學史話。
周作人在其文學觀和人生觀的雙向作用下完成了對陶淵明詩文的接受。辭達、意誠、恬淡,是周作人對陶淵明詩文的論斷,從文學形式到作品內涵的精準與深刻的解讀,正體現了周作人的文學理想與創作追求。1918年底和1919年初,周作人先后發表《人的文學》與《平民的文學》,首倡“人的文學”與“平民文學”的文學主張。1920年1月,他在《新文學的要求》中針對新文學的“人生派”與“藝術派”的利弊作了理論辨析,主張“人生的文學”[2]207/二,即“人道主義的文學”“理想主義的文學”[2]210/二,這種文學的“文學的主位”必須是“人的本性”,其次是“文學的本質”[2]208/二。周作人對陶淵明詩文的見解與觀點,也是對他的人本主義文學價值觀的最佳詮釋。同時,對諸多陶學問題的思考,對鐘嶸、沈約、杜甫等人觀點的反駁,也為他的人本主義文學觀提供了旁證。不僅如此,周作人還汲取了陶淵明的生存智慧。周作人人生觀的主導傾向是外儒內道、無為而為、以釋補儒的“出世”。像白居易、蘇軾等先賢一樣,周作人在人生最苦厄的時段慕陶詠陶,安頓自我,流露出濃重的隱趣和出世心理,這也從側面為他時時不畏以“叛徒與隱士”“流氓與隱士”自名做了充足的注腳。
注釋:
① 文中引文的所在冊數在頁碼后標注,如23/九。
② 周作人《往昔三十首·邵雍》詩曰:“……邵子獨擊壤,有意擬康衢。淵明擅說理,泰山不可逾……”“淵明”一詞,王仲三先生解釋為“指文章內容深刻而文字簡明”見王仲三《周作人詩全編箋注》(學林出版社1995年版第85頁)。本文取此說,認為此詩與陶淵明無關。
參考文獻:
[1] 周建人.魯迅和周作人[J].新文學史料,1983(4).
[2] 周作人.周作人散文全集[M].鐘叔河,編訂.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
[3] 丁福保.清詩話[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 郭紹虞.清詩話續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 [清]胡式鈺.竇存·詩竇[M].北京:中國書店,1985.
[6] 龔斌.陶淵明集校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7] 楊伯峻.論語譯注[M].北京:中華書局,1980.
[8] 丁福保.歷代詩話續編[M].北京:中華書局,1983.
[9] [元]吳澄.吳文正集[M].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0] 陳邇冬.韓愈詩選[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4.
[11] [宋]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96.
[12] [梁]蕭統.文選[M].[唐]六臣,注.四部叢刊初編:第311冊.上海:上海書店,1989.
[13] [清]彭定求,等.全唐詩[M].北京:中華書局,1960.
[14] 周作人.老虎橋雜詩[M].止庵,校訂.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13.
[15] [清]仇兆鰲.杜詩詳注[M].北京:中華書局,1979.
[16] 周作人.知堂雜詩鈔[M].長沙:岳麓書社,1987.
[17] 止庵.周作人傳[M].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10.
〔責任編輯 劉小兵〕
ZHOU Zuo-ren’s Acceptance of TAO Yuan-ming’s Poems
LIU Zhong-wen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The worship of ZHOU Zuo-ren to TAO Yuan-ming makes his book citing and evaluating TAO Yuan-ming and his works. He regards TAO poem honest, Tao essays figurative and TAO a unique poet.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AO Yuan-ming poetry, ZHOU Zuo-ren takes YAN Zhi-tui and HAN Yu as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idence and demonstrates his humanism literature value view. At the same time, ZHOU Zuo-ren got the survival wisdom, settled the mind and opened the mentality in prison through TAO Yuan-ming’s poetry.
Key words:ZHOU Zuo-ren; TAO Yuan-ming; poetry; acceptance
作者簡介:劉中文(1964-),男,黑龍江青岡人,教授,博士,碩士生導師。
收稿日期:2015-04-30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6?5261(2016)01?0096?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