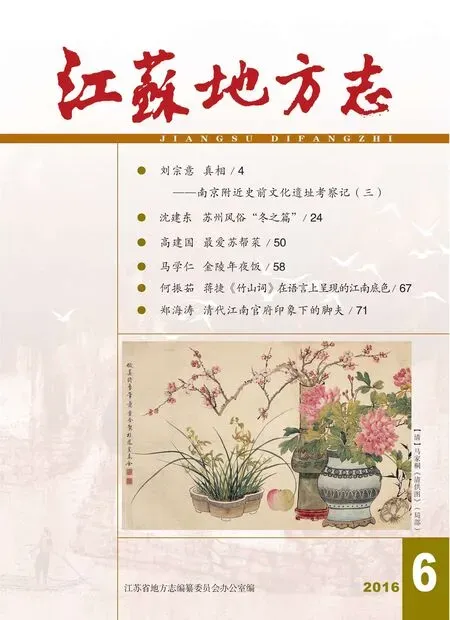泰州“號子”錦拾
◎ 張樹俊
泰州“號子”錦拾
◎ 張樹俊




大家知道土家族、苗族在長期生產勞動過程中形成了插秧整“插秧酒”,薅草打“薅草鑼鼓”,抬東西喊“號子”等習俗。與土家族、苗族不同的是,泰州人不只是抬東西的時候打號子,在田里干活特別是干重活都有打號子的習慣。泰州的勞動號子品類繁多,以秧歌、窯工、車水、耕田、打場、挑擔號子等內容為普遍。解放初期,茅山栽秧號子曾經唱進中南海,林湖栽秧號子“格上段”被中央音樂學院地方音樂教材和江蘇省小學音樂教材選用。
一、興化栽秧號子
泰州的茅山的號子源遠流長,可追溯到秦滅六國,四海一統的時候。為固萬世之基,秦始皇大征民夫,修筑長城。孟姜女尋夫送寒衣,行至山海關,看到老弱病殘背石扛土,不堪重負,又不敢在監工面前喘氣呻吟,遂教他們用“哼號”“咳號”一打一答的方法來順氣省力,并逐步形成了原始的勞動號子。這時,茅山籍的民夫也于其中學會了號子。后來幸存的民夫回到家鄉,便將孟姜女所傳號子在勞動時打起來,果然鼓起了大家的勞動勁頭。后來,茅山人民在長期的生產勞動中,不斷編唱出新的號詞,逐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茅山號子。茅山號子其實是一個廣義的概念。從表現勞動的形式上可分為車水號子、栽秧號子、薅草號子、挑擔號子、碾場號子、摜把號子、放牛號子等;從音樂結構上可分為長號子、短號子。狹義的茅山號子是指車水號子和栽秧號子,其中“栽秧號子”在茅山號子中獨占鰲頭,俗稱“小妹妹”。這與人們的性格以及勞動分工有關。一般說來,男人嗓子粗、力氣大,踏車水,挑擔碾場,打起號子來粗獷豪放,急促有力;女人聲音尖,心兒細,栽秧薅草,順藤理根,專心細致,打起號子來輕盈細膩,婉轉悠揚。茅山號子演變至今,已成狹義上的號子了。人們習慣在表現緊張的農活時打車水號子,即短號子;在表現輕松的農活時打栽秧號子,即長號子。茅山號子以舒緩平實的音調旋律,明快有力的音樂節奏,快慢自由的演唱速度,分合有致的歌唱形式,形成了高低協調,詠嘆自如的獨有的民歌特色。在演唱風格上,茅山人打號子行腔穩健、咬字有力、吐音清晰、富有彈性,真正體現了民族演唱方式的特色。茅山號子傳遞感情、理想,解放前為革命斗爭服務;解放后為重大歷史事件,土改、合作化、大躍進服務;改革開放以來,著重歌頌經濟騰飛,農民新生活。具體唱法是一人領唱,眾人應和。激越的歌聲與勞動節奏和諧交融,鄉音鄉情與人們樸素的感情愿望相交匯,有調節情緒、增添干勁之作用。林湖栽秧號子。里下河水鄉以種稻為主,農家人很看重栽秧,栽秧之日,總要備足酒菜,宴請栽秧幫工,稱“吃栽秧飯”;飯后,由插秧能手下田扯第一把秧,謂“開秧門”;扯秧前,先用手向秧苗澆水,謂“趕秧風”,以免手腕中“秧風”紅腫疼痛。栽秧時節,原先空蕩的田野轉眼沸騰起來,水車轉動的“吱吱”聲、牛鞭甩舞的“叭叭”聲、秧把拋落的“啪啪”聲……彼落此起。這時候,一陣陣清脆悠揚的秧歌,更貼著片片水田,穿梭在碧綠盎盎的秧行間,九曲回旋,不絕如縷。秧歌,作為農耕文明不可或缺的章節,深深鍥刻在歷史的印記里。而流傳于里下河一帶的林湖栽秧號子,又以其獨特的魅力,成為泱泱秧歌民謠中的翹楚。林湖栽秧號子已傳唱了千百年。舊社會,婦女在家庭中沒有多少言論自由。于是,她們利用打號子的機會來表達自己的思想,來訴說自己的心事。號子大都即興編來,口耳相傳,內容都是表達她們的愛憎與愿望,自然而鮮活地再現了水鄉人勤勞樸實的性格、淳厚平和的民風、凝聚向心的心理……厚土的底氣,秀水的滋潤,使林湖栽秧號子具有一種時空穿透力。林湖栽秧號子和近鄰茅山號子、戴窯號子有所不同。茅山近泰州,故號子中每多海陵調;戴窯近東臺,故窯號中每雜臺城音;而林湖在版圖上居興化之中,栽秧號子委婉抑揚,可謂地道的本域之音。林湖是生長秧歌的地方,1979年的《興化民歌選》中林湖栽秧號子有18首。
二、靖江打豆號子
藝術源于生活,精品在于繼承和升華。打豆號子作為聲樂演唱作品有它音樂的獨特創新,同時,融“三情”于一曲的歌詞,也是打豆號子繼承和升華的藝術特色。特色之一,打豆號子表現了收豆的鄉間風情。收豆一般在夏末早秋時節,拔豆要起大早,挑豆鋪豆總在上午,打豆一般在午后。所以,打豆號子貫穿于收豆勞動的全過程。舊時鄉間,并不是每戶人家都有一塊曬場,誰家有一塊較大的場地,鄰戶可以借用,這就自然形成舊時收豆人們會聚的風情。太陽升高了,田里人們起大早拔好的黃豆上沾著的露水開始干了,各家各戶出門收豆了,這時,豆田里就熱鬧起來。隨后,打豆場上,“一記高來一記低,連枷打得蓬蓬飛”,一幅收豆打豆的勞動風情畫面表現得既真實又形象。特色之二,打豆號子表現了青年男女的純樸愛情。谷場打豆,為鄉間男女提供了會聚的場地,因而也為他們談情說愛提供了機會。靖江人稱之為“調情”民歌的打豆號子,把打豆場上男女之間純真的愛情表現得既幽默又風趣,既歡愉又逗樂,往往鄉間少男少女的萌芽愛情,就是在這“調情”的號子聲中滋生的,以至后來相親相愛,終結良緣。打豆號子歌詞繼承了舊時號子中的底蘊,藝術上作了升華,同時又想到了黃豆可磨成豆漿,由磨豆漿而想到靖江人最愛聽的錫劇小折子戲《雙推磨》,于是,表現鄉間男女純真愛情的歌詞出現了:“半勺黃豆半勺水,磨出豆漿把哥嘗”“我和妹妹雙推磨,磨出豆漿甜又香”。特色之三,打豆號子表現了收豆的勞動熱情。靖江鄉間流行的打豆號子,是在生產力落后的條件下唱出的,但莊稼人自有他們的苦樂觀,面對鋪滿田間的金黃的豆角,他們心中自然有著“種瓜得瓜、種豆得豆”的收獲甜蜜,自然會迸發出揮汗如雨、肩挑重擔的勞動熱情。豐收的歡樂溢滿心頭,打豆的號子盡情呼出:“豆子蹦到人臉上,笑聲飛到云天里”“我們的家鄉賽天堂,莊稼拔節也帶響”,把打豆場上人們勞動的熱情渲染得更高昂。“連枷伴著歌聲唱,唱得太陽更輝煌”,唱出了打豆男女對美好生活的展望,把打豆號子推向了演唱高潮。
三、溱潼窯工號子
溱潼鎮窯業從清朝開始,至今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了,最鼎盛時,在不到0.3平方公里的湖西莊區域里,建有108座土窯。與窯業伴生的窯工號子匯合著喜鵲湖的流水聲,獨具特色,悠揚綿長。協調生產、渲染氣氛、積蓄力量、鼓舞情緒、提高效率……需要統一的號令將濕漉漉的汗水擰起來,將共同的意志擰起來。與其它勞動號子一樣,窯工號子是美化了的號令。不同于其它地方的窯工號子,溱潼湖西莊窯工號子不只是單純的“吭——唷——嘿、吭——唷——嘿”,它融入了水鄉的文化和民俗,曲調工巧、內容豐厚。溱潼湖西莊窯工號子自成一體,大致分成五個系列:抬頃號子、做磚號子、裝窯號子、窨水號子、出窯號子,生動反映了窯工們從挖泥制作土坯,到把土坯制作成磚頭的全過程。此外,還有由窯工號子派生出來的卸貨號子、拉草號子及對照窯主、窯民生活的四季歌。歷經久遠,溱潼湖西莊窯工號子一度難以詮釋,許多字音含糊不清、許多內容似是而非,昔日的窯工們只是依靠祖輩、父輩揮不去的記憶唱和著。挖掘、保護、傳承這一民間文化瑰寶,地方文化工作者們為解讀窯工號子做出了不懈的努力。溱潼湖西莊窯工號子除婦女唱的做磚號子溫柔婉轉外,大多具有粗獷跌宕的豪放。溱潼湖西莊窯工號子分“平調”“髙梆子”“喉號”“急煞腔”四種腔調。用中音打的號子是“平調”;用高音打的號子是“髙梆子”;用縮緊喉頭的尖音打的號子是“喉號”;緊急情況下打的號子是“急煞腔”……裝窯號子是窯工號子的主歌,更顯力與陽剛的張揚,多用“急煞腔”。“急煞腔”突出一個“急”字,要求挑工裝擔時手的動作快,路上行走腳步奔跑快,口中號子也就打得快。“急煞腔”一陣緊似一陣,此起彼落,鏗鏘有力,豪邁奔放。溱潼湖西莊窯工號子多為七字段,內容常是即興創作,卻樸素清新、朗朗上口。“抬頃”是每年四五月間為全年準備制磚、制瓦的泥土,泥土多取于當地頃二、頃三荒田的河塘。抬頃號子由一人起腔,眾人搭腔。號子粗獷、豪放,常帶譏諷含蓄做坯。女工們“清頭布,花圍裙”,端磚上棱打的號子婉轉動聽。裝窯號子分三段,第一段起擔打“平調”;第二段“響雷了,要下雨啦!”打“急三腔”;第三段“天晴了,快滿了”打“喉號”。激昂的裝窯號子是窯工們為了調節艱苦的體力勞動隨機哼出的曲調,跟他們的勞動過程緊密相關。“窨水”工人很辛苦,打的號子低沉、緩慢,有些怨聲寡氣。出窯因出窯工的身份不同,出窯號子也有不同的內容和感情。窯主自己出窯,打的號子歡快;雇工出窯,打的號子低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