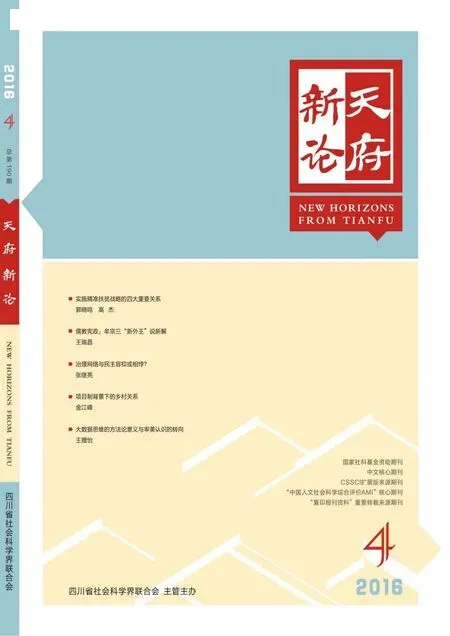從三代之禮到萬國公法:試析郭嵩燾接受國際法的心路歷程
范廣欣
?
從三代之禮到萬國公法:試析郭嵩燾接受國際法的心路歷程
范廣欣
摘要:本文試圖溝通晚清首任駐外公使郭嵩燾的傳統學術著作和他出使前后的日記、奏稿及書信,以探討其對外交涉的依據。郭氏詮釋儒家經典時指出,“三代賓客之禮”包含對外交涉的真理。出使前后通過閱讀 《萬國公法》等國際法譯著,并與“萬國公法討論會”交往,他才意識到近代外交應以“萬國公法”為依據。然而,郭氏接受“公法”,并不意味著放棄“三代之禮”,恰恰相反,他是將“公法”當成“三代之禮”精神在當代的體現而加以推崇。
關鍵詞:郭嵩燾 經典詮釋 近代外交 國際法 萬國公法 三代賓客之禮
郭嵩燾 (1818-1891),湖南湘陰人,光緒二年 (1876)起出使西歐,為近代中國首任駐外公使。與其繼任者 (多為洋務知識分子和職業外交官)相比,郭氏的經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他從早年為湘軍籌餉開始就與洋人打交道,歷任廣東巡撫、駐英法公使,親身參與了從后鴉片戰爭時代到同光中興中國外交的近代轉型;另一方面,他是翰林出身,同曾國藩、劉蓉、羅澤南等人同為湖南理學的代表人物,由于仕途不順,他一生中許多時間是在家鄉著書立說,教育子弟。他的洋務經驗如何影響其著述?他在傳統學問方面的深厚積淀如何影響他對近代外交的看法?以往的學者,研究郭嵩燾外交觀念,往往重視他早年的洋務經驗,而忽略了他浸潤其中的傳統學養所起的作用;研究近代外交轉型,往往著眼全局,卻對個別關鍵人物的心路歷程不夠重視。①關于近代外交轉型,請參見Immanuel C.Y.Hsu,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及田濤 《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濟南出版社,2001),下文將作具體討論。研究郭嵩燾的學者,對其外交思想與傳統學問的聯系往往注意不夠。比如黃康顯強調郭氏對傳統的背離,認為他所受到的傳統教育是一種束縛,只有當他與西方世界發生直接接觸以后才獲得了前進一步的決定性力量。見Owen Hong-hin Wong,A New Profile in Sino-Western Diplomacy:The First Chinese Minister to Great Britain(Hong Kong:Chung Hwa Book cp.,Ltd,1987),pp.100-102,105-106。持類似觀點比較著名的還有鐘叔河:《論郭嵩燾》,《歷史研究》,1984年第1期。汪榮祖強調郭氏“思想的敏銳,以及對西方認識的深切”,強調他與當時政治和社會環境的沖突,而不是他與傳統的聯系。見汪榮祖:《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燾與道咸同光時代》,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3,弁言頁2-3。王興國對郭氏思想從政治、外交到哲學、文藝方方面面都有介紹,但是沒有致力考察郭氏思想不同側面之間的內在關聯,尤其沒有探究郭氏外交思想的學術淵源。見王興國:《郭嵩燾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頁281、287-288。目前所見,只有郭廷以指出郭嵩燾的外交見解“主要得之于學問”,韋政通指出郭嵩燾的洋務理念來自傳統,可惜兩位前輩學者并未具體分析郭嵩燾的傳統學術著作,從中發掘郭氏外交理念的思想淵源。見郭廷以:《郭嵩燾先生年譜》(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頁2-6;韋政通:《中國十九世紀思想史》(上),臺北:東大圖書,1991,頁449-458。
本文試圖在郭嵩燾的傳統學術著作中發掘他對近代外交的體會,并將這些內容與他在日記、奏稿和書信中對“萬國公法”(今譯國際法)的描述和討論聯系起來,考察他對“懷柔遠人”的重新詮釋和對三代之禮的憧憬如何幫助他理解萬國公法,并接受其作為處理中外關系的基本準則。必須指出,郭嵩燾出使西洋,正是萬國公法輸入和應用的結果。但是,直到出使之后,他對萬國公法才有進一步認識,后者一步步占據了他考慮外交問題的中心,成為他心目中三代之禮的當代依據。下文首先討論郭嵩燾如何在三代之禮與近代外交之間建立起聯系。
一、三代之禮與近代外交
光緒元年十一月,郭嵩燾出使英國之前曾經因馬嘉理案彈劾云南巡撫岑毓英。①馬嘉理 (A.R.Margary)為英國駐華使館工作人員,1875年迎接英國探險隊從緬甸進入云南時,為中國邊民殺害。郭嵩燾后來正是因為馬嘉理案,被朝廷任命為欽差大臣赴英致歉。其奏折一開始并不切入正題,而是以相當篇幅議論周禮:
竊臣考 《周禮》一書,百官之職,皆有事于賓旅,而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列之軍、嘉二禮之上。行人所司之饗食、掌客所供之牲牢,至優至渥。六官所掌諸典禮,無若是之詳者。環人、行夫送迎賓客,一以禮之。未嘗不嘆三代圣王享國長久,其源皆在于此。何也?遠方賓客,萬里之情畢達,邦國之事宜、生民之疾苦,巨細自得以上聞。春秋列國以禮相接,文辭斐然,其立國或遠在唐虞之前。秦漢以來,此禮日廢,國祚之久長亦遠不及三代。……頃年以來,西洋諸國環集中土,事故繁多,乃稍講求三代賓客之禮,而其強兵富國之術,尚學興藝之方,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國本者,實多可以取法。洋人又樂與中國講求,助之興利,以蘄至富強。〔1〕
在郭嵩燾看來,對外交往自古以來就是國家的重要職能,關系到國家的前途和命運,在這一方面三代提供的最重要的經驗是以禮待人,促進交流,了解實際情況,發展儒家理想中類似人與人之間相處那種親密而友好的關系,而不是采用武力征服或者對抗的政策。春秋列國代表的意義,不再是傳統儒家譴責的禮壞樂崩、列國紛爭,而是當時中國外交所要追求的理想狀態。更為耐人尋味的是,郭氏認為,重新“講求三代賓客之禮”有助于中國與“西洋諸國”在平等互利基礎上發展近代外交,并學習他們的富強文明。
這篇奏折因為引用 《周禮》討論當時的外交,被軍機章京批評“立言不倫”。直到郭嵩燾去世以后,好友王先謙為他整理遺稿,還覺得郭氏的觀點過于激進,不見容于士林,因此對原文作了大量刪改,特別是從朝貢制度的角度解釋三代賓禮,從而凸顯中外之間上下尊卑、華夏蠻夷的分野。②軍機章京的批評見郭氏“自記”,經王先謙刪改的奏折,題為 《請將滇撫岑毓英交部議處疏》,兩者均作為 《奏參岑毓英不諳事理釀成戕殺英官重案折附上諭》之附錄收入 《郭嵩燾奏稿》,頁349-350。有關王先謙對郭氏奏折的刪改,請參見范廣欣:《郭嵩燾遠人觀念的變遷》,《二十一世紀》,第104期 (2007年12月),頁40-41。王先謙的修改違背了郭嵩燾的原意。后者在卸任署理廣東巡撫之后、光緒元年重獲起用之前曾經有八年時間返回湖南居住,主要從事傳統經史學術的批評和整理,完成的著作包括 《大學章句質疑》《中庸章句質疑》《禮記質疑》和 《校訂朱子家禮》。③出使前,郭嵩燾將這四種著作寄存在李鴻章處。見 《郭嵩燾日記》(第三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頁57。前三部著作都涉及對儒家經典中有關中外關系論述的反思。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些著作中郭氏提出了自己對“懷柔遠人”這一傳統的獨特解釋,一方面從精神上否定了明清以來的朝貢制度,另一方面也嘗試溝通三代賓客之禮與近代平等外交。
“懷柔遠人”這一說法直接源于 《中庸》哀公問政章,所以下文首先以 《禮記質疑》之中庸篇和 《中庸章句質疑》有關內容為依據討論郭嵩燾對“懷柔遠人”的理解。《中庸》原文講“柔遠人”一共有三處。首先是提出名目:“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然后是講功效:“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最后是講具體的作法:“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事,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漢唐經學的傳統傾向將“柔遠人”與“懷諸侯”連起來解釋。鄭玄的注就明確指出:“‘遠人’,蕃國之諸侯也。”唐朝孔穎達作 《五經正義》解釋“柔遠人則四方歸之”,便是承襲鄭玄的說法:“‘遠’,謂蕃國之諸侯,‘四方’,則蕃國也。”〔2〕這里面隱含兩層意思:首先是強調中外之分,(《周禮·秋官大行人》:“九州島之外,謂之蕃國”),然后是等級尊卑 (天子與諸侯是君臣關系)。這顯然是反映了漢、唐以來天朝大國、唯我獨尊的心態。郭嵩燾對這個說法持什么態度呢?
在 《禮記質疑》中,郭氏并未對“蕃國之諸侯”的說法作出直接響應,他質疑的是鄭玄對“所以懷諸侯也”下面一句“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的解釋。這里涉及一個分段的問題。鄭玄把這句話當成下一段的開始,所以根據下文的意思解釋“一,謂當豫也。”郭氏則把這一句看成是上一段的總結,所以結合哀公問政章前面部分講五達道、三達德的內容,指出這句話的意思是說,治理天下國家的這九條基本的政治原則背后都有普遍的道德倫常的依據。《禮記質疑》原文如下:
此節始說到政上,究其實,皆達道 〔即通常所說的五倫——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之所以行也。修身,本也。天下國家之九經,統乎君也。親親,父子兄弟之推也。大臣、群臣、庶民、百工,君之推也。尊賢也、遠人也、諸侯也,朋友之推也。〔3〕
這里講“遠人”是“朋友之推”,分明就有“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的意思了。講“天下國家有九經”統之于五倫,各有歸屬,并不是郭嵩燾的首創,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在其 《讀四書大全說》中就提出這樣的觀點。有證據表明郭氏的確受到王夫之 《讀四書大全說》的影響。①郭氏在學問上受王夫之的影響很深,《禮記質疑自序》表明這本書的創作本身就是受到王夫之 《禮記章句》的啟發。見 《郭嵩燾詩文集》,頁21。光緒二年臨行之前他還上奏朝廷要求以王夫之從祀孔廟。見 《請以王夫之從祀文廟疏》,《郭嵩燾奏稿》,頁351-352。但是王氏原文雖然講“尊賢、懷諸侯為盡朋友之倫”,卻沒有為“遠人”歸類。就這一點而言,郭氏的確發前人所未發。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多少都有上下之分,唯有朋友一倫在這方面的界限最為模糊,可見郭氏講“柔遠人”強調的不是等級尊卑,而是相互之間的交流溝通,與所謂“蕃國之諸侯”的解釋有相當差異。
在 《中庸章句質疑》里面,郭嵩燾就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場:
章句云: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涂,極允。船山謂:旅者,他國之使,修好鄰國而假道。又如失位之寓公與出亡之羈臣,皆旅也。當時禮際極重,一言一動之得失,所
以待之者即異,故嘉善而矜不言不能者,亦當以其漂泊而矜之也。〔以上大體為王氏原文〕列遠人于諸侯之上,其非聘使可知。送往者,過此而他逝者也。迎來者,來就本國者也。鄭注謂:“蕃國之諸侯”,失之。〔4〕
從這段話可以看出對“懷柔遠人”的解釋有不同的傳承,郭氏大體上站在朱熹、王夫之一邊,反對鄭玄和孔穎達的觀點。
朱熹有關“柔遠人”的解釋在 《中庸章句》中因應原文也有三段,以下分別就朱熹原注、王夫之的觀點和郭氏的取舍,作詳細分析。首先解釋名目,“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這個說法出自《孟子·告子下》,按朱熹的解釋,“賓,賓客也。旅,行旅也。皆當有以待,不可忽之也”〔5〕;然后解釋功效,“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涂,故四方歸”,也是出自 《孟子》;②見 《孟子·梁惠王上》:“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公孫丑上》:“天下之旅皆悅而愿出于其路矣”。再解釋具體做法,“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③以上朱子對“柔遠人”的解釋見 《四書集注·中庸章句》,頁42-43。很明顯,朱熹用“賓旅”或“天下之旅”釋“遠人”,與鄭注、孔疏不同。
郭嵩燾引用王夫之的觀點,同前文一樣,也是出自 《讀四書大全說》。原文除了郭氏所引部分以外,在“旅者,他國之使”前面還有“所謂賓旅者,賓以諸侯大夫之來覲問者言之”,為郭氏所不取。④王夫之原文見 《讀四書大全說·中庸》,收入 《船山全書》(六),岳麓書社,1991,頁524-525。聘問是指古代國與國之間交好遣使訪問。具體地講,既有諸侯對諸侯遣使 (《禮記·曲禮下》:“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的意思,也有諸侯對天子遣使 (《禮記·王制》: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的意思。把兩部分重新合起來看,即可知王夫之是在朱子“無忘賓旅”的基礎上作進一步的發揮。他在另一處地方便直接用“聘問之使”來釋“遠人”。〔6〕可見,王夫之的原文除了“他國之使”外,還有把“遠人”解釋為諸侯派出的使節的意思。
郭氏的取舍表明他一方面贊同把“遠人”釋為“天下之旅”,并且接受王夫之的意見把“旅”再落實到“他國之使”即外交使節上來,另一方面卻一定要強調 《中庸》經文里面“遠人”和“諸侯”并舉而且次序優先,因此“遠人”不是指諸侯的使節,而是真正意義上的國與國之間的外交使節(“列遠人于諸侯之上,其非聘使可知”很明顯就是對王夫之的響應)。
通過以上分析,郭嵩燾對“懷柔遠人”的理解就清楚了:“遠人”指的是他國的外交使節,即包括專門派遣到本國來的使者,也包括途經本國去第三國執行使命的人 (“送往者,過此而他逝者也,迎來者,來就本國者也”。)“柔遠人”處理的是大致對等的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既不同于鄭玄所謂天子同蕃國之諸侯的關系,也不同于王夫之所說的諸侯之間的“內交”,因此可以用來指導當時的洋務。經過郭氏解釋,“懷柔遠人”仍然具有道德倫理的基礎,具體意義卻發生了變化,不再是鄭注孔疏強調的君臣關系,而是“朋友之推”,郭氏高度重視外交禮儀 (“當時禮際極重,一言一動之失得,而所以待之者即異矣”),同時在禮儀之外也強調交往過程中的互相體諒、包容(“然善自宜嘉,而不能者亦當以其漂泊而自矜之”)。
《四書集注》用 《大學》的推及模式 (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由內而外,層層推進)來解釋“天下國家有九經”,明確講“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7〕這樣便把“柔遠人”放到了 《大學》治國平天下的脈絡里面。由上文可知,郭嵩燾是接著朱熹、王夫之的傳統來提出他對“懷柔遠人”的解釋。因此,檢查郭氏在《大學章句質疑》里對治國平天下的問題所闡發的意見,應該有助于我們對他“懷柔遠人”的觀念作進一步了解。
《大學》原文講:“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郭氏同朱熹的分歧,主要在如何解釋“絜矩之道”。在朱熹看來:“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愿,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8〕這里關鍵在于“因其所同,推以度物”,我以為是推己及人的意思:因為人心是相通的,大家分享共同的倫理價值觀念和實際需要(這一點并不因種族地域的差異而不同),所以只要回歸自己的本心,再把它向外推出去,就能實現天下太平的理想。
郭嵩燾不能滿足于這樣一個簡單的解釋,而要考慮其中具體運作的過程,他結合自己處理洋務的經驗指出:“絜矩亦從恕上推出,然恕只是推己及人。至于平天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能盡由己推去,直須度量人情之好惡,準人而推之己。大學……于平天下章說個‘絜矩’字,則是就人之適宜處言之。”他的意思是講在他所看到的世界局勢里面,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君主 (主權)和統治方式,互不隸屬,而且各國人民的實際情況和具體需要 (“情之好惡”)也可能不同,因此不可以說一個國家的問題解決了,把成功的經驗向外推廣,就可以天下太平,而一定要設身處地考慮別國的實際情況和具體需要再作出判斷。最后的結論是平天下不能像治國那樣依靠“政教”,因為沒有一個道德權威中心來作標準,各國之上沒有一種既定秩序,所以只能講究“相處之法”。這個說法同傳統中國王朝講“懷柔遠人”時所堅持的天朝中心觀念已經格格不入了。另一方面,他還是相信人心有共通之處,有些基本的價值觀念為人們所普遍接受,并且清楚地講出來:“絜矩者,矩操于身,盡天下之善惡以矩絜之,而自行其裁成輔相之宜。老老、長長、恤孤,身之矩也。一國之人心同,天下之人心亦同。”〔9〕他是在承認各國互不隸屬、國情有差異的基礎上堅持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相處有共同的道德倫理作依據,并不因為種族、地域的差異而改變。這一點是對朱熹的繼承。
簡言之,郭嵩燾正是循著另一詮釋傳統,即從朱熹到王夫之的宋明理學的詮釋傳統,形成他自己的獨特理解:“遠人”是指他國的外交使節,“懷柔遠人”處理的是大體上對等的國與國的關系,依據的普遍道德原則是“朋友之推”。郭嵩燾對三代賓客之禮的理解和在他作為中國駐英法公使的外交實踐不能不受這一理論總結的影響。
郭氏所面臨的問題是,三代賓客之禮雖然是中國外交的理想境界,在現實中卻久已湮滅,對西洋諸國也沒有感召力和約束力,那么,究竟什么是中西雙方可以遵循的共同依據?什么是三代之禮精神在當代的體現?①郭嵩燾一向認為禮樂制度應該因革損益,與時俱進,但是制度背后的基本價值,所謂“禮樂之精意”卻亙古常新,不能背棄。見《郭嵩燾日記》第一卷。出使前后的經驗告訴他,“萬國公法”是中西雙方均可信賴的國際規范和三代之禮精神在當代的體現。檢查郭氏遺留下來的日記、奏稿和文集,他對“萬國公法”的認識主要得益于三種不同的經驗,包括:一、他對在華傳教士丁韙良 (W.A.P.Martin,1827-1916)等人所譯公法著作的閱讀;二、他與“萬國公法討論會”(Association for the Reform and Codification of the Law of Nations,今譯“國際法改進及編纂協會”)的交流;三、他在出使途中和出使以后對西方國際法體系實踐和效用的觀察。限于篇幅,以下主要討論郭氏如何通過閱讀丁韙良的譯著發現“萬國公法”,如何通過與“萬國公法討論會”的交流對公法有更深入的了解。
二、郭嵩燾與丁韙良譯 《萬國公法》
徐中約認為中國要完全進入國際社會,必須滿足兩個條件,其一是承認國際法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其二是十九世紀七十年代以后在國外設立使館。〔10〕在近代史上,前者以丁韙良譯 《萬國公法》為最初的開端,后者由郭嵩燾使英得以實現。郭嵩燾的出使與丁韙良譯 《萬國公法》有直接的關系。
1839年,林則徐禁煙時就曾叫人翻譯瑞士人滑達爾 (E.Vattel)所著 《國際法》(Le Droit des Gens)片段,以供與英方交涉之用,后來譯文以《萬國律例》為名收入 《海國圖志》。但是直到總理衙門建立之后,由于中外交涉日繁,清政府才覺得迫切需要一部國際法的完整譯本,1863年當時主持總理衙門的文祥請求美國公使蒲安臣 (Anson Burlingame)推薦一部為西方各國承認的國際法權威之作,蒲安臣便向文祥介紹了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及其正在翻譯的惠頓著 《國際法原理》(Henry Wheaton,Elements of International Law)。惠頓的這部著作當時在各國外交界享有盛名,在此之前,為敦促清政府派遣駐外使節,在中國海關任職的英國人赫德(Hart)已經把有關章節譯成漢文送呈總理衙門。〔11〕在恭親王奕欣的支持下,丁韙良的翻譯得到中國學者的幫助。改訂本以半文言寫成,適合中國士大夫閱讀,于1864年正式刊行,題名為 《萬國公法》。其中三百本被發給辦理對外事務的官吏和各省督撫,以供參考。①1865年,《萬國公法》傳到日本。1873年,日本學者開始把這一通過丁韙良的譯著正式輸入東亞的法律體系稱為“國際法”。以上經過見 《王鐵崖文選》,頁123-129;梁伯華:《近代中國外交的巨變——外交制度與中外關系變化的研究》,香港商務印書館,1990,頁53-54。到20世紀初,中國留日學生對國際法的廣泛介紹才使流行于日本的一套國際法詞匯得以確立,從而取代了丁韙良等人使用的“萬國公法”、“公法”之類的舊術語。見田濤:《晚清國際法輪入述論》,《天津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頁102。丁韙良由于他的貢獻被清政府授命主持同文館,并兼“萬國公法”教習,繼續從事西方國際法的翻譯,在郭嵩燾出洋前后同文館還出版了他與中國同事合譯的 《星軺指掌》和 《公法便覽》。②《星軺指掌》中星軺也就是星使,指皇帝的使者,因為天節八星主使臣持節宣威四方。這里沿用來指近代駐外公使,因此書名的意思就是出使指南。此書譯自德國人馬爾頓(Martens)《外交指南》(La Guide Diplomatique)。此書是丁韙良在同文館期間翻譯的專門論述公使領事問題的著作,也是同文館翻譯的第一本國際法著作,當時正值中國考慮遣使駐外之際,可見其現實針對性。關于 《星軺指掌》和 《公法便覽》兩書的翻譯和出版,請參見田濤:《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頁65-70。
“萬國公法”所受到的重視表明清政府,尤其是主持外交的勢力,在經歷了一系列慘痛的失敗之后,已不得不開始放棄天朝大國、唯我獨尊的心態。為了有效地利用國際法維護自己的權益——1858年 《天津條約》規定的十年修約之期即將到來以及日本在臺灣挑起沖突,都帶來新的刺激——遣使駐外的問題也越來越提上議事日程。與郭嵩燾私交甚篤的李鴻章在決策過程中起了關鍵作用。③臺灣事件告一段落以后,李氏就提議朝廷遣使日本:“自來備邊馭夷,將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廢,各國互市、遣使,所以聯外交可以窺敵情……即泰西各大邦亦當特簡大臣……其中國交涉事件有不能議結或所立條約有大不便者,徑與該國總理衙門往復辯論,隨時設法。”后來他又奏請在秘魯、南洋等地派駐外交代表,認為不僅可以保護當地華人,也有利于海防。馬嘉理事件后,他就明確支持遣使英倫:“若有關外交無傷國體者,似尚可以允行。”分別見王彥威、王亮編纂:《清季外交史料》(一),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3,影印北平外交史料編纂處1932-1933刊本,卷1,頁10;卷2,頁17-19;卷17,頁22。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了馬嘉理事件,朝廷終于認識到派遣外交代表更符合自己的利益,郭嵩燾才順理成章地奉命出使英倫。④有關郭氏出使以前的情況,如十年修約、日本侵臺和馬嘉理事件及其對朝廷決策派遣公使駐外的影響,詳見Immanuel C.Y.Hsu,China’s Entrance,pp.163-179.必須指出,直到此時此刻,萬國公法作為中外交涉的根本依據還沒有進入朝廷的視野——隨著中外交往的增加,總理衙門一方面表示愿意作一些相應的調整,另一方面還不忘強調“中外體制不能無異”,實際上是拒絕采用西方國際交往通行的規范;李鴻章雖然采取更為開明的態度,也只看到訂立和遵守條約在交涉過程中的作用。⑤關于總理衙門的態度分別見 《總署復英使中外體制不能無異照會》,《清季外交史料》卷2,頁28;《總署奏駐京使臣與部院大臣往來禮節未便置之不議片》,《清季外交史料》卷3,頁16-17。
郭嵩燾在同治二年 (1863年)九月至同治五年 (1866年)五月間曾任廣東代理巡撫,多次處理外交事件,比較重要的有與荷蘭互換條約,從香港引渡太平天國余部侯管勝等。用他自己的話說:“在粵處置洋務無不迎機立解”。但是他所依據的東西要么是不平等的雙邊條約,要么是“以理求勝”、“稍明洋情”等以往的交涉經驗。〔12〕雖然《萬國公法》恰好在這段時間翻譯刊行,但沒有證據表明郭氏在處理上述事件時有所運用。《萬國公法》在地方上的影響似乎遠不如外人預期的那么大。卸任以后連續八年賦閑在家,直到光緒元年(1875年)他才因文祥推薦奉詔進京,開始與任同文館總教習的丁韙良有所接觸。根據丁韙良回憶,有一次郭嵩燾拜訪他,問中國首應辦者為何事,丁氏回答在西方大國設置使館,后來郭嵩燾被任命為欽差大臣出使英國,令他感到非常驚異。〔13〕
光緒二年 (1876年)使英之前,郭嵩燾在日記中記下了與丁韙良的多次談話,有時是談論學問,有時是談公務,如商派出洋官學生。光緒二年二月,丁韙良把尚未出版的 《星軺指掌》譯稿拿給郭嵩燾看,此書專門論述公使、領事問題,是同文館正式翻譯的第一本國際法著作,郭氏認為其中第四十九、五十節“尤多見道之言”。這是兩人討論“萬國公法”的最早記錄。〔14〕光緒四年 (1878年)三月,郭嵩燾在巴黎還收到丁韙良寄來的新譯 《公法便覽》三部。〔15〕顯然不僅是交流學問的意思,而是希望郭氏在對外交涉時有所憑借。
出洋之前,郭嵩燾的文字中并不曾提及 《萬國公法》一書。但是可以肯定郭氏至少在出使期間對 《萬國公法》一書有仔細的研讀。光緒四年七月,郭嵩燾與萬國公法會學者討論公法學科史的時候,就指出對方所著 《公法論》中提到的克婁迪爾斯在丁韙良所譯 《萬國公法》中稱為虎哥。①即近代國際法的奠基者格老秀斯(Hugo Grotius)。《萬國公法》原文第一頁便指出“公法之學,創于荷蘭人名虎哥者。”他與爭梯立斯 (AlbericusGentilis)同為公法史上兩個最重要的人物,前者長在文獻整理,可以稱為考據學,后者長在發明義理,可以稱為性理之學。〔16〕考慮到郭嵩燾和他最親密的朋友都是湖南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郭氏對克婁迪爾斯的推崇可想而知。從日記可以發現,光緒五年 (1879年)六月十七日回到湖南省城長沙不久,郭嵩燾便從倫敦帶回的行李中找出 《萬國公法》一書,寄給老友朱克敬。〔17〕可見郭氏在出使期間,身邊就帶著這部書,或許正是由于他的推薦才激發朋友閱讀的興趣。②除去 《星軺指掌》《公法便覽》和 《萬國公法》,郭嵩燾參考的公法學著作,可能還有 《公法千章》。收到 《公法便覽》前一個星期,他在日記便提到“丁韙良譯 《公法千章》”。見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頁547。《公法千章》為丁韙良與聯芳、慶常合譯,1899年才由同文館出版。田濤認為可能譯自英國法學家霍爾(William Edward Hall)的 《國際法總論》(A Treatise on International Law,1880)。見田濤:《國際法輸入》,頁98。從時間上看這一推測顯然不合情理,郭氏不可能在1878年見到1880年才出版的英文著作之中譯本。
晚年郭嵩燾為丁韙良的 《中西聞見錄選編》作序,高度評價他對中西文化交流的貢獻,說他在同文館的工作“汲汲焉勤誨而不倦”,把他與首倡西學的利馬竇、著書尤精的偉勒亞力 (Alexander Wylie,1815-1887)相提并論,著重指出他對傳播西學的功績在“講明而傳習之”,“三人者相望數百年,號為博覽,而冠西 (即丁韙良)之功尤偉矣”。丁韙良能夠得到這樣的贊譽,顯然與他對萬國公法的推介有密切的關系。這篇序言的最后一句尤能表現郭對包括萬國公法體系在內的西方學問的看法——“西學之淵源,皆三代之教之所有事,而冠西之為人,為足任道藝相勖之資,為尤難能也。”〔18〕他強調的是西學與儒家的理想不僅不矛盾,而且有內在的契合。
有趣的是,郭嵩燾關于三代之禮和近代外交具有可比性的觀點在國際場合得到丁韙良的公開呼應。1881年丁韙良訪歐期間,曾在柏林召開的東方學學者大會上宣讀了一篇題為 《古代中國國際法遺跡》的報告,第一個把春秋時期的國家間關系規則與近代國際規則進行比較,認為中國古代有初步國際法存在。他還感嘆:“今所傳者,惟散見于孔孟之書,諸子百家之說,以及稗官野史之所記,而周禮一書最足以資考證。”〔19〕他和郭氏都肯定從 《周禮》中可以發現古代國際法的遺跡,是出于彼此影響,還是因為不謀而合,我們不得而知,但他們看法的契合至少可以說明,當時受中國文化熏陶的人容易把先秦時期的賓客之禮同公法放在一起考慮。我們可以發現,西方傳教士以及許多公法學家眼中的公法,同郭嵩燾這樣的儒者眼中的三代之禮,至少有三處共同點:一、都寄予著強烈的道德理想,雖然內容不盡相同(對前者來講是神意或者人類理性,對后者來講是三代圣王理想);二、都可作為現實社會中的實踐依據,盡管郭氏不得不承認,公法在西方有深厚的學術傳統,而且學術與政治形成良好的互動,而三代之禮在中國已近湮沒;三、無論作為道德理想,還是實踐依據,都具有普世價值,而不是屬于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專利。
三、郭嵩燾出使以后對萬國公法的認識
光緒二年閏五月,郭嵩燾完成 《擬銷假論洋務疏》,提出他在出使以前對外交比較系統的看法。此疏由于多觸忌諱,因而受人阻撓,最后并未奏呈。郭嵩燾在“自記”中說:“嵩燾時方求免出洋,以事勢且棘,謀遂以身任之……論次辦理洋務源流本末,以求解于人言。”〔20〕其中內容,我覺得啟發比較大的有兩條。第一是要有理可循:“理者,所以自處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審曲直,勢足而理固不能違,勢不足而別無可恃,尤恃理決折之……深求古今得失之故,熟察彼此因應之宜,斯之謂理。”第二是要“處之得其法”。中外交往的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處理得當,是難得的機會;處理不當,“往往小事釀成大事,易事變成難事,以致貽累無窮”。〔21〕
這里“理”是“法”的依托,“法”是“理”的體現,“理”的內容比較確定,主要是儒家的一整套價值觀念,落實到外交上即表現為誠信或忠信篤敬,也包括對歷史上的經驗教訓和對外交涉的規律性總結,但是“法”的具體內容是什么,標準是什么,郭嵩燾沒有給出答案,也許他本人當時仍在探索之中:畢竟三代之禮在中國已接近湮沒,對西洋列強也不具有約束力。提到辦理洋案,他已經知道“西洋公法,通商各國悉依本國法度”,但是面對當時的現實——“會審公所一依西洋法度以資聽斷”(即通商口岸領事裁判權的行使),卻仍然覺得“中國一切無可據之勢,惟當廓然示以大公”。〔22〕出國之后,通過閱讀公法著作、與各國官員和學者 (尤其是“萬國公法討論會”成員)交流,他對“萬國公法”才有進一步認識,后者一步步占據了他考慮外交問題的中心,并且和他對三代之禮的憧憬結合起來。
光緒二年十一月,使英途中李鴻章推薦的外籍隨員馬格里 (Macartney)與郭嵩燾談起“西洋交兵,不殺俘虜”等有關戰爭的國際法內容,郭氏頗有觸動,以為“即此足見西洋列國敦信明義之近古也”。〔23〕“敦信明義”是肯定其合理性,“近古”是講符合中國上古(三代)的理想。
同年十二月六日,抵達倫敦前兩天,郭嵩燾在日記中第一次正式提到“萬國公法”的創立,他說:“近年英、法、俄、美、德諸大國角立稱雄,創為萬國公法,以信義相先,尤重邦交之誼。致情盡禮,質有其文,視春秋列國殆遠勝之。”〔24〕首先強調的是它的道德基礎,在他看來,萬國公法不僅符合儒家的理想,而且條文詳細、內容豐富,與他曾經盛贊的“春秋列國以禮相接”比起來代表更高的水平。按照今天的說法,這是一種合法性的認同,用來排除中國朝廷和士大夫接受它的心理障礙。耐人尋味的是,這段話出現在根據總署要求寄回去以供參考的 《使西紀程》上,同一天的私人日記卻沒有相應的內容。他是有心利用這樣一個機會向朝廷介紹他對萬國公法的認識。
到達倫敦以后,由于所攜國書并無充當公使文據,也沒有列上副使劉錫鴻的姓名,引起一些不方便,光緒三年(1877年)二月,郭嵩燾上表朝廷說明情況,指出:“竊查西洋公法,遣派公使駐扎各國,皆以國書為憑。”就在這一奏疏中,郭嵩燾進一步闡明看法:“西洋以邦交為重,蓋有春秋列國之風,相與創立萬國公法,規條嚴謹,諸大國互相維持,其規模氣象實遠出列國紛爭之上。日本一允通商而傾誠與之相結,誠有見于保國安民之計,于此有相維系者。”這是目前所見郭氏奏稿中第一次直接出現“萬國公法”的字樣。事實上有向朝廷大膽進言建議接受萬國公法體系作為處理國家間關系的基本準則,而不再把它當作傳統體制內一個御夷工具的意思。郭氏不僅承認公法的道德基礎,而且強調它的實際效用,能夠給列國紛爭提供一種秩序;雖然源于西洋,但是可以為我所用,日本被接納就是一個榜樣。①郭嵩燾:《國書并無充當公使文據清改正頒發折》,《奏稿》,頁365。郭氏一到倫敦,就與日本駐英外交官有交往,對日本學習西洋的成就有深刻印象。見 《倫敦巴黎日記》,頁108,129,136。
總署接到奏折后卻沒有對郭氏有關萬國公法的主張作出直接響應,只是就事論事,表示:“知照內閣,一律頒給敕書,以昭慎重。此后奉使有約各國大臣應即照此辦理。”至于副使劉錫鴻,則改派出任駐德公使。〔25〕李鴻章在三月二十六日給郭嵩燾的信中就此評論:“欽差大臣從此裁去副使名目,而藉聯德之交,實屬一舉兩得。”〔26〕頒授國書一事說明清政府雖然不很主動,但還是接受國際慣例,裁去副使,或許更有意義。傳統上,清朝向藩屬國派遣欽差大臣,宣示皇恩浩蕩,往往是一正一副兩個人,而西洋外交制度向無此例。朝廷的反應說明中國雖然不很積極,不很主動,還是逐漸地拋棄朝貢體制的殘余,接受近代外交的規則。
光緒三年八月,萬國公法討論會給郭嵩燾寄來材料,這是有記載的雙方第一次接觸。②以下關于萬國公法會與郭嵩燾的接觸,參考了張建華:《郭嵩燾與萬國公法會》,《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1期,頁280-295。郭氏在日記中指出“此會為修改萬國公法,以臻妥善”,并對材料內容有如下描述:“大抵言各國習教不同,不能以習教之同異分別輕重,一當準情度理行之。所以見示,亦自表其于中國無猜嫌也。”材料英文原文如何,我們不得而知,但是如前文所述,“準情度理”四個字正與郭氏處理外交的一貫思路相契合;“不以習教之同異分別輕重”,則是強調公法雖然起源于歐洲基督教國家之間,卻代表普遍的公平和正義,非基督教國家也應該得到公平對待,因此是真正的“萬國公法”而非“西洋公法”。這一點當時有關國際法譯著均未提到。丁韙良譯《萬國公法》還有意加強其基督教色彩。直到1880 年 《公法會通》譯出,才明確肯定:“公法雖出于泰西奉教諸國,而始行于西方,然不局于西方,亦不混于西教……蓋公法不分畛域,無論東教西教,儒教釋教,均目為一體,毫無歧視也。”①《公法會通》卷1,第5-7章,轉引自田濤:《國際法輸入》,頁75-76。此書原作者為德國法學家步倫 (J.C.Bluntschli,后譯為伯倫知理)。郭嵩燾還提到公法會中人認為英印政府應對馬嘉理案承擔責任,“其言多公平如此”,考慮到郭氏正是因此事而出使,之前對英國公使威妥瑪的咄咄逼人又多有領教,他心中的感受可想而知。〔27〕
光緒四年二月,郭嵩燾從日本公使那里知道八月份將在德國舉行第六屆萬國公法會年會:“各國交際,輕重得失,反復較論,以求協人心之平,而符天理之宜。西洋諸國所以維持于不斷,皆由學士大夫酌情審義,相與挾持于此間,所以為不可及也。”日本公使還提議“中國與日本于此尤應考求,必應一往會議。”〔28〕以后更幾番熱情相邀,商談有關事宜。通過日本公使的引薦,郭嵩燾與公法會中人有了直接的來往。他逐漸得出結論:萬國公法是各國學者反復辯難討論的產物,具有深厚的學理基礎,與儒家的人心天理之說不僅不矛盾,而且頗為契合;同時受到西方各國政府的尊重,一經采用,就有普遍的約束力,戰爭期間也不例外。〔29〕
七月,郭嵩燾正式接受萬國公法會的邀請,派正在法國學習公法的馬建忠②李鴻章獲悉郭兼任法使后,向他推薦此人。見李鴻章:《正月二十六日覆郭筠仙欽使》,《朋僚函稿》,卷20,頁5。為代表參加在德國法蘭克福的集會。〔30〕八月,郭嵩燾還在倫敦親自旁聽了公法會對法蘭克福大會所議各條款的討論,感慨:“其議論之公平,規模之整肅,使人為之神遠……惜中土列國時無此景象,雖使三代至今存可也。”〔31〕在他看來,這就超越了春秋列國的水平,三代的賓客之禮終于找到了現實的依托!法蘭克福大會也的確向中國提出一些忠告:
一、為與亞細亞不同教之國相接,當另立章程,其中小有變更,亦當與亞細亞不同教之國相接,不宜專任歐洲之意為之;一、東方各口領事干與地方公事,為必不宜;一、從前論公法交際宜持平者數家,當使之盡意,條議其便利, 以便推求。〔32〕
這些內容已經觸及不平等條約的基礎和重要條款 (如領事裁判權),有助于中國爭取平等待遇,因此受到郭氏的重視,其中第一條尤其反映了法學家超越強權政治、包容文化和宗教差異、使公法成為各國平等交往的普遍依據的愿望,直到今天也是國際關系中值得追求的理想。需要指出的是,當時主要的國際法譯著如 《萬國公法》,乃至 《公法會通》都肯定列強的領事裁判權。〔33〕與公法會的接觸肯定為郭嵩燾限制領事裁判權的努力提供了新的動力。
除了參與這些交流活動外,郭嵩燾還對萬國公法學科的發展表現出濃厚的興趣,他在光緒四年七月到九月很短的時間里面就先后研讀了屠威斯(Travers Twiss)所著 《公法論》③當為他于1856年在倫敦出版的著作 《兩篇介紹國際法學的演講稿》(Two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Law)。見田濤:《國際法輸入》,頁186。二篇和傅蘭雅(John Fryer)所譯費利摩(R.J Phillimore)著 《萬國交涉公法論》(Commentaries Upon International Law),并且罕見地在日記中留下大段心得體會。〔34〕當時馬建忠在巴黎政治學院專習公法,郭氏不厭其煩地向他仔細詢問有關課程,總結經驗教訓,并作詳盡的記錄。〔35〕
直到光緒五年閏三月,郭嵩燾已經卸任回國,萬國公法會還給他寄來書籍一包,以供閱讀。〔36〕與萬國公法會的接觸,使郭嵩燾感到在萬國公法里面可以找到中國所需要的公平和正義。
當時歐洲正值俄土戰爭 (1877-1878),俄國咄咄逼人,土耳其無力自保,卻得到英法的支持。④1877年,俄國以解放巴爾干斯拉夫人為由,對土耳其作戰,一度兵臨君士坦丁堡,卻由于英國干涉,未能占領首都和黑海海峽。1878年,英、奧反對俄土和約建立由俄國控制的大保加利亞等條款,發起柏林會議,迫使俄國讓步。郭嵩燾非常注意局勢的發展,他在日記中提到俄、奧、德三國“私相定約”:“五大國各駐兵土境,迫令土人改易制度從西洋,保民制國,諸國皆得與聞。”——這正是清廷最怕落到自己頭上的命運。但是遭到英國反對,理由是“土耳其亦自立之國,萬國公法無相逼脅之理”〔37〕郭氏未嘗不知道英國同俄國爭霸的實質,卻仍為表面的理由所吸引。我們可以以前述 《擬銷假論洋務疏》中對理勢關系的闡發來考慮這個問題。在郭氏眼中,萬國公法體現了國際關系中的“理”,而英俄爭霸則是“勢”的一種,像土耳其或者中國,實力不濟,只有堅持以萬國公法為依據才能得理,化被動為主動,進而利用客觀形勢爭取外國援助,在危急關頭保障自己的生存。①丁韙良譯 《萬國公法》便用土耳其接受公法與各國訂約以保障自主的例子,暗示中國接受西方國際法體系,很可能影響郭氏的判斷。見 《萬國公法》,頁469。另見田濤:《國際法輸入》,頁50-51。
光緒五年 (1879年)歸國途中經過列強在東南亞的殖民地,郭嵩燾的想法已不像來時那么樂觀,西方的擴張野心令他憂心忡忡,但是出使期間的經歷使他得出結論:“歐洲大小各國皆守萬國公法,其勢足以自立”。〔38〕在他看來,接受“萬國公法”是弱小國家主權和獨立的保障。
到光緒十年 (1884年),他批評左宗棠對法開戰“一勞永逸”的主張,第三次講到萬國公法的創立,“西洋積強已數百年,而慎言戰,擬定萬國公法,以互相禁制。”〔39〕他覺得當時最緊迫的問題是維持和平,而萬國公法則提供了一套不須訴諸武力而通過協商談判解決爭端的規則。隨著認識深入,我們可以看到郭氏對“公法”作用的闡發逐漸由高調轉為低調,但是他運用“公法”為中國爭取和平的基本信念并未動搖。
四、余論:郭嵩燾與近代中國肯定國際法的潮流
田濤 《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一書令人信服地指出,中國的傳統文化并沒有成為人們接受西方國際法的阻礙,相反,人們從傳統的王道政治理想和禮治原則出發很快便承認國際法的規范具有普遍正義性、國際法體系包含了理性的精神,從而自始至終對國際法維持肯定性的評價。他把晚清讀書人接受國際法的過程分為兩個階段,即19世紀下半期和20世紀初,認為郭嵩燾是前一階段,尤其是洋務時期思想家中全心全意肯定國際法的代表人物。〔40〕
對田書的結論,尤其是其中關于郭嵩燾的論述,我覺得有兩點需要補充:第一,如果說接受“萬國公法”逐漸形成一種時尚潮流,那么郭嵩燾便是這股潮流最初、最有影響和最堅定的倡導者。第二,郭嵩燾雖然是中國讀書人接受“萬國公法”的倡導者之一,他卻比大多數后來者對“萬國公法”有更深入的了解,因此與這股潮流實際上存在距離。
為什么說郭氏是中國人接受國際法最有影響、最堅定的倡導者?最有影響,因為與王韜、鄭觀應不同,郭嵩燾不是在殖民地或通商口岸活動的“邊緣人”,而是進士和翰林出身,屬于傳統社會的精英階層,他起來號召接受西法所產生的示范作用和遇到的阻力,遠非搞洋務出身的人可以比擬。②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率先盛贊“萬國公法”的出使日記 《使西紀程》寄回國后,由同文館出版,很快便因為保守士大夫的強烈反彈,被勒令毀版,卻因為由上海 《萬國公報》連載而廣為傳播。
最堅定,是因為郭嵩燾與晚清官僚體制中的大多數人相比更愿意接受“萬國公法”的普遍約束力。郭氏離任以后,萬國公法會繼續與新任公使曾紀澤保持來往。田濤認為曾氏對國際法表現了同樣的興趣和熱情。〔41〕在我看來,并非如此。根據曾紀澤光緒五年五月十四日的日記:
萬國公法會友土愛師 〔即前引郭嵩燾日記“屠威斯”〕來,談極久。言東方諸國未入公法,會中人深愿中國首先倡導云云。余答以中國總理衙門現已將 《公法》一書擇要譯出,凡遇交涉西洋之事,亦常征諸 《公法》以立言,但事須行之以漸,目下斷不能錙銖必合者。公法之始,根于刑律,《公法》之書,成于律師。彼此刑律不齊,則意見不無小異。要之,公法不外“情理”兩字,諸事平心科斷,自與公法不甚相悖。至于中國之接待邊徼小國、朝貢之邦,則列圣深仁厚澤,乃有遠過于公法所載者。西洋人詢諸安南、琉球、高麗、暹羅、緬甸之人,自能知之。③曾紀澤:《曾紀澤日記》,岳麓書社,1998,頁890。本文作者根據文意對標點作了調整。
從字面上看,曾紀澤的主張即處理中西關系大體上以“萬國公法”為依據,在東亞則繼續維持朝貢體制,“萬國公法”并不適用。即使當作中西交往的依據,曾紀澤對公法的態度也不能與郭嵩燾相比,他對公法的基本定位是刑律而不是禮法,更不是大經大法,把公法化約為“情理”,也不免會對章程本身重視不夠。這段話曾經被廣泛引用來說明曾紀澤對公法的態度。實際上,日記中還有其他的說法存在,三個月前 (三月十四日,是年閏三月),曾紀澤與日本駐英公使談及朝鮮和琉球問題,指出:
西洋各國,以公法自相維制,保全小國附庸,俾皆有自立之權,此息兵安民最善之法。蓋國之大小強弱,與時遷變,本無定局。大國不存吞噬之心,則六合長安,干戈可戢。吾亞細亞洲諸國,大小相介,強弱相錯,亦宜以公法相持,俾弱小之邦足以自立,則強大者亦自暗受其利,不可恃兵力以凌人也。〔42〕
這里曾氏似乎認為亞洲諸國相處也應該引入公法。前后兩段話結合起來我們便可以看出,其實曾紀澤對公法并沒有固定的立場,他害怕西方引用公法挑戰中國對藩屬的宗主權,便宣稱公法在東亞并不適用,但是,面對日本的擴張野心,他又期望引用公法加以限制。總之,公法在他看來只是維護朝貢體制的工具。曾紀澤與洋人打交道經驗豐富,又懂英文,尚且如此,可以想見當時朝廷和士大夫主流對公法的接受程度。
郭嵩燾一開始就意識到朝貢體制與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出使之前他已經提出辦理洋務要改弦更張,當時他的理想狀態還沒有超出“春秋列國以禮相接”的水平。出使之后,對以西方為主導的國際社會的運行機制的觀察和接觸,與萬國公法會中人的交流,都使他的想法發生很大變化。他不僅自覺地運用萬國公法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爭取平等待遇,而且在思想上認同萬國公法的權威,承認它的普遍約束力,認為與春秋列國交聘相比萬國公法更加符合“三代之禮”的精神。與保守派和清流黨不惜利用排外情緒使用武力捍衛傳統體制不同,郭嵩燾認為無論如何都要維持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與李鴻章等洋務派官僚處理外交只會依據“情理”和條約不同,郭氏發現光靠“情理”不夠,還必須有雙方共同遵循的法則,這個法則不應是外國強加的不平等條約,而必須是體現普遍道德理想的“萬國公法”。①包括李鴻章和總理衙門官員在內的當權者,對國際法的基本內容和背后的學理并無真正的了解,也不曾嘗試這么做。“萬國公法”只被看作是防止洋人提出進一步要求的工具,而不被用來積極恢復中國失去的權利;只有對外交涉的意義,而不具備內在的約束力。
郭嵩燾對國際法體系的過高估計顯而易見。依據公法交涉要憑借對手自律和國際輿論發生作用,最終依靠的是道義的力量,在十九世紀晚期那個霸權主義、帝國主義橫行的時代影響無疑是有限的。②在列強看來,國際法是適用于歐美“文明”國家之間的法律,他們在對華交涉的時候依據的不是國際法的原則和規則,而是不平等條約。直到1948年大名鼎鼎的 《奧本海國際法》還認為:“中國的文明尚未達到使它的政府和人民在各方面都了解并遵行國際法準則必要的程度。”《奧本海國際法》,卷1,1948,頁46-47。轉引自朱奇武:《中國國際法》,頁42。然而我們的分析不能到此為止。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外交面臨的基本問題之一是從以天朝禮儀為紐帶的朝貢體制轉入以國際法為基本架構的近代西方條約體系。這一過程曲曲折折,反反復復,伴隨著許多陣痛,先前中國人幾乎完全沒有類似的經驗,所謂“春秋國際公法”,去時已遠,而且其內容及思想支撐與近代國際法大相徑庭。③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國際法淵源可追溯到春秋列國,如前所述,丁韙良就是一個代表。見洪鈞培:《春秋國際公法》,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但是,郭嵩燾在接受這一體系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將“萬國公法”看作是三代之禮的現實依托,他不僅為處理當時的中外關系找到了根據,也在西學的資源和中國的傳統之間建立起有機聯系。
最后解釋為什么郭嵩燾與晚清接受公法的潮流實際上存在距離。郭氏對國際法的思考與十九世紀后半期的主流,無論是洋務派還是維新派,都有本質區別。其一,郭嵩燾在“萬國公法”中發現的道德理想,既是對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時代強權政治的否定,也是對傳統中國朝貢體制的否定。在他看來,從三代延續到春秋的理想的國際交往模式在漢唐以后已經日趨墮落,鴉片戰爭以來,清朝政府的一系列對外政策不僅是失敗的,而且在道義上也站不住腳。所以,接受“萬國公法”必須對華夏中心觀念以及排外和仇外的傳統作深刻的反省。而大多數讀書人心目中的王道政治擺脫不了朝貢體制的影子,他們肯定的是過時的制度而不是批判性的理想,骨子里是守舊多于前瞻。
其二,郭嵩燾既重視公法背后特殊的歷史淵源,也重視其具體條文。他明白儒家和公法的最后理想都是天下大同,但是出發點并不相同,前者相信等差,而后者卻立足于主權平等。大多數讀書人往往只看重“大同”而忽略“小異”,甚至用抽象的情理架空具體條文。原因并不復雜:他們在擁抱公法之前,往往只是讀過二手的介紹,至多讀過傳教士的譯文,而后者有些地方刻意迎合中國人的需要,有些地方從基督教的觀點出發,具有高度的選擇性,對人們全面了解公法無疑是有缺陷的。甚至可以說,吸引許多人的不是公法的原意,而是其譯文中對中學的比附。郭氏不僅詳細地研究過有關譯著,而且從萬國公法會和留學生那里了解到學術前沿的知識,又有運用公法與西方政府打交道的直接經驗,因此對公法的復雜性有更多了解。
其三,關于國際法的實際效力問題,與國內讀書人不同,郭氏有較為清醒的認識,而并不被理想主義沖昏頭腦。田濤引用郭嵩燾對“萬國公法”的評價并不全面,基本上是他早期的文字。〔43〕實際上,面對強權政治和國內應付失當,郭氏對“萬國公法”的期待逐漸由高調轉向低調,早期他希望能夠以“萬國公法”為基礎,在中西之間建立起長遠的和平合作關系,后來則主要希望以“萬國公法”作為中外談判解決矛盾、防止戰爭的管道。他逐漸明白國際政治里面理想與現實并存,國際法的條文里面,同樣也是理想與現實并存,不能因為現實而否定理想,也不能因為理想而無視現實,否則一定會在交涉中吃虧。國際法也好,整個外交也好,都只是維護國家權益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改變不了國家積弱的現實,盡管其成功運用可以在既定的實力之限制下,為國家減少一些損失,乃至為內政改革創造較好的外部環境。晚清一般讀書人對“萬國公法”寄予了不切實際的期望,彷佛一經接受,便找到為萬世開太平的良方,而不需要對傳統文化進行苦痛的反省,對內政進行積極的變革。這樣,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徹底否定國際關系中的理性精神,接受強權即公理,也就其來有自了。
參考文獻:
〔1〕郭嵩燾.奏參岑毓英不諳事理釀成戕殺英官重案折附上諭 〔A〕.郭嵩燾奏稿 〔C〕.楊堅輯補.岳麓書社,1982.347 -349.
〔2〕鄭玄,孔穎達.禮記正義 〔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1442-1445.
〔3〕郭嵩燾.禮記質疑 〔M〕.岳麓書社,1992.628-629.
〔4〕郭嵩燾.中庸章句質疑 (下)〔M〕.長沙:養知書屋光緒十六年刻本.8上.
〔5〕孟子集注 〔A〕.四書集注 〔C〕.岳麓書社,1997.491-492.
〔6〕王夫之.四書箋解·中庸 〔A〕.船山全書 〔C〕.岳麓書社,1991.144.
〔7〕中庸章句 〔A〕.四書集注 〔C〕.岳麓書社,1997.43.
〔8〕大學章句 〔A〕.四書集注 〔C〕.岳麓書社,1997.15.
〔9〕郭嵩燾.大學章句質疑 〔M〕.長沙:思賢講舍光緒十六年刊本.25上、26上.
〔10〕Immanuel C.Y.Hsu,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118.
〔11〕王鐵崖.中國與國際法:歷史與當代 〔A〕.王鐵崖文選 〔C〕.鄧正來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298;中國大百科全書·法學卷 〔M〕.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4.192.
〔12〕郭嵩燾.玉池老人自敘 〔M〕.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9.64-67.
〔13〕郭廷以,等.郭嵩燾先生年譜 〔M〕.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478.
〔14〕〔15〕〔16〕〔17〕〔23〕〔24〕〔27〕〔28〕〔29〕〔30〕〔31〕〔32〕〔34〕〔35〕〔36〕〔37〕〔38〕郭嵩燾.倫敦與巴黎日記〔M〕.岳麓書社,1984.6、16、18,555,676,1009,59,91,302,506,524、553、589,690、697、700,719,724-725,675-676、746-748,704-707,965-996,465,954.
〔18〕郭嵩燾.郭嵩燾詩文集 〔M〕.楊堅點校.岳麓書社,1984.68.
〔19〕洪鈞培.春秋國際公法 〔M〕.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5.4-5;王鐵崖.王鐵崖文選 〔M〕.鄧正來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3.276-278;田濤.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 〔M〕.濟南出版社,2001.79-81.
〔20〕〔21〕〔22〕郭嵩燾.郭嵩燾奏稿 〔M〕.岳麓書社,1982.362,359,361.
〔25〕總署奏請補發使英郭嵩燾等敕書折附上諭 〔A〕.王彥威,王亮.清季外交史料:卷9〔C〕.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3.27.
〔26〕李鴻章.三月二十六日覆郭筠仙欽使 〔A〕.朋僚函稿:卷19〔C〕.臺北縣:文海出版社,1963.5.
〔33〕〔40〕〔41〕〔43〕田濤.國際法輸入與晚清中國 〔M〕.濟南出版社,2001.47-48、76,356-357,124,169-171.
〔39〕郭嵩燾.再致李傅相 〔A〕.郭嵩燾詩文集 〔C〕.楊堅點校.岳麓書社,1984.219.
〔42〕曾紀澤.曾紀澤日記 〔M〕.岳麓書社,1998.859.
(責任編輯:趙榮華)
[收稿日期]2016-05-06
[作者簡介]范廣欣,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研究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