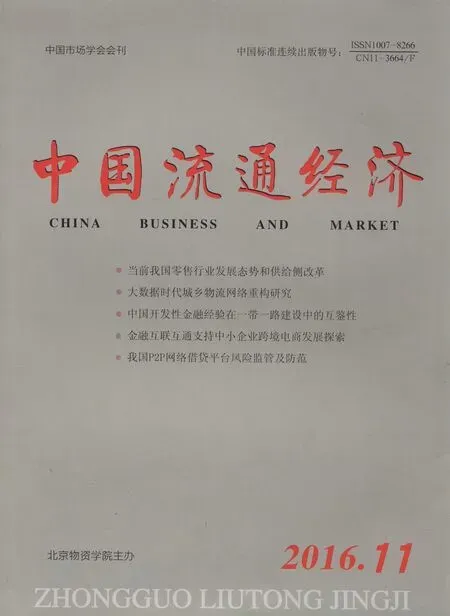中國開發性金融經驗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互鑒性
姜安印,鄭博文
(蘭州大學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00)
中國開發性金融經驗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互鑒性
姜安印,鄭博文
(蘭州大學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研究中心,甘肅蘭州730000)
中國開發性金融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為中國經濟發展注入了強大動力。總結中國開發性金融的實踐經驗,不僅有助于重新認識開發性金融在中國金融市場中助力實體經濟發展的作用機理,同時也是“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充分借鑒中國開發性金融的經驗,實現共贏發展的現實需要。中國開發性金融的實踐經驗,一是創新了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機制;二是彌補產業升級和民生社會事業發展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三是利用規劃理念為金融支持區域發展和國際合作提供科學路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可借鑒和應用中國開發性金融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形成的投融資機制、開發性金融的市場培育模式等。
“一帶一路”;開發性金融;中國經驗;互鑒
一、引言
2015年6月,習近平主席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儀式上發表主旨演講,在祝賀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協定簽署的同時,充分肯定了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多邊開發銀行在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支持,并表示中國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也愿意在國際舞臺上發揮更大的作用。既肯定了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在過去30多年中利用自身融資優勢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做出的貢獻,同時也向世界說明,中國在獲得國際支持的同時,已經探索和總結出一整套不僅適用于中國,同時可以向世界各國展示和利用的經濟發展理念和模式。開發性金融(Development Financing)在中國產業成長和體制成長中的獨特作用,不僅是這些經濟發展理念的代表之一,而且作為連接政府和市場的重要橋梁,也為后發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一定的啟示。
近年來,在金融危機的影響下,各國政府在推進一系列關鍵性戰略目標中,對開發性金融的重視程度不斷提高,這其中包括利用開發性金融維持金融體系穩定,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技術換代升級,籌集中長期融資,培育各類產業的前沿市場等等。但開發性金融作為一種較為先進的金融工具,各個國家對其金融運作的原理和主要功能的認識還存在差異。過去幾十年曾經出現過部分國家開發性金融機構在政府支持的背景下,主動與他國開發性金融機構進行資金實力比拼,謀求官方信用支持以提升信貸額度,忽視債務人、債權人經濟實力和政治風險的情況,造成金融領域的“軍備競賽”。[1]中國的開發性金融也走過了一個逐步探索運作方式、贏利模式和風險管理制度的過程。國家開發銀行從1994年成立至今,在為“兩基一支”(即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提供長期建設資金支持的同時,建立起一整套完整的投融資體制機制,通過市場化運作不僅緩解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一些瓶頸制約因素,而且還幫助完成了一些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建設和重點產業的市場培育,加深了同周邊地區的經濟合作,獲得了部分發展中國家的理解和認同。
“一帶一路”發展倡議提出至今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果,目前已經有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參與其中,30多個沿線國家簽署了共建“一帶一路”合作協議,20多個國家已經開展國際產能合作,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絲路基金為代表的金融合作不斷深入,“一帶一路”發展倡議進入實質性的落實階段。要真正實現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在具體的操作層面,既需要考慮不同國家之間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民情等在內的各種地緣性差異,同時還需要找到能被沿線國家普遍接受和認同的開發模式及合作途徑。作為中國發展經驗的典型代表,開發性金融在國內國際的實踐經驗和特點是否能夠成為滿足這些普適性要求的金融形式,并轉化為這些國家可實際操作的模式,需要對中國開發性金融的特點和運作機理加以深入分析。
鑒于此,本文擬在對開發性金融理論研究進行梳理總結的基礎上,通過對中國開發性金融支持中國基礎設施建設、推動產業轉型升級、統籌區域協調發展、實現國際合作互利共贏等方面發揮作用的體制機制及其原因進行總結,進而探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中國開發性金融模式中可以借鑒的經驗。
二、開發性金融研究文獻述評
縱觀國內外開發性金融理論研究的軌跡,開發性金融的研究基本來源于對政策性金融研究的不斷演化和深入,研究內容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開發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的關系,由此對開發性金融的概念進行界定。二是開發性金融的功能作用,即開發性金融如何通過自身的準公共性特征,在推動工業化、城市化、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平抑經濟周期波動等方面發揮作用。
從國外學者的研究來看,目前還沒有對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的內涵和外延等內容進行比較分析的文獻。從現有文獻看,國外學者大都將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合并成一個概念進行分析研究。他們的研究主要側重于從產業轉移、信息經濟學、交易成本理論等領域出發論述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為什么存在及其作用和效果。例如,美國學者查莫斯·約翰遜(Chalmers Johnson)[2]和齊斯曼(John Zysman)[3]通過研究一致認為,政策性金融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戰略工具。而齊斯曼在約翰遜的基礎上通過研究認為,一個國家的政府憑借政策性金融機構,在國家戰略高度上可以將資金連續地從傳統部門向新興部門進行配置轉移。還有一些學者從信息經濟學理論出發,對政策性金融存在的必要性進行分析。斯蒂格利茨和維斯(Joseph Eugene Stiglitz&Andrew Weiss)[4]站在“逆向選擇”角度進行討論,發現由于金融市場上信息不對稱,自由競爭市場上的“信貸配給”可能成為一種長期均衡現象,造成一些市場上的主體很難得到融資機會,因此需要政府進行介入引導,而政策性金融恰好是政府介入引導金融市場的一種重要形式。威廉姆森(Oliver Eaton Williamson)[5]則從“道德風險”的角度加以分析,認為在降低市場交易成本、緩解信息不對稱和幫助提高社會福利等方面,政策性金融有特殊優勢。此外,許多日本學者對二戰后日本經濟快速增長背后財政投融資的功效進行了實證分析,認為政策性金融可以分為直接功效和間接功效。直接功效是指借助政策性金融貸款,可以提高企業獲得資金的可能性,同時通過政策性金融的低利率帶來的補助功效;間接功效是指政策性金融的貸款行為所產生的誘導效應。[6]在直接功效方面,小椋正立、吉野直行[7]提出的以日本開發銀行為代表的政策性銀行,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為日本基礎產業提供大量資金扶持的同時,也對農業、中小企業等弱質行業進行了補助和保護。在間接功效方面,東京大學的日向野、崛內大原[8]等認為,因為信貸市場中的信息不對稱現象,開發性金融機構憑借不以利潤最大化為行動原則介入金融市場后,就可以緩解這種信息不對稱現象,提高整個金融市場的資金配置效率,同時通過對民間金融機構融資的誘導作用,促進主導產業的發展。
從國內學者的研究來看,近20年對開發性金融研究的理論成果不斷得到豐富。其中在開發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關系的研究上,理論界有三種認識。一種主要分析開發性金融與政策性金融的關系,例如,陳元[9]和其當時所領導的國家開發銀行[10]認為,政策性金融是較為低級的開發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是對傳統政策性金融的發展,而李揚[11]、林勇和張宗益[12]認為,開發性金融是政策性金融的有機組成部分,政府參與本身就說明開發性金融具有明顯的政策傾向性,應當屬于政策性金融范疇。另一種著力于開發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三者之間的關系分析,例如,以白欽先、王偉[13]為代表的學者認為,開發性金融以性質區分,應分為開發性政策性金融和開發性商業性金融,張朝方、武海峰[14]則認為,開發性金融是兩個集合即政策性金融范疇和商業性金融范疇之間的交集部分,是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之間相互融合產生的金融形式。第三種則完全不同于以上兩種觀點,李志輝、王永偉[15]認為,開發性金融是一種獨立的金融形態,它不同于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會利用融資推動制度和市場建設,從而達到一國政府希望實現的特定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的資金融通方式。陳元[9]12在總結開發性金融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關系時,對之前的認識進行了深化,認為開發性金融不是政策性、商業性的機構屬性問題,而是一種金融方法。袁樂平、陳森[16]將以上三種觀點總結為三種金融形式間的包含與被包含關系、交叉關系和并列關系,提出在理論上應跳出政策性金融框架思維,在投融資期限結構上重新考慮開發性金融和傳統金融之間的互補關系。盡管對這三種關系的研究理論界尚未達成一致,但隨著國家開發銀行金融實踐活動的不斷深入,尤其是自2008年以后,整個理論界對于開發性金融的內涵和外延的認識開始逐步向國家開發銀行定義的內容靠攏。這一概念包含三個核心要素,即特定的主體、特定的任務和特定的目標。所謂特定的主體,即在一個國家或者某個國家聯合體中建立的某些具有國家信用特征的金融機構;特定的任務就是在金融市場上,不僅要為某些特定需求者提供中長期融資,而且還憑借建設市場和健全制度的方式,同時推動市場主體和自身業務的發展;特定的目標就是加快經濟發展,促進經濟長期增長,實現其他政府目標的一種特殊金融形式。
在開發性金融的功效研究方面,部分研究者如溫守義[17]、高媛媛[18]、何江[19]等通過對開發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的關系分析,認為開發性金融實際上是在延續政策性金融的扶植功能、逆向選擇功能、誘導性功能、擴張性功能、補充性功能和專業性服務與協調功能。還有一部分專家學者從開發性金融具有的獨特性角度出發進行分析,認為除了具有上述功能外,開發性金融還具有彌補政策性金融缺陷功能、有效運用和放大政府信用在市場建設中的功能、連接政府和市場的橋梁功能、規劃指導功能、平抑經濟周期波動功能以及風險防范功能等[15,9]15,12。還有眾多學者針對開發性金融的這些功能在推進城市化建設、國家高新產業區發展、中小企業發展以及政策性金融機構轉型升級等方面具體的運作機理進行了研究。近期的研究文獻主要集中在開發性金融在“一帶一路”建設中如何發揮作用、建設的重點合作等領域。
通過對已有文獻的梳理,開發性金融作為我國經濟發展領域一項重要的金融形式,其獨特作用已經得到了理論界的廣泛認可,但針對開發性金融理論和實踐的研究仍在不斷深入,尤其是開發性金融在國際合作和開發中的作用以及在區域合作中的可借鑒模式仍需不斷探索。
三、中國開發性金融取得的成果
中國開發性金融發展的歷史,從實踐來看,實際上就是國家開發銀行在政策性銀行的基礎上不斷改革,逐步向開發性銀行轉變的歷史。1998年之前,國家開發銀行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同屬國家政策性銀行。由于宏觀經濟、自身管理體制以及成立時承接的政策性項目效益較低等問題,其1997年的不良貸款率一度高達40%。1998年以后,國家開發銀行通過三次信貸改革、重組接收以及探索建立市場機制等一系列舉措,逐步開始向開發性金融機構轉變,自身實力不斷增強,到2015年底,已經發展成為總資產超過12.62萬億元、凈利潤達到1 027.88億元、發行債券余額超過6.69萬億元、不良貸款率僅為0.81%的全球最大的開發性金融機構。①更值得關注的是,國家開發銀行在開發性金融領域的不斷探索和實踐,不僅為化解中國城市化發展、產業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等領域存在的瓶頸因素提供了解決路徑,同時也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開發性金融理論和實踐模式。
(一)為城鎮化建設提供大量資金,助推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國家開發銀行第一個使用開發性金融支持城市化建設的項目始于安徽蕪湖。1998年,國家開發銀行與安徽省政府簽署投融資合作協議,為蕪湖建投提供10.8億元十年期貸款,用于包括公路建設、城市供水系統改善和廢物處理填埋場建設等在內的6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經過13年的資金運作,蕪湖市基礎設施完備的區域從1998年的38平方公里擴展到2012年的150平方公里,形成了“四縱十橫”的交通網絡,躍升為安徽省經濟、文化、交通的次中心。這種將國家開發銀行融資優勢與地方組織協調優勢結合起來推進城市化建設的模式成為國家開發銀行推動城市化建設的“蕪湖模式”。之后,國家開發銀行開始與多個城市合作,全力推進各地城鎮化建設,圍繞軌道交通、機場建設等傳統行業,拓展市政管網、醫療健康、智慧城市等領域,促進城鎮化發展模式提升。截至2015年末,國家開發銀行公共基礎設施行業貸款余額達到人民幣1.19萬億元,為完善城市服務功能、提升城市承載能力、推動新型城鎮化發展提供了充足的資金支持。同時,國家開發銀行為鐵路、公路、電力、農林水利等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項目提供了充足的資金保障,截至2015年末,國家開發銀行鐵路行業貸款余額達到人民幣7 209億元;公路行業貸款余額達到人民幣1.56萬億元;電力行業貸款余額達到人民幣7 831億元;水利行業貸款余額達到人民幣3 112億元。龐大的資金投入,不僅帶動了中國不同區域之間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同時也帶動了相關產業的轉型升級。
(二)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資金保障,助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
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升級是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途徑和主要內容,國家開發銀行圍繞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重點行業、重點領域,發揮開發性金融的獨特作用,為自主創新產業、綠色環保產業、節能減排產業、高新技術產業、文化產業等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在包括奇瑞汽車、比亞迪電動汽車、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敦煌月牙泉治理工程、太湖水污染治理、蘇州河治理、三峽工程、生物制藥、移動通信4G標準研制、文化產業基地、電影院線建設,以及廣東、福建、遼寧的核電工程在內的多個項目中,國家開發銀行投資金額均超過千億元,為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發揮了重要作用。僅2015年,國家開發銀行就發放戰略性新興產業貸款2 530億元。截至2015年末,綠色信貸貸款余額人民幣1.57萬億元,節約標準煤7 188萬噸,減排二氧化碳1.8億噸、二氧化硫204萬噸,節水5億噸。
(三)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支持民生社會事業發展
基礎設施、基礎產業和支柱產業發展水平滯后是制約中國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因素之一。國家開發銀行在業務重點上,將大量融資投向中西部“兩基一支”項目,拉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縮小其與東部地區的差異。僅2015年,就新增中西部貸款人民幣5 494億元;新增東北老工業基地貸款人民幣774億元;新增西藏和4個省份藏區貸款人民幣160億元;新增新疆貸款人民幣228億元。在絲綢之路經濟帶、柴達木循環經濟試驗區、陜西西咸新區、貴州貴安新區等西部重點建設項目上貸款金額逐年增加。同時,國家開發銀行充分發揮在促進社會和諧穩定發展中的作用,將大量資金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項目。僅2015年就發放棚戶區改造貸款人民幣7 509億元,同比增長近1.84倍。截至2015年底,國家開發銀行發放助學貸款余額累計562億元,占全國助學貸款市場份額的80%以上。服務中小企業貸款余額達2.82萬億元,其中小微企業貸款余額1.12萬億元,惠及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農戶、創業青年、城市下崗職工等各類社會群體,覆蓋制造業、農林牧漁業等近20個行業。
(四)開展國際投資合作,探索開發性金融國際互利共贏模式
國家開發銀行在重點支持“兩基一支”項目和民生金融的同時,還進行了開發性金融的國際合作,與多個國家在基礎設施、裝備制造、金融、農業、民生、能源等領域進行了項目合作,通過解決合作國的難點問題,探索開發性金融在國外更有效的合作共贏方式,先后合作設立了中非基金、中葡基金、絲路基金等多個投資平臺。另外,國家開發銀行將已經在中國運行較為成熟的開發性金融理念和方法通過各種合作方式在海外進行擴展,借助規劃合作和市場化的原則,針對合作國經濟發展的特點挖掘項目,設計適合當地金融市場特點的金融產品和金融工具,為中國開發性金融的國際實踐積累了大量經驗。截至2015年末,國家開發銀行外幣貸款余額2 760億美元,跨境人民幣貸款余額690億元,成為中國銀行業對外投融資的主力。境外代理行網絡進一步發展,國際業務代理行全球分布初具規模,已與104個國家和地區的747家銀行建立代理行關系。
四、中國開發性金融實踐的理論意義
(一)創新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機制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看,具有公共產品特性的基礎設施項目,本身對資金需求量特別巨大,具有建設周期長、沉淀成本高、需求彈性小等特點。[20]85在私人資本、商業信貸和政府投資等投資主體中,私人資本在基礎設施具有共享性且缺乏有效的投資風險防范條件下,逐利目標無法短期內實現,因而主動投資的動力不足;而商業信貸在短期獲利與基礎設施運營成本要求長期攤銷的目標不一致,以及基礎設施投資擔保體系不完善的情況下,也會動力不足。在私人資本和商業信貸都不愿介入的背景下,只能由政府通過發行市政債券或者通過財政資金進行投資。但從中國的實際情況看,市政債券發行尚處于探索研究階段,而不同地區和區域基礎設施建設所需的財政資金極大地依賴于政府稅收實力的支撐,如果沒有充足的財政稅收保障,基礎設施建設將會明顯滯后。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開發性金融在對傳統政策性金融改造升級的基礎上,將政府信用和市場機制緊密結合,建立起一種在國家信用基礎上進行市場績效考量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模式。即在風險控制方面,充分發揮地方政府的組織優勢、政治優勢和信用優勢,在地方政府信用基礎上通過引導建立基礎設施建設融資平臺,推進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達到降低成本、控制風險的目的;在投融資總量控制方面,在地方政府部門對基礎設施建設每年預算支出基礎上,對未來3~5年現金流進行預測,計算貸款金額,控制貸款總體規模。這種完整的風險控制、項目篩選、投資扶持和盈利共享的投融資模式,成為社會信用制度落后條件下促進基礎設施建設和經濟社會發展非常有效的一種金融形式。[21]
(二)彌補產業升級和民生社會事業發展中的“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
一個國家或地區在產業發展升級和民生事業發展過程中,都可能遇到兩種情況:一方面,產業和民生事業對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有重大影響,但社會資本受制于規模和短期逐利的影響,無力將資源有效足額配置到這些項目中,同時,國家財政手段也無力或無法滿足這些項目發展的需求;另一方面,國家財政在行政權力的介入下,引導大量財政資金投入風險較高的產業領域和回報較低的民生項目,但由于政府對于產業運行狀況的敏感度較低,同時也缺乏對民生社會事業發展持續“造血”的相應機制,尤其是在信用缺失和制度落后的情況下很容易產生資源浪費,同時還有可能進一步削弱對社會資本的吸引力,導致產業升級和民生改進項目的停滯。在這種情況下,開發性金融通過市場化原則和信用、制度建設等,有效地彌補了我國產業轉型升級和民生社會事業項目建設中的兩種“失靈”。在彌補“市場失靈”方面,按照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總體要求,開發性金融首先向“市場失靈”領域配置金融資源,然后通過培育市場貸款主體,引入政府協調和增信等手段,不斷增強金融信息和金融資源的獲得性,[22]通過信息溢出效應,引導社會資本的流向,實現資本在市場中的優化配置,降低了市場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促進了金融市場的完善,推動了社會資本向重點產業和領域的聚集。在彌補“政府失靈”方面,開發性金融采取推動信用建設的方式,利用組織增信將政府信用運用于重大項目融資中,項目風險通過政府進行過濾,降低了投資項目的成本和不確定性因素,提高資金利用效率和成功獲得投資回報的可能性。[23]同時開發性金融通過市場機制所建立的政府、銀行、企業和市場為一體的融資平臺,可以降低商業銀行可能面臨的信用風險和不同產業內企業面臨的貸款門檻,充分調動社會資本參與產業發展的積極性,促進金融交易。這些做法不但提高了地方政府和企業對信用建設的認同度,同時也促進了產業升級和民生事業發展中投融資體制的暢通與完善。
(三)規劃理念為金融支持區域發展和國際合作提供科學路徑
從世界各國發展歷程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要想具有較為長遠且具有操作性的目標和步驟,都進行過科學規劃。一個科學性和實踐性很強的規劃能夠在經濟活動中,合理配置生產要素、提高資金使用效率,防止出現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有效進行風險防范。[20]107從2003年開始,中國開發性金融的主要機構——國家開發銀行開始運行通過融資啟動規劃的模式,即在進行項目投融資之前,將前期規劃作為國家開發銀行與資金需求方進行合作的突破口,通過規劃確立項目融資最終實現的全局目標,在規劃中對各種要素資源進行統籌配置。在促進國內區域協調發展中,國家開發銀行將自身的融資規劃與不同區域經濟社會發展規劃進行對接,確保雙方合作能夠既滿足合作方經濟社會發展趨勢,又使融資項目的實施具有規劃保證,最大限度地減少盲目投資和重復建設,確保融資項目的成功實施。在國際項目合作中,國家開發銀行通過建立與合作國政府及有關部門的長期規劃合作,按照合作國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挖掘項目,并有針對性地設計適合這些國家金融市場的產品和工具,在推動雙方項目合作成功的基礎上,充分調動起當地政府和企業的積極性,順利實現合作共贏。[20]262在規劃過程中,國家開發銀行通過完善規劃專門機構和工作體制機制,在培養自有規劃人才隊伍的同時,建立覆蓋經濟社會發展主要行業和領域的專家庫,保證了規劃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從這個意義上講,國家開發銀行成為這一方面的融智銀行,不僅為經濟社會的發展提供了融資服務,同時也為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高度專業化的知識服務。規劃先行也成為發現制約經濟發展瓶頸問題、制定各種創新性戰略、推動融資項目發揮積極作用、促進區域協調發展和國際合作共贏一條有效的科學路徑。
五、中國開發性金融的借鑒性
“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目標是通過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激發各國的發展潛力,最終實現經濟發展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繁榮。從目前許多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研究結果來看,這些國家經濟發展有幾個特點。一是基礎設施較為落后。一些學者按照因子分析法對“一帶一路”60多個沿線國家和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進行了分級評價,分數越高,基礎設施越完善。從分級結果看,新加坡在這60多個國家中指數評級最高,達到100,其他國家和地區有一半以上基礎設施指數還不到60。[24]二是產業基礎較為薄弱。一些學者對“一帶一路”沿線的東南亞、中亞、南亞、西亞和非洲地區的經濟特點進行分析,認為這些地區經濟上的主要劣勢在于工業基礎薄弱、產業結構形式單一,發展基礎技術、高新技術的能力很弱。[25]三是區域合作和經濟轉型缺乏資金支持。全世界目前31個低收入國家中,大部分為“一帶一路”沿線的非洲國家和個別亞洲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開始逐步起飛、擺脫貧困的過程中,一方面有可能不再滿足多邊援助機構進行軟貸款和資金補貼的限定條件,另一方面它們仍然不具備通過全球資本市場建立可靠融資渠道的能力。[1]7任何謀求區域合作和加速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愿望,都會由于巨大的資金缺口而被迫中止。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遇到的問題,在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中也不同程度地出現,而開發性金融模式在推進中國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的改觀、促進產業轉型升級和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極大地幫助中國解決了這些領域存在的問題。這一模式所總結出來的經驗和做法成為推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解決上述問題可以借鑒的思路之一。
(一)借鑒中國開發性金融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形成的投融資機制
目前世界上主要的開發性金融機構有30家,其中多邊開發機構8家,國家開發銀行18家,另外還有4家具有中國因素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從18家國家銀行所處的地理位置來看,基本都屬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這些國家的開發銀行資金來源、商業模式、治理結構并不完全相同,從近幾年的發展成果看,這些單一開發性金融機構的總權益和總貸款都出現了快速增長,但無論從數量還是增長速度來看,中國的國家開發銀行總資產和總權益都增長最快,[1]179這與其建立了較為先進的投融資理念密不可分。因此,在“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各個國家都可以在現有模式的基礎上,結合本國開發性金融業務特點,充分借鑒和吸收中國開發性金融在融資領域的做法和經驗,為基礎設施建設迅速積累資金。同時,隨著中國參與和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和絲路基金的正式運轉,中國在開發性金融中積累的經驗也將逐步滲入這些組織的政策體系、運作方式和發展遠景目標當中,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的建設、組織和實施中,為項目實施國建立起完善、多元化、可持續的資金保障機制。通過各個國家內部開發性金融的經驗借鑒和外部國際性開發性金融組織的協同發展,可以有效地形成適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實際的基礎設施建設投融資新的體制機制。[21]89
(二)借鑒開發性金融的市場培育模式
發展中國家轉型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約束條件是市場機制不成熟、不健全,“一帶一路”沿線大部分國家也不例外,這將嚴重阻礙這些國家產業的轉型升級進程。建立成熟健全的市場機制需要對市場進行培育,而市場培育的核心是對融資主體的信用進行培育,同時完善風險管控制度。從中國開發性金融的經驗來看,國家開發銀行擔當了市場先行者的角色,通過承擔風險、厘清誤解,突破了產業發展的低迷狀態,降低了不成熟市場中的風險、推動了前沿市場的發展,為社會資本的投資建立起信心。在國家開發銀行先行先試的努力中,改善了融資方的信用狀況和項目運作的治理結構,超越了商業銀行的局限,實現了市場培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發展中,完全可以通過開發性金融機構搭建起政府和市場的橋梁,憑借本國的主權信用,降低融資成本,并依托開發性金融搭建政府與市場、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間合作的平臺,以較小規模的投資帶動更大規模的投資,推動本國產業轉型升級獲得充足的資金支持。
(三)借鑒開發性金融的融智優勢
從中國開發性金融的實踐成果來看,中國國家開發銀行通過10多年的“規劃先行”理念,系統推動了區域、行業、戰略客戶的國內規劃工作,探索出國家規劃咨詢合作、國家規劃編制、雙邊合作規劃等國際規劃形式,搭建起業務發展規劃編制與實施的初步框架,形成了涵蓋國際國內、行外行內的規劃體系。國家開發銀行通過系統規劃,按照區域和城鎮規劃、產業規劃、社會規劃、市場規劃、融資規劃和富民規劃等分層次、多角度的規劃,推動了各方資金對項目可行性和成本收益可靠性的重新認識,幫助國際和國內多個項目獲得了融資。[1]181與此同時,最大程度地利用了行內專業人員和關鍵領域專家學者的智慧為國家開發銀行的中長期投融資提供了前瞻性、主動性的目標和方向。“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開發性金融可以利用國內和國際開發性金融機構的專業人員和專家學者,通過前期規劃,為本國重要產業、重要區域和重要融資開展充分論證和研究,建立具有一定贏利模式的項目架構,在推動國際和國內開發性金融機構和組織幫助解決各國經濟發展獲得軟貸款與資金補貼限定條件的同時,通過可行性項目吸引全球資本進行投融資活動,逐步建立起長期的可依賴的融資渠道。運用開發性金融機構的融智優勢,最終實現“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繁榮和國家之間的互利共贏。
注釋:
①本文關于國家開發銀行的相關數據除特別標注外,均來源于2013年至2015年國家開發銀行年度報告(http:// www.cdb.com.cn/gykh)。
[1]中國開發性金融促進會.全球開發性金融發展報告(2015)[M].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6:205.
[2]JOHNSON C.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the growth of the industrial policy[M].Pale Alto:Stanford University,1982:36-78.
[3]ZYSMAN J.Government,market and growth: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politics of industrial change[M].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23-65.
[4]STIGLITZ J,WEISS A.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information[J].Americaneconomicreview,1981(77):228-231.
[5]WILLIAMSON.Costly monitoring,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and equilibrium credit rationing[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86(18):159-179.
[6]瞿強.經濟發展中的政策性金融——若干案例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62-65.
[7]小椋正立,吉野直行.稅制與財政投融資[M].東京:東京大學出版社,1984:105-131.
[8]日向野,崛內大原.政策性金融資源配置問題研究[M].東京:亞洲經濟研究所,1987:72-79.
[9]陳元.開發性金融與中國經濟社會發展[J].經濟科學,2009(4):11.
[10]國家開發銀行,中國人民大學聯合課題組.開發性金融論綱[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140-152.
[11]李揚.國家目標、政府信用、市場運作——我國政策性金融機構改革探討[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6(1):14-19.
[12]林勇,張宗益.論現代金融體系下的開發性金融的理論定位[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7(5):16-18.
[13]白欽先,王偉.開發性政策性金融的理論與實踐探析[J].財貿經濟,2002(4):56-59.
[14]張朝方,武海峰.政策性金融、商業性金融和開發性金融的關系[J].商場現代化,2007(12):272-273.
[15]李志輝,王永偉.開發性金融理論問題研究——彌補政策性金融的開發性金融[J].南開經濟研究,2008(4):6.
[16]袁樂平,陳森,袁振華.開發性金融:新的內涵、理論定位及改革方向[J].江西社會科學,2012(1):96-97.
[17]溫守義.開發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分析[D].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2006:16-17.
[18]高媛媛.基于政策目標的中國開發性金融模式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2007:16-17.
[19]何江.我國開發性金融可持續發展研究[D].重慶:重慶師范大學,2011:11-12.
[20]陳元.政府與市場之間[M].北京:中信出版集團,2012.
[21]姜安印.“一帶一路”建設中中國發展經驗的互鑒性——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例[J].中國流通經濟,2015(12):88.
[22]陳元.開發性金融與中國城市化發展[J].經濟研究,2010(7):7-8.
[23]嚴華.開發性金融支持產業升級的效應分析[J].浙江金融,2011(6):22.
[24]鐘飛騰.對外投資新空間——“一帶一路”國別投資價值排行榜[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89-91.
[25]李紹榮.對“一帶一路”發展戰略的經濟學分析[J].學術前沿,2016(3):45-46.
責任編輯:林英澤
A Research on the Mutual Reference of China's Development Financing Experience in“the Belt and Road”Construction
JIANG An-yin and ZHENG Bo-wen
(Lanzhou University,Lanzhou,Gansu730000,China)
We have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development financing,which is the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summarizing of China's experience of development financing will be helpful for us to hav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mechanism of how development financing drives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economy in financial market;it is also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to realize the win-win development by learning lessons from China' s experience.The related experiences of China include:first,making innovation in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of infrastructure;second,recovering the“market failure”and“government failure”in industrial upgrade and social issues;and third,providing the scientific path for finance to support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Countrie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should learn and apply China's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mechanism of development financing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rastructure,and the market cultivation pattern of that.
the Belt and Road;development financing;China's experience;mutual reference
F832.32
A
1007-8266(2016)11-0050-08
2016-09-08
2015年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項目“一帶一路”專項之“絲綢之路產業合作機制研究”(15LZUJBWZX013)
姜安印(1961—),男,甘肅省會寧縣人,蘭州大學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轉型與產業成長;鄭博文(1979—),男,甘肅省天水市人,蘭州大學經濟學院產業經濟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產業組織理論和循環經濟產業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