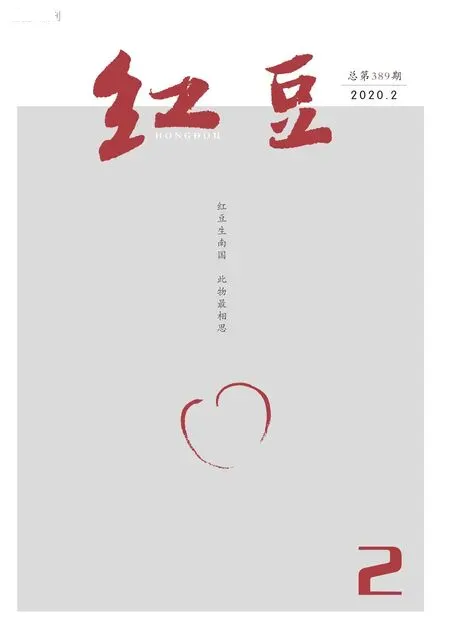硯邊信手(一)
朱以撒,男,1953年生,福建泉州人。現為福建師范大學美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福建省書法家協會副主席,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會副主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作家書畫院副院長。在國內報刊發表大量散文、隨筆,出版散文集《古典幽夢》《腕下消息》等多部,作品入選眾多選本并獲獎。書法作品廣有流傳和影響。
師法無名
學碑學帖皆學古人上乘之作,這是一種共識,但是陸儼少認為:“不要選名氣大的碑帖去學。名碑帖只要看就可以了。要揀那些無名的、而字又讓你非常喜歡的碑帖去學,這樣,要么學不成,一旦學成了那字就是你自己的。”大多數人擇碑帖還是會循大名家一路,因為千百年來都如此。但也有自己的路徑,如陸儼少所認為的,就顯示出個人精神生活的自由,未必依傍“取法乎上”。
歷史上大名頭書家、名碑名帖,數量還是有限的。而非大名頭書家、碑帖,反而是一個汪洋大海。以兩晉書法為例,大名家也就是陸機、王羲之、王獻之、王諸人,而民間寫經、碑刻、磚刻書法則不勝枚舉。人們師王羲之,王就是箭垛,被萬箭穿透。由于集中于王書,也就不免相互伯仲,都寫得像王羲之,又彼此相似之至。學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的就更明顯了,寫得點畫逼真,造型無誤,可謂合其法度。大名家的影響力太大了,如果一個人說自己從未學“二王”的書法,而是涉民間無名氏書法,則是會被認為非正派之舉。可是大名家的風格太鮮明了,給人的制約也太大了,就如同植物界之松柏楊槐諸樹種,何人不知?在給后人提供了一條通衢大道的同時,也使同行于這條大道上的人們,表現出奇地一致。
南朝梁蕭統認為:“譬陶匏異器,并為入耳之娛,黼黻不同,俱為悅目之玩。”陶匏作為民間樂器,其質當然質樸無華,它的聲響,當然比不得金聲玉振。但是陶匏發出來的聲響有自己的特色,也是能給人帶來精神上的享受的,非金玉之聲可替代。如果只有金玉之聲,高雅之至,卻不免過于單一。天地間應有萬千聲響方為常道,每一種聲響的自身都有其美蘊其內,如此交匯方為豐富。明人屠隆就認為:“稗官小說,螢火之光也。諸子百家,星燎之光也。夷堅幽怪,鬼燐之光也。淮南莊列,閃電之光也。道德楞華,若木之光也。六經,日月之光也。”光有強弱、大小、遠近之別,卻都可以為光,趨光而行,不昧于道。小名書家在書法史上遜色,甚至不為世所重,然而畢生為書,還是有其與眾不同處——任何一點小的變革都是很值得珍惜的,都是可資摹仿的。這些小名家數量如此之多,各懷珠玉,往往時勢使然,于暗處沉睡或不為世人所知。在一些作品被追捧而競相效仿時,另一些作品正清冷之至。那么,時之所重,我之所輕;時之所輕,我之所重,選一些不為時人所熱的前人作品效仿,也就避開了與人同學的一種方法。當然,這里也存在著一些危險性,因為這些小名氣甚至無名氏的作品,盡管有特色在內,但不足也很明顯,倘不能去粗取精,也易于學偏,沾染上一堆弊端。而如果學好了,剔除其糟粕,擷取其精華,其面目不為眾人所詳識,反而更有新鮮感。如果能融會貫通使之豐富,那真的就如陸儼少所說:“那字就是你自己的。”
一個人在選擇碑帖時不以大名家和著名碑帖為范,而意在小名家這種想法著實有些奇怪。就如同一個人不吃精糧而去吃粗糧,讓人匪夷所思,似乎此路徑偏頗之至。從另一個角度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每一件作品的歷史地位、審美價值也非板上釘釘座次不變。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審美判斷,有自己的審美座次,未必要隨大流追定勢,喜好大名家之作。有的人可能慕鴻鵠之于九萬里高翔,有的人可能追鷦鷯之于灌木叢中之自在。隨著書法文獻的出土、出版,一些舊日不見流傳之處,如此精采并不亞于名作,只有審美僵化的人才會無動于衷。這些非時代書法主流的、非書法史上的定論之作,它們的美不應忽視。
陸儼少認為個人“非常喜歡”是很要緊的,個人非常喜歡,可以在無名碑帖上寫出一些錦繡來。因此,個人喜歡就能挖掘自己的才華,走向深入。故袁枚說:“千古無臧否,于心有主張。”
一生一幅
言說漢代書法,總是離不開《張遷》《曹全》《乙瑛》《禮器》。它們是漢隸的代表。從隸書角度審視,這些名作都發育得十分成熟,很純粹、典型,而且一碑一世界,碑碑不雷同,令人迷戀。可是,這樣的風格是如何形成的?作者除了書寫這一方碑之外,還留下什么作品?這些問題都是難以言說清楚的。一個人的一生能留下一幅作品千古不磨,此生也不虛度了。但是一個人如果有不同時期的作品留下,讓人考量其繼承與發展,有更綿密的脈絡,透露更多的信息,也就會使人有更全面的認知。可是像這些漢隸作品,卻以孤立的形象出現,顯得十分突兀。北朝碑刻中也多此現象,《始平公》奇崛,《張女》秀逸,《嵩高靈廟》樸拙,卻再也找不到之前或之后的作品。這很像空中飄下一枚鮮艷的羽毛,抬頭仰望,再無痕跡,不禁讓人遐思。
越往后,書法家的創作量越大,留下的作品也就越密集,由青年至晚年,都有明晰的印記,讓人從環環相扣的創作鏈上考量他們是如何發展轉捩的。同時又可以看到在某個時段的轉折太重要了,突破瓶頸后,打開了后來的廣大空間。當然,也可以從中看到前人的某些失誤,以致影響了后來的發展。可以說,作品的環節越緊密,就越完整地反映一個人的創作精神、創作技藝。譬如弘一,在李叔同時代是一個面目,出家事佛又呈現另一個面目,可以在其作品中尋找到漸變的軌跡。譬如于右任,先是以碑體行書名世,后來研究標準草書,書風漸漸生變。這種變化由若隱若現到全然改變,是可以找到其中轉折點的,因為作品罄露了一切。若沒有一定數量的作品就有一定的困難,不知其所以然。李白一生有多少詩稿啊,居然都風吹雨打去,只剩下《上陽臺帖》,當然就有被人質疑的理由了。時日忽忽,許多作品消失了,并非它們不夠好,兵燹水火都是它們消失的客觀原因,這也使得孓遺之作變得珍貴無比。
作家丁玲曾提出“一本書主義”,她的意思是真實不虛的——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好書,那么誰都打不倒你。當然,這本書是需要經過檢驗的。因為在書里,蘊藏著作者的全部能量。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今日看來,結構、語言不免陳舊,但放在當時,就是名著,讓人仰望,這就使人和書緊緊聯在一起。如今每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多達四千部,每個人都寫得很快,一部接一部,卻因有量無質淹沒在匆匆步履中。而書法家一年中創作的作品數量也很可觀,其中很有一部分是應酬之作,精心之作并無幾多。“一本書主義”就是倡導精品意識,不失之粗,失之俗。古代有些詩人,詩不可謂不多,卻總是寫一些玉樓、金殿、鴛鴦、翡翠這些世俗之物而喪失品位。只有心存敬畏,才有恭謹之心,不至于胡亂涂抹以多為榮。宋人陳善對文章的評價可謂嚴厲,他認為:“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辭》一篇而已。唐無文章,惟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一篇而已。”這個評價苛刻無比,但是時間的檢驗更苛刻公正,不在乎書者何人何地位,亦不在創作數量多少,而在乎質量。譬如漢隸中那些非豐碑大碣者,如《樂山蕭壩佐孟機崖墓題記》《薌他君石祠堂石柱題記》,少有人問津,也許作者就是起于甕牖窮鄉人家的芻牧仆役,不為人所知,卻有如此明快簡潔的筆調。千載之后的人,盡管審美趣味不知與漢時相異多少,卻還能被它們的美感所打動,把它們看得很重。在漢代,蔡邕無疑最著名了,所書《熹平石經》四十六方碑,字數約二十萬字,為第一部官定石刻經本,當時效仿者無數,非其他書家可以比擬。千年后,問誰人研習《熹平石經》,恐無人應答。因此,即便官隸,有其影響,也難以維持長久。
每一幅作品都有自己的命運,或消失或存在,或千古流芳。
好神情
明人盛懋循在談到曲藝行家的演唱效果時這么說:“行家者,隨所妝演,無不摹擬曲盡,宛若身當其處,而幾忘其事之烏有;能使人快者掀髯,憤者扼腕,悲者掩泣,羨者色飛。”
清人李漁也談道:“如其離、合、悲、歡,皆為人情所必至,能使人哭,能使人笑,能使人怒發沖冠,能使人驚魂欲絕。”
每一個寫作者、表演者,最終的表現效果都可以從閱讀者、欣賞者的表情上得出。
每一個人的作品都有表情,因為情性各異,筆下自然不同,觀者喜好也決不相類。往往在欣賞一個展覽時感到了作品表情的相似。這個相似肯定不是創作前相互約好的,而是相互暗合的。緣于審美趨向都如此相同,也就不一而同,有如伯仲。“時風”就是統一創作表情的一種力量,如秋風掃落葉,被掃到一個角落里。人被時尚審美的秋風裹挾著,不由自主。宋時書壇中人時而學李宗鍔、宋綬、韓琦,時而學蔡襄、王安石,世風如是,無可奈何。譬如時下對作品的裝飾,有如在新衣上打補丁,這里打一方,那里打一方。這么做究竟有沒有道理,但見有人做了,又得到名利了,也就跟著打補丁,以示跟上潮流。這樣的作品多了,置于展廳,不僅每件作品表情奇怪,整個展廳也充滿了不自然的氣味。審美“場”的生動,就是要求每位作者表現自我,關注個人的細微感覺,而不是風雅不作、齊竽競嘈這么一種狀態。有時欣賞一個個人書法展覽,展覽的表情也是公共化的,關照公共需求的,而少了那些私人的隱秘部分,也因此沒有什么辨識度。
留意于外物往往成趣。正因為這樣,那種消解個人表情的力量也滋長起來了。
作品的表情如人的表情,或莊重、安和,或詼諧、奇詭,或舒朗、急切,不同時段不同變換,極盡豐富。一個人寫楷書,楷書面目是一種表情;到了行草,又是另一番了。人們觀展就是在差異的表情前思索、玩味,感到趣味盎然。欣賞古人作品展的人最多,因為那些久違了的表情,我們無法還原了,因此最值得品咂,記取于心。今人也學晉人,也學唐人,卻多是此時表情。表情生于那個時代,縱使把《蘭亭序》臨得酷肖之至,還是當代人的烙印在上。有表情的作品總是足資把玩。清人鄭板橋的書法就使人喜不自禁,忽俯忽仰,忽正忽欹,忽肥扁忽奇長,曲盡其態可謂其書。相比之下,金農之漆書就表情呆滯,其一味排疊有如堆物。從書體審讀,行書草書表情生動,楷、隸、篆表情安和居其靜,這也使書法家把行草書糅入了楷、隸、篆,使之成為行楷、草篆、草隸、碑體行書,使人觀之無僵坐冬夜之索然,有忽上春臺之快哉。
作品表情的流露貴于自然而然。不自然的表情就是做出來的、勉強為之的。那種故做英雄氣,逞強使性,使得滿紙張狂,有如婢做夫人,裝都裝不像。那種擅長小幅式小字徑者,偏試穎強做巨幅大字以應時尚,也就露出空虛來了。尋常心態尋常寫,最好。信札為文人最自然之神情表現,字無須多、無須大,隨性信手一幅乃成,敘述兩人離別既久十分想念,告知近來肚子疼腦門熱,都是一些生活瑣屑。有誰會在信札中裝腔作勢,或者弄一番裝飾呢?由于沒有,自然如水之下流煙之上尋,故一幅下來,百態橫生。表情的不自然是可以感受的,盡管人隱于后,讓筆墨線條置于前,但用意了,刻意了,使性了,下力了,超過了自然的幅度,就流露出來了。譬如徐生翁的作品,如折木拗峭,只用方不使圓曲,也就免不了僵硬氣,表情生硬。晉人在品藻人物時用了“好神情”,他們的作品的確是好神情。“這是一個活潑愛美,美的成就極高的一個時代”,宗白華顯然十分喜愛這么一種狀態。
相由心生——通常都這么認為。表情不只是皮肉上的松緊,不只是筆墨功夫的生熟。總是有一種對美的追求在調節著,使淺薄轉為敦厚,花俏轉為質樸,使人期待不至于落空。
蝴蝶兒
清人哈斯寶在分析《紅樓夢》時,談到一個如何引人入勝的方法:“那蝴蝶兒卻忽高忽低、忽遠忽近地飛舞,就是不落在花兒上。忍住性子等到蝴蝶兒落在花上,慌忙去捉,不料蝴蝶又高飛而去,折騰好久才捉住,因為費盡了力氣,便分外高興,心滿意足。”他說的是表現情節要如“蝴蝶兒”,讓讀者跟著走,趣味盎然,最終獲得美感。這樣的筆法不是直接地給人震撼,更不是強化灌輸給讀者,而是輕松地忽遠忽近,忽高忽低地引導,使人非讀下去不可。
哈斯寶稱這種手法為“拉來推去之法”,就像一個人撲蝴蝶,過程婉曲,最后有得。
這個過程虛的成分很多,飄忽不定,游移變化,而不是實打實地敘述。在古人的書法作品中,不下蠻力而以虛法為之者,可以說是智慧之舉,使一件作品多出搖曳來,不使人一目了然,反而生出探魅之心。當然,書法作品是沒有故事情節展開的,它用來引導讀者的就是點線的運用和分布的機巧。一般說來,既然在白紙上寫黑字,總是要把它裝滿才不枉空間之實在,猶如一池春水,總要有密集的魚群。因此以密如蟻陣的方法來應對空間就很常見。倘若有人購買書法作品,也希望能如此炮制,字寫滿了再多幾枚印章,使其密不透風以為劃算。明人李東陽曾批評:“若平鋪移布,雖多無益。”一般人不予理會其中含義,以為紙面上物質材料多了,如字多、印多,就不吃虧。這種想法把生活經驗代替審美理解了,因此很實在,也很壅滯,一紙之內密集充塞天地,如文抄公之抄寫,以苦勞勝出。苦勞往往得到同情——人們對苦勞者的體力付出總是懷有憐憫之心,有時也不經意地忽略了它和審美的界限,給予好評。這也使揮毫的藝術性降了下來,工匠般地寫的人多了起來。宋人楊萬里認為:“善用兵者,以一令十,以十令萬,是故萬人一人也。”這就是語言的作用——雖然少卻有活力,遠勝多。魯智深打鎮關西,三拳即罷,不再多費筆墨了,蕩開一筆寫其他,讓人覺得怎么這么快就解決,似乎“蝴蝶兒”還未落下,生出許多追問。董其昌行書留下那么多空白,于實在人眼中不免浪費空間指腕懈怠了。可是這些空白讓人平和下來。空白讀起來都是疑問,它是虛的,可任人想象填充的,它映襯了黑的部分,倍覺云煙渺茫之中無限丘壑在焉。
如何讓人覺得入勝?頗費猜想。明人李騰芳曾談到一個對比法:“如有一個俊人要引出一個村的作拌,越顯得此人俊。”這個“作拌”就是引導、挑逗之意,如一池水要蕩出點漣漪來方得趣。因此他認為最大的特點就是要“活,不要死”。這和飛動的“蝴蝶兒”是一樣的——輕盈、靈動。反之,深重的、沉實的、粗壯的點線則無此作用。如勻稱均衡有如玉箸的小篆,它平正安穩,并無逗引之勢。唐人顏真卿《家廟碑》的廊廟氣色,一副莊重森嚴之調,自然也談不上活潑詼諧。而行草中的秀逸者,一條游絲飛動地拉了下來,云破月現砉然天開,使原先平靜的場面倏忽激越起來。其中附著的瀟灑舒暢,又使人由此延伸到作者的才氣情調,覺得不是一個死守規矩郁而不明的人。元人楊維楨的草書奇峭夭矯,往往于此中有線拉開,使人大喜。可是他太頻繁運用,反而使人厭倦。可見,引導也不可一味如一。譬如那個眾所周知的“狼來了”的故事,因為使用多次,最終以無人理會結束。
讀戰國時《曾乙侯鐘銘》,覺得夸張過甚搔首弄姿,反而有齊竽競嘈之感。李騰芳談到了“逗”的妙處:“逗如逗留之逗,蓋將就說出又不說,須逗一逗。如此,文字方有吞吐。”逗一逗,引而不發,似現而隱。吞而吐,不可一味吐之,那種紙面上亂花迷眼,藻飾沸騰,繁密錯縟,往往把“逗”給消解了。
語言魅力就是引入,不是門洞大開了無婉曲,又不可藏之過深難以接引,因此真須如“蝴蝶兒”那般,使它忽高忽低地飛,使讀者忽緊忽慢地追,饒有興趣漸入佳境,最終得手。
二手經驗
清人章學誠認為:“富貴公子,雖醉夢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語;疼痛患難之人,雖置之絲竹華宴之場,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歡笑。”清人趙執信也表達了大致相同的意思:“富貴者不可語寒陋,貧賤者不可語侈大。”按他們的認識,一個人如果沒有親身的經歷,就不可能獲得第一手的經驗。那么,他要表現自己之外的生活場景就完全沒有可能。如此說,一個人最后就是本色的個體,只能是自己的延伸,包括他的言語行為。
一個人的實際人生是沒有第二次的,他的體驗也就是純粹個人,難以與他人同,難以與故我同。對于每一個人來說,都是自行其道、自行其是,處于各自的空間、層面——所謂宿命就是如此。可是一個人為文、為藝就不能僅僅止于本色之功,文藝的功能就是使人萌生超越現實的理想,同時掌握超越的技法,使自己成為超人。清人蒲松齡寫《聊齋志異》,那些幽冥世界中的狐怪花妖,蒲松齡未有與之交集卻能于筆下惟妙惟肖。近五百篇,入異域幻境,假狐鬼抒懷,令人競相評點,一時風行天下。蒲無此經歷,但有此傾向:“才非干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篇。”正是勤于搜集且能集腋為裘,以致有此奇書。書法家學王羲之書,能回到東晉那個時代,見到拂麈清談、服藥飲酒、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的場景嗎?但還是許多人寫了一手清雅的羲之書法,再現了晉人筆下的風采。時間永遠是一維的,無可逆,晉人到不了唐朝,宋朝與清人遙隔煙水,那么學古人只能是精神指向上的,肉身難為,這就是二手經驗在起作用了。
清人李漁曾出語驚奇:“我欲做官,則頃刻之間便臻榮貴;我欲致仕,則轉盼之際又入山林;我欲作人間才子,即為杜甫、李白之后身。”這一說法聽起來很離奇,卻顯示了一個具體的人的能動性——摹仿一個人的外在,探悉他的內涵,體驗創造的樂趣。古人雖不見了,可見得到的是他們的筆墨,從筆墨里可以揣摹一個人的精神、氣度,心慕之,手追之,于時光煙云中逐漸接近。一個人學宋人米芾書,從現實之近而達虛幻之遠,體驗其顛倒淋漓的脾性,得其認,不少人失敗了,筆下的形、神皆與那個古人相距甚遠,時日和精力都白瞎了。這樣的遭遇只能暗自嘆息與這個古人真的無緣——面前永遠是一堵墻,讓他無法進入。不過有喜劇效果的追求也不少,很多人懷疑《蘭亭序》非王羲之所作,目標一致,貼近的手法卻不同,有的從晉時書體的存在研究,有的則從文學語言的特征推敲,也有人從晉人書法的譜系圖展開分析,還有的人從哲學思想深入。很巧的是,方法雖然不同,終了得出的結論都是一致的,認為《蘭亭序》為偽作。可見貼近古人方法有多種,卻都須如李漁所言——夢往神游,設身處地。
晉人殷浩說:“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是啊,如果一個人不像自己,那是多么不真實。但是,我們樂意追古人,是為了提升品位,使筆下有古風、古意。這樣,我們對于把書法學得酷肖古人者,仍要給予贊賞——承傳是不應忽略的,它意味著今人在二手經驗下激發出來的心智,到達了那個遙遠的疆域。黑格爾曾認為一個人不能脫離他生存的時代,就像一個人不能脫離他的皮膚。但是前人已有了通變的力量——神交古人、思接千載、神游萬古、精騖八極。這樣,一個人沒有經歷秦漢,無論唐宋,卻能寫得一手秦篆漢隸唐楷宋行,這是如何的神奇。清人金圣嘆有“三妙”之說,可為“二手經驗”最佳注解:“心存妙境,身代妙人,天賜妙想。”
生路熟路
一個把筆揮毫的人,一生可能臨摹多少前人之作?肯定是一個難以考量的數字。一生僅學一家叮住不放的人理應沒有,總會旁涉其他使之延伸。如何不像老僧守廟般地守住一家呢?是人之探索心性使然也。明人唐順之就談道:“老家必不肯抄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這樣的學說固步自封持守家法,意在純粹而避駁雜。時過境遷,為學之道漸寬,以博涉諸家融匯新知為務,反而視守之以一為硁硁小道了。
宋人黃庭堅的學書過程涉獵極廣,可以開列出一串長長的名單。除了表明他好學善學之外,也給人一個啟示,自成一家是以博學諸家為基礎的。書法文獻越來越豐富,有如百花競妍云霞興蔚,令人若山陰道上行不暇應接,如果不多學幾家豈能罷休。于是有在南帖上下功夫,盡得紙本風流妍妙;亦有迷醉于北朝碑版,于是承中原古法鐵骨堅硬。有的人又不甘于僅學碑或僅學帖,有志于碑帖融匯,在北碑南帖間往來,有如庖廚調味,此多彼少或此少彼多,流連中考量增損往往成趣。如果一個人守一家之法持守不輟,也就如掘一口井,向下用力就是,等待泉水破土而出。如果取法諸家,就如同掘許多口井,井下的水又要成為一個水網絡,那么就復雜之至了。這個人的綜合能力就要超人,才可能采荊南之杞梓,收會稽之箭竹,總萃合作。成功的人博涉而優,于筆下已難以窺探剔析學秦漢學北朝,體狀風雅,理致清新,是五代韋莊所稱:“擷芳林下,拾翠巖邊,沙之汰之,始辨辟寒之寶;載雕載琢,方為璉瑚之珍。”
一個人在一件優秀的書法作品面前能停留多久,二十年,還是三十年?譬如《蘭亭序》,一個癡迷的人對它的欣賞、臨摹,從生到熟,到熟透,是不是能夠始終保持新鮮感、神秘感?從心態上來分析,產生倦意必不可免。新異的喜好對于一個人來說不可抑制,人固有的探索意識,總是對陌生的未知領域產生極大的興趣。在陌生之境有著與《蘭亭序》不同的審美風格存在,盡管聲名不及,但是那些獨到的美感,或古拙質樸、野獷豪放、雄闊豐潤,都非《蘭亭序》所有。三國曹植曾說:“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有如讀慣了宮廷文學的人,發現民間筆法也生動之至。
往往是移情別戀使書風生出轉捩,大羹玄酒也會轉向于山野蔬筍。清人鄭燮青年時楷書極其精工,不失為一條正途。后來雜糅諸體又添畫技,也就越發走一條生僻之路,生出筆下的奇怪來。陌生的表現沒有先例,都指向未知,使人不受筆法畦畛束縛,生出先鋒精神——不甘于守而樂于游弋。史上成名后的書法家總是十分珍視其結果,守住這么一個攤子也不枉一生,未必再開新境。那些陌生之境無所指向,往往超出了個人的才智和體驗,能不慎之?只有那些能放下此時的聲名的人,會更具備浪漫主義式的精神之旅——秘密總是存于深處。“衰年變法”,這個提法太具有挑戰性了——一個年事已高的人,他的體力與精神還能具備如此敦龐大雅的氣度嗎?成功的人寥寥無幾,甚至變得令人失望,但是這種不甘囿守軒軒于雞群之志,使人言說時的神情充滿莊重。
一個人走熟路不免慣性生焉,以致毫無蘊藉,一個人于陌路小心探求充滿歡喜。在博爾赫斯筆下經常有迷宮的意象,使人感到陌生處行走之不易,不是迷路就是多走了彎路,顯示出探路者的孤獨,祈望在心智的引導下走出迷宮被燦爛的陽光照徹。書道與世道一樣,不是條條路徑通長安的。有的人恪守于大道,如元人趙孟,一直循王羲之一路行。寄跡康衢,結軌驥,勝算就大了,同時可稱之為正宗。一條新路徑由他形成,大家也都行于此,卻又相互蹈襲毫無孤獨探險的樂趣。趙孟頫的身后,那么多人傍其門墻,一時擾攘,卻不愿離群獨行,以致生意盡矣。可見篳路襤縷開啟山林的不易,而追隨現成者又過于聰明了。宋魏慶之《詩人玉屑》曾言:“但得有錢留客醉,那須騎馬傍人門。”,這個“錢”可視為一個人的內在指向,游離于眾人之外,得獨行之樂。
責任編輯 侯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