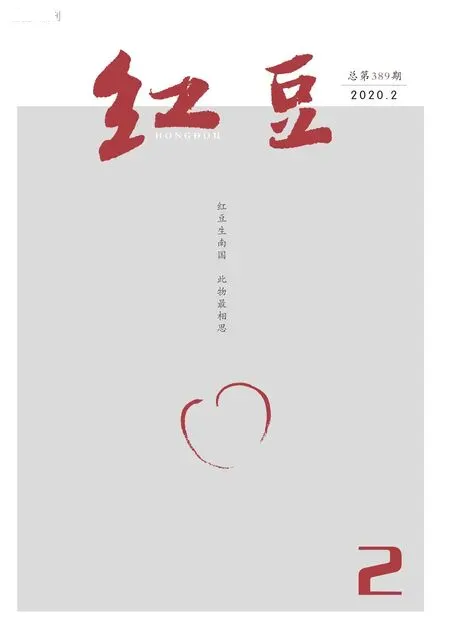祈禱心靈的安靜
趙豐,陜西戶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陜西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第五屆冰心散文獎、第二屆孫犁文學獎、第三屆柳青文學獎、首屆陶淵明散文獎獲得者。
心靈的安靜,是人類至高的境界。如何在喧囂的世界里,為自己尋得一方安靜的樂土,除了自然的山水,就是人的內心。常常,我在捫心自問:你找到了自己心靈里的那一方凈土了么?除了禪佛,除了基督,剩下的恐怕就是哲學了。閱讀哲學,是一次次凈化自己心靈的過程。除去心靈的污垢,那顆心就會安靜下來。
普羅提諾的《什么是生命物,什么是人》里提到通過哲學將靈魂和軀體分離。可見對他來說,哲學就是一種安頓身心的方式,而不僅僅是知識的形態。
好多年來,我在西方哲人的敘述里度過自己生命的分分秒秒。當我走近普羅提諾這位西方最后一個古代哲學家時,歲月已經為我的面容刻寫下無數的皺褶,發際間有了許多的白發。幾天不洗發,一根根白發就凌亂地在頭頂伸長,彎曲,孤零零地顯示。網頁上,普羅提諾的圖像很模糊,久遠的時光讓他的形象變得捉摸不透,眼神亦如雕刻一般。可是他的思想,卻是這樣清晰。他如是說:人的生命歸宿在于人自己。
普羅提諾生活的時代,是有史以來最悲慘的時代之一。這個時期,大多數人低下了頭,把命運交給了神,只有少數人在黑暗中點燃人性的火種,普羅提諾就是其中之一。對于物質,對于靈魂,他的表述是這樣的:物質是由靈魂創造出來的,物質并沒有獨立的實在性。每個靈魂都有其自己的時刻;時刻一到靈魂就下降并進入到適合于自己的肉體之內。
在這里,我不想討論物質和靈魂(也可以說是精神)的關系,那是哲學家的事情。我所關注的,只是人的靈魂的存在。這并非說我可以脫離物質成為一個純碎靈魂的人。不食人間煙火,我還遠遠修煉不到那樣的境界。普羅提諾所關注的,是人類個體生命中屬于自己的靈魂。每個靈魂的顯現都是不同的,都有著屬于自己的時刻。誰能剝奪了人獨立思考的時刻?你可以鎖住他的手腳,在牢獄里限制他身體的自由,卻無法限制他的思想。這就是靈魂的偉大。
普羅提諾出生在埃及,基本是在希臘的文化傳統中接受教育。他曾經參與皇帝戈爾迪的東方遠征,后來在戈爾迪被羅馬軍隊暗殺以后,他就放棄了遠征而最終定居在羅馬。羅馬這個偉大而古典的城市就成為他靈魂的棲息地。在這里他修訂和發展著柏拉圖哲學,創造著“新柏拉圖主義”,撰寫出了許多作品,都由他的弟子波爾菲里收集和編撰在《九章集》中。
普羅提諾思想的本體,是神圣的三位一體,即太一、精神和靈魂。何為太一?按照柏拉圖的觀點,普羅提諾稱呼為“善”,是無法被形容的。語言僅只能指向它,甚至很多用來稱呼它的名字都不是真名。它無法用語言說明,是現實世界神秘的來源。普羅提諾給我們提供了很多類比。精神像是太陽光,它將太一照亮,通過它太一凝視自己。精神就是現實事物的原型(柏拉圖理念)的來源和基礎。在精神中,思維和思維的對象以及知覺者和被知覺的事物之間是統一的。現實的下一層級是靈魂,它是理性或雜亂的思想。這里存在著一種更高級的向內的靈魂,以及一種低級的向外的靈魂。普羅提諾稱靈魂低級的部分為自然。正是靈魂中自然的部分產生出了現實的物質世界。而在人類的身上同時存在著靈魂的兩部分。是更加關注與肉體有關的靈魂的低級層次,還是向內去沉思精神的更高級的存在,取決于人們自己的選擇。
這樣的解釋看起來虛無縹緲,簡單說就是:與肉體相連的靈魂是低級的層次,與精神相連的靈魂是高級的層次。不錯,靈魂是潛藏于人的肉體之中的。按照唯物論的觀點,先有肉體,后有靈魂。肉體是靈魂的附著物。魯迅筆下的祥林嫂為死去的丈夫捐門檻,就是要為他的肉體尋找一個歸宿之地。她堅信,只要讓丈夫的肉體有了寄托的場所,其靈魂就會回歸。祥林嫂自然是凡人,并不懂得尋找與自己的丈夫精神相連的靈魂。
祥林嫂死去的丈夫精神在何處?我知道么?在中學時學習這篇課文時,講這篇課文的是孫承學老師。他是一個高度殘疾者,走路一瘸一拐,但他卻用自己充滿激情的普通話啟示我們:祥林嫂的丈夫死了,但他的精神卻活在祥林嫂的肉體之中。祥林嫂如果明白了這一點,就不會去為丈夫捐門檻了。
孫老師是否知道普羅提諾?這是一個永恒的謎。因為孫老師過早就去世了。他殘疾的身體無法支撐起更為漫長的人生,僅僅四十歲,他就死于心肌梗塞。我們死后還記得今生嗎?普羅提諾沉思著說:對于這個問題的答案是十分合邏輯的,但并不是大多數近代神學家們所要說的。記憶只關系到我們在時間之中的生命,但我們最美好的、最真實的生命卻是在永恒之中。是的,孫承學老師永存于我記憶里的,永遠是那個彎腰走路的、最真實的、最鮮活的生命體。
祥林嫂,你不要捐門檻了吧!朦朧中,我的耳畔傳來普羅提諾的聲音——相隔著遙遠的時光隧道,他的語音雖然蒼老,但卻如此清晰。佇立在生命的地平線上,他延伸著他的思考:隨著靈魂之趨于永恒的生命,它便將記憶得愈來愈少;朋友、兒女、妻子都會逐漸地被遺忘;最后,對于這個世界的事物我們終將一無所知,而只是觀照著理智的領域。個人的記憶將不存在,個人在靜觀式的所見之中是不會察覺到自己的。靈魂將與no-us合二為一,而并不是其自身的毀滅:nous與個人的靈魂同時是二而一的。
是的,生活仍將繼續,亡人會漸漸被淡忘。理智,將統領我們的一切。我們活著的人,依然要將靈魂與肉體合為一體。
為靈魂祈禱吧。普羅提諾垂下高貴的頭顱,為我做了一個雙手合十的動作。
漫長的冬天已經過去,迎接我的是春光明媚,是花草綻放。在這樣的季節,討論靈魂與肉體的問題顯然不合時宜。去踏青,去春游,去曬太陽。我的祖母在春天里總是不會閑著,在田野里拔豬草,采摘野菜,撫摸著一朵野花,她會半天身子不動,仿佛靈魂沉浸在其中。祖母當然是一個鄉下的女人,不會懂得哲學,但這并不影響她的思考。那一刻她也許在想著:春天如此美好,但這野花終究會凋謝,我何不在它青春盎然的時刻,享受她的芳香呢?
祈禱靈魂的安靜。祖母的那一刻,表述的就是這樣的意象。普羅提諾自然不認識我的祖母,但他知道同我的祖母一樣的與他同時代的許多普通的人:男人和女人,高貴的或者低賤的。無論是誰,只要靈魂還生活在純粹的本質世界之中,它就不曾與生活在這同一個世界之中的其他靈魂分離開來;但是只要它一旦與一個身體結合在一片,它就有了要管理較自己為低的事物的任務,而且由于有了這一任務它便與其他的靈魂分離開來,其他的靈魂也各有其他的身體。除了少數人在少數的時刻而外,靈魂總是束縛于身體的。
我一直在尋找著一種安靜的生活,但這太難了。太多的無奈,太多的嘈雜,太多的瑣事困擾著我的身子,壓迫著我的神經。逃離生活,這幾乎是不可能的。只要我的肉體還存在,它就會向我索要物質的東西。唯一的辦法是:減少物欲,躲避嘈雜,只留下生命所需的基本保障。然后,拓展自己的內心世界的空間,向書本、向文字、向大自然索取自己的所需。其實,按照普羅提諾的說法,安逸的生活也就在那里,每一個生存對于任何另一個生存都是通明透亮的,無論是在廣度上還是在深度上;光明是通過光明而進行的。他們每一個的自身之中都包含著一切,并且同時又在另外的每一個之中都見到了一切,所以處處都有一切,一切是一切而每一個又是一切,這種光榮是無限的。他們每一個都是偉大的;微小的也是偉大的;太陽是一切的星,而每一座星又都是一切的星與太陽。每一種里面都以某種存在方式為主導,然而每一種又都彼此反照著一切。
太陽反照我的內心。這就是我多年來生活的基本規律。陽光進入我的心靈,燦爛,而且包容了一切。陽光下的一切,透明,燦亮,黑暗和煩惱,苦痛和齷齪,一切都被它化為烏有。
普羅提諾既是一個終結又是一個開端——就希臘人而言是一個終結,就基督教世界而言則是一個開端。對于被幾百年的失望所困擾、被絕望所折磨的古代世界,普羅提諾的學說也許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卻不是令人鼓舞的。但對于粗鄙的、有著過剩的精力而需要加以約束和指導但不是加以刺激的野蠻人的世界來說,則凡是普羅提諾教導中能夠引人深入的東西都是有益的,因為這時候應該加以制止的壞東西已經不是萎靡而是粗暴了。把他的哲學中可以保存的東西流傳下來的這項工作,是由羅馬末期的基督教哲學家們來完成的。
從3世紀開始,新柏拉圖主義一直是希臘—羅馬世界的主導哲學,直到公元6世紀,當時的羅馬皇帝查士丁一世關閉異教的學園為止。但即使在此后,它仍然不絕如縷,直到642年伊斯蘭教入侵亞歷山大里亞,普羅提諾在羅馬開課授徒。他建立了一整套自己的哲學體系,而且在他的著作中,比較詳細地闡述了自己的美學思想。
通過基督教神學家們的宣傳,普羅提諾深刻地影響了中世紀歐洲的美學思想和審美趣味,并對長期內歐洲的宗教藝術的發展,起了相當大的支配作用。因此,他在西方美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就取決于此。
我感興趣的是,普羅提諾的哲學思想中國古代老子竟一脈相承。老子騎青牛出關時,被關令尹喜所阻,被迫留下五千言以過關。這本短短五千言的著作,是我國道家學派和道教最著名的一部經典。它綜羅百代,廣博精微,短短的五千文,以“道”為核心,構建了上至帝王御世,下至隱士修行,蘊涵著無比豐富的哲理體系,而其中所涵括的美學思想,對我國兩千余年的文化藝術影響深遠。而老子的“道”在概念指定上,與普羅提諾的“太一”極其相似。老子認為“道”是指形而上的道,《老子》一書開頭第一句話便是“道可道,非常道”。可以說老子在對宇宙萬有,生命本源的定義上,有和普羅提諾一樣的態度———不可言說。老子所說的“道”不是物質實體,而恰恰相反,它是產生整個物質世界的總根源,是超越了物質與精神的一種狀態。在老子看來,“道”是第一性的,而世界萬物是從“道”派生出來的,是第二性的。因此老子稱:“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同樣,在普羅提諾看來,“物體之所以美,是由于它分有了來自神的理性”。
想要了解普羅提諾的身世的人往往會失望。他從未告訴過任何人他的出生日期,因為他不想有人紀念或慶祝他的生日。對于哲人而言,關注生年遠比關注生日重要。人們所知道的,是他二十八歲產生了學習哲學的沖動。為此他常常滿心悲哀地逃課,因為老師所講的,根本不是自己想要的東西。還有他的一些細節,譬如寫文章從不仔細檢查,因為視力很差;他并不看重字是否寫得漂亮,也不注重音節、拼寫,只是全身心地沉醉于思想之中;他早年能寫很漂亮的毛筆字,晚年已無暇顧及寫字;他講話的時候,滿臉都被理智之光照亮;他的外表原本就富有魅力,在講話時更顯得動人心魄。在他的身上,人們可以洞察到一顆偉大的靈魂,公義的的生活,純潔的道德,高尚的語氣,尊嚴、端莊伴隨著無畏、鎮靜、安寧的氣質,以及照耀在這一切之上的神圣的理想之光。
祖母臨終時的情景,我是目睹了的。我的少年的夜晚,是陪著祖母度過的。煤油燈的光影里,祖母在搖著紡車。吱呀吱呀的響聲,宛若她心靈里的聲音。油燈燃完了最后一滴油,祖母紡完了最后一根線,頭靠在土墻上歇息,一直到我清晨醒來,她依然是那個樣子。再后來,我才明白了,祖母再也不會醒來。油燈、土炕、土墻,成為安置祖母靈魂的物象。多少年之后,當我知道了普羅提諾,我才恍悟,祖母倚著土墻死去,其實是一種祈禱心靈安靜的方式。
責任編輯 盧悅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