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想象與隱喻:胡塞爾的圖像意識分析①
朱 全 國
(中南民族大學(xué)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4)
感知、想象與隱喻:胡塞爾的圖像意識分析①
朱 全 國
(中南民族大學(xué) 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湖北 武漢 430074)
摘要:感知是圖像意識產(chǎn)生的基礎(chǔ),從感知出發(fā),胡塞爾的圖像意識可以分為三類,即建立于感知上的圖像意識、建立于想象基礎(chǔ)上的圖像意識、在想象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對對象的整體把握的圖像意識。胡塞爾在討論話語形式時(shí)總是強(qiáng)調(diào)形象化,多次將其放到圖像意識的討論之中。胡塞爾對話語形式的分析同樣也適用于圖像意識,并且可以從三種話語表述形式中分離出三種不同的圖像表述方式:象征性圖像表述、現(xiàn)實(shí)感知基礎(chǔ)上的圖像表述、類似于現(xiàn)實(shí)感知基礎(chǔ)上的圖像表述。正是在這種對比關(guān)系中,語言符號意識與圖像意識顯示出區(qū)別:在語言符號意識行為中,認(rèn)識行為與直觀行為的結(jié)合使語詞成為意向的統(tǒng)一體并進(jìn)而產(chǎn)生意義;在圖像意識行為中,人們首先面對的是一些形象化的元素。圖像意識行為強(qiáng)調(diào)相似性的作用,而語言符號則不強(qiáng)調(diào)相似性。語言符號與構(gòu)成圖像的符號在立義方式上不同,前者依托于相鄰性,后者則借助于相似性。
關(guān)鍵詞:胡塞爾;圖像意識;感知;想象;隱喻
胡塞爾不僅開創(chuàng)了意識現(xiàn)象學(xué),對于現(xiàn)象學(xué)運(yùn)動具有奠基之功,同時(shí)也為人們理解自身與世界提供了新的思路與方法。圖像意識是他關(guān)于意識分析的非常重要的內(nèi)容,他對圖像意識的分析為當(dāng)代藝術(shù)研究提供了眾多啟示。正如倪梁康在《圖像意識的現(xiàn)象學(xué)》中所指出的那樣:“每一個(gè)圖像意識都本質(zhì)地含有三種客體以及與此相關(guān)的三種立義。他認(rèn)為在這三種客體和三種立義之間存在著本質(zhì)的聯(lián)系。”[1]很顯然,胡塞爾的圖像意識是一個(gè)十分龐大的認(rèn)識系統(tǒng),涉及感知、想象、客體、意識、直觀、非直觀等一系列問題。
一、感知:從表象到圖像
胡塞爾認(rèn)為,人們可以把包括表象在內(nèi)的任何一種行為表述出來,這一切表述就存在于與之相應(yīng)的話語形式之中。這些表述并不只是局限于對感知的表述,還可以對精神層面進(jìn)行表述。“表述可能具有純粹象征的功能。精神的表述,亦即須表述的行為的思想對應(yīng)圖像,就附著在語言表述上并且與它一同復(fù)活,即使那個(gè)行為本身并未由理解者進(jìn)行。我們無須自己進(jìn)行感知就可以理解一個(gè)對感知的表述,無須自己詢問就可以理解一個(gè)對問題的表述,如此等等。”[2]9可見,表述行為可以分為感知層面的表述和精神層面的表述兩個(gè)部分。無論哪個(gè)層面的表述行為都涉及兩個(gè)方面:一是對于外部的事物的判斷,二是基于自身體驗(yàn)的判斷。話語的含義由這種判斷構(gòu)成,而不是由構(gòu)成話語的語詞的意義來形成;同時(shí),對于外部事物的判斷并不由外部事物本身來形成,而是由構(gòu)成這些事物的表象來協(xié)助完成。從表象的角度出發(fā)來看構(gòu)成判斷的事物,使其具有雙重身份,一方面這些表象的確指向外在事物,但另一方面卻又屬于人們意識的范圍。
在胡塞爾的表象行為里,既包含了感知、想象、回憶、期待,同時(shí)也包含了圖像意識與符號意識。感知是表象行為的基礎(chǔ),它本身不斷發(fā)生變化,但無論如何變化,有一點(diǎn)是可以肯定的,即感知與表象行為之間具有聯(lián)系。另一種情況也必定會引起人們的注意,并不是所有表象行為中一直伴隨著感知,如人們看一幅圖畫時(shí),表象行為并不是由對構(gòu)成圖畫的事物的現(xiàn)實(shí)實(shí)存世界本身的感知構(gòu)成,而是借助于想象通過直觀來達(dá)到形象化,進(jìn)而完成表象行為。“感知不僅可以變換,而且可以消失,而在此同時(shí)表述卻不會停止它所始終具有的意指功能。聽者不必向花園看便可以理解我的語詞和整個(gè)語句;只要他信任我的真實(shí)性,他無須感知便可以得出同一個(gè)判斷。也許他具有通過想象而完成的某種形象化,也許他不具有這種形象化。”[2]15就話語而言,無論是否具有感知,也無論是否通過形象化,表述的意指都可以使人們獲得意義;就圖像而言,表象行為則往往伴隨著形象化,進(jìn)而達(dá)到意義的傳達(dá)。“聽者并不感知花園,但他也許熟悉這個(gè)花園,直觀地表象這個(gè)花園,將那個(gè)被表象的烏鶇以及被陳述的過程置入到花園之中,并由此根據(jù)說者的意向而借助于單純的想象圖像來完成一個(gè)相同意義的理解。”[2]17
很顯然,感知對于圖像意識的產(chǎn)生具有根本性的作用,但感知屬于第一性的意識,在這一點(diǎn)上不同于圖像意識。對一個(gè)對象而言,感知本身并不包含意義,但感知本身卻規(guī)定了意義。感知行為與意向、意指緊密相連,從而使之有可能建立起產(chǎn)生新的意義的秩序。如人們在一幅畫中看到一些曲線,看這個(gè)行為本身并不具有什么特別的含義,但看的方式與為何而看這樣的行為卻賦予了這些曲線以意義。當(dāng)人們的感知行為規(guī)定了這些曲線一些意向或意指時(shí),這些曲線就被統(tǒng)一于這些意向或意指之中,如這些曲線可能表現(xiàn)的是水面。這里面包含了三個(gè)過程:首先是感知;其次是在感知基礎(chǔ)上形成的意向秩序;最后是這些意向秩序所體現(xiàn)的意義指向現(xiàn)實(shí)中與之相關(guān)的事物。
與感知結(jié)合在一起的是體驗(yàn),甚至可以說體驗(yàn)涵蓋了感知。“在體驗(yàn)本身之中的不是對象,而是感知,是這樣或那樣的心緒;因此,體驗(yàn)中的認(rèn)識行為建立在感知行為的基礎(chǔ)上”[2]24,“體驗(yàn)構(gòu)造著一個(gè)認(rèn)識,這個(gè)認(rèn)識以確定的、素樸的方式一方面與表述體驗(yàn)、另一方面與有關(guān)感知融合在一起”[2]25。體驗(yàn)所形成的認(rèn)識行為使人們把某一事物認(rèn)識為某物,這一點(diǎn)在胡塞爾看來同樣適用于圖像,他說:“圖像地顯現(xiàn)出來的客體,例如在想象和回憶中的同一個(gè)墨水瓶,是稱謂表述的可感受的載者。從現(xiàn)象學(xué)上說,這就意味著,一個(gè)與表述體驗(yàn)相結(jié)合的認(rèn)識行為以這樣一種方式與圖像化行為相聯(lián)系,我們將這種方式客觀地稱作對圖像地被表象之物的認(rèn)識,例如對我們的墨水瓶的認(rèn)識。”[2]25很顯然,圖像是人們體驗(yàn)和認(rèn)識行為的結(jié)果,這一結(jié)果建立于感知的基礎(chǔ)之上,它指向現(xiàn)實(shí)之物,卻不同于現(xiàn)實(shí)之物。圖像客體是人們認(rèn)識與體驗(yàn)的精神產(chǎn)物,此時(shí)的圖像意識顯然已經(jīng)不完全屬于第一性意識的直觀性行為,而是屬于第二性意識的非直觀行為,更確切地說,圖像是屬于想象的。“因?yàn)閳D像客體在這個(gè)表象中絕對什么都不是,這個(gè)體驗(yàn)毋寧說是某個(gè)由想象材料(想象-感覺)組成的結(jié)合體,它滲透了一定的立義行為特征。體驗(yàn)這個(gè)行為與具有一個(gè)對對象的想象表象,這兩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2]25
上述討論顯示出感知本身的復(fù)雜性,其復(fù)雜性也決定了胡塞爾圖像意識的多層面性*肖偉勝在《視覺文化與圖像意識研究》一書的“圖像意識的認(rèn)識論”部分論述現(xiàn)象學(xué)的圖像意識時(shí),給出了一個(gè)明晰的結(jié)論,他結(jié)合海德格爾、胡塞爾等人關(guān)于感知的認(rèn)識,認(rèn)為現(xiàn)象學(xué)的感知可以分為四個(gè)層面,即本源性感知、簡捷性感知、符號感知、圖像感知,在此基礎(chǔ)上形成了以感知表象、想象表象、符號表象、圖像表象為基礎(chǔ)的四種圖像意識。這四種圖像意識構(gòu)成了廣義的圖像意識。參見:肖偉勝《視覺文化與圖像意識研究》,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1年版。。胡塞爾的感知至少具有三個(gè)層面:一是建立在與對象直接關(guān)系基礎(chǔ)上的物理感知,它感知的是對象的物理性質(zhì);二是建立在與圖像關(guān)系上的想象感知,它感知的是與對象相似的圖像;三是建立在對對象整體之上的整體感知,它感知的是對象的整體。這一點(diǎn)從倪梁康對胡塞爾的圖像客體的討論中可以得到清楚的認(rèn)識。倪梁康認(rèn)為胡塞爾的圖像意識體現(xiàn)出來的圖像客體具有三種類型:第一類是圖像的“物理客體”,主要是指圖像的物理性質(zhì),如顏色、紙張等,即“圖像事物”;第二類是指作為精神產(chǎn)物的圖像,這是與“物理客體”相對應(yīng)而存在的“精神圖像”,是整個(gè)呈現(xiàn)于人們眼前的圖像,即“圖像客體”;第三類是“被展示的客體”,即“圖像主題”。“我們也可以用一句話來描述圖像意識的這個(gè)結(jié)構(gòu):這個(gè)印刷的紙或這個(gè)加框的油布等等(圖像事物)是關(guān)于這個(gè)或那個(gè)東西(圖像主題)的圖像(圖像客體)。”*倪梁康《圖像意識的現(xiàn)象學(xué)》對“圖像意識中的三種客體”“圖像意識中的三種立義”“圖像事物和圖像客體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相應(yīng)立義之間的關(guān)系”“圖像客體與主題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相應(yīng)立義之間的關(guān)系”進(jìn)行了深入分析,本文此處表述及術(shù)語皆參照此文。。我們也要看到,這三種類型的客體是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的,“圖像事物”是產(chǎn)生“圖像客體”的基礎(chǔ),而“圖像客體”則體現(xiàn)出“圖像主題”。如果不存在著“圖像事物”,那么“圖像客體”就成為無本之木,更談不上“圖像主題”了。
在分析了胡塞爾的感知與圖像意識之間的關(guān)系后,一個(gè)問題緊接著就擺在了人們面前:這些“圖像事物”是如何在一起形成“圖像客體”并進(jìn)而展現(xiàn)出“圖像主題”的?這涉及胡塞爾現(xiàn)象學(xué)所提出的意指、充實(shí)、意向等相關(guān)論述。充實(shí)在胡塞爾那里呈現(xiàn)為靜態(tài)充實(shí)與動態(tài)充實(shí)。在靜態(tài)充實(shí)中,各種“圖像事物”具有相對固定的意義,這取決于人們的體驗(yàn)與認(rèn)識行為的結(jié)果,如人們用波浪式的曲線表示水,水就成為用曲線所體現(xiàn)出來的東西,曲線就成為從屬于被意指的水的存在,并且與水合為一體。很顯然,曲線在這里具有象征的意味——它成為水的象征,而這種象征意味就是人們體驗(yàn)與認(rèn)識的結(jié)果。胡塞爾在分析“語詞的普遍性”時(shí)指出:“語詞的普遍性也就意味著,同一個(gè)語詞通過它所具有的統(tǒng)一意義而包容著(或者,如果這有所背謬的話,也可以說,‘偽稱是’包容著)一個(gè)在觀念上受到固定限制的可能直觀的雜多性,以至于這些直觀中的每一個(gè)都可以作為一個(gè)同等意義的稱謂認(rèn)識行為之基礎(chǔ)來起作用。”[2]28這種觀點(diǎn)對圖像意識同樣有效,“圖像事物”有許多基本的顏色、線條,本身就具有普遍性的意義,它可以使人們在具體事物并不在場的情況下而被理解。這種“圖像事物”所具有的普遍性既是認(rèn)識的、體驗(yàn)的,同時(shí)也是想象的結(jié)果,因?yàn)樗鼈冸m然并不屬于一個(gè)特定的感知行為,但在意指對象時(shí)又具有直觀性。
動態(tài)充實(shí)不同于靜態(tài)充實(shí),在動態(tài)充實(shí)中,各個(gè)認(rèn)識行為在時(shí)間上不具有一致性,這就使其意向充實(shí)處于過程狀態(tài),而不像靜態(tài)充實(shí)那樣意向已經(jīng)被充實(shí)。正是基于這樣的區(qū)別,動態(tài)充實(shí)就伴隨著對“圖像事物”的“同一性意識”“同一性體驗(yàn)”以及“認(rèn)同行為”。“在現(xiàn)象學(xué)上,從行為方面來看被描述為充實(shí)的東西,從兩方面的客體,即被直觀到的客體這一方面和被意指的客體另一方面來看則可以被表述為同一性體驗(yàn)、同一性意識、認(rèn)同行為;或多或少完善的同一性是與充實(shí)行為相符合并在它之中‘顯現(xiàn)出來’的客體之物。”[2]33在這一過程中,相似性因其具有的指向?qū)ο笾锏奶攸c(diǎn)使這種認(rèn)同行為成為可能。“這是在關(guān)于認(rèn)識的說法中表述出來的對同一事態(tài)的又一不同指辭。含義意向以充實(shí)的方式與直觀達(dá)成一致,正是因?yàn)檫@個(gè)狀況,那個(gè)在直觀中顯現(xiàn)的、為我們所原初朝向的客體才獲得了被認(rèn)識之物的特征。”[2]33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已經(jīng)可以部分得出胡塞爾對于圖像意識的一些認(rèn)識了:建立于感知基礎(chǔ)上的表象行為屬于人們的表述行為,它涉及感知的表述,也涉及精神層面的表述;感知的復(fù)雜性決定了胡塞爾所討論的圖像意識的多層面性;感知是圖像意識產(chǎn)生的基礎(chǔ),結(jié)合了人們的體驗(yàn)與認(rèn)識行為,屬于第一性的意識;圖像意識既具有直觀性的感知屬性,也具有非直觀性的精神屬性。
二、想象:圖像意識與語言符號意識
胡塞爾在對意識行為進(jìn)行分析時(shí),其對象主要集中于圖像意識與以語言為代表的符號意識。這兩種符號意識都具有想象的屬性,在意識行為里,兩者既有共同之處,同時(shí)也體現(xiàn)出各自的不同,這就從某種程度上體現(xiàn)出了圖像意識與語言符號意識之間的差別。
語言在胡塞爾的現(xiàn)象學(xué)分析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分析的對象雖然包含了語言與圖像兩個(gè)方面,但從所舉的例子來看,絕大部分屬于語言方面。不過要指出的是,雖然絕大部分例子屬于語言,但并非意味著他的分析對于圖像無效,兩者都是表象行為的部分,都屬于想象,只不過兩者在表述行為的方式上存在著差異。胡塞爾首先分析了話語的三種表述行為。他認(rèn)為,人們可以把任何一種行為表述出來,話語的形式、句式、名稱、陳述等都可以用恰當(dāng)?shù)姆绞秸宫F(xiàn)出所要表述的意義。盡管所有行為都是可以表述的,但并不意味著所有行為因此也都起著含義承載者的作用,這是因?yàn)楸硎鲂袨槭嵌嗔x的,如果表述行為不能夠得到統(tǒng)攝,如沒有在形式或內(nèi)容上得到統(tǒng)一的認(rèn)識,那么它就不可能形成較為明晰的意義。
他提出的第一種話語表述行為是象征性的話語表述,這種話語形式中的語詞與所指的意義結(jié)合在一起,話語本身就構(gòu)造意義,無需人們進(jìn)行感知便可以直觀地顯示意義。胡塞爾提出的第二種話語表述行為主要是指“我們指稱那些我們正在體驗(yàn)的行為并且借助于這種指稱來陳述我們對這些行為的體驗(yàn)”[2]10-11。體驗(yàn)本身具有超越性,既可以是對事物的體驗(yàn)又可以是對內(nèi)心的體驗(yàn),基于體驗(yàn)的判斷形成了語句的意義。這就意味著體驗(yàn)本身并不產(chǎn)生含義,含義產(chǎn)生于對體驗(yàn)的判斷。這種話語表述行為可稱為“以述謂的方式剛剛體驗(yàn)過的行為”。第三種話語表述行為是“從屬于相關(guān)行為的判斷活動或客體化活動”[2]12,這種行為并不是對行為本身進(jìn)行判斷,而是在行為基礎(chǔ)上的判斷。藝術(shù)品往往就呈現(xiàn)為這樣一種話語表述行為。表述行為中所呈現(xiàn)出來的感知并不是對現(xiàn)實(shí)的感知,而是類似于對現(xiàn)實(shí)的感知,話語所體現(xiàn)出來的只是與現(xiàn)實(shí)的感知相符合而已。這是一種基于想象的表述行為:“我們在這里可以考慮這樣一些狀況:在沉浸于一組想象的同時(shí),我們在正常的陳述中如此地指稱那些顯現(xiàn)給我們的東西,就好像它們是被感知的一樣;我們也可以考慮那種報(bào)告敘述的形式,在此形式中,童話詩人、小說家等等不是對現(xiàn)實(shí)的事件,而是對他藝術(shù)想象的創(chuàng)造‘進(jìn)行陳述’。”[2]13以感知為中心,胡塞爾實(shí)際上認(rèn)為話語表述行為體現(xiàn)出意義的三種方式:一是通過語詞的象征性而使話語的意義顯現(xiàn)出來,這里并不涉及感知;二是通過感知,以愿望與判斷相結(jié)合的方式使意義呈現(xiàn)出來;三是通過類似于現(xiàn)實(shí)感知的想象使意義呈現(xiàn)出來。
除了第一種話語形式的意義相對較固定外,第二種和第三種話語形式的表述——無論是直接建立于感知的基礎(chǔ)之上還是建立于類似于感知的基礎(chǔ)之上——都與感知有關(guān)系。但建立于感知基礎(chǔ)上的意義卻因?yàn)楦兄袨榈牟煌尸F(xiàn)出不同的意義。進(jìn)行感知的人由于自身以及所處境況的不同,感知也就不同,這就使感知行為所產(chǎn)生的意義呈現(xiàn)出多樣性。但這并不意味著事物或?qū)ο蟮囊饬x不可捉摸,由于作為感知的對象是同一事物,這就使所有的感知行為與所要感知的對象聯(lián)系在一起,從而使所有的感知行為獲得了相對統(tǒng)一的意義。如人們對一棵樹的感知,可以從不同的行為著手,如顏色、形狀等,但這些感知行為都與所要感知的樹聯(lián)系在一起,它們與樹之間存在著各種意向關(guān)系,并在這棵樹中實(shí)現(xiàn)了統(tǒng)一。
基于胡塞爾在討論話語形式時(shí)總是強(qiáng)調(diào)其形象化,并且多次將其置于圖像意識的討論之中,人們可以清晰地看到,胡塞爾對話語形式的分析同樣也適用于圖像意識。我們可以從他的三種話語形式中分離出三種不同的圖像表述方式。胡塞爾的圖像意識具有多重含義,它有時(shí)泛指精神圖像,有時(shí)指物質(zhì)存在的圖像,有時(shí)又指實(shí)物,這就決定了在對其話語表述方式與圖像表述方式的對應(yīng)分析中,圖像意識所體現(xiàn)的層面有所不同。
第一種圖像表述行為與象征性的話語表述行為對應(yīng),可稱為象征性圖像表述。一個(gè)線條,一種顏色,一件事物,在被人們長期進(jìn)行某種有目的的意義賦予后,就具有了相對固定的意義。要承認(rèn)的是,最開始人們賦予它們意義時(shí)是在感知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但當(dāng)意義開始固定時(shí),感知行為就逐漸退場,意義的固定意味著感知最終出局。當(dāng)這些意義固定的線條、顏色、事物等出現(xiàn)于人們眼前時(shí),人們無需感知就可以直觀地發(fā)現(xiàn)其意義。第二種圖像表述行為與“以述謂的方式剛剛體驗(yàn)過的行為”的話語表述方式相對應(yīng)。對這種圖像對象的理解是建立于感知尤其是體驗(yàn)的基礎(chǔ)上的,同時(shí)結(jié)合了人們的愿望與判斷,如當(dāng)一個(gè)圖像對象呈現(xiàn)出來,就包含了人們的期待及感知行為對圖像意義的理解。第三種圖像表述行為與話語“從屬于相關(guān)行為的判斷活動或客體化活動”的話語表述行為相對應(yīng)。這里面并不直接涉及現(xiàn)實(shí)感知,而是以“類似于現(xiàn)實(shí)感知的想象”為基礎(chǔ)。如人們面對“圖像客體”時(shí)所形成的與現(xiàn)實(shí)事物之間的相似性想象。
要指出的是,上述關(guān)于話語表述行為與圖像表述行為之間的對應(yīng)關(guān)系并不意味著在語言符號意識或圖像意識中存在著這樣三個(gè)階段。在具體作品的表述中,無論是話語表述還是圖像表述,這三個(gè)階段都是綜合性的存在。象征性的表述行為、基于現(xiàn)實(shí)感知的表述行為與想象性的類似于現(xiàn)實(shí)感知的表述行為在同一個(gè)作品中可能同時(shí)存在,只不過人們在理解時(shí)感知所處的地位不同,因此意義產(chǎn)生的方式也不同。同時(shí),感知方式的不同也使得意義有所不同。盡管感知的地位、方式有所不同,但當(dāng)面對同一作品時(shí),感知行為最終總是要與這一對象聯(lián)系在一起,這就使多樣的感知行為獲得了相對統(tǒng)一的意義,作品的意義也就呈現(xiàn)出來了。
上面所分析的是圖像意識行為與語言符號意識行為所具有的共同性,那么兩者之間有什么區(qū)別呢?胡塞爾對這一問題有著自己深刻的看法,從他的相關(guān)表述中,人們可以看到如下三點(diǎn)差別:
第一,是話語形式中的語詞與圖像符號在面對對象物時(shí)所呈現(xiàn)出來的差別。在話語形式中,語詞之所以與對象物產(chǎn)生聯(lián)系是由于語詞中所包含的認(rèn)識行為,認(rèn)識行為與直觀行為的結(jié)合使語詞成為意向的統(tǒng)一體進(jìn)而產(chǎn)生意義。在圖像意識行為中,人們首先面對的是“圖像事物”,這些“圖像事物”本身具有一些形象化的元素。如果我們不考慮語言文字的象形因素——事實(shí)上語言文字的象形因素在現(xiàn)實(shí)中已經(jīng)弱化到幾乎無法意識的地步了——那么語詞給人們的更多地是象征意味,如“水”這個(gè)詞,在人們面對它時(shí)更多地是與較為寬泛的概念聯(lián)系在一起的,而不是與這個(gè)詞最初的形象聯(lián)系在一起。這一點(diǎn)在以字母為基礎(chǔ)的語言中表現(xiàn)得尤其明顯。而在“圖像事物”中,形象化是最主要的特征,如人們在面對一個(gè)線條時(shí),這個(gè)線條就具有十分明顯的形象化特點(diǎn)。
第二,圖像意識行為與語言符號意識行為相比較而言,圖像意識行為強(qiáng)調(diào)相似性的作用,而語言符號則不強(qiáng)調(diào)相似性。胡塞爾說:“任何一個(gè)通過直觀意向而完成的對一個(gè)符號意向的充實(shí)都具有認(rèn)同綜合的特征。但是反過來卻并不是在每一個(gè)認(rèn)同綜合中都進(jìn)行著一個(gè)恰恰是對含義意向的充實(shí)以及恰恰是通過一致直觀的充實(shí)。”[2]50這說明,符號意向的充實(shí)是建立于直觀意向之上的,兩者結(jié)合形成認(rèn)同綜合的特征,但并不是每一個(gè)認(rèn)同綜合都與符號的含義意向及直觀意向的結(jié)合相對應(yīng)。在廣義上講,雖然每一個(gè)認(rèn)同都可以作為一個(gè)認(rèn)識,但在狹義上來看,認(rèn)同的綜合都具有自己的目的,正是這一認(rèn)同的目的性使每一個(gè)認(rèn)同綜合與符號的含義意向及直觀意向具有雙向?qū)?yīng)性。那么,是什么決定了認(rèn)同的目的性呢?胡塞爾將其歸于“客體化行為的領(lǐng)域”,“在較狹窄和最狹窄意義上的所有的認(rèn)識統(tǒng)一的起源地,都是在客體化行為的領(lǐng)域之中”[2]50-51。客體化的行為使在感知與想象基礎(chǔ)之上的符號意向得到充實(shí),并構(gòu)建起自身的表述行為。非客體化的行為則不具有這些特點(diǎn),因?yàn)樗鼈儫o法形成認(rèn)識上的統(tǒng)一。正是在客體化的行為中,胡塞爾對圖像與符號進(jìn)行了比較,由于他提到的符號主要是語言,所以對圖像與符號之間的比較其實(shí)就是圖像與語言符號之間的比較,符號在標(biāo)示事物時(shí)并不體現(xiàn)出相似性的獨(dú)特地位,因?yàn)榉柤瓤梢耘c所標(biāo)示的事物相似,也可以不相似。圖像則不然,圖像“通過相似性而與實(shí)事相聯(lián)系,如果缺乏相似性,那么也就談不上圖像”。就相似性本身來說,它意味著判斷與認(rèn)識。作為圖像而言,它是人們在面對客觀事物或?qū)ο髸r(shí),通過判斷與認(rèn)識行為形成的結(jié)果,“它的顯現(xiàn)為‘圖像’的對象便通過相似性而被認(rèn)同為在充實(shí)行為中被給予的對象”[2]53。
第三,語言符號與構(gòu)成圖像的符號在立義的方式上是不同的,前者借助于相鄰性,后者借助于相似性。當(dāng)人們感知到語言符號時(shí),圍繞這些符號形成一系列意義,它們共同充實(shí)著認(rèn)識行為,人們可以直接從符號進(jìn)入到意義之中,在這些認(rèn)識行為中構(gòu)建起自己的意義世界。但在圖像中則不然,構(gòu)成圖像的符號如線條等,當(dāng)置于圖像的整體時(shí),它們與其他構(gòu)成圖像的符號一起成為一個(gè)意向的統(tǒng)一體,認(rèn)識行為通過相似性使想象得到充實(shí)。這就事實(shí)上明確地暗示了語言與圖像之間的差別在于:語言符號并不是泛指話語系統(tǒng),而是構(gòu)成話語形式的語詞;圖像符號并不是指圖像本身,而是構(gòu)成圖像的線條、顏色等可以直接感知的東西。不過,從話語系統(tǒng)與圖像的整體立義來看,話語系統(tǒng)的意義是由語言符號組成的系列而產(chǎn)生的,圖像意義則是在由構(gòu)成圖像的那些符號所形成的意向統(tǒng)一體的基礎(chǔ)上產(chǎn)生的。胡塞爾說:“客體化行為的所有現(xiàn)象學(xué)區(qū)別都可以被回歸到建構(gòu)著它們的基本意向和充實(shí)之上,這些意向和充實(shí)是通過充實(shí)綜合而得以統(tǒng)一的。而在意向方面的唯一最終區(qū)別便是在符號意向和想象意向之間的區(qū)別,前者是通過相鄰性而形成的意向,后者是由相似性而引發(fā)的意向。”[2]60-61語言符號可以表現(xiàn)實(shí)物,但在這兩者之間還夾雜著語詞的含義,這就意味著語言符號所引起的對實(shí)物的認(rèn)識必然借助于語詞的含義,從語言符號到實(shí)物之間是通過相鄰性而實(shí)現(xiàn)的。圖像所引起的對實(shí)物的認(rèn)識則是借由圖像與對象之間的相似性而實(shí)現(xiàn)的。
三、圖像化與隱喻:語言與圖像之間關(guān)系的進(jìn)一步認(rèn)識
圖像化是胡塞爾不斷提及的一個(gè)詞語,無論是在語言符號還是圖像符號中都涉及圖像化。他的圖像意識行為包含了感知與想象,其中感知又構(gòu)成了想象的基礎(chǔ)。語言符號意識和圖像意識屬于非直觀行為,非直觀行為又是建立在直觀行為基礎(chǔ)之上的,在語言符號意識與圖像意識里都存在著圖像化行為。
當(dāng)人們面對語詞“樹”的時(shí)候,可能首先喚起的經(jīng)驗(yàn)就是關(guān)于樹的一般性的特征,就是這個(gè)東西具有構(gòu)成樹的要素,這些要素就成為樹的含義。可以作如下設(shè)想:最初人們形成樹的含義或觀念時(shí)并不是憑空產(chǎn)生的,而是在體驗(yàn)的基礎(chǔ)上達(dá)到對樹的認(rèn)識,人們最初體驗(yàn)的樹必然是一些具體的物理存在的樹。但隨著對樹的一般性要素的把握,樹的較為普遍的意義形成了,最終當(dāng)人們提到樹的時(shí)候,形象性弱化了,只余下含義與概念性的存在。語言符號也因此具有某些程度上的象征性,從圖像意識來看,語詞體現(xiàn)出象征性的圖像意識。這些現(xiàn)象在語言符號的文字中體現(xiàn)得十分明顯,如在中國的象形文字中,人們還可以看到形象化在文字中的部分留存。但在絕大部分漢字中,人們已經(jīng)很難看到其形象化的一面。在西方以語音為主的語言中,形象化就更難覓其蹤影了。因此,作為無客體化行為的語詞而言,其意向具有無限的可能性,是一種自在的存在。
但是,當(dāng)人們提到“這棵樹”時(shí),相對于“樹”而言情況則有所不同。這里包含了明確的指向,是這棵樹而不是其他的樹。于是,樹就從一般性含義之中脫穎而出,在具有明確指向的同時(shí)被賦予客體化的行為。而客體化行為在上面人們只提到“樹”時(shí)并不具備,只有在“這棵樹”出現(xiàn)時(shí)才出現(xiàn)。客體化的行為伴隨著感知與認(rèn)識行為,感知與認(rèn)識也在此時(shí)浮現(xiàn)出來。在“樹”的基礎(chǔ)上形成的所有意向關(guān)系,在此時(shí)找到了意向的統(tǒng)一,在這個(gè)客體化過程中得到了較穩(wěn)定的秩序。于是,關(guān)于這棵樹的經(jīng)驗(yàn)、體驗(yàn)與認(rèn)識,使語言符號“這棵樹”的意向關(guān)系得到充實(shí),在想象的基礎(chǔ)上,這棵樹得到圖像化。并且,意向關(guān)系越充實(shí),關(guān)于這棵樹的形象就越逼真,圖像化就越完善。
就單個(gè)語詞而言,每一個(gè)語詞的客體化行為都會形成含義或判斷,這些含義與判斷都包含于述謂的表述行為之中,并形成相應(yīng)的圖像化。當(dāng)語句形成話語形式時(shí),每一個(gè)相應(yīng)的表述行為都被統(tǒng)一于話語這一形式之中,并且在話語形式中再一次被客體化,從而使各個(gè)表述行為單元得到充實(shí),它們之間的意向關(guān)系得到進(jìn)一步充實(shí),話語意義在其中逐漸明晰起來,最終在話語基礎(chǔ)上得到相應(yīng)的圖像化。一部小說,一首詩歌,其話語形式的最終完成,就是伴隨著不斷客體化與圖像化的過程,其意義正是在這種客體化與圖像化的過程中得到實(shí)現(xiàn)的。
在人們面對一個(gè)圖像時(shí),則情況又有所不同。如在面對一幅畫時(shí),首先讓人進(jìn)行感知的是“圖像事物”即畫的顏色、線條形狀以及畫布的大小、圖形的分布等具有物理性質(zhì)的事物。語詞引起的想象最初是由語詞的具有象征性的含義而引發(fā)的認(rèn)識與經(jīng)驗(yàn)構(gòu)成,進(jìn)而被客體化,而“圖像事物”則由這些客體存在的事物引發(fā)想象。構(gòu)成“圖像事物”的每一個(gè)存在本身往往也具有象征意義,如線條的不同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意義,但在圖畫中,這些線條并不是單一地呈現(xiàn)出來的,而是系統(tǒng)地呈現(xiàn)出來。系統(tǒng)呈現(xiàn)使構(gòu)成圖像的事物在一開始就具有意向的同一性,多個(gè)因“圖像事物”而具有的意向關(guān)系在圖像里被系統(tǒng)化與秩序化。與語詞符號最初呈現(xiàn)出的意向關(guān)系的不確定性不同,圖像中的意向關(guān)系在一開始就被統(tǒng)一起來,“圖像事物”作為一個(gè)整體呈現(xiàn)出來而不是作為單一的存在。認(rèn)知、想象等意識行為都是以這個(gè)整體為基礎(chǔ)充實(shí)其中的意向關(guān)系,從而使圖像展現(xiàn)出來,也即是“圖像客體”得以實(shí)現(xiàn)。
很顯然,在圖畫中不僅涉及圖像化,而且還存在著圖像的圖像化問題,并且這些問題都與客體化的行為密不可分。這可以分為兩個(gè)步驟來進(jìn)行說明。在面對“圖像事物”時(shí),客體化的行為充實(shí)了“圖像事物”的意向關(guān)系,并達(dá)成統(tǒng)一,形成“圖像客體”,這是第一個(gè)客體化行為與圖像化行為。當(dāng)“圖像客體”呈現(xiàn)出來時(shí),客體化行為基于相似性的判斷與認(rèn)識,與世界的實(shí)在的物理事物形成新的意向關(guān)系的同時(shí),充實(shí)這些意向關(guān)系從而使“圖像客體”完成對“圖像主題”的表述,這個(gè)過程可以稱為對圖像的圖像化。
如果人們把語詞圖像化與圖像的圖像化的客體化行為所具有的不同置于一邊,僅僅從意義的充實(shí)行為來看,兩者在意義的充實(shí)上具有相似性。胡塞爾說:“在每一類符號意向中都續(xù)接地包含著一個(gè)確定的充實(shí)(或者說,一個(gè)確定的充實(shí)組),而在這個(gè)充實(shí)中重又續(xù)接地包含著一個(gè)確定的充實(shí),如此等等。這種特殊性也可以在某些直觀意向那里找到。當(dāng)我們通過一個(gè)圖像的圖像來表象一個(gè)實(shí)事時(shí)便是如此。”[2]69這個(gè)過程如果用上述術(shù)語來表示就是:符號和“圖像事物”在客體化的行為中得到各自的充實(shí),并形成語詞的圖像化和“圖像客體”(包括圖像的圖像化所形成的圖像客體)單元,這些單元相互結(jié)合并統(tǒng)一起來,最終在后繼的客體化行為中指向話語系統(tǒng)的意義主題和“圖像主題”。
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在“圖像客體”向“圖像主題”轉(zhuǎn)化的過程中,相似性作為一種判斷與認(rèn)識行為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語詞的圖像化過程中起重要作用的是相鄰性。這樣一來,就與人們平常所使用的兩個(gè)術(shù)語——隱喻與轉(zhuǎn)喻——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從話語角度看,隱喻與轉(zhuǎn)喻代表著兩種話語模式,這一點(diǎn)在雅各布遜的《隱喻和轉(zhuǎn)喻的兩極》一文中也得到了很好的說明[3]。隱喻話語模式體現(xiàn)的是以相似性為基礎(chǔ)的模式,轉(zhuǎn)喻話語模式體現(xiàn)的是以相鄰性為基礎(chǔ)的模式。從轉(zhuǎn)喻與隱喻的角度出發(fā),語言符號意識與圖像意識具有與之相應(yīng)的模式。
隱喻的產(chǎn)生,依據(jù)兩個(gè)基本要素:一是相似性,二是替代關(guān)系。當(dāng)在相似性基礎(chǔ)上形成替代關(guān)系時(shí),隱喻的話語模式就成為可能。在話語系統(tǒng)中,兩種模式都存在。不過在不同種類的作品樣式中,占據(jù)主要位置的模式是不同的:在敘事型作品樣式里,如小說、敘事詩,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是轉(zhuǎn)喻;而在表現(xiàn)型作品里,如抒情型的詩歌里,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則是隱喻。就上面的語言符號意識與圖像意識而言,情況也是相似的。在語言符號客體化的行為里,語詞起著最基本的作用,每一個(gè)語詞都可能引起一個(gè)圖像化的行為或判斷行為,它們與其他語詞共同形成系統(tǒng)性的意向關(guān)系,這種意向關(guān)系的形成是在一個(gè)語詞向另一個(gè)語詞的移動中逐漸建立起來的,也即是說,話語的意向關(guān)系的形成是在語詞客體化行為中依據(jù)相鄰性為基礎(chǔ)的。因此,從話語的模式上看它是屬于轉(zhuǎn)喻的。但并不是所有的話語都只是從一個(gè)語詞向另一個(gè)語詞移動,在這些語詞中,有可能一些具有相同意義的但同時(shí)具有不同指稱的語詞往往會形成一個(gè)不同于其他語詞的組合,它們遵循著從一個(gè)語詞向另一個(gè)語詞的過渡,但同時(shí)又體現(xiàn)出相似的含義,它們之間的替代會形成隱喻。在這個(gè)意義上人們可以說,在語言符號意識里,轉(zhuǎn)喻是最基本的話語模式,而隱喻的話語模式則可以看成轉(zhuǎn)喻話語模式的變種。
在圖像意識里,情況則顯得不同。正如上文所說,在圖像意識里,客體化行為往往經(jīng)歷著“圖像事物”的圖像化和圖像的圖像化這樣兩個(gè)階段。與語詞不同的是,這些“圖像事物”雖然都是個(gè)體,但卻以整體的方式呈現(xiàn)于人們面前。人們可以對每一個(gè)“圖像事物”如圖像的線條、顏色等進(jìn)行理解,但卻不可避免地受制于統(tǒng)一意向。正如一幅關(guān)于鳥的畫,各種線條與顏色以及其他物理質(zhì)料構(gòu)成了它的“圖像事物”,盡管每一個(gè)“圖像事物”有可能都具有各自的意義,在客體化行為中都可能形成圖像化,形成各自的“圖像客體”,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因受制于統(tǒng)一的意向,這些建立于不同“圖像事物”基礎(chǔ)之上的“圖像客體”必然要形成一個(gè)統(tǒng)一的“圖像客體”,即圖像的圖像化。不難發(fā)現(xiàn),無論是單純的依據(jù)于某個(gè)“圖像事物”的圖像化,還是依據(jù)于各個(gè)“圖像客體”單元的圖像的圖像化,相似性作為認(rèn)識與判斷都起著主要的作用。如人們之所以把一條波浪線看成水,主要是人們基于對水的日常形態(tài)的認(rèn)識與體驗(yàn),也即是波浪線與水紋具有相似性。同樣,在圖像的圖像化過程中最后形成的“圖像客體”,在客體化行為中同樣與實(shí)物體現(xiàn)出相似性,這也是“圖像主題”得以實(shí)現(xiàn)的原因。當(dāng)“圖像客體”成為與之相應(yīng)的實(shí)物的替代品時(shí),就具有隱喻的屬性。正是在這個(gè)意義上,人們不難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隱喻是圖像的天然屬性。
胡塞爾關(guān)于圖像意識的論述對人們深入理解圖像及其他藝術(shù)具有深刻的啟示:“一個(gè)自在存在的對象永遠(yuǎn)不會是一個(gè)與意識和意識自我無關(guān)的對象。事物,無論是未被看見的事物,還是實(shí)體可能的事物,即不是被經(jīng)驗(yàn)到的,而是可被經(jīng)驗(yàn)的那種事物,或者說,也許可被經(jīng)驗(yàn)到的事物,它們都是周圍世界中的事物。”[4]顯然,他擺脫了人們以往以主客二元對立模式理解圖像與對象的方式,建立起了以意識為中心的理解路徑。就藝術(shù)而言,他實(shí)際上提供了一種新的理解方式。其次,他從現(xiàn)象學(xué)的角度揭示了藝術(shù)作品意義的豐富性。“這些在直觀上清晰地或晦暗地、明顯地或不明顯地共同呈現(xiàn)的東西(它們構(gòu)成了實(shí)際知覺場的一個(gè)常在的邊緣域),并未窮盡一個(gè)在我覺醒時(shí)被我意識到‘在身邊’的世界。相反,在其存在的固定秩序中,它伸向無限。現(xiàn)時(shí)被知覺的東西,多多少少清晰地共在的和確定的(或至少某種程度上確定的)東西,被不確定現(xiàn)實(shí)的被模糊意識到的邊緣域部分地穿越和部分地環(huán)繞著。”[5]人們所明了和知曉的作品意義是人們已經(jīng)知覺到的意義,還有豐富的意義存在于意識之中有待人們發(fā)現(xiàn),正如有學(xué)者所指出:“胡氏認(rèn)為,邏實(shí)論和科學(xué)主義恪守了絕對客觀主義的哲學(xué)立場,其實(shí)質(zhì)是遮蔽了人生存于其中的生活世界的基礎(chǔ)地位,取消了人的生存自由和價(jià)值意義。很多學(xué)者面對這樣一場危機(jī)都在苦思冥想,尋求出路。胡氏率先開出了一貼‘生活世界’的救世藥方,主張要能擺脫這場危機(jī)就必須回歸到‘生活世界’之中,極力主張從‘人本’角度認(rèn)識世界,研究意義。”[6]在這樣的路徑下,胡塞爾的理論尤其是他關(guān)于圖像的意識,就直接啟發(fā)了薩特、海德格爾與梅洛·龐蒂等人。
參考文獻(xiàn):
[1]倪梁康.圖像意識的現(xiàn)象學(xué)[J].南京大學(xué)學(xué)報(bào)(哲學(xué)·人文科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01(1):32-40.
[2]胡塞爾.邏輯研究:第2卷[M].倪梁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3]福柯,哈貝馬斯,等.激進(jìn)的美學(xué)鋒芒[G].周憲,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3:148.
[4]胡塞爾.現(xiàn)象學(xué)的方法[M].黑爾德,編;倪梁康,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166.
[5]胡塞爾.純粹現(xiàn)象學(xué)通論[M].李幼蒸,譯;倪梁康,選編.北京:商務(wù)印書館,1992:90.
[6]王寅.語用學(xué)之理論前沿——簡論普遍語用學(xué)和新認(rèn)知語用學(xué)[J].外國語文,2015(5):52-58.
責(zé)任編輯韓云波
網(wǎng)址:http://xbbjb.swu.edu.cn
DOI:10.13718/j.cnki.xdsk.2016.03.016
收稿日期:①2015-11-23
作者簡介:朱全國,文學(xué)博士,中南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教授。
基金項(xiàng)目:國家社會科學(xué)基金項(xiàng)目“西方語言哲學(xué)中的圖像意識及其與文學(xué)的關(guān)系研究”(14BZW021),項(xiàng)目負(fù)責(zé)人:朱全國。
中圖分類號:I01;J0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841(2016)03-0123-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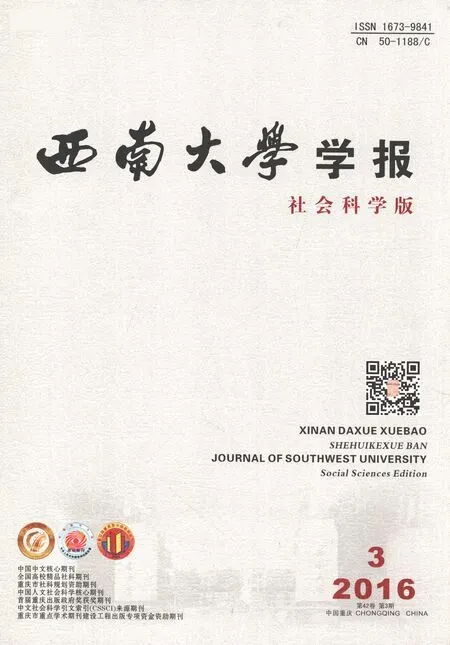 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6年3期
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2016年3期
- 西南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科學(xué)版)的其它文章
- 論合音與漢語音節(jié)構(gòu)成及語音規(guī)則的關(guān)聯(lián)①
——基于中原官話28個(gè)方言點(diǎn)的語料 - 建筑業(yè)農(nóng)民工健康狀況及保護(hù)因素研究①
- 教育統(tǒng)籌權(quán)漂移、統(tǒng)籌成本與城鎮(zhèn)化推進(jìn)的關(guān)聯(lián)度①
- 促進(jìn)就業(yè)抑或強(qiáng)化“福利依賴”?①
——基于城市低保“反福利依賴政策”的實(shí)證分析 - 城鎮(zhèn)化時(shí)期農(nóng)村糾紛化解中的“關(guān)系效應(yīng)”研究①
- 連片特困地區(qū)旅游扶貧與生態(tài)保護(hù)耦合態(tài)勢研究①
——以重慶市武隆縣仙女山鎮(zhèn)為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