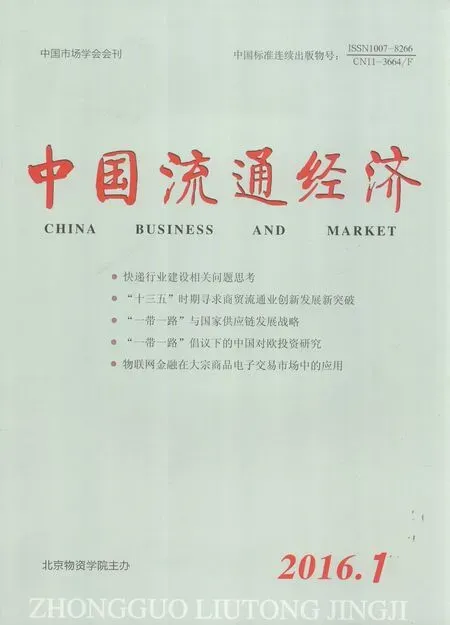標桿學習對企業主流與新流創新的影響
方金城,朱 斌
(1.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福州350116;2.福建工程學院交通運輸學院,福建福州350108)
?
標桿學習對企業主流與新流創新的影響
方金城1、2,朱斌1
(1.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福州350116;2.福建工程學院交通運輸學院,福建福州350108)
摘要:標桿學習對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均具有促進作用,但不同類型的標桿學習對兩種技術創新具有不同的影響效應與作用機理。競爭性標桿學習和功能性標桿學習,分別通過以直接影響為主和間接影響為主的綜合作用路徑,正向促進企業主流技術創新;兩類標桿學習對企業新流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應均通過間接影響路徑起作用。組織慣例更新在標桿學習影響企業主流技術創新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而在標桿學習影響企業新流技術創新中則起完全中介作用。
關鍵詞:標桿學習;主流技術創新;新流技術創新;組織慣例更新
一、引言
企業是我國技術創新的主體,也是國家推進創業創新的重要載體,其持續創新是新常態下我國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關鍵引擎和動力保障。[ 1 ]相關研究指出,在當前激烈的競爭環境下,任何一種創新所造成的優勢都是不能持久的。[ 2 ]為實現持續創新,企業既要強化主流技術創新,又要孵化推進新流技術創新。技術創新二元性理論認為,主流技術創新是企業已有投資獲益或實現盈利的關鍵,而新流技術創新則為企業未來成功奠定基礎。[ 3-4 ]因此,研究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的影響因素及其作用機制,對我國企業培育、建立主流與新流雙元驅動的持續創新模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相關研究評述
標桿學習是施樂公司(Xerox)首創、經美國生產力與質量中心(APQC)推動發展起來的一種獨特的經營理念和管理方法。在歐美,企業標桿學習已被廣泛用于包括度量監控部門的績效管理與質量控制,業務職能部門的客戶服務、物流配送、生產制造和研究開發等多個領域。盡管標桿學習已被視為支持企業績效提升與競爭優勢獲取的重要管理工具,[ 5 ]然而就其對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
新的影響作用與機制,現有研究尚未有系統性的理論探討。目前學界對標桿學習是否促進或者抑制企業技術創新存在爭議。作為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研究的鼻祖,坎特(Kanter)[ 6 ]最早研究指出,企業新流技術創新是知識密集型的創造活動,需要制定共同目標,開展團隊作業式的標桿學習,通過博采眾長快速消化吸收最新前沿知識,形成不墨守成規的思維模式和經營理念。博杰拉漢納與阿貝提(Badguerahanian & Abetti)[ 7 ]研究認為,企業新流技術創新應注重利用標桿學習從組織外部獲取新思路、創造新方法和開辟新知識體系,摒棄淘汰與新流技術體系不相適應的陳舊知識、業務慣例與技術路徑。登雷爾(Denrell)[ 8 ]指出,由于各個企業的經營慣例和組織模式各不相同,在一種情境下有效的最佳實踐知識在其他情境未必有同樣的效果。企業任何層次的技術創新都是企業系統要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它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并非一蹴而就的,因此無論主流還是新流技術創新,若僅憑單純的標桿學習都是難以獲得的。勞森與參孫(Lawson & Samson)[ 9 ]則認為,從組織智商角度看,標桿學習對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都是必要而且重要的,廣泛的標桿學習有利于塑造、更新和改變組織的心智模型,促進組織智商的訓練與提高。目前學界已有不少學者認識并關注到組織慣例更新在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中的重要作用,這為本文從組織慣例動態性理論深化研究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的影響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視角。
三、理論基礎與研究假設
(一)研究變量的概念內涵與分析單元界定
1.標桿學習
標桿學習是不斷評估企業產品、服務、作業流程、管理模式等與行業內外領先企業的差距,充分借鑒他人的先進經驗,改進不足,提高競爭力,從而實現趕超一流企業、創造卓越績效的良性循環過程。其本質上是一項面向實踐、定點趕超的組織學習活動。按照學習對象與目標層次差異,標桿學習可劃分為競爭性標桿學習和非競爭性標桿學習/功能性標桿學習兩個分析單元。[ 10 ]其中,競爭性標桿學習(Competitive Benchmarking)是企業以行業競爭對手為基準,通過競爭分析,將競爭對手的產品、服務、工藝流程以及特定經營成果作為標桿進行比較學習和趕超發展的管理活動。而功能性標桿學習(Functional Benchmarking)是指企業跳出行業或地區的界限,搜尋和研究其他行業領先者產品、服務背后的最佳作業方式或工作流程,不斷學習改進、創造優秀業績的管理過程。
2.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
主流技術創新(Mainstream Innovation)是企業以公司現有市場或客戶需求為導向,運用既有知識技能,在現有技術架構下,對產品服務、工藝過程、材料設備和市場渠道的各類改善與優化,類似于漸進性技術創新;新流技術創新(Newstream In?novation)是企業以潛在市場為突破口,運用新的科學與工程知識,開發新技術工藝、研制新產品服務、創造新的市場需求,類似于突破性技術創新。[ 11-13 ]
3.組織慣例更新
組織慣例更新是指當組織慣例的執行環境發生變化時,組織慣例能夠主動地進行“搜尋”,進而實現組織慣例與新環境相適應,增強組織慣例效能的過程。[ 14 ]從結果看,組織慣例更新可劃分為行為慣例更新和結構慣例更新兩個分析單元,其中前者主要反映為組織行動參考、行為范式與準則的變動調整,它包括組織行為規范、業務流程、作業程序與操作模式的變革或重構;后者主要用以表征組織對環境變化的動態響應程度,它包括組織層級架構、業務體系、資源配置、戰略部署與經營計劃的適應性調整。[ 15-16 ]
(二)研究假設
1.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
(1)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技術創新
德魯(Drew)[ 17 ]利用知識管理和資源基礎理論研究了北美企業技術創新中的標桿學習應用,認為同業對標學習通過搜尋、內化并提升來自競爭者的最佳實踐能力,能促使企業不斷完善既有業務的組織思考和行為方式,從而達到以對手知識獲取推進技術持續性改進的目的。岡查洛克(Goncharuk)[ 18 ]以烏克蘭乳品業為例,研究了無邊界競爭性標桿學習在企業技術追趕中的應用問題,認為無邊界競爭性標桿學習有利于企業明確技術開發和創新方向,緊隨市場領導企業制定正確的戰略決策。王永華等[ 19 ]認為,功能性標桿學
習是企業學習先進的一種新的系統科學的有效方法,它能彌補企業創造力資源短缺的不足。借鑒行業外部卓越企業的典范經驗和做法,有助于企業獲取、整合并積蓄企業賴以營造持久競爭優勢的關鍵技術和經營訣竅等無形資源的能力,從而為企業價值創造、競爭成功和獲得持續成長奠定堅實的基礎。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1:標桿學習對企業主流技術創新有顯著影響。
H1a:競爭性標桿學習正向影響企業主流技術創新;
H1b:功能性標桿學習正向影響企業主流技術創新。
(2)標桿學習和新流技術創新
勞森與貝爾薩尼(Lawson & Bersani)[ 20 ]運用投入產出分析方法研究了標桿學習對美國印刷業發展的影響,認為同業對標雖然能使行業內企業運作效率的絕對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也導致企業之間相對效率差距日益縮小,創新戰略日益趨同,產品、質量、服務甚至供應銷售渠道大同小異。陳威等[ 21 ]分析了企業標桿學習中的“羊群效應”,認為同業標桿學習容易導致近親繁殖和同質化現象,從而影響行業新流技術創新。巴赫曼(Bach?mann)、[ 22 ]史平多利尼(Spendolini)[ 23 ]等研究認為,跨行業借鑒領先企業卓越作業方式或特定領域最佳實踐典范,有利于企業擺脫本領域傳統思維束縛,衍生并促進行業條條框框之外的啟發性思考,對企業突破性創新具有重要的意義。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2:標桿學習對企業新流技術創新有顯著影響。
H2a:競爭性標桿學習負向影響企業新流技術創新;
H2b:功能性標桿學習正向影響企業新流技術創新。
2.標桿學習和組織慣例更新
坎普(Camp)[ 24 ]認為,標桿學習通過以最佳績效為基準,樹立企業學習和追趕的目標。在尋找和追求這一目標的過程中刺激每個員工都參與到這一活動中。全員標桿學習能推動個人學習和組織學習、個體知識與集體知識、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的共享擴散與相互交換,它有利于新知識、新技術和操作程序的產生。更多新知識、新技術的運用也就為組織慣例更新帶來了更多選擇。組織慣例會通過“試錯”“選擇”機制[ 25 ]對標桿學習成果進行“市場選擇”,[ 26 ]最終實現組織慣例的有效更新。蒙克豪斯(Monkhouse)[ 27 ]研究指出,向對手學習能使企業保持對技術、市場的靈敏性,充分了解競爭對手的可能活動、產品或服務最新工藝設計、客戶基礎以及供應鏈等資訊,有利于企業準確預測或認清行業技術與市場發展趨勢,動態調整業務結構與經營戰略。韓永進與陳士俊[ 28 ]研究指出,標桿學習是企業進行最佳實踐、進入先進的知識管理模式的重要途徑。通過標桿學習,企業重新思考和改進經營慣例,構筑自己的最佳實踐,從而實現趕超一流企業和創造優秀業績。安德森、亨里克森與阿爾賽斯(Andersen,Henriksen & Aars?eth)[ 29 ]研究認為,功能性標桿學習是一種以典范學習行動為導向的教育方式,它讓企業有機會借鑒優秀企業的成功經驗與先進理念,以改造自己的經營模式和業務流程。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3:標桿學習對組織慣例更新有顯著影響。
H3a:競爭性標桿學習正向影響組織行為慣例更新;
H3b:功能性標桿學習正向影響組織行為慣例更新;
H3c:競爭性標桿學習正向影響組織結構慣例更新;
H3d:功能性標桿學習正向影響組織結構慣例更新。
3.組織慣例更新和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
(1)組織慣例更新和企業主流技術創新
穆爾曼(Moorman)等[ 30 ]認為,組織慣例更新是組織記憶系統新陳代謝的重要機制。由于既有的組織記憶會阻礙企業員工的創造性思維和對新知識及信息的吸收,并且通過戰略、價值系統、權力分配、組織期望等強化員工舊有的認知和行為方式,使企業難以識別和利用潛在的創新機會,因此企業技術創新必須重視組織慣例更新。博杰拉漢納與阿貝提[ 31 ]在梅蘭日蘭鑄造業興衰案例研究中指出,企業主流技術創新主要著眼于企業既有技術體系的完善與提升,其創新過程需要在企業現行技術架構下調整或打破企業原有流程、模式與運行規則,通過整合或重置企業內部資源結構,
形成變革能力,推進企業優勢資源與技術延伸,不斷豐富企業現行技術體系的知識性積累。阿科古恩(Akgün)等[ 32 ]指出,在穩定的環境下,組織對于組織慣性、規則和信念等進行低程度上的改變,會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組織漸進式創新。曾俊健等、[ 33 ]徐尚飛[ 34 ]通過對我國東北和珠三角地區企業實證研究指出,慣例遺忘是組織主動遺忘的重要測量維度,適度的慣例遺忘對企業漸進性創新具有正向影響。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4:組織慣例更新對企業主流技術創新有顯著影響。
H4a:組織行為慣例更新正向影響企業主流技術創新;
H4b:組織結構慣例更新正向影響企業主流技術創新。
(2)組織慣例更新和企業新流技術創新
塔什曼與安德森(Tushman & Anderson)、[ 35 ]萊維特與瑪奇(Levitt & March)[ 36 ]指出,當作為“創造性的毀滅”的根本性技術變革出現的時候,行業中已有企業更可能失敗,其根源就在于組織過去成功經歷所形成的“能力陷阱”和“慣例依賴”。由于慣例的結構性植入和重復使這種情況不斷得到強化,組織對新技術變革的努力也因此落空。米科拉(Mikkola)[ 37 ]指出,新流技術創新從創意思維產生到研發創造和商業化量產過程都離不開組織慣例更新。他認為,對一個企業而言,組織慣例更新不僅會影響企業新流技術創新的初始階段,而且會影響其執行階段。也許一個新創意的誕生并不困難,但是執行往往更困難。因為新流創新執行是對舊有習慣和行為模式的改變甚至顛覆,這將會與現有體制發生沖突甚至是劇烈的沖撞。企業新慣例建構是其新流技術創新得到合理執行并順利落地轉化為企業實際生產力的重要保證。根據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5:組織慣例更新對企業新流技術創新有顯著影響。
H5a:組織行為慣例更新正向影響企業新流技術創新;
H5b:組織結構慣例更新正向影響企業新流技術創新。
4.組織慣例更新的中介作用
阿科古恩[ 38 ]從組織主動遺忘視角分析了組織慣例更新的作用,認為企業管理者必須主動地遺忘企業原有的不符合當前業務發展最新趨勢要求的知識架構、戰略思維和業務部署,以利于組織吸收更新層次的知識,建立更加適應技術創新需要的組織慣例和思維模式。劉亞軍、胡義偉[ 39 ]指出,企業“核心能力剛性”問題的根源是組織慣例的剛性。組織慣例必須隨著環境的變動而及時、順利地進行變異,這是企業突破“技術創新路徑依賴”、克服“核心能力剛性”的根本出路,同時也是標桿學習能否促進企業技術創新的關鍵。此外,從技術創新模糊前端控制角度看,組織慣例更新能擴大企業邊際搜索,推動企業主動接受和評估新的市場和技術信息,它是企業創意生成、創造力開發、產品概念設計、新產品開發管理的重要基石。[ 40 ]相反,組織慣例鎖定則使企業組織機構趨于僵化而缺乏柔性,形成并陷入創新認知和決策的狹隘視野,進而難以在組織思維模式、運營結構和價值觀等方面進行革命性的拋棄或改變,企業技術創新也無從談起。[ 41 ]綜上,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H6:組織慣例更新在競爭性標桿學習與企業主流技術創新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H7:組織慣例更新在功能性標桿學習與企業主流技術創新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H8:組織慣例更新在競爭性標桿學習與企業新流技術創新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H9:組織慣例更新在功能性標桿學習與企業新流技術創新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
結合上述各研究變量間影響關系的理論分析與命題假設,本文建構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的概念模型如圖1所示。

圖1 標桿學習影響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的概念模型
四、變量測量量表設計與數據獲取
(一)量表設計
在充分吸納國內外相關量表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本文結合上述研究變量的構念內涵,對標桿學習、組織慣例更新、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的初始量表進行設計。繼而,通過福建九地市規模以上企業問卷調查,運用信度分析、效度分析和專家意見征詢方式對各研究變量的測量量表進行凈化修正,刪除掉信度效度判別欠佳的測量題項。
經凈化修正后,標桿學習量表主要采用題項CBM1—CBM6作為競爭性標桿學習的測量工具,采用題項FBM1—FBM7作為競爭性標桿學習測量工具。組織慣例更新量表采用題項BRU1—BRU5作為行為慣例更新的測量工具,采用題項SRU1—SRU4作為結構慣例更新的測量工具。主流技術創新采用題項MIT1—MIT5進行測量,而新流技術創新則采用題項NIT1—NIT6進行測量,具體題項編號及其測量內容如表1所示。

表1 研究變量的測量題項及編碼設計
(二)實證調研與數據獲取
以上述凈化修正過的量表為內容,利用李克特(Lik?ert)7級量表法編制調研問卷。繼而,筆者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3月期間,通過企業走訪、委托管理咨詢公司、培訓機構以及校友協助等方式,向福州、廈門、泉州、漳州、莆田、寧德、龍巖、三明和南平等福建九地市規模以上生產企業發出問卷430份,剔除漏答、一致性回答等不符合要求的問卷后,得到有效問卷/樣本292份。從樣本分布看,涉及國有、私營、合資多種企業性質,行業覆蓋汽車、電子、信息,機械、化工、紡織、冶金、建筑和交通運輸等多個行業,包括職工人數從100人以下到1000人以上的不同規模企業。樣本屬于非同質性的企業組群,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且樣本總量超過農納利與伯恩斯坦(Nunnally & Bernstein)[ 42 ]等學者建議的較佳樣本量要求,因此調研數據可用于本研究
的模型結構測試。
五、實證檢驗與結果分析
(一)相關分析變量間存在相關關系是建立結構方程模型的前提。對上述各研究變量進行相關分析,得到變量之間的皮爾森(Pearson)相關系數及其顯著性情況(如表2所示)。由表2可見,解釋變量競爭性標桿學習、功能性標桿學習分別與被解釋變量主流技術創新、新流技術創新存在顯著的正向相關,中介變量行為慣例更新和結構慣例更新也分別與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存在顯著性相關關系,這初步驗證了本文前述的研究假設。下面運用結構方程模型(SEM)對這些變量之間的關系進行更為精確的驗證,以佐證前面提出的標桿學習對企業主流技術創新與新流技術創新的影響及作用機制的理論假設。

表2 研究變量的相關性分析
(二)結構方程模型擬合與檢驗
1.初始結構方程模型建構與擬合檢驗
根據前述理論假設與概念模型,運用AMOS 19.0軟件對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的影響關系模型進行圖形化建模與擬合分析,得到模型擬合的卡方值與自由度之比χ2/df=4.369,近似誤差均方根估計RMSEA=0.074,均方根殘差RMR=0.058,擬合優度指數GFI=0.895,比較擬合優度指數CFI=0.967,塔克-劉易斯指數TLI=0.931,規范擬合指數NFI=0.876,如表3所示。從模型標準化路徑系數擬合結果看,作用路徑“競爭性標桿學習→新流技術創新”的C. R.一致性檢驗值為1.699,小于最低判別標準1.96;且顯著性水平p=0.061>0.05,統計檢驗不顯著。同樣,作用路徑“功能性標桿學習→新流技術創新”的C.R.=1.815<1.96;顯著性水平p=0.057>0.05,未能通過顯著性檢驗。故上述兩種作用路徑總體影響效應不顯著,下文模型修正將予以剔除。其他作用路徑的參數估計均達到判別標準要求,予以保留。

表3 初始結構方程模型的估計參數
2.模型修正及中介效應檢驗
根據初始SEM模型擬合檢驗結果,剔除影響效應不顯著的作用路徑,并運用AMOS19.0軟件對修正后的模型再次擬合分析,得到模型整體擬合優度χ2/df=3.754,RMSEA=0.069,RMR=0.052,GFI= 0.907,CFI=0.971,TLI=0.955,NFI=0.893。盡管RMR>0.05和NFI<0.9未達到判別標準要求,但其與標準臨界值總體較為接近,其偏差屬于社會科學領域研究容許范圍;[ 43 ]從擬合優度各指標性能看,模型修正后的擬合優度比修正前的有較大幅度改善。根據表4的模型參數估計看,修正后的模型所有參數的標準化估計值總體適中,C.R.一致性檢驗值均大于1.96,參數估計的標準差也都大于0,且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因此,可認為修正后的SEM模型擬合程度基本滿足標準要求。從修正后的SEM模型擬合檢驗結果看,除假設H1a、H1b、H2a、H2b、H6、H7、H8和H9外,其余假設均獲得了驗證支持。
借鑒溫忠麟等[ 44 ]和巴倫與肯尼(Baron & Ken?ny)[ 45 ]提出的結構方程模型中介效應判定原理,對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新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中的組織慣例更新中介效應進行統計性驗證分析。從競爭性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看,二者存在正相關關系(參見表2);且存在競爭性標桿學習→主流技術創新直接作用路徑、競爭性標桿學習→行為慣例更新/結構慣例更新→主流技術創新間接作用路徑,作用路徑系數均為正數(如表4所示);故競爭性標桿學習正向影響企業主流技術創新,組織慣例更新在競爭性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H1a獲得支持、H6未獲得支持。從競爭性標桿學習和企業新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看,二者正相關(參見表2);且二者間僅存在競爭性標桿學習→行為慣例更新/組織慣例更新→新流技術創新的間接作用路徑(參見表4),路徑系數均為正數;其直接作用路徑的影響系數未達到顯著性水平,直接作用不顯著(參見表3);故競爭性標桿學習正向促進企業新流技術創新,且組織慣例更新在競爭性標桿學習和企業新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H2a未獲得支持、H8獲得支持。同理,功能性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技術創新正相關;且二者間不僅存在直接作用路徑,還存在以組織慣例更新為中介的兩條間接作用路徑,路徑系數均為正數;因而功能性標桿學習正向促進企業主流技術創新,組織慣例更新在二者影響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H1b獲得支持,H7未獲得支持。功能性標桿學習和企業新流技術創新正相關;且僅存以組織慣例更新為中介的兩條間接作用路徑,路徑系數均為正數;直接作用路徑的影響系數未達到顯著性水平,故功能性標桿學習正向促進企業新流技術創新,組織慣例更新在二者關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即H2b和H9都獲得支持。至此,本文所有命題假設得到了檢驗,最終修正并經檢驗通過的結構方程整體模型及變量關系圖如圖2所示。

表4 修正后的結構方程模型估計參數

圖2 修正后的結構方程整體模型擬合檢驗輸出結果
六、結語
(一)結論
福建九地市規模以上企業問卷調查與統計性實證分析表明,標桿學習、組織慣例更新和企業主流、新流技術創新之間呈現如下作用關系與影響效應:
第一,標桿學習正向影響企業主流技術創新,不同類型的標桿學習對企業主流技術創新影響作用均存在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兩種作用路徑,但其影響效應與機理存在一定的差異。其中,競爭性標桿學習對主流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是通過以直接影響(β=0.273)為主、間接影響(β=0.25)為輔的綜合路徑實現的,而功能性標桿學習對主流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則是以間接影響(β=0.254)為主、直接影響(β=0.185)為輔的綜合路徑實現的。
第二,組織慣例更新在標桿學習和企業主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就競爭性標桿學習與主流技術創新關系而言,行為慣例更新是競爭性標桿學習促進主流技術創新的重要中介;而在功能性標桿學習與主流技術創新關系中,結構慣例更新是功能性標桿學習促進主流技術創新的重要途徑。
第三,標桿學習對企業新流技術創新具有正向影響,且這種影響是通過組織慣例更新為中介的間接影響起作用的。就競爭性標桿學習而言,行為慣例更新(β=0.086)和結構慣例更新(β=0.09)是企業競爭性標桿學習促進新流技術創新兩個同等重要的必備條件。而從功能性標桿學習對新流技術創新的促進效應來看,企業結構慣例更新(β= 0.147)則比行為慣例更新(β=0.061)更為關鍵和迫切。
第四,組織慣例更新對標桿學習促進企業新流技術創新起完全中介作用,即無論企業采取何種類型的標桿學習,其新流技術創新突破都必須重視以組織慣例更新為前提。
(二)主要貢獻
本文研究結論和主要理論貢獻如下:
第一,標桿學習對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均具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這一結論從實證研究角度進一步支持了目前學界多數學者所持的標桿學習技術創新促進論的觀點。2010年以來,我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已連續6年在全國開展標桿學習實踐活動,有效促進了工業企業產品質量與技術創新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企業正在逐步從“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其事實上也佐證了標桿學習對企業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的正向促進效應。
第二,對于企業主流技術創新而言,組織慣例更新是標桿學習促進主流技術創新的重要橋梁,企業實施任何類型的標桿學習,如若不重視對現有慣例的適應性調整,那么其主流技術創新必然“大打折扣”。對企業新流技術創新而言,組織慣例更新是標桿學習促進新流技術創新的先決條件和必要前提,如若不革新慣例、破除傳統思維模式和運作機制等條條框框的束縛,那么企業無論采取何種形式的標桿學習,其新流技術創新都將無從談起。研究從組織慣例動態性理論視角,綜合運用統計計量研究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細化探討了不同類型標桿學習對不同層次技術創新的差異化影響及作用機制,它彌補了現有相關研究缺乏定量化實證研究的不足,對我國企業因勢利導把握好標桿學習和企業技術創新影響關系、有的放矢地培育、形成主流與新流雙元技術創新模式具有一定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當然,本文研究也存在如下缺陷:一方面,研究主要采用Likert 7級量表法編制調查問卷,受限
于方法本身缺陷,其調查結果不可避免地存在主觀性偏差和測量外部效度欠佳的不足;另一方面,研究主要以福建九地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為對象進行統計性實證分析,其研究樣本多樣化程度偏弱。此外,為簡化研究,本文尚未考慮外部環境、企業資源要素與成長階段等因素對“標桿學習和主流與新流技術創新影響關系”的調節效應。后續研究將圍繞上述研究不足進行拓展改進,以期進一步提高研究結論的可推廣性和系統性。
參考文獻:
[1]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中國經濟新常態(修訂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49-62.
[2]Edison Tse.源創新:轉型期的中國企業創新之道[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12:35-37.
[3]Gnyawali D R,Grant J H.Enhancing Corporate Ven?ture Performance Through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1997,5(1):74-98.
[4]Atoche Carlos.Capability Lifecycles:an Insight from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y Evolution in Emerging Economies[J]. Cladea’s Annual Assembly,2007,1(2):326-327.
[5]Camp Robert C.Benchmarking- The Search for Best Practices that Lead to Superior Performance[J].Quality Prog?ress,1989,22(2):70-75.
[6]Kanter R M,North J,Richardson L,et al.Engines of Progress:Designing and Running Entrepreneurial Vehicles in Established Companies,Raytheon's New Product Center,1969 –1989[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1,6(2):145-163.
[7]、[31]Badguerahanian L,Abetti P A.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Merlin- Gerin Foundry Business:A Case Study in French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 [J].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1995,10(6):477-493.
[8]Denrell J.Selection Bias and the Perils of Benchmark?ing[J].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5,83(4):114-119+134.
[9]Lawson B,Samson D.Develop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Organisations:A Dynamic Capabilities Approach[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1,5(3):377-400.
[10]Harrington H.James.The Complete Benchmarking Im?plementation Guide:Total Benchmarking Management[M]. New York:McGraw-Hill,1998:14-17.
[11]Terziovski Mile.Building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Or?ganizations:an International Cross-case Perspective[M].Lon?don:Imperial College Press,2007:73-85.
[12]朱斌,吳佳音.自主創新進程探索:主流與新流的動態演進——基于福建省兩家制造型企業的案例研究[J].科學學研究,2011,29(9):1389-1396.
[13]Bin Z,Weiqiang O.Mainstream and New-stream Pat?terns for Indigenous Innovation in China:Evidence from Local Manufacturing Firms[J].Journal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in China,2013,4(1):55-70.
[14]Nelson R R,Sidney G.Winter.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M].Cambridge:Belknap,1982:106-114.
[15]劉海建.企業組織結構的剛性特征及對戰略變革的影響[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07,28(3):126-132.
[16]劉海建,周小虎,龍靜.組織結構慣性,戰略變革與企業績效的關系:基于動態演化視角的實證研究[J].管理評論,2009,21(11):92-100.
[17]Drew S A W.From Knowledge to Action:The Impact of Benchmarking on Organizational Performance[J].Long Range Planning,1997,30(3):427-441.
[18]G.Goncharuk A.Competitive Benchmarking Tech?nique for“the Followers”:A Case of Ukrainian Dairies[J]. Benchmarking:An International Journal,2014,21(2):218-225.
[19]王永華,朱雨良,王永貴.標桿管理與價值創新——未來企業營造競爭優勢的組合工具[J].華東經濟管理,1999,13(1):26-27.
[20]Lawson A M,Bersani K S,Fahim-Nader M,et al. Benchmark Input-output Accounts for the US Economy,1992 [J].Survey of Current Business,1997,77(11):36-82.
[21]陳威,葉成,黃玲.標桿管理在企業應用的“羊群效應”及其規避分析[J].財會通訊·綜合(中),2012(10):45-46.
[22]Bachmann A E J.Global Competitiveness with a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Focus[C]//Engineering Management Conference,1990.Management Through the Year 2000-Gaining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IEEE International. IEEE,1990:310-313.
[23]Spendolini M J,Friedel D C,Workman J A.Bench?marking:Devising Best Practices from Others[J].Graphic Arts Monthly,1999,71(10):58-62.
[24]Camp Robert C.Benchmarking——The Search for Best Practices that Lead to Superior Performance[J].Quality Progress,1989,22(2):70-75.
[25]Cyert R M,March J.A Behavioral Theory of the Firm [M]. 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1963:93-107.
[26]Biggart N W,Beamish T D.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Conventions:Habit,Custom,Practice,and Routine in Mar?ket Order[J].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003,29:443-464.
[27]Monkhouse E.The Role of Competitive Benchmarking
in Small-to-medium-sized Enterprises[J]. Benchmarking for Quality Management & Technology,1995,2(4):41-50.
[28]韓永進,陳士俊.企業知識管理最佳實踐和標桿學習的內涵及關系[J].科學管理研究,2007,25(1):81-84.
[29]Andersen B,Henriksen B,Aarseth W.Benchmarking of Project Management Office Establishment:Extracting Best Practices[J].Journal of Management in Engineering,2007,23 (2):97-104.
[30]Moorman Christine,Anne S.Miner.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Memory on New Product Performance and Creativ?ity[J].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97,1(34):91-106.
[32]、[38]Akgün A E,Byrne J C,Lynn G S,et al.Organiza?tional Unlearning as Changes in Beliefs and Routines in Orga?nizations[J].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Change Management,2007,20(6):794-812.
[33]曾俊健,陳春花,李潔芳,等.主動組織遺忘與組織創新的關系研究[J].科研管理,2012,33(8):128-136.
[34]徐尚飛.組織主動遺忘對技術創新的影響研究[D].大連:東北財經大學,2013.
[35]Tushman M L,Anderson P C,O’Reilly C.Technology Cycles,Innovation Streams and 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s:Organization Renewal through Innovation Streams and Strate?gic Change[J].Managing Strategic Innovation and Change,1997,34(3):3-23.
[36]Levitt B,March J G.Organizational Learning[J].Annu? al Review of Sociology,1988,14:319-340.
[37]Mikkola J H.Portfolio Management of R&D Projects:Implications For Innovation Management[J].Technovation,2001,21(7):423-435.
[39]劉亞軍,胡義偉.組織慣例視角下的企業“核心能力剛性”新解[J].現代財經,2009(5):49-52.
[40]Reid S E,De Brentani U.The Fuzzy Front End of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for Discontinuous Innovations:A Theo?retical Model[J].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2004,21(3):170-184.
[41]Gilbert C G.Unbundling the Structure of Inertia:Re?source Versus Routine Rigidit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5,48(5):741-763.
[42]Nunnally J C,Bernstein I H.Psychometric Theory[M]. New York:McGraw-Hill,1994:56-78.
[43]吳明隆.結構方程模型——AMOS的操作與應用[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233-239.
[44]溫忠麟,張雷,侯杰泰,等.中介效應檢驗程序及其應用[J].心理學報,2004,36(5):614-620.
[45]Baron R M,Kenny D A.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173.
責任編輯:林英澤
The Impact of Benchmarking on Corporate Mainstream and New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FANG Jin-cheng1,2and ZHU Bin1
(1.Fuzhou University,Fuzhou,Fujian350116,China;2.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Fuzhou,Fujian350118,China)
Abstract:Benchmarking can promote corporate mainstream and new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but different types of benchmarking present diverse effects with different mechanisms. Competitive benchmarking and functional benchmarking positively promote enterprises’main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comprehensive acting paths based on direct influence and indirect influence,respectively. The promotion effects of these two types of benchmarking on corporate new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are both through indirect path. Organizational routine update plays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in influencing corporate main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benchmarking,while it plays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in influencing corporate main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 by benchmarking.
Key words:benchmarking;main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newstream technology innovation;organizational routine update
作者簡介:方金城(1977—),男,福建省福清市人,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博士生,福建工程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技術與創新管理、系統工程與管理等;朱斌(1957—),女,江蘇省靖江市人,福州大學創新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技術創新與技術轉移、科技管理等。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規劃基金“企業創新管理探索:主流與新流創新的沖突與協同”(項目編號:15YJA630109)、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網絡權力視角下鏈式產業集群知識傳播網絡鎖定與重構研究”(項目編號:71403052)
收稿日期:2015-10-29
中圖分類號:F27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8266(2016)01-01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