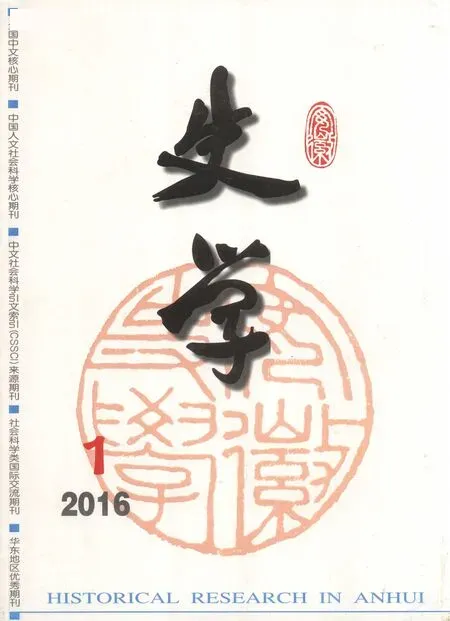中世紀(jì)英國公地共同體與窮人
趙文洪
(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 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
中世紀(jì)英國公地共同體與窮人
趙文洪
(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北京100006)
摘要:本文探討了中世紀(jì)英國窮人群體的社會(huì)特征、基本生活狀況,公地共同體中公共地和公共權(quán)利對于窮人的巨大救濟(jì)作用,公地共同體成員對窮人的其他救助措施,高度評(píng)價(jià)了公地制度救助窮人的社會(huì)功能。
關(guān)鍵詞:中世紀(jì)英國;公地制度;救助;窮人
從私有財(cái)產(chǎn)產(chǎn)生、財(cái)富分化開始,人類社會(huì)便有窮人群體。在農(nóng)業(yè)時(shí)代,世界各國的窮人群體占總?cè)丝诘谋壤艽螅辉诓簧偕鐣?huì),窮人是人口的主體,窮困是整個(gè)社會(huì)生活的基本狀態(tài)。因此,窮人永遠(yuǎn)是社會(huì)良心最為關(guān)注的群體。
歐洲公地共同體*指實(shí)行公地制度的村莊或者莊園共同體。,作為一個(gè)在社會(huì)最底層的直接勞動(dòng)生產(chǎn)者中存在了至少千年的協(xié)作性的生產(chǎn)生活共同體,必然會(huì)與窮人產(chǎn)生深刻的聯(lián)系。史實(shí)表明,這一共同體的巨大倫理價(jià)值和維護(hù)社會(huì)穩(wěn)定的功能,首先就存在于它同窮人的關(guān)系之中。可以說,拋開窮人,公地共同體、公地制度的研究便失去了最重要的價(jià)值。迄今,筆者尚未見到國內(nèi)關(guān)于公地共同體、公地制度與窮人關(guān)系的研究成果。本文試以英國為主做一探討。
一、窮人及其生活狀況
(一)誰是窮人?
這個(gè)問題涉及漫長的中世紀(jì)中人們對“窮人”的認(rèn)識(shí)。
從一些資料看,中世紀(jì)早中期,在社會(huì)上層人士那里,窮人作為一個(gè)社會(huì)階層,并不是以貧窮為基本特征,而是以最沒有自我保護(hù)能力為基本特征。我們可以看看他們對社會(huì)等級(jí)的劃分。
教皇偉大的格雷戈里(Gregory the Great ,590—604年在位)曾經(jīng)將人分為統(tǒng)治的和被統(tǒng)治的兩個(gè)等級(jí)。窮人無疑在第二等級(jí)之中,雖然他并未單獨(dú)指出有個(gè)窮人群體。
著名神學(xué)家格雷先 (Gelasian) 也認(rèn)為世界上只存在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這兩個(gè)等級(jí)。但是,他在論述統(tǒng)治者的義務(wù)的時(shí)候,卻無意地涉及了“窮人”這一社會(huì)群體。他把統(tǒng)治者再分為兩群人:武人(軍人);被委以精神的“權(quán)威”或世俗的“權(quán)力”者(神職人員和國王)。這兩群人之下就是弱者。國王的主要義務(wù)就是保持其所管束的武人們不去壓迫弱者。在弱者中,特別要保護(hù)寡婦與孤兒,其次是窮人(paupers)。這就明確表示:窮人屬于被統(tǒng)治的弱者階層。他還說,國王保護(hù)的對象是僧侶(clergy)、權(quán)勢者(potentates)、窮人。
其實(shí),早在7世紀(jì)初,西班牙神學(xué)家塞維利亞的伊西多爾(Isidore of Seville)就表示了相同的看法。在他的論述中,依次出現(xiàn)過主教、君主、“窮人的壓迫者”這三個(gè)統(tǒng)治者群體或者階層。窮人未被直接論述,只當(dāng)作消極的犧牲者。
總之,對于社會(huì)上層而言,“窮人”是指無力保護(hù)自己的自由或成年男性。是“人民”中之未武裝部分*喬治·杜比:《三個(gè)等級(jí)》(Georges Duby,TheThreeOrders,FeudalSocietyImagined), 芝加哥大學(xué)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5、96—97頁。。
一段記載891年某地的居民戰(zhàn)勝海盜的文字,非常具體地表明何為9世紀(jì)英格蘭人眼中的窮人,以及他們的社會(huì)地位:
武人們沖出城墻,擊敗了進(jìn)犯者。當(dāng)?shù)厝藢⒋舜螒?zhàn)斗的戰(zhàn)利品分為三份:第一份給戰(zhàn)斗者,論功行賞;第二份堆在教堂;第三份分給祈禱的人和窮人(poor people)。這是一次不尋常的分配:傳統(tǒng)上,未參加戰(zhàn)斗者是不能分享戰(zhàn)利品的。為了說明這種反傳統(tǒng)的分配方式之正確性,記載者論證道:這次戰(zhàn)斗是神圣的,是由當(dāng)?shù)卣麄€(gè)基督教社會(huì)共同進(jìn)行的。雖然其中的武人們執(zhí)武器奮戰(zhàn)于疆場,但是,勝利應(yīng)該歸功于全體居民。因?yàn)椤霸谶@次不容易的戰(zhàn)斗中,祈禱者和未武裝者,不斷地祈禱上帝,求其賜給我們?nèi)蚀取!边@里重要的是出現(xiàn)了一個(gè)未參加戰(zhàn)斗,同僧侶一起祈禱的“窮人”群體②喬治·杜比:《三個(gè)等級(jí)》(Georges Duby,TheThreeOrders,FeudalSocietyImagined), 芝加哥大學(xué)出版社1980年版,第94—95、96—97頁。。
以上是從社會(huì)分工角度看“窮人”。我們當(dāng)然還必須從占有財(cái)產(chǎn)多少的角度看 “窮人”。
中世紀(jì)英格蘭農(nóng)民按照法律身份分為自由持有農(nóng)與習(xí)慣佃農(nóng)(維蘭),等等;按照財(cái)產(chǎn)持有量,分為超過1維爾蓋特(平均30英畝*維爾格特(virgate)的面積差別很大,從15—80英畝不一,但一般認(rèn)為約30英畝。見奧斯汀·雷恩·普耳:《從末日審判書到大憲章 1087—1216》(Austin Lane Poole,F(xiàn)romDomesdayBooktoMagnaCarta1087—1216,second edition),牛津1955年版,第43頁。類似的土地面積單位還有碼地(yardland)。)、1維爾蓋特、1/2維爾蓋特、1/4維爾蓋特持有者和經(jīng)濟(jì)地位最低的持有5英畝以下土地的茅舍農(nóng)(cotsetla ,cotter)。自由持有農(nóng)和習(xí)慣佃農(nóng)中又分別包括不同經(jīng)濟(jì)地位的農(nóng)民。一般來說,1/2維爾蓋特以下的土地持有者均屬于小持有者(smallholder)*轉(zhuǎn)引自多諾西·懷特洛克編:《英國歷史文獻(xiàn)》第1卷(Dorothy Whitelock,ed.,EnglishHistoricalDocuments,vol.I,c.500—1042,second edition),倫敦1979年版,第393、394頁。。
維蘭(不自由農(nóng))社會(huì)地位低,經(jīng)濟(jì)收入總體很低,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比較富裕者。
科斯敏斯基(E.A.Kosminsky)在分析英國1279年7個(gè)米德蘭郡的土地持有情況后得出結(jié)論:32%的耕地是領(lǐng)主直領(lǐng)地;40%的耕地由維蘭持有;28%的耕地由自由人持有;約1/5的農(nóng)民持有約1維爾蓋特土地,多于2/3的農(nóng)民持有半維爾蓋特土地,少數(shù)高度成功的家庭持有100英畝或者更多土地。人口增加導(dǎo)致份地面積縮小:1279年,13500個(gè)份地中,46%為10英畝以下,可能接近維持生計(jì)的極限*科斯敏斯基:《英國農(nóng)業(yè)史研究》( E.A.Kosminsky,StudiesintheAgrarianHistoryofEngland),牛津1956年版,第230—237頁。。同時(shí)期艾爾頓村統(tǒng)計(jì)情況大致相同:修道院長(也就是該村的領(lǐng)主)的直領(lǐng)地包括3海德耕地,16英畝草地,3英畝牧場,3個(gè)磨房,河中的捕魚權(quán)*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一個(gè)中世紀(jì)村莊的生活》(Frances and Joseph Gies,LifeinaMedievalVillage),哈珀·派侖尼爾出版社(Harper Perennial)1991年版,第72、72—73頁。。佃農(nóng)中首富戶是約翰。他是自由持有土地的富裕農(nóng)民,持有1海德(6維爾蓋特,或者144英畝)領(lǐng)主的土地,有自己的10個(gè)佃農(nóng):一個(gè)自由的1維爾蓋特土地持有者(virgater),9個(gè)茅舍農(nóng)⑦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一個(gè)中世紀(jì)村莊的生活》(Frances and Joseph Gies,LifeinaMedievalVillage),哈珀·派侖尼爾出版社(Harper Perennial)1991年版,第72、72—73頁。。
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Frances and Joseph Gies)根據(jù)經(jīng)濟(jì)狀況將農(nóng)民大體上分為三個(gè)等級(jí)。最低級(jí)的或者無土地,或者只有太少的土地,不足以養(yǎng)活全家。中級(jí)持有半維爾蓋特或者1維爾蓋特土地。半維爾蓋特土地(12到16英畝)在好年成的時(shí)候可以供養(yǎng)父母和子女。1維爾蓋特土地除了供養(yǎng)全家外,還可以用剩余產(chǎn)品來贖買維蘭義務(wù),甚或購買土地。最高層是少數(shù)持有40英畝、50英畝,甚至100英畝土地的富戶*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一個(gè)中世紀(jì)村莊的生活》,第71、72頁。。
以上這些數(shù)據(jù)說明幾點(diǎn)。第一,只有半維爾蓋特土地和完全沒有土地的人肯定是生活窘迫的窮人。他們在正常年份,可以勉強(qiáng)維持生活,但是一旦遇到歉收和其他收入減少或者開支增加的事情,便會(huì)陷入極度貧困。第二,這樣的人很多。
筆者沒有找到關(guān)于公地共同體確定“窮人”標(biāo)準(zhǔn)的材料。但是,有證據(jù)表明,誰是窮人,由一定的程序加以認(rèn)定。比如,在秋季收割莊稼之前,要由莊園法庭或者部分有威望的村民決定哪些窮人可以去地里拾穗。這也就是說,有資格去拾穗者就肯定是村民們眼里的窮人了*在某村,有記載:“衰弱者,經(jīng)過莊園管家的檢查,經(jīng)兩名佃農(nóng)同意,可以從收割開始時(shí)即從事拾穗。”奧特:《早期村莊的一些村規(guī)》(Warren O.Ault,“Some Early Village By-Laws”),載《英國歷史評(píng)論》(TheEnglishHistoricalReview)第45卷第178期,1930年4月。。
(二)窮人的生活狀況
我們可以通過對中世紀(jì)英國一般勞動(dòng)者的生產(chǎn)、生活狀況的了解來推知窮人的生活狀況。因?yàn)樯鐣?huì)底層生產(chǎn)、生活的一般狀況,也就是平均狀況。當(dāng)這個(gè)平均狀況比較好的時(shí)候,低于它的窮人的狀況就不是特別地貧苦;而當(dāng)這個(gè)平均狀況不太好,或者很不好的時(shí)候,那么窮人的狀況就很不好了。
國內(nèi)史學(xué)界已經(jīng)有多位學(xué)者比較深入地研究過中世紀(jì)歐洲農(nóng)民的生活水平問題*南開大學(xué)歷史系等編:《中外封建社會(huì)勞動(dòng)者狀況比較研究論文集》,南開大學(xué)出版社1989年版;馬克垚:《西歐封建經(jīng)濟(jì)形態(tài)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侯建新:《現(xiàn)代化第一基石》,天津社會(huì)科學(xué)出版社1991年版;侯建新:《社會(huì)轉(zhuǎn)型時(shí)期的西歐與中國》,濟(jì)南出版社2001年版;侯建新:《農(nóng)民、市場與社會(huì)變遷》,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2年版;徐浩:《農(nóng)民經(jīng)濟(jì)的歷史變遷——中英鄉(xiāng)村社會(huì)區(qū)域發(fā)展比較》,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2年版。。他們引用的材料和數(shù)據(jù)表明,由于歐洲相對于同時(shí)代世界其他地區(qū)的自然環(huán)境非常好,土地產(chǎn)出量很高,人口又不是特別多,因此,那里的農(nóng)民,包括其中的窮人,在一般情況下,生活還是溫飽有保障的。筆者就窮人問題收集的資料,也基本印證了他們的看法。這里不再重復(fù)展示這些材料。
但是,畢竟由于整個(gè)社會(huì)生活水平低*中世紀(jì)人的平均壽命:“據(jù)一個(gè)詳盡研究過一千五百個(gè)中世紀(jì)人骨骼的著名科學(xué)家的計(jì)算,在中世紀(jì)時(shí)代,死亡率的‘最高點(diǎn)’是在四十二歲,而在今天它的‘最高點(diǎn)’是在七十二歲。”“在一打或一打以上的兒童里,可能不會(huì)有三、四個(gè)兒童活得到成年的。” 湯普遜著、耿淡如譯:《中世紀(jì)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史》下冊,商務(wù)印書館1961年版,第347、348頁。,社會(huì)最底層的窮人的生活壓力還是很大。另外,雖然歐洲的自然環(huán)境在世界范圍內(nèi)是非常優(yōu)越的,是極其有利于農(nóng)業(yè)和牧業(yè)生產(chǎn)的,但是,畢竟難免自然災(zāi)害。據(jù)記載,1106年、1125年、1144年、1160年、1172年、1196年、1209年、1224—1226年都有饑荒*羅伯特·佛西爾:《中世紀(jì)西方農(nóng)民的生活》(Robert Fossier,PeasantLifeintheMedievalWest,Translated from French to English by Juliet Vale),拜茲爾·布萊克威爾有限公司(Basil Blackwell Ltd.)1988年版,第80頁。。有很多證據(jù)表明窮人生活的窘迫、艱辛、痛苦。我們引用一些歷史學(xué)者們對中世紀(jì)歐洲(英國包括在其中,因?yàn)榕c歐洲其他國家差別不大)一般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者生產(chǎn)、生活狀況的描述吧。
湯普遜說:“那些農(nóng)民所處的苦難而又殘酷的境遇,使他們的感覺性變得如此遲鈍而又麻木,以致我們會(huì)大吃一驚。甚至近代生活中最主要的禮貌是被漠視的。在氣候很熱的時(shí)候,男人一絲不掛地在田間和婦女并肩工作著。”當(dāng)時(shí)有人“看到大多數(shù)農(nóng)民在市場日子里,在街道上和在村莊廣場上走來走去,不披上什么衣服,甚至袴子也不穿,為的要涼快。他們這樣赤身露體地進(jìn)行他們的工作。當(dāng)有些僧侶震驚于這種景況而憤怒地加以申斥的時(shí)候,他們粗暴地回答道:‘那管你們什么事?’”
“中世紀(jì)農(nóng)民,在一間泥地的茅屋內(nèi),是沒有人工照明的。用柴把作為火炬是有危險(xiǎn)的,因?yàn)槲蓓斆┎菘赡苤穑恢劣谙灎T,他無力置備。而且,在天暗之后,他沒有什么事情可做。他不能再工作。他不能讀書,因?yàn)樗麤]有書;即使有書的話,他也不知道怎樣讀。……臥床是什么樣呢!它僅僅是屋角里的一堆草秸,有著惡蟲而常常又是潮濕的。他是不脫衣服睡覺的。”*湯普遜:《中世紀(jì)經(jīng)濟(jì)社會(huì)史》下冊,第378頁。
喬叟(Geoffrey Chaucer,1343—1400年)筆下的窮寡婦只有一間茅舍,分為臥室和廳堂兩部分,她與公牛、母牛、羊住在一起,過著一種“煙熏火燎般”的生活,那只名叫“腔得克立”(Chauntecleer)的大公雞和7只雞婆不時(shí)地跑進(jìn)跑出。房屋沒有通風(fēng)設(shè)施,即使有也很簡陋。通常沒有煙囪,煙霧只能通過門、窗、墻壁和屋頂?shù)目p隙散發(fā)出去*亨利·斯坦利·貝內(nèi)特著、龍秀清等譯:《英國莊園生活 1150—1400年農(nóng)民生活狀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200,235、67頁。。
羅伯特·弗西爾(Robert Fossier)認(rèn)為,歐洲農(nóng)村的生活基本上是貧困的。由于自然災(zāi)害和戰(zhàn)爭動(dòng)亂,饑荒不斷發(fā)生。從10世紀(jì)后期到11世紀(jì)中期,普通人民災(zāi)難深重。有時(shí)候(如約1030年),天災(zāi)波及整個(gè)大陸,還伴隨著瘟疫流行。有一首描述1030年或者1035年饑荒的敘事詩,對人民的營養(yǎng)缺乏有客觀描述:瘦瘠的身軀和腫脹的腹部,微弱的聲音。這些人最后昏迷。有記載說,在某地(Tournus),由于極度饑餓,人們居然出售和食用人肉,或者挖掘尸體和殺死兒童(不過,羅伯特·弗西爾認(rèn)為,這樣的記載可能不真實(shí))*羅伯特·弗西爾:《中世紀(jì)西方農(nóng)民的生活》,第79、80頁。。
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特別指出了艾爾頓村農(nóng)民中地位最低的茅舍農(nóng)的窮困。該村法庭卷宗中多次提到交不起稅費(fèi)的窮人,大多數(shù)是茅舍農(nóng)。他們中間有人“挨家挨戶乞討面包”。窮苦婦女貝特麗絲·波恩(Beatrice Bone)1273年在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乞討,“由于虛弱……在上午9點(diǎn)前,摔倒并死在那里”,兩天后才被一位女親戚發(fā)現(xiàn)。瓊(Joan)是一位“5歲的窮孩子,在外乞討時(shí)掉下河橋淹死”*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一個(gè)中世紀(jì)村莊的生活》,第83頁。。
至于食物,也有關(guān)于短缺和劣質(zhì)的記載:“窮人們在冬季要忍受更多的饑餓和痛苦。……救助他們是一種善舉:面包和淡啤酒在他們就是一桌筵席;冷肉冷魚好比是烤鹿肉;在禮拜五和齋戒日,一個(gè)小錢的淡菜,一個(gè)小錢的雀麥,對這些鄉(xiāng)巴佬來說,無異于一頓豐盛的美宴。”這說明,在一些時(shí)候,還有根本吃不飽、需要救濟(jì)的窮人。
一份1293年留下的農(nóng)村財(cái)產(chǎn)清單為我們展示了一個(gè)窮人全部遺留下來的動(dòng)產(chǎn):一小塊地毯,兩張床,一塊墊子,一個(gè)銅盤子,一個(gè)三腳架,總共價(jià)值33先令8便士⑤亨利·斯坦利·貝內(nèi)特著、龍秀清等譯:《英國莊園生活 1150—1400年農(nóng)民生活狀況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8、200,235、67頁。。這當(dāng)然只是一個(gè)例子,但是也反映出窮人的貧窮情況。
綜上所述,似乎可以得出以下結(jié)論:在沒有自然災(zāi)害、疾病等非正常因素影響的時(shí)候,中世紀(jì)英國絕大多數(shù)窮人都可以維持溫飽;當(dāng)有這些因素影響的時(shí)候,如果沒有來自外部的救濟(jì),窮人的基本生存受到威脅;正常情況下連基本生存都難以維持的窮人也存在著。
二、公地共同體對于窮人的價(jià)值
窮人為什么在莊稼收獲正常年份大致能夠維持溫飽,在減產(chǎn)或者災(zāi)荒時(shí)多數(shù)人不會(huì)餓死?一個(gè)根本的原因就是存在著有利于窮人生存的公地制度。對此,研究公地制度史的專家們多有肯定。
麥克羅斯基(Deirdre McCloskey)指出,低效率的公地制度能夠長期延續(xù)的原因是,在中世紀(jì)和更早期,公地制度是農(nóng)戶們提供自我保障的有效的方式*格雷哥里·克拉克:《共識(shí):公共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效率和制度改變》(Gregory Clark:“Commons Sense:Common Property Rights,Efficiency,and Institutional Change”),載《經(jīng)濟(jì)史雜志》(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第58卷第1期,1998年3月,第75頁。。可以推論,在所有農(nóng)戶中,自我保障對于窮人更加重要。哈蒙茲(J.L and Hammonds)指出,土地和公共權(quán)利為公地勞動(dòng)者提供了一定的社會(huì)地位。它們給他一定的保障和相對于其他人的獨(dú)立*J.L 和哈蒙茲:《村莊勞動(dòng)者,1760—1832》(J.L and Hammonds,TheVillageLabourer,1760—1832),倫敦1911年版,第10頁。。勞動(dòng)者無疑包括窮人。歐文(C.S.Orwin)把圈地后實(shí)行資本主義方式經(jīng)營的農(nóng)莊,同一直保持公地制度的萊克斯頓村進(jìn)行了對比。他說,在20世紀(jì)中期的英國,每個(gè)農(nóng)戶都有3個(gè)無地的勞動(dòng)力。而在萊克斯頓公地共同體,領(lǐng)工資的勞力極少,大多數(shù)村民都有土地以及公共權(quán)利。對于1英畝條田的權(quán)利使得他能夠種莊稼和出賣糧食,并且他有權(quán)利把20只羊放在莊稼茬地,在休耕地上度過一年的剩余時(shí)間。而1英畝圈起來的地則沒有同等價(jià)值*C.S.歐文:《對公地的觀察》(C.S.Orwin,“Observations on the Open Fields”),載《經(jīng)濟(jì)史評(píng)論》 (TheEconomicHistoryReview)第7卷第2期,1938年5月,第134頁。。這就高度肯定了公地制度對于無地和少地的窮人的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大衛(wèi)·索格·曼(David Sugar Man)和羅尼·華靈頓(Ronnie Warrington)把歐洲前工業(yè)時(shí)代的經(jīng)濟(jì)稱之為“道德經(jīng)濟(jì)”。他們指出,“道德經(jīng)濟(jì)”的遺留物中,就有公地共同體全體成員對公地、牧場和森林的共同權(quán)利*大衛(wèi)·索格·曼和羅尼·華靈頓:《土地法,公民身份和“英國性”》(David Sugar Man and Ronnie Warrington,“Land Law,Citizenship,and the Invention of‘Englishness’”),載約翰·布陸爾和斯太夫斯編:《近代早期的財(cái)產(chǎn)概念》(John Brewer and Staves,eds.,EarlyModernConceptionsofProperty), 倫敦和紐約1995年版,第96頁。。顯然,這些權(quán)利所體現(xiàn)出的道德精神,最典型、最鮮明的是對窮人的照顧。
下面,我們再具體分析公地制度對于窮人的價(jià)值。
(一)公地制度對于窮人最大的價(jià)值是公共地
每個(gè)公地共同體都有面積很大的公共地(common land)*遺憾的是,關(guān)于公共地的資料實(shí)在太少。參見J.M.尼森:《享受公共權(quán)利者:公共權(quán)利、圈地和英國社會(huì)變革,1700—1820》(J.M.Neeson,Commoners:CommonRight,EnclosureandSocialChangeinEngland, 1700—1820),劍橋大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第159頁。。公共地包括天然牧場地、沼澤地、荒地、林地等等,也可以叫做未開墾地。它們不僅面積大,而且提供日常生活所需燃料(莊稼茬要留在地里喂牲畜)、礦石、木材、灌溉和帶動(dòng)水力磨的水,等等*戴爾曼:《公地制度及其他》(Carl J.Dahlman,TheOpenFieldSystemandBeyond),劍橋1980年版,第115頁。。小溪流(sikes)、田埂(balks)、道路兩側(cè)(roadsides)等等地方,也是牧草生長地*歐文夫婦:《公地》(C.S.and C.S.Orwin,TheOpenFields),牛津1967年版,第132頁。。沼澤地除了放牧,還可以有限制地割草*奧特:《中世紀(jì)英國公地耕種:村規(guī)研究》(Warren.O.Ault,Open-fieldFarminginMedievalEngland:AStudyofVillageBy-laws),倫敦1972年版,第120、25頁。。這些地方都是經(jīng)濟(jì)價(jià)值很高的牲口飼料來源地。17世紀(jì)末英國估計(jì)有約700萬英畝未用于耕種和放牧、但一經(jīng)改進(jìn)即可放牧的各類土地。15、16世紀(jì)時(shí),這類土地當(dāng)然還要多得多*霍斯金斯:《英國大地面貌的形成》(W.G.Hoskins,TheMakingoftheEnglishLandscape),紐約1970年版,第137、138頁。。所以,馬克·布洛赫說:“公有地(即公共地——引者)的益處是多方面的。荒地和森林為牲口保證了牧場的補(bǔ)充。這些,無論是草地,還是休閑地,在通常情況下是不可能做到的。”“公有地產(chǎn)是村莊或小村子中可耕地的附屬部分或延長部分。”*馬克·布洛赫著,余中先、張朋浩、車耳譯:《法國農(nóng)村史》,商務(wù)印書館2003年版,第202、203頁。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草地都在溪流岸邊,但是,在雨水充沛的好季節(jié),道路旁邊或者掉轉(zhuǎn)犁頭的地方(畦頭)的青草也會(huì)生長得很茂盛。在羊毛、羊皮、羊肉銷售旺盛,奶牛為農(nóng)戶鮮奶來源,耕畜為唯一的拉犁動(dòng)力的時(shí)代,草地的價(jià)值是耕地的兩到三倍。這說明作為公共權(quán)利的客體的荒地對于窮人有多么重要⑩奧特:《中世紀(jì)英國公地耕種:村規(guī)研究》(Warren.O.Ault,Open-fieldFarminginMedievalEngland:AStudyofVillageBy-laws),倫敦1972年版,第120、25頁。!
有的公地史學(xué)專家認(rèn)為,使用公共地的公共權(quán)利(commons)是資本主義時(shí)代以前舊村莊的根本標(biāo)志。因?yàn)樗鼈兘o予勞動(dòng)者和小土地占有者獨(dú)立于工資的保障。還有的專家認(rèn)為公共權(quán)利是財(cái)產(chǎn)權(quán)利樓梯上的最低一級(jí)。著名公地史專家宮訥(Gonner)和歐文夫婦也持類似觀點(diǎn)*J.M.尼森:《享受公共權(quán)利者:公共權(quán)利、圈地和英國社會(huì)變革,1700—1820》,第17頁。。保爾·芒圖具體地描述了公共地對于窮人的好處*保爾·芒圖著,楊人楩、陳希秦、吳緒譯:《十八世紀(jì)產(chǎn)業(yè)革命 英國近代大工業(yè)初期的概況》,商務(wù)印書館1983年版,第117—119頁。。尼森(J.M.Neeson)指出,看似荒廢的公共地,對于村莊里無地或者少地的窮人*耶林(J.A.Yelling)等人認(rèn)為,“在公地村莊,完全無地的勞工幾乎沒有。”耶林:《1450—1850年英國公地和圈地》(J.A.Yelling,CommonFieldandEnclosureinEngland1450—1850),倫敦1977年版,第215頁。但是,后來的研究卻表明,村莊里有大量無地農(nóng)民。荒地對于窮人的意義就更加重要了。,有著至關(guān)緊要的價(jià)值。窮人從公共地里得到的肯定最多,因此1790年代英國舉國上下在討論對圈地的補(bǔ)償?shù)臅r(shí)候,窮人的苦難得到了很多人的關(guān)注*J.M.尼森:《享受公共權(quán)利者:公共權(quán)利、圈地和英國社會(huì)變革,1700—1820》,第174,164、171,12頁。。他還舉例說,在1760年代早期,圈地調(diào)查員(surveyor)托馬斯·考珀(Thomas Cowper)在威靈鎮(zhèn)(Wellingborough)調(diào)查時(shí),發(fā)現(xiàn)了有一個(gè)叫理查德·西泊威爾(Richard Hipwell)的人,他擁有可以放牧一頭牛的公共地,以及從公共地獲得60只羊吃的灌木的權(quán)利*J.M.尼森:《18世紀(jì)北安普頓郡圈地的反對者》(J.M.Neeson,“The Opponents of Enclo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Northamptonshire”),載《過去與現(xiàn)在》(PastandPresent)第105期,1984年11月,第119頁。。尼森說,公地共同體成員,當(dāng)然包括少地或者無地,以及無明確的公共權(quán)利可稽的窮人,可以自由地進(jìn)入公共地采摘野生植物的果實(shí)。另外,由于荒地和林地的面積比較大,各個(gè)村莊之間看管并不嚴(yán)格,偶爾進(jìn)入鄰村荒地和林地取點(diǎn)什么東西也是非常正常的。記載表明,那些偷盜野獸的人隨意就進(jìn)入了其他村子的公共地。至于私人的林木地,他們經(jīng)常要路過,也經(jīng)常在里面拾蘑菇,甚至打野兔⑤J.M.尼森:《享受公共權(quán)利者:公共權(quán)利、圈地和英國社會(huì)變革,1700—1820》,第174,164、171,12頁。。喬治·W.格蘭瑟姆(George W.Grantham)指出,法國1791年法令保證每一個(gè)敞田制下的居民有權(quán)在公地上養(yǎng)6只羊、1頭牛。在1860年代前期,這些權(quán)利的價(jià)值對于窮人來說,可能已占他們收入的20%*喬治·W.格蘭瑟姆:《19世紀(jì)耕種中持續(xù)的公地耕種方式》(George W.Grantham,“The Persistence of Open-field Farming in Nineteenth-Century Farming”),載《經(jīng)濟(jì)史雜志》(TheJournalofEconomicHistory)第40卷第3期,1980年9月,第523頁。。弗朗西斯·吉斯與約瑟夫·吉斯指出,艾爾頓村的村民只要向領(lǐng)主交1/4到2便士,就可以在領(lǐng)主林中放牧豬。一頭母牛一年產(chǎn)大約120加侖到150加侖奶,遠(yuǎn)比近代水平低。但是,1加侖奶能夠賣半便士,在當(dāng)時(shí)收入水平普遍較低的情況下,價(jià)值不菲*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一個(gè)中世紀(jì)村莊的生活》,第148、149頁。。艾立克·克里奇(Eric Kerridge)指出,諾福克郡的公共權(quán)利慷慨到了允許無地的公地成員可以放養(yǎng)1頭奶牛。北安普頓郡克特爾郊外,任何人都可以在布爾頓·拉提摩爾的800英畝公地上放養(yǎng)1頭奶牛*艾立克·克里奇:《英國的公地》( Eric Kerridge,TheCommonFieldsofEngland), 曼徹斯特大學(xué)出版社1992年版,第73、71頁。。瓊·瑟克(Joan Thirsk)指出,一些農(nóng)舍、旅館、磨坊、農(nóng)場住房等等,甚至原來的建筑物的地基,其占有者也有放牧權(quán)。比如,某地一位婦女是村里100名宅基地所有者之一,她證實(shí)16世紀(jì)90年代她住在村子時(shí),可以根據(jù)習(xí)慣在沼澤地里放牧60頭奶牛、8頭公牛、20只年幼的牲口、30匹馬、1000只綿羊*瓊·瑟克:《英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論文集)(Joan Thirsk,TheRuralEconomyofEngland),哈姆伯頓出版社(The Hambledon Press)1984年版,第139頁。。

現(xiàn)在,我們具體看看窮人們到底能夠從荒地和林地獲得哪些物質(zhì)資源。
第一是放牧牲畜,從而獲得肉類、蛋類、奶類、毛皮類產(chǎn)品。
曾經(jīng)在自給自足自然經(jīng)濟(jì)環(huán)境里生活過的人,都知道家禽對于生活的重要——它們是(雞、鴨、鵝)蛋的主要來源,而蛋又是日常生活中最普通、最方便、最受歡迎的蛋白質(zhì)食物。此外,在牛、馬、驢這類作為農(nóng)業(yè)畜力的大型牲口受到高度保護(hù)、不輕易宰殺的情況下,豬還是最主要的肉食來源。在每天都食用牛奶的地區(qū),奶牛則是不可或缺的蛋白質(zhì)供應(yīng)者。中世紀(jì)歐洲人的食物結(jié)構(gòu)同中國人有很大差異:前者食物中的肉、蛋、奶所占的比重遠(yuǎn)遠(yuǎn)大于后者。這就決定了雞、鴨、鵝、豬、奶牛在民眾日常生活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中世紀(jì)歐洲人不種棉花,不穿棉布衣服,麻織品和羊毛織品是最主要的服裝種類。在自給自足的環(huán)境下,自己得種麻和養(yǎng)羊。這就決定了綿羊的飼養(yǎng)對于家庭生活,主要是窮人家庭生活的重要。因?yàn)楦辉<彝タ梢愿嗟匾蕾嚨绞袌錾先ベ徺I*農(nóng)民和領(lǐng)主都把羊視為“搖錢樹”(cash crop)。盡管價(jià)值1或者2先令——豬為2.5先令一頭。但是它們用途多:毛、肉、奶、糞、皮(書寫,能夠持久保存)。早春生羊羔,12周后就可以跟隨母羊吃草了。6月中旬剪毛運(yùn)到市場去賣。中世紀(jì)一頭羊的毛為1磅到2.5磅,近代為平均4.5磅。一頭母豬一年產(chǎn)兩胎崽,一般每胎產(chǎn)7只小豬。多的一年產(chǎn)到19頭。喂一年就可以宰殺。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一個(gè)中世紀(jì)村莊的生活》,第147、148頁。,而窮人則主要靠自給。
而所有這些動(dòng)物的喂養(yǎng)方式,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不是圈養(yǎng),而是散養(yǎng),也就是讓它們自己在戶外找食。可以想象,如果沒有廣大的荒地和林地提供野草、野果、蟲蟻,它們怎么生活?
第二是獲得燃料*吉恩·伯賴爾:《中世紀(jì)森林中的公共權(quán)利:13世紀(jì)的爭論和沖突》(Jean Birrell,“Common Rights in the Medieval Forest:Disputes and Conflicts in the Thirteenth Century”),載《過去與現(xiàn)在》(PastandPresent),第117期,1987年,第28頁。。
農(nóng)民每天都要做飯、燒水,冬天還要生爐子取暖,這都需要燃料,而且是大量的燃料。生產(chǎn)和生活中,還有其他需要大量燃料的事情。比如,改良酸性土壤以及建筑房屋所需要的石灰,它是用石灰石高溫?zé)贫傻摹沂?dāng)然要耗費(fèi)大量燃料。中世紀(jì)歐洲建筑多以石頭為材料,但是后來也有用磚的。燒制磚塊同樣需要大量燃料。人們用樹干、樹枝、灌木等來燒磚。甚至蕨類植物雖然又輕又薄,燃燒時(shí)間很短,但是也被用來燒磚窯。
植物燃燒之后形成的灰燼是前工業(yè)時(shí)代種莊稼所需要的肥料的重要來源。在公地共同體內(nèi),除了莊稼需要灰燼做肥料,草地也需要。
由此可見,燃料的重要,絕對不亞于食物。大量的燃料只能取自面積廣大的地面。如果地面的私有程度很高的話,那么,少地或者無地的窮人就真的只能餓死或者凍死了!而幸運(yùn)的是,由于窮人一般都享有對于廣大的荒地和林地的公共權(quán)利,他們因此而得到了拯救。
村莊的荒地能夠?yàn)檗r(nóng)村人提供什么燃料呢?籠統(tǒng)地說,一切灌木、喬木、野草都可以當(dāng)做燃料。比較普遍的是:森林和樹木稀疏的林地里從樹上掉下來的枯枝;丘陵上的草根;在石南叢生的地方(heath)、山坡、溪谷(vale)一帶生長的荊豆屬植物(furze,gorse)和蕨類植物(bracken,fern);泥炭地上和石南叢生地上存在的泥炭;甚至樹上掉下的葉子曬干后也可以用做柴火。只要是樹木身上的東西,比如樹根、樹皮、鋸木屑,等等,都可以做燃料。證據(jù)表明,所有北安普頓郡的森林都是共同體成員的寶藏。比如,羅金漢森林(Rockingham Forest)中的布里格斯多克(Brigstock)莊園就規(guī)定,其中的54個(gè)茅舍,每個(gè)有權(quán)每年獲得6捆灌木(brakes)。
就像在我國草原地帶和高原地帶一樣,灑落在地里的牲口糞便,主要是馬、牛這類大型牲口的糞便,也可以取回家曬干做燃料。在植物資源不是很充足的時(shí)候,牲口糞便更加重要。齊平·諾頓(Chipping Norton)村規(guī)定,共同體成員可以用頭頂或者背負(fù)的方式將牲口糞便取回家。
在日常燃料中,英國農(nóng)村使用的荊豆屬植物最為普遍,因此也最為重要。荊豆屬植物一是生命力頑強(qiáng),到處生長,是特別豐富的燃料來源;二是它們?nèi)紵饋砗蠡鹆μ貏e大。因此,一般的茅舍、面包房、啤酒釀制店都用來當(dāng)燃料,取暖也用它。在密集開墾農(nóng)田的區(qū)域,100英畝面積野地上生長的荊豆屬植物,往往意味著要為整個(gè)村莊共同體提供一個(gè)冬天的取暖燃料。富人和窮人都愛用它做燃料。但是,窮人似乎與這種植物有更加特殊的關(guān)系——也許是他們選擇其他燃料的可能性要比富人少。因此,當(dāng)我們閱讀圈地運(yùn)動(dòng)中的圈地協(xié)議時(shí)發(fā)現(xiàn),在講到圈地給窮人帶來的痛苦的時(shí)候,往往都提到他們再也不能打荊豆屬植物了。對那些失去土地或者公共權(quán)利的窮人給予補(bǔ)償時(shí),相關(guān)文件都提到荊豆屬植物。因此,早在圈地運(yùn)動(dòng)之前,一些村莊便會(huì)出現(xiàn)圍繞是否讓窮人獲取荊豆屬植物做燃料而產(chǎn)生的爭議。比如,1727年5月,莫爾頓·品克尼(Moreton Pinkney)村的陪審團(tuán)試圖限制那些地產(chǎn)價(jià)值少于5英鎊一年——面積10英畝或者少一點(diǎn)——的人的權(quán)利。在牛津郡的伯瑞克修道院(Berwick Prior),砍伐荊豆屬植物的權(quán)利主要屬于窮人。在圈地的時(shí)候,許多茅舍農(nóng)就說他們的茅舍附帶著多少荊豆屬植物的權(quán)利。附帶有獲得荊豆屬植物權(quán)利的茅舍的租金比沒有此權(quán)利的租金要高。在貝德福德郡(Bedfordshire), 1英畝荊豆屬植物值45先令6便士*J.M.尼森:《享受公共權(quán)利者:公共權(quán)利、圈地和英國社會(huì)變革,1700—1820》,第173、174、176、177,160頁。。
第三是獲得建造、修繕房屋的地皮和材料。
新來者如果是租住領(lǐng)主或者其他人的房屋的話,那么他有維護(hù)、保養(yǎng)房屋的責(zé)任。莊園法庭卷宗里經(jīng)常會(huì)記錄某人因?yàn)闆]有盡到維護(hù)房子的責(zé)任而受到處罰。在艾爾頓村,1306年,莊園法庭要求女住戶阿爾杜莎·柴普琳(Aldusa Chapleyn)找到擔(dān)保人以確保她“在下次法庭開會(huì)之前將她住的房子修理得如同她接受它時(shí)那樣好”。兩年后,威廉·柔威海德(William Rouvehed)也被要求“修復(fù)和重建其居住的房子,使其完好如他交納入住費(fèi)(gersum)住進(jìn)去時(shí)一樣”*弗朗西斯·吉斯和約瑟夫·吉斯:《一個(gè)中世紀(jì)村莊的生活》,第88、89頁。。
新來村莊共同體落戶的人中間,有的必須自己蓋房子住。有些地方規(guī)定,新來者必須從當(dāng)日傍晚開始建造房子。如果次日早晨房子里冒出了炊煙,就說明他是有能力在本村莊定居的——因?yàn)樗绻貌坏酱迕駧椭脑挘灰怪g怎么能夠建起一棟房子來呢?而有了村民幫助,就說明他的人緣是不錯(cuò)的。人緣不錯(cuò)的人在本村落戶當(dāng)然不會(huì)給大家?guī)硗{或者麻煩。
荒地上建有窮人們的各種質(zhì)量和類型的房子,比如棚舍、茅房、簡陋住屋,等等。公地共同體成員們認(rèn)為這些荒地太不值錢,所以他們并不阻止少數(shù)窮人在那里安家和居住。保爾·芒圖說,“那些用公地上取來的輕便材料建成的小屋,雖非根據(jù)已有的權(quán)利,但是根據(jù)一種默許而建造的這類房屋為數(shù)倍增:雇農(nóng)和擅自住在公地上的人為數(shù)很多,人們讓他們在不屬于他們的地產(chǎn)上拿些東西,這對這些勞動(dòng)者的艱苦和不穩(wěn)定的生活會(huì)帶來一點(diǎn)暖和。”*保爾·芒圖:《十八世紀(jì)產(chǎn)業(yè)革命 英國近代大工業(yè)初期的概況》,119—120頁。
建造、維修房屋的地皮,一般免費(fèi)取自荒地;木材,免費(fèi)取自林地。這對于窮人是多大的利益!
第四是其他用途。
1.布匹晾曬地。每家都要自己織布,布匹在進(jìn)入縫制衣服的程序之前,必須漂洗或者染色,曬干后再使用。晾曬的布匹都要占比較大的地面,而且最好是在空曠的地方,以最大可能地吸收陽光和得到良好的通風(fēng)條件。我們見到許多資料提到窮人在荒地上晾曬布匹。比如,在約克郡的某些地方,貧窮織工在將其成批的布匹漂洗或染色之后,便把它們攤曬在公共地上④J.M.尼森:《享受公共權(quán)利者:公共權(quán)利、圈地和英國社會(huì)變革,1700—1820》,第173、174、176、177,160頁。。
2.照明光源。中世紀(jì)歐洲夜晚的照明靠什么?富有者是靠蠟燭,但是蠟燭比較貴,一般的窮人是難以長期使用的。那么,窮人主要靠什么呢?主要是靠油脂比較多的植物。在塞爾本( Selborne)地區(qū),記錄表明,當(dāng)夜晚變得漫長的時(shí)候,不僅最貧窮的人,就連一般的小農(nóng)們也在廚房和牛奶房里用樹枝照明。在英國農(nóng)村,到處都生長著的燈心草也是晚上照明的物品,1/4便士的燈心草可以照明一個(gè)晚上,非常便宜。
3.干草垛頂和底墊。農(nóng)民們生產(chǎn)生活高度依賴的牛、馬、羊等大型牲口靠什么度過寒冷而無青草的冬季呢?最主要的是靠干草。也就是秋天從專門種草的條田和其他牲口可以吃的草地里收割的青草,曬干后儲(chǔ)存起來供冬季牲口食用。每年的收割、儲(chǔ)存干草,都是和收割、儲(chǔ)存糧食一樣重要的農(nóng)活。只是干草和糧食的儲(chǔ)存方式不同:一在室外,一在倉庫。干草的儲(chǔ)存方式是在家門口的露天處將其碼成圓形或者其他形狀的草垛,像一座座小山一樣地點(diǎn)綴著村莊的冬季外景。與此相伴的另一類小垛,是儲(chǔ)存過冬蔬菜的菜垛。村民們將一些可以儲(chǔ)存的蔬菜堆在地上,外面用植物厚厚地遮蓋,既保溫,又防雨雪。草垛、菜垛的尖頂就像房屋的尖頂,必須有瓦片一類的物品來抵御漫長的冬季中的雨雪風(fēng)霜。而從荒地和林地中獲取的灌木、燈心草、蘆葦?shù)鹊葪l狀物,就是村民們常用的材料。
碼干草堆的時(shí)候,把防潮的蕨類植物墊鋪在最底層,這樣干草既容易干,又可以防止老鼠來偷吃,因?yàn)樗鼈兌疾怀赞ь愔参铩?/p>
4.石頭和沙礫。石頭是建筑房屋、牲口圈、圍墻等的重要材料,也是家里日常生活中敲打、墊鋪、堵塞等活動(dòng)的用具。沙子也是荒地和林地可以提供的必需物品。茅舍的地板每周要撒一次沙子,用來吸臟物、塵土和油膩。沙子也是用來搽洗碗碟的物品。比如,牛津郡的金漢(kingham)堂區(qū)的細(xì)沙可以用來搽洗精致金屬器皿,零售時(shí)1磅價(jià)格為1便士。而共同體成員則可以免費(fèi)得到。某村規(guī)定,只有村民才可以取石頭和沙礫,否則罰款很高:要交1英鎊給領(lǐng)主,交2先令6便士給發(fā)現(xiàn)違規(guī)行為者。
5.牲口睡墊和有機(jī)肥。中世紀(jì)英國農(nóng)村的大型牲口在室內(nèi)睡在墊鋪的植物上,其中包括從荒地和林地取回的樹葉、比較柔軟的野草。記錄表明,蕨類植物比麥桿更加防潮濕,往往在冬天用來墊牲口圈。當(dāng)人們把牲口糞便與這些植物一起掏放到田間時(shí),它們也是非常好的有機(jī)肥。
6.牲口飼料。窮人沒有土地或者只有極小面積的土地來種植糧食,他們沒有太多的糧食來喂養(yǎng)豬這類牲口,因此主要靠野外放養(yǎng)。但是,在嚴(yán)寒的冬季,無論是否將豬關(guān)起來,都要給它們喂食物,否則會(huì)挨餓,甚至可能餓死。富人可以用家里囤積的糧食喂,而窮人就更多地或者完全地依靠從荒地和林地獲得的野生植物和植物果實(shí)來喂養(yǎng)了。山毛櫸就是很重要的一種飼料。
農(nóng)戶家里的耕畜以及奶牛過冬靠什么?一般地,主要是依靠秋天收割的干草。但是,窮人或者是儲(chǔ)存的干草不夠,或者是根本就沒有儲(chǔ)存。那么,他們靠什么來為牲口提供冬季飼料呢?也是靠野外植物。比如,主要用做燃料的荊豆類植物就是很好的飼料。把它剁碎后,可以在直到來年4、5月的漫長季節(jié)里喂馬和公牛。19世紀(jì)有個(gè)叫巴克勒貝利(Bucklebury)的村莊共同體成員在請?jiān)阜磳θΦ貢r(shí)說,他們的牲口在冬天除了荊豆類植物外就沒有別的飼料了。
7.編織籬笆的材料。每家每戶都有個(gè)露天小院子。院子必須圍起來。富裕人家可以用木板做柵欄。但是窮人就只能靠灌木枝條了。冬天要把羊圍圈在露天環(huán)境喂養(yǎng)飼料,也必須有個(gè)活動(dòng)籬笆。在這些情況下,荒地和林地里的灌木就起大作用了。材料顯示,林子地面有生長快速的榛子樹(hazel),可以用來編織活動(dòng)籬笆(hurdle),用于關(guān)羊,還可以用來補(bǔ)籬笆的缺口。
8.蔬菜蓬架、莊稼芽苗覆蓋物。一些蔬菜需要用枝條等進(jìn)行支撐;還有一些藤類植物,必須用棍子、桿子等做成蓬架,使之在上面伸展,大面積接受陽光,并且將果實(shí)垂掛在蓬架上,不至墜落地面。
9.家庭小用具。在商品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時(shí)代,它們都可以從市場上購買。但是,在自然經(jīng)濟(jì)條件下,一般只能自己動(dòng)手制作了。制作不是太難,難的是原材料的取得。由于有了對荒地和林地的公共權(quán)利,窮人們就解決了原材料問題。他們用枝條或者野草做成清掃煙囪的刷子;用燈心草、蘆葦做蓋屋頂?shù)牟牧希挥脽粜牟菥幙棾稍S多物品,比如籃子、墊子、玩具等等;用蘆葦、燈心草來墊床鋪,做墻面涂料的纖維結(jié)合物;用粉碎后的蕨類植物包裝那些易碎的物體以免摔碎;將有些灌木燒成灰,做成球,用于制造肥皂、玻璃。
10.遺落的羊毛。荒地和林地里到處都生長著荊棘,有的地方甚至荊棘密布。當(dāng)綿羊,尤其是處在羊毛最濃厚、最容易脫落季節(jié)的綿羊經(jīng)過荊棘叢的時(shí)候,大量的羊毛便被荊棘上面的刺掛掉了。被掛掉的羊毛很多,甚至有人認(rèn)為,被掛掉了大約一半的羊毛!也有人認(rèn)為沒有鉤掛掉這么多。無論如何,一個(gè)村莊的羊都是數(shù)以千計(jì)的。幾千只羊在荊棘叢里被掛掉的羊毛數(shù)量肯定非常大。有位史學(xué)家(Dorothy Hartley)非常具體地分析了實(shí)際情況:在寒冷的冬天,羊吃的飼料很少,所以羊毛變薄,只是緊貼著羊皮長出一層很短的毛,羊的身上主要還是老毛。但是,到了夏天,由于老毛的重量大,對于本身正在迅速增加重量的羊來說,就像肥胖的人再穿上厚重的衣服一樣,是一個(gè)需要消耗能量的重力負(fù)擔(dān);夏天的炎熱更使得保暖的厚羊毛嚴(yán)重阻礙散熱——這一切,都使得老毛慢慢地脫落。理想的剪羊毛季節(jié)是正好老毛要脫落的時(shí)候,但是羊倌卻不剪母羊毛,尤其是那些生羊羔早的母羊,因?yàn)橐o它們保暖。結(jié)果是,到了8月的時(shí)候,“老母羊在生小羊羔的那片牧場上行走,掉下一塊塊羊毛。”因此,擁有采集羊毛公共權(quán)利的共同體成員就拾起它們?nèi)ゼ徔棥_@種羊毛不但免費(fèi)而且質(zhì)量很好,可以用來做精細(xì)的毛料。一頭小母羊的未脫脂的羊毛重約9磅。而3磅(脫脂后為2磅)羊毛就可以織一件男人的緊身內(nèi)衣了。粗羊毛還可以做被子、地毯等等。
11.可以食用和出售的野生植物及其果實(shí)。荒地和林地是食品的采集地,榛子、栗子都是好食品,經(jīng)常被拿到城市市場去賣。1英畝未砍伐的灌木叢最多可以生產(chǎn)30英擔(dān)(cwt,等于120英磅)的榛子。它們被帶去在鄉(xiāng)村和城市售賣。有人注意到,如果采集后把它們裝在盒子里,埋在地下,那么可以保存到來年的2月2日圣燭節(jié)(Candlemas)。在秋天,人們除了采蘑菇自己做湯吃之外,還把它們曬干了一串串掛起來,既可以留著自己吃,又可以出售。采集塊菌者以2先令6便士1磅的價(jià)格將它們賣給鄉(xiāng)紳們。還有大量可以當(dāng)蔬菜和藥物的植物:細(xì)葉芹屬植物(chervil)、茴香(fennel)、薄荷(mint)、野麝香草(thyme)、牛至屬植物(marjoram)、琉璃苣(borage,其葉可以用做調(diào)味品)、野生羅勒(basil)、艾菊(tansy)。可以做色拉和蔬菜的還有:嫩山楂(hanthorn)、野生含酸液的植物(sorrel)、菊苣屬植物(chicory)、蒲公英(dandelion)葉、色拉地榆(salad burnet)、婆羅門參(goatsbeard)、萵苣(lettuce)、苦苣菜(sow—thistle)、繁縷(chickweed)、歐菁草(yarrow)、田芥草(charlock)、蟋蟀草(goosegrass)。記載表明,村民們廣泛地采集這些野生植物預(yù)防疾病、保健身體。還有各種各樣的草莓、葡萄,其他的野果。當(dāng)然,還有兔子、飛禽、水中的魚類,等等動(dòng)物。公地共同體成員們可以自由地進(jìn)入公共地采摘這些東西。貧窮的男村民的妻子們也采摘野花和草莓去外面零售。最值得注意的是,居然有以從公共地中獲得物品為生的勞工。比如在凱特林(Kettering)地方 ,一個(gè)叫薩繆爾·馬丁(Samuel Martin)的人和他的妻子就是以獲得溪流中的菖蒲和燈心草去售賣為生的。大規(guī)模圈地運(yùn)動(dòng)進(jìn)行的時(shí)候,此類人的境遇引起了很多人關(guān)心。僅僅靠在荒地中采集某一種植物,就可以維持一家人的生計(jì),這說明在一些村子里,荒地和林地的面積是何等地大。
12.偷獵場地。荒地,尤其是林地,由于其面積大,并且往往同其他村莊的荒地或者林地相連,必然是野生動(dòng)物的家園。尤其在中世紀(jì)早期,英國大地上真是森林密布,荒草連天。那個(gè)時(shí)代野生動(dòng)物的種類比今天要多得多,所以,草叢與樹林里野生動(dòng)物的稠密和活躍情況可以想見。我們知道,野生動(dòng)物既是純粹娛樂性質(zhì)的打獵活動(dòng)的追逐目標(biāo)(主要對于國王和領(lǐng)主而言),又是蛋白質(zhì)類食物的重要來源(富人、窮人都吃野味)。既然獵物眾多,對于食物不足的窮人來說,到荒地和林地里偷獵就是補(bǔ)充食物、改善伙食的重要途徑了。記載表明,那些偷盜野獸的人隨意就進(jìn)入了其他村子的公共地*J.M.尼森:《享受公共權(quán)利者:公共權(quán)利、圈地和英國社會(huì)變革,1700—1820》,第166—171、176—178頁。從上一注釋直到本注釋,正文中的資料都引自本注釋引用的著作。由于資料寶貴且筆者未能從其他地方找到相似資料,故而從同一著作中引述較多,特此說明。。
1390年,英國議會(huì)發(fā)現(xiàn)勞工和仆人“養(yǎng)有靈提(獵犬名)和其它動(dòng)物,在假日,當(dāng)好人們在教堂的時(shí)候……他們卻去主人們的公園、林地等處打獵”。議會(huì)法令禁止他們打獵。自14世紀(jì)末期開始,越來越多的莊園法庭記錄農(nóng)民偷獵的情況,大多數(shù)情況下,偷獵的目標(biāo)是魚和小獵物。處罰很嚴(yán),某莊園法庭命令,該村所有獵物都要砍掉一條腿。1450年代,某村的4名村民因?yàn)橥但C兔子、野雞等而被罰款6鎊*阿瑟·P.莫娜漢:《同意,強(qiáng)制和限制,議會(huì)民主的中世紀(jì)起源》(Arthur P.Monahan,Consent,Coercion,andLimit,TheMedievalOriginsOfParliamentaryDemocracy),麥克吉爾女王大學(xué)出版社( Mc 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7年版,第163、164頁。。
這說明偷獵現(xiàn)象非常普遍。
(二)公地共同體救濟(jì)窮人的其他措施
除了公地制度賦予窮人的公共權(quán)利之外,公地共同體還對窮人有具體的救助措施。這里簡要介紹兩種。
第一是給予窮人拾穗的權(quán)利。
公地制度下的莊稼收割,一是要趕時(shí)間,因?yàn)槭崭顣r(shí)間是集體捆綁的;二是農(nóng)戶經(jīng)常要請鄰居或者外來人幫忙;三是收割下來放在莊稼地里等待運(yùn)送回家的一個(gè)一個(gè)的莊稼捆很小;四是村規(guī)規(guī)定,收割的時(shí)候只能割莊稼穗,下面很長的一截莊稼茬要留著供集體放牧牲畜。這四個(gè)方面的因素,造成收割時(shí)大量麥穗的遺落。有人估計(jì),拾穗者一天可以掙到與收割者工資同樣多的收入。大量的違規(guī)拾穗記錄和罰款記錄表明,違規(guī)拾穗者眾多。這說明,遺落的麥穗確實(shí)不少。
在某些社會(huì)的傳統(tǒng)中,遺落在地上的麥穗,是屬于土地和莊稼的主人的。在羅馬法中,拾穗是財(cái)產(chǎn)權(quán)之一部分:“農(nóng)業(yè)之業(yè)主有為其利益支配穗子的絕對權(quán)利。”撒利克法(Salic law)規(guī)定:“如果任何人在收割季節(jié)未經(jīng)他人同意在他人地里拾穗,他將被罰”若干便士。有資料顯示,中世紀(jì)窮人在公地共同體內(nèi)拾穗,似乎也要經(jīng)土地主人同意。
但是,應(yīng)該是受基督教的影響*這里摘引《舊約》的一些句子以資佐證:“在你們的地收割莊稼,不可割盡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遺落的。不可摘盡葡萄園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園所掉的果子,要留給窮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利未記》第19章。)“你進(jìn)了鄰舍的葡萄園,可以隨意吃飽了葡萄只是不可裝在器皿中。你進(jìn)了鄰舍站著的禾稼,可以用手摘穗子,只是不可用鐮刀割取禾稼。”(《 申命記》第23章。)“困苦窮乏的雇工,無論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負(fù)他。要當(dāng)日給他工價(jià),不可等到日落。”“你在田間收割莊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給寄居的與孤獨(dú)寡婦。”(《申命記》第24章。)“這些貧窮人,如同野驢出到曠野,殷勤尋找食物;他們靠著野地給兒女口。收割別人田間的禾稼,摘取惡人余剩的葡萄;終夜赤身無衣,天氣寒冷毫無遮蓋。在山上被大雨淋濕,因沒有避身之處就挨近磐石。”(《約伯記》第24章。),公地共同體排斥有勞動(dòng)能力者的拾穗權(quán),而把穗子留給了窮人和其他弱者。拾穗是窮人的權(quán)利,這得到了公認(rèn)*奧特:《有關(guān)拾穗的村規(guī)和收割莊稼的問題》(W.O.Ault,“By-laws of Gleaning and the Problems of Harvest”),《經(jīng)濟(jì)史評(píng)論》(TheEconomicHistoryReview,New Series),第14卷第2期,1961年。。我們見到過許多這方面的村規(guī)。比如,1286年,紐營頓的村規(guī)規(guī)定:“經(jīng)全體法庭成員通過,本莊園任何人均不得在秋季接待任何有收割能力者為拾穗者。”1405年,某村明確規(guī)定,凡有能力收割而一天獲得1便士工資及食物者,不得在秋季拾穗,否則罰款12便士。某村規(guī)定,太老、太幼、太弱者準(zhǔn)許拾穗。身體健全而未被要求收割者也可拾穗——不過,有證據(jù)表明,他們是村里的窮人。在拉姆塞(Ramsey)地區(qū)的一個(gè)莊園里,村規(guī)規(guī)定,在莊稼被收割完后的3天期間,“貧窮的男女應(yīng)被允許拾穗”。1282年,有一個(gè)給王室莊園管理人的指示規(guī)定:“年幼、年老、衰弱不能工作者應(yīng)該在秋天當(dāng)莊稼捆已經(jīng)搬走后拾穗。”有村規(guī)規(guī)定,在所有莊稼均被收割,并且所有麥捆均被搬走前,不得在任何地方拾穗;違規(guī)拾穗者和同意違規(guī)拾穗者都將受到處罰,罰金相同;佃農(nóng)不得接納外來者拾穗。
第二是給予窮人直接的救濟(jì)。
在中世紀(jì)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shí)間內(nèi),基督教教會(huì)承擔(dān)了重要的救濟(jì)窮人的功能。但是,隨著經(jīng)濟(jì)社會(huì)環(huán)境的變化和教會(huì)自身的演變,尤其13世紀(jì)和14世紀(jì)早期,人口增加,窮人增加,教會(huì)從總體上承擔(dān)的救濟(jì)窮人的功能越來越衰弱。到13世紀(jì)末期,窮人已經(jīng)經(jīng)常被教會(huì)忽視了。甚至早在13世紀(jì)早期就有教會(huì)法學(xué)家發(fā)現(xiàn),原來那種把教會(huì)的主要收入之一什一稅分為主教報(bào)酬、神職人員報(bào)酬、教堂維護(hù)費(fèi)用、救濟(jì)窮人的四分法已經(jīng)不復(fù)存在。“如今,主教們把一切據(jù)為己有”。史料這樣記載:到14世紀(jì)上半葉,有人譴責(zé)神職人員濫用濟(jì)貧制度,發(fā)現(xiàn)他們像狼瓜分獵物一樣瓜分屬于基督、教會(huì)、窮人的財(cái)物,只要是他們自己消費(fèi)不了的,任何東西他們都將藏于箱子里、柜子里,有時(shí)候埋在地下。
教會(huì)濟(jì)貧制度瓦解,另一原因是:在諾曼征服后,許多英國堂區(qū)被世俗貴族交給了修道院或者總教堂的牧師會(huì)(cathedral chapters),這就同時(shí)把救濟(jì)堂區(qū)窮人的責(zé)任轉(zhuǎn)給他們了。由于去總教堂或者修道院領(lǐng)取救濟(jì)物路程遠(yuǎn),而且由于當(dāng)時(shí)通訊條件非常落后,事先又不知道是否能夠領(lǐng)到救濟(jì)物,因此,窮人經(jīng)常覺得不值得耽誤很多時(shí)間去做沒有把握的事情,因而不去。而在堂區(qū),牧師們自己也很窮困,根本管不了窮人。
在這種形勢下,公地共同體承擔(dān)了最主要的濟(jì)貧功能。
在英國,公地共同體居民在教會(huì)體系之外自己救濟(jì)貧民。在13世紀(jì),許多地方的教堂院子里,都有“施舍桌子”(dole table)。1287年,英國埃克塞特教區(qū)主教(Exeter diocesan)發(fā)布的命令表明,接受捐贈(zèng)的箱子是由俗人而非神職人員放置在教堂①蒂安娜·伍德:《中世紀(jì)經(jīng)濟(jì)思想》(Diana Wood,MedievalEconomicThought),劍橋大學(xué)出版社2002年版,第57頁。。
在英國某些地方,習(xí)慣規(guī)定,某些新租種份地的佃農(nóng),必須公開承諾:他們將按照習(xí)慣的標(biāo)準(zhǔn)給某些年老力衰的佃農(nóng)以住處、食物、衣服和燃料。這些佃農(nóng),有的是老佃農(nóng)的親屬,比如子女;但是,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同老佃農(nóng)之間毫無親屬關(guān)系。這個(gè)承諾是非常鄭重的:它在莊園法庭或者村民會(huì)議上當(dāng)著大家的面被記錄于法庭卷宗。如果老人被忽視了,沒有得到應(yīng)該得到的照顧的話,村民們還可以把承諾人和老人兩方帶入法庭,進(jìn)行審理并且做出判決②克里斯托弗·戴爾:《英國中世紀(jì)村莊共同體及其衰落》(Christopher Dyrer,“The Engilsh Medieval Village Community and Its Decline”),載《不列顛研究雜志》(TheJournalofBritishStudies),第33卷第4期,1994年,第407—429、415—416頁。。這種強(qiáng)制性的、可以稱之為濟(jì)貧責(zé)任制的制度,表現(xiàn)了那個(gè)時(shí)代基層社會(huì)對窮人的重視。
1295年,英國某法庭記錄中提到有關(guān)提供給窮人的住宿和食物數(shù)量方面的習(xí)慣。這種習(xí)慣有點(diǎn)像我國古代農(nóng)村建立“義倉”的習(xí)慣。受基督教友愛精神的教化,許多人為了靈魂得救,多行善事。重點(diǎn)是多救助窮人。我們看到,從中世紀(jì)早期以至16世紀(jì)都鐸時(shí)代,不少村民死前立遺囑留下錢財(cái)幫助村里窮人納稅。在英國基層社會(huì),還有一種專門交給教會(huì)用來濟(jì)貧的稅收,叫做俗人稅,由村莊共同體負(fù)責(zé)向居民收集和交付給教會(huì)。這一稅收的征繳開始于1334年,因此,基層社會(huì)納稅與濟(jì)貧之間的聯(lián)系可以回溯至14世紀(jì)。中世紀(jì)晚期,英國的各個(gè)堂區(qū)都建造或者從捐獻(xiàn)者那里得到專門供窮人住的房子,比如1451年在劍橋郡的埃爾斯沃斯(Elsworth),就在教堂的院子里建有一所這樣的房子③克里斯托弗·戴爾:《英國中世紀(jì)村莊共同體及其衰落》(Christopher Dyrer,“The Engilsh Medieval Village Community and Its Decline”),載《不列顛研究雜志》(TheJournalofBritishStudies),第33卷第4期,1994年,第407—429、415—416頁。。
與公地共同體的濟(jì)貧相比,政府發(fā)揮濟(jì)貧功能遠(yuǎn)遠(yuǎn)落在后面:是在黑死病之后的1349年才開始的。
三、結(jié)語
通過無償使用公共土地、鄰里之間互相救濟(jì)來維持窮人的生存,這樣一種社會(huì)救助制度,是歐洲公地共同體偉大的創(chuàng)舉。它體現(xiàn)了重義輕利、重情輕利、待人如己的道德精神,是理想主義的持久、廣泛、深入的實(shí)踐。在公地共同體中,公私并存、人己并存,公、私、人、己都有著確定的地盤、獨(dú)立的地位、明確的身份。這些地盤、地位、身份不僅存在于物質(zhì)形態(tài)之中、日常生活之中,更重要的是,存在于共同體成員的血液與心靈之中。它們是習(xí)慣、是法律、是道德、是信仰。這是人類文明的寶貴財(cái)富和遺產(chǎn),值得后人永遠(yuǎn)的珍視和研究。今天,世界多數(shù)國家都實(shí)行市場經(jīng)濟(jì)這種經(jīng)濟(jì)運(yùn)行方式,要做到揚(yáng)其長避其短,趨其利避其害,是否可以從公地制度中吸取某些經(jīng)驗(yàn)?
責(zé)任編輯:汪謙干
The Community of the System of Common Field and the Poor People in Medieval England
ZHAO Wen-hong
(Institute of World History,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6,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makes research on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or people as a rural social group in medieval England,their basic status of life,the great role played by common land and common rights in the community of the system of common field in maintaining poor people’s life,other relief measures of the members of common field communities,and makes high comment on the social relief function of the system of common field.
Key words:Medieval England;system of common field;relief;poor people
作者簡介:趙文洪(1958-),男,湖南長沙人,中國社會(huì)科學(xué)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dǎo)師。
中圖分類號(hào):K561.3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5-605X(2016)01-01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