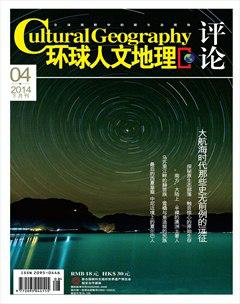地理學派文化觀下中日韓三國人的耐性比較研究
王偉
摘要:中國、日本、韓國這東亞三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國,在歷史上同屬于漢文化圈,它們在很多方面都有著共同或相似之處,但三者在民族性格、人的行為方式方面還是存在著相當的差異,如在對待自然和人際關系的耐性這一問題上便呈現出很大的不同。本文從地理學派有文化觀的視角出發,對中日韓三國人的耐性表現差異做出解釋,希望以此揭示出地理環境與文化之間的辯證關系,并對地理學派文化觀的歷史地位做出客觀評價。
關鍵詞:地理學派;地理環境決定論;中日韓;耐性
一、以孟德斯鳩為代表的地理學派的文化觀
孟德斯鳩是近代西方學者中的“地理環境決定論”者,其觀點在眾多著作中多有體現,因此,在國內相關研究中,學者們通常將孟德斯鳩視為地理學派的創始人,并將其劃分到“地理環境決定論”者的行列中。
其實,在孟德斯鳩之前,法國著名政治理論家和歷史學家波丹也對相關問題早有過闡述。波丹認為,人們居住的自然環境不同會導致人的性格不同,同時對社會也會產生各異的作用和影響,如他指出山地居民發生革命和暴亂的幾率要比住在平原居民大得多。“他甚至把古代雅典國家的三個不同政治派別與其三個不同的地理區域相聯系,認為這是由于地理環境的不同使其居民形成不同的性格所致”。 波丹類似的論述和列舉的事例還有很多,盡管有些學者批評他“結論很帶推測性,科學價值甚少”, 但從其力圖從人們的生活環境中探尋人類歷史發展變化原因的努力中可以看出,他已經摒棄了中世紀教會神學的說教,不再將人類社會的生活現象及歷史發展歸結到上帝那里。這種思想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下還是有很大進步意義的。
孟德斯鳩的地理環境思想受到波丹的重大影響,他在波丹論述的基礎上更加深化并有所推進,其很多觀點我們可以在他的著作《論法的精神》中看到。孟德斯鳩認為,世界上不同的氣候類型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性格,在人們的心態上也體現出差別。而人們的這些不同又造成了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換句話說,地理環境決定人們的性格和心態,人們的性格和心態又決定人文社會環境,這是其“地理環境決定論”的要旨所在。
二、中日韓三國人的耐性比較
筆者最近看了由東亞文化研究專家金文學寫的一本書——《東亞三國志:中、日、韓文化比較體驗記》,書中對中日韓三個國家的國人性格特征、生活習慣和文化觀念進行了生動的描述和比較。在這其中,對于三國人的耐性分析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感觸頗深。
在這本書中,作者首先不必諱言道,日本人急躁的性格在國際社會上是公認的,僅從走路姿勢這一點我們便可見一斑。日本人走路特別快,總是急匆匆,因此腦袋總是伸向前方,有人將其形象的比喻為“烏龜狀身姿”。日本人的急躁不僅僅從文化學者的描述中可以看出來,事實上也有相關數據支持這個觀點。有資料統計過,日本大阪人走路的速度為每秒鐘1.6米,這在全世界都可以排在冠軍位置。此外,一直以來,我們經常妄自菲薄感嘆中國人的素質低,把中國人闖紅燈過馬路稱之為“中國式過馬路”,實際上這種過馬路方式并非是中國“特色”,我們的鄰居——日本人在等紅燈、等電梯時仍然表現出沒耐性,不能在原地一動不動。
和日本人相比,韓國人的低忍耐力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韓劇中我們最常聽的一句話就是“叭利”,它的中文意思是快點。韓國長輩經常在“叭利”聲下敲打著晚輩的腦袋催促其快些吃飯、快些睡覺,甚至連上廁所也不放過。可以說韓劇中中國人最能聽懂的就要數“叭利”了。因此對于韓國人來說,最大的美德非一個“快”字莫屬。
與日本人和韓國人的急躁大相徑庭的是中國人的“慢慢的”,“慢慢的”這個詞表現出了中國人超強的耐性。在中國人使用的詞匯中形容慢節奏的詞句基本都是褒義,如“閑庭信步”、“從容不迫”、“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甚至包括“慢條斯理”這個詞也是褒多貶少:意味說話做事有條有理,不慌不忙,盡管說話做事慢騰騰,卻從從容容,不慌不忙,水到渠成。“慢慢的”似乎已經成為了中國人的一種處世哲學,干的越慢才能干的越好,這與韓國人的“叭利”哲學真是天差地別。
以上從三個不同的側面比較了中日韓三國人的耐性,中日韓三國同屬漢文化圈,但即使是對待同一件事情,如飲酒問題上,三國人仍然有所不同。中國人喝酒講究慢和品,而且經常將個人和公共事務帶到酒桌上來。在中國可以通過酒來消愁,亦可通過酒來解憂,高興的時候要喝酒,失意的時候也要喝酒,這是中國特有的一種“酒文化”。韓國人在這方面和中國基本相似,及其強調品的過程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的享受。但日本人則不同,總是盡量快喝快走,無視飲酒過程中的愉悅。
三、中日韓三國人耐性差異解讀
稍加分析后我們會發現,韓國人的性子急和日本人的急躁卻不盡相同。日本人走路快、沒有耐性實際上是對不良社會環境容忍度低的體現,而且對于浪費時間不僅難以容忍,甚至到了憎惡的地步。而韓國人則正好相反,對環境有一定的忍耐力,在人際關系上容易產生急躁情緒。
為什么文化上同屬一源的三個亞洲國家在耐性問題上表現出如此的差異呢?在回答這一問題時我們通常認為這是由于各自不同的歷史體驗、風土人情以及人們的行為方式、民族慣習所導致的。但除此之外,其中卻也不乏一些地理環境方面的因素在起一定的影響作用,在這方面地理學派可以給我們一些有益的啟示。
地理學派對類似的文化現象也有過研究,如在回答古希臘為什么能創造出杰出的藝術這個問題時認為,希臘所處地區多海島和山地,人們只能以打獵和捕魚為生,飲食來源很不穩定,人與自然處于頑強抗爭的關系。而且地中海地區四季分明,夏季干燥少雨,這樣的地理環境具有很大的刺激性和啟發性,給人們留下了很大的思維空間,因此該地區才出現了舉世皆知的希臘文明。
按照同樣的思路來看,日本人耐性特征與地理環境因素不無聯系。從地理環境來看,日本所處的環境相對優越,日本人自古受惠于青山秀水,習慣了在潔凈的環境里生活,因此對于污濁環境的忍耐力較低,所以對于不利于自身行為的外界環境容易急躁。這種急躁雖然看似不是什么好性格,但卻讓日本人養成了清潔、環保的好習慣,這一點還是需要他國人向其學習的。但在處理人際關系問題上,日本人卻與前者表現截然相反,具有忍耐力超強的一面,這是受到了日本傳統文化的影響的結果,日本人自古就有很強的情感控制能力,而且這被視為一種美德,所以即使人們意見相左也很少出現劍拔弩張的局面,以力求保持和諧的人際關系。
相對日本人而言,韓國的地理位置就沒有那么舒適了,韓國人生活在與大陸相連的不太優越的環境里,在客觀環境的制約下不得不對現有狀況保持著一定的忍耐力和承受力。或許是因為這種忍耐和承受無所釋放,所以韓國人的感情特別奔放,在人際關系上缺乏容忍,如若與人意見不和就忍無可忍的一吐為快。
中國人“慢慢的”節奏下所隱含的極強的忍耐力,則“是從古至今在嚴厲的自然環境和不斷發生戰亂的歷史環境中養成的。中國土地遼闊,但時局卻經常因天災人禍處于動蕩不安的狀態,所以人口的流動性、流動距離特別大。在交通不便、兵荒馬亂的年代,人們逃荒路上要花很多時間,所以性子急是要不得的,必須學會‘慢慢的。悠然也就成了中國人在這種自然和社會環境中生存下來的智慧”。
四、小結
總之,地理學派的文化觀認為地理環境是社會發展的決定因素,一切人類的社會活動都是地理環境的必然結果。地理環境決定文化的形態,有什么樣的地理環境就會造就出什么樣的文化。這是一種典型的“必然論的人地觀”。
這種地理環境決定論觀點無疑夸大了地理條件對文化的作用,忽視了社會因素、人文因素的影響。但是,從歷史進程來看,地理學派的一些觀點仍有進步之處。它注意到了地理環境與人類社會之間的關系,并將一些現象聯系在一起,從而開創了從社會、自然與人類的關系中去尋找文化發展動因的研究方向。雖然其對地理環境與社會歷史現象之間的解釋并不完全科學,但畢竟已開始走出歷史唯心主義的迷宮,比以往從宗教神話傳說來解釋文化發展要進步的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