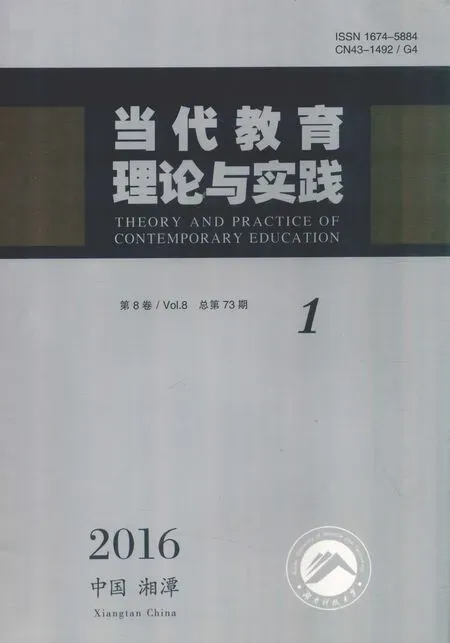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法社會學分析——以湖南湘西自治州人民陪審員制度實踐為樣本的考察
?
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法社會學分析——以湖南湘西自治州人民陪審員制度實踐為樣本的考察
李智偉
(吉首大學 法學與公共管理學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單行法律,但在《決定》實施過程中,卻存在著人民陪審員隊伍構成現狀與“大眾化”設計初衷相背離和履職水平低等情況。本文試圖以湖南西部人民陪審員制度實踐為樣本,從法社會學的視角分析以上情況的產生原因,為改進我國基層法院陪審員制度提出建議。
關鍵詞:人民陪審員制度;法社會學;湖南西部

2005年5月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正式實施。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第一部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單行法律,《決定》系統地規定了我國人民陪審員的性質、地位、職責、陪審案件范圍、人民陪審員的名額及產生辦法、培訓和經費保障等方面的內容,《決定》實施10年來,全國各級法院均按照《決定》認真開展人民陪審員工作,人民陪審員在我國的司法審判實踐活動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截至2014年底,全國法院人民陪審員共約20.95萬人,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219.6萬件*①數據來源:《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李少平副院長答記者問》,載http://legal.people.com.cn/n/2015/0425/c188502-26903013.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7月18日。①,占當年全國一審案件總數的23.6%*②數據來源:最高法院院長周強在2015年3月12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所作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中指出,全國法院2014年全年審結一審刑事案件102.3萬件,一審商事案件278.2萬件,一審知識產權案件11萬件,一審涉外商事案件5 804件,一審民事案件522.8萬件,一審行政案件15.1萬件,全年共審結一審案件929.98萬件。②。但從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踐來看,在人民陪審員的履職方式、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條件等方面面臨困擾與爭議,甚至在學界和審判實務界都存在著對人民陪審員的制度存廢之爭。鑒于此,筆者擬以湖南湘西自治州的人民陪審員制度實踐為考察對象,從小范圍著手,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施情況作一個評判和研究。
1人民陪審員選任:制度設計與實際情況的沖突
人民陪審員制度是“人民群眾在司法領域依法管理國家事務的一種最重要、最直接的形式。通過陪審這座橋梁,動員和組織人民群眾以陪審員的身份參與案件審判活動,讓普通群眾協助司法、見證司法、掌理司法,充分體現司法的民主功能,可以更集中地通達民情,反映民意,凝聚民智,在更大程度上實現人民民主。”[1]從這里可以看出,突出體現司法的“大眾化”功能是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設計初衷和重要目標。
湘西州基層法院于2005年、2009年和2013年集中選任了三批人民陪審員,截至2014年底的人民陪審員隊伍組成基本情況如表1。
表1湘西州基層法院人民陪審員基本情況統計表

從表1可以看出,該地區334名人民陪審員中,從職業分布來看,基層干部151人,人民團體成員8人,事業單位職員28人,專業技術人員29人,這些“吃公家飯”的人員合起來占到了該地區陪審員總數的64.67%,這看上去與陪審員制度設計的“大眾化”初衷還有較大差距。之所以出現以上現象,筆者經調研和分析認為有四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決定》對人民陪審員的選任條件定位過高,與本地社會實際有所脫節。雖然在社會轉型的大背景下,湘西州傳統的城鄉二元化結構逐漸松動,但從總體上看,該地區在湖南省屬于經濟和城鎮化相對落后、農村人口仍占較大比例的欠發達地區,所轄基層縣市均為國家級或省級貧困縣(市)。根據有關資料顯示,2010年,該地區常住人口為2 547 833人,而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為146 777人*③數據來源:該地區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主要數據公報,見http://www.xxz.gov.cn/news/xwdt/gsgg/201110/t20111026_25361.html,最后訪問時間:2015年7月18日。③,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僅占常住人口的5.76%。而《決定》對陪審員的學歷要求為“一般應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從以上數據可見,該地區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不高,又由于該地區經濟較為落后,本地能發揮文化程度較高人員水平的“高精尖”單位較少,待遇相對低,具有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自然選擇前往發達地區就業,這樣該地區絕大部分大專以上學歷的人員便集中到了機關、事業單位,該地區人民陪審員隊伍中“吃公家飯”的人員過多也就不可避免了。

二是在本地社會中,群眾對人民陪審員的認知度低。曾有資料顯示,在對湖南東部發達地區的某全國經濟百強縣關于人民陪審員制度的調查中,“高達52.7%的成年公民回答從來沒聽說過人民陪審員制度”[2]。在湘西州,因經濟社會發展和群眾整體文化水平等方面的因素影響,這個比例應該更高*④筆者曾在下基層調研時發現,一些人民陪審員至少是在被單位推薦擬任命為人民陪審員后才大致了解人民陪審員的基本概念;法院內部有些從事綜合行政事務的干警甚至都不清楚人民陪審員的概念。④。盡管基層法院在每次選任陪審員之前都通過當地電視臺、網站、社區宣傳欄等方式發布了報名公告,但真正前來主動報名的人員較少。有基層法院法官表示“我們這種地方,大部分群眾特別是農村老百姓傳統觀念還是比較重,一方面認為與‘打官司’沾邊的都不是什么好事;另一方面認為法官都是高高在上的,自己去當陪審員和法官坐一張桌子會‘擔待不起’,主動報名的人于是就不多。”*⑤本文中引用的訪談對象話語為綜合訪談對象的意思表示而成,非訪談對象原話,下同。⑤三是法院的功利主義考量。我們從以上表格中可以看到,通過組織推薦而被選任為人民陪審員的比例高達82.3%。在調研中,我們也看到,在目前的操作中,選任人民陪審員的目的與其說是增強司法透明度,還不如說是為了完成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陪審員的陪審率指標和人民陪審員選任指標數。基于這方面的考量,作為法院,在人民陪審員的選任工作中就是以完成指標任務為直接目的,直接與各單位聯系,由單位推薦是既簡單又可靠的方法。一方面,由單位推薦的人民陪審員,只要把握《決定》中的幾個硬性條件,其“德能勤績廉”等方面應該是沒多大問題的,法院也不用承擔“用人失察”的風險;另一方面,有單位的人畢竟好管理一些,在陪審工作中如果有什么問題,也可以由單位出面,好協調處理。在這種功利主義驅使下,法院的人民陪審員選任就變得“簡單”了,個別法院甚至將人民陪審員的選任名額分攤到各個單位或鄉鎮,將各個單位的法制股長、各個鄉鎮的人大主席盡數選任過來,更從一定程度上剝奪了普通農民、普通工人、普通群眾等被選任為人民陪審員的機會。四是法院實用主義的影響。筆者在下基層調研時,還發現在個別基層法院仍然存在著審核不嚴,造成有不宜擔任陪審員的人員,如司法所長、本院退休法官等*⑥關于退休、離任法官能否任人民陪審員的問題,《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關于人民陪審員選任工作若干問題的答復》(法政[2005]63號)作出了明確答復:“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后,曾在基層人民法院工作的,不得在原任職的基層人民法院擔任人民陪審員”,“法官從人民法院離任后,擔任人民陪審員的,不得參與原任職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⑥,被選任進入陪審員隊伍的情形。按理說,陪審員的選任應經過法院、司法局、人大等幾道程序把關,為何仍出現此類情形?該法院相關人員也表示了他們工作上的考慮:“選任公告發出去后,他們所在單位就把他們推薦過來了,雖然我們在資格審查的時候也發現了這個問題,但我們這個小縣城,各單位之間都是熟人,低頭不見抬頭見,以后很多工作都還需要單位間互相支持。畢竟那幾位同志都是在基層司法所工作,并非在‘司法行政機關’,他們也有一定的基層司法調解經驗和水平,所以我們就想著打打‘擦邊球’就過去了,而且他們在我們單位也沒有陪審過幾件案子,我們想著應該沒事。我們單位那幾位退休老同志也積極報名,熱情很高,最高院的那個《答復》我們也是確實不知道,他們有審判經驗,對案子又容易上手,能減輕法官很大的辦案負擔,而且每次來參審還有補助,相當于一種‘返聘’,我們的考慮也是何樂而不為,就把他們請過來了。”
2人民陪審員履職:制度要求在司法實踐中的異化
從制度的設計考慮來看,是希望通過人民陪審員參加審判活動,提升群眾的參與度,達到司法審判透明、公正的目的。但筆者發現,該地區法院在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數逐年增加的現實下,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兩極化”的現象顯得較為嚴重,2013年,該地區各基層法院選任的陪審員參審案件最多的達90多件,但普遍在10件以下,甚至有的參審案件為零。以某基層法院2013年為例,該院當時共有陪審員22人,其中有1名陪審員共參審了49件案件,接近占該縣法院所有陪審案件的四分之一,成為了“專業陪審員”;有2人全年只參審1件案件,另外11人參審案件數為零,成為了“榮譽陪審員”,而且根據各基層法院法官的反映,除了參審不平衡外,陪審員“參而不審、合而不議”的現象也十分突出,進一步加劇了與人民陪審員制度“大眾化”參與的設計初衷相背離的情況。通過分析,筆者認為造成這一尷尬現實情況的原因有三個方面。一是法院在實際操作中缺乏對陪審員的合理管理機制。《決定》中雖然規定了人民陪審員要采取隨機抽取的方式,但沒有指出隨機抽取如何進行,而且“隨機抽取”只是選派人民陪審員參加庭審操作方面的一個步驟,并不是在訴訟程序方面的強制性規定。于是在審判實踐中,該地區“隨機抽取”的形式大部分是由各業務庭、人民法庭對照人民陪審員花名冊和所留的聯系電話自行隨機聯系人民陪審員前來參審。但有些陪審員因工作忙,通知幾次不能來,造成辦案法官和合議庭不愿再請,因此,愿意來的少數陪審員便成了法官首選的“常客”;有些法官因手頭案子多,嫌“隨機抽取”較麻煩,長期只請幾位固定陪審員“輪流坐莊”,產生了一批“駐庭編外法官”和“陪審專業戶”;有的基層法院轄區較大,從減少陪審員參加陪審的舟車勞頓和法庭用人方便等方面的考量,將選任的人民陪審員分到幾個派出法庭固定使用等。因目前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對人民陪審員參審仍然只能取決于其主觀意識。且在對人民陪審員的日常管理,本地區的基層法院普遍認為“人民陪審員不來參審、是否參而不審、審而不議,這些都不是大的原則性問題,大家都在一個小縣城里,相互熟識,有些還是在單位有一定職務的領導,作為法院,總是要給他們一些方便,不能因為他不來參審而駁他面子,這樣誰都尷尬。”有了這層考慮,法院對人民陪審員變成了“放羊式”管理,只要陪審員不犯原則性的錯誤或沒有擔任《決定》中明確不能任陪審員的職務,就一直保留他的陪審員資格,直到屆滿,再提請人大免職。二是人民陪審員自身利益對比的考量。正如前文所說,該地區的陪審員大部分有自己的單位,有著自己的本職工作,有的還是單位領導。部分人民陪審員始終認為自己的第一要務是要搞好自己的本質工作,對這部分人來說,“陪審員”這個稱謂最大的意義就是頭頂上的一個“光環”、一種榮譽的象征,陪審工作只是他們的一個“兼職”,因此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閱卷、調查、參與案件各個環節,而且陪審員是否能履職、是否能勝任陪審工作基本上與他們本職工作和福利待遇不掛鉤。在參加審判活動的陪審員中,部分陪審員或者認為自己發表的意見在法官面前“沒有用”,不想說;或者認為自己畢竟是“外行”,對法律知識了解得不透徹,掌握得不純熟,怕到時候說錯了會對整個案件產生負面影響,不敢說,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民陪審員“陪而不審、審而不議”的現象。三是與法官“同職同權”的定位導致人民陪審員“自我認同價值”缺失。該地區基層人民法院對人民陪審員的選任、使用、培訓等方面都是以法官的標準來操作,在學歷、教育背景、庭審要求和培訓標準甚至誤工補助等方面都要求人民陪審員要與法官趨同一致。一方面,作為人民陪審員,在參審時對法律應用、庭審駕馭等專業領域肯定比不上法官;另一方面,由于“法官中心主義”,法官往往在合議庭中起到絕對主導和控制權,陪審員的一些建議和意見往往被法官的意思所“淹沒”,本應作為人民陪審員優勢的釋案說理等方面的功能被也被稀釋;再次,有些法官對人民陪審員的定位主要就是組成“合議庭”,用來緩解日益增加的辦案壓力,將人民陪審員作為庭審的“點綴”。以上種種原因使得法官和當事人都認為陪審員大多數時候并沒有發揮什么作用,陪審員也對自己的定位感到茫然,“沒有社會的廣泛認同或有效參與,陪審員的自我價值難以實現,消極或怠于履行職權又怎能避免?”[3]
3對進一步完善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建議
在對待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存廢問題上,幾乎每個基層法官反映,在某些案件中,人民陪審員在辦案過程中確實起到了積極作用。許多法官指出,“在我們這種少數民族地區,民風彪悍,老百姓認理不認法的情況時有發生,你和他去講法律那是講不通的了,判了后他又認為你對他不公,到處上訪。在這種情況下,在當地具有較大威望的人就能在息訴息訪方面起到很大的作用,有這類人的出面,案子比單純用法律來解決要有效得多。”

該地區法院2010-2014年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情況統計表
從表2可知,雖然人民法院所收案件數和人民陪審員參審案件數節節攀升,但5年里人民陪審員所參審的案件中,調撤率保持在15%-19%之間;5年里人民陪審員所參審的案件中,上訴率都在7%左右。參審案件數多,調撤率不低,上訴率不高,從這組數據的一個側面可以看出,人民陪審員在該地區法院確實發揮了較好的作用。人民陪審員了解社情民意,案件當事人在感情上、心理上較為認同,有利于推動民事案件調解工作的順利開展,拉近了法官與群眾的距離,提高了調解成功率,對促進社會和諧穩定和“案結事了”起到了積極作用。
因此,從大的方面來看,我國堅持人民陪審員制度是符合建設法治中國的設計需要的,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也對人民陪審員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貫徹《決定》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既有制度本身的一些缺陷,也與我們身處的社會現實有關,對此,我們不能“因噎廢食”,而應該結合新形勢進行進一步修改和完善。一是要對人民陪審員進行“精準定位”。通過適當降低人民陪審員的學歷要求,加強對陪審員道德品行和辨別是非能力方面的考察,使陪審員的任命和使用脫離與法官“同職同權”的軌道,讓更多的人民群眾有機會擔任人民陪審員,進一步發揮陪審員熟悉社情民意和對生活經驗事實判斷的優勢,逐步實行人民陪審員不再審理法律適用問題,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讓人民陪審員的選用真正回到“大眾化”的設計初衷上來。二是進一步完善人民陪審員參審機制。針對在審判實踐中存在的一些人民陪審員怠于履職的現象,建議明確由人大牽頭,建立人民陪審員履職檔案,并形成通報制度,按年度向人民陪審員所在單位、社區進行通報,對于長期不履職的人民陪審員,要建立退出機制,及時免職。三是要進一步落實人民陪審員“隨機抽取”機制。建立人民陪審員信息庫,對人民陪審員從職業、專業技術等方面實行分類管理、分類抽取。合理確定每個人民陪審員每年參與審理案件的數量比例,要為每個人民陪審員每年參與審理案件設定上限,防止“專職陪審”“駐庭法官”現象。四是要加強對陪審員工作的經費保障。建議在省級層面,針對各地不同情況,對人民陪審員的經費保障作一個標準化規定,并與時俱進,適當逐年提高人民陪審員的補助標準,做到專款專用,從待遇上解決陪審員的補貼、獎金和福利等問題,解除陪審員的后顧之憂,激發陪審員的工作積極性。五是落實培訓機制。陪審員人數較多,隊伍龐大,陪審員的培訓重點在基層。建議由省級人大、法院、司法行政部門建立人民陪審員培訓流程規范并出版讓廣大人民陪審員淺學易懂、能深入淺出的培訓教材。培訓重點要放在人民陪審員對案件的事實認定、人民陪審員庭審禮儀、庭審紀律等方面。
參考文獻:
[1] 楊維漢,鄭良.讓普通群眾協助司法、見證司法、掌理司法[EB/OL].(2010-05-14)[2015-07-18].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0-05/14/c_12102700.htm.
[2] 廖永安,劉方勇.人民陪審員制度目標之異化及其反思[J].法商研究,2014(1):85-92.
[3] 廖永安.社會轉型背景下人民陪審員制度改革路徑探析[J].中國法學,2012(3):147-159.
(責任校對王小飛)
中圖分類號:D92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5884(2016)01-0172-05
作者簡介:李智偉(1985-),男,湖南冷水江人,碩士研究生,湘西自治州中級人民法院政治部法官管理科副科長,主要從事法律文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14
doi:10.13582/j.cnki.1674-5884.2016.01.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