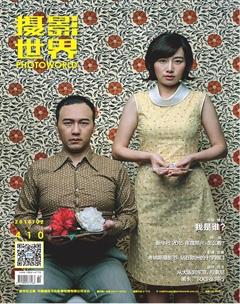手機,我的親密“備機”
潘超越




作為一名攝影記者,不論是拍攝突發事件,還是日常新聞,大多數情況下“一機一鏡”或者“一機多鏡”滿足不了工作需求,“備機”是必需的。在選擇“備機”時,有人偏愛使用同款相機,比如佳能EOS-1Dx或者尼康D4S這樣的專業相機;有人偏愛攜帶一臺專業單反相機加一臺準專業單反相機,或者一臺專業單反相機加一臺微單TM/無反相機。而對我而言,最親密的工作備機則是手機。
不過,很多人對手機攝影的態度過于嚴肅了,喜歡拿手機照片和專業相機拍出的照片做比較,卻忘了手機攝影的初衷—隨時隨地記錄和分享。而我喜歡的,正是在手機里2000像素見方的感光元件上,專業與業余打破了隔閡,大師和菜鳥可以平等對話。
定格新聞現場的好幫手
我是一名新華社常駐中東地區的攝影記者,從2013年9月至今,我帶著手機去過所有工作過的新聞現場,發現手機似乎可以擺脫單反相機“拖油瓶”的標簽。某些情況下,比如在沖突事件中、貧民窟里、長途跋涉后,反而會因為小巧和便捷的特點成為拍攝的主力。
其中,最令我難忘的是2013年底經歷的一起埃及騷亂。前一晚還暢想在穆斯林國家度過“平安夜”的奇妙場景,第二天一早我就被“曼蘇拉市安全部門大樓被炸,造成15人死亡、過百人受傷”的消息叫醒。驅車三個小時抵達事發現場,我聞到建筑廢墟上的煙灰揚起,看到情緒激動的民眾在附近聚集,聽到聲討“穆兄會”的口號聲此起彼伏。很快,人潮涌動,朝著市中心最寬的馬路挺進。游行,這是自2011年以來,埃及民眾表達情緒最直接的方式。
在沖突地區工作的報道攝影師都知道“十分鐘守則”,即在短時間內完成拍攝工作,不等待、不戀戰。但是,剛到埃及不久,我缺乏經驗,容易被刺激場面沖昏頭腦,忘我地跟拍游行隊伍。直至距我不到50米的人群中爆發出一股黑煙,我才意識到這場游行終將釀成暴力事件—民眾點燃了一輛媒體用車,開始將情緒發泄到人群中的記者身上。
外國人面孔和單反相機自然是此時最惹眼的元素,我身邊的青年開始用阿拉伯語向我質問。片刻后,我將相機放入背包,拿出手機,指指身邊同樣拿著手機拍攝的本地人,青年的態度瞬間發生轉變,就像面對一位放下武器的士兵一樣,“降者不殺”。在意識到危險,準備撤離后,我用手機拍下這一刻的畫面(圖02),隨后消失在人群中。這張照片后來獲得了2014 美國手機攝影獎MPA(Mobile Photography Awards)新聞攝影類第一名,也讓我第一次感受到手機在突發事件現場對攝影記者的重要價值。
2014年6月,我與同事一起報道敘利亞七年一度的總統選舉。我們來到尚有反對派與政府軍交戰的城市霍姆斯。一路上,政府軍士兵一方面保護我們的安全,另一方面監督我們的采訪內容。每當我將鏡頭對準在戰爭中損毀的建筑和武器時,總會得到士兵“善意”的提醒:“你們是來報道大選的。”
霍姆斯老城是受損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我們借著想采訪位于一座用作投票站的教堂為由,得以一睹老城風貌。然而,用專業設備拍攝這樣的場面顯然會引起身邊士兵的警惕。當我放下“長槍短炮”,掏出手機拍攝時,他們對于我的警惕放松多了,甚至提出合影留念的要求。趁著間隙,我站在一處十字路口,用手機拍攝到一名剛完成投票的居民,走過受損嚴重的樓房(圖03)。他萎靡的背影和建筑間深邃的街道,訴說著一場似乎結束遙遙無期的戰事。
用手機照片幫助新聞當事人
“法德爾島”村是位于埃及尼羅河三角洲的一個難民村,村民主要是第四次中東戰爭從巴勒斯坦而來的戰爭難民的后裔。設身處地去想,難民,尤其是未成年的難民,對于鏡頭的情感是復雜的:一方面,他們像同齡人一樣,對拍照這事好奇;另一方面,由于從小形成的自卑感,又懼怕鏡頭。所以,在難民村里面對單反相機的孩子總是躲躲閃閃。
完成當天報道任務之后,我放下單反相機,拿起手機跟著孩子探索整個村子。而這些兒童難民也同樣放下他們先前的拘束,我的拍攝變得輕松起來,手機成為眼睛的延伸,自由地紀錄著。
一名男孩兒從我身邊跑過,向伙伴喊了話,大意似乎是說“快來看這個中國人!”我聽不懂他說什么,但能感受到他的笑容很真誠。
我拍下了小男孩的身影(圖05),離開村子返回開羅的路上,將這張照片上傳至Instagram個人賬號,同時將另外一張照片在我所參與的Everyday Egypt(每日埃及)項目賬號上發布,呼吁對難民村的關注。隨后幾天內,我在社交媒體上陸續收到其他攝影師跟進報道的資訊和好心人提供幫助的留言。我想,這也算自己對“有用的攝影”的一次實踐吧。
記錄日常生活的好伙伴
作為攝影記者,相機是賴以謀生的工具,也是“戰斗的武器”。但在埃及摩西山,我第一次產生了丟下“武器”的念頭。
來埃及不登摩西山,就好像到中國不爬長城一樣。然而,因為嚴峻的西奈半島局勢加上夜間徒步10小時的挑戰,登頂膜拜先知摩西接受《十誡》的地方,還是令不少游客望而卻步。
2015年10月,我到摩西山拍攝,直到山腳下,我對行李做了最后精簡,背包里留下一件厚衣、一些食物補給、一臺裝有14mm-24mm鏡頭的尼康D800相機和一部iPhone 6 Plus手機。漫漫長夜,我與一行來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走在靜謐的西奈山脈,耳邊聽到的只有腳步聲、喘息聲和心跳聲。隨著海拔上升,厚衣裹到身上;隨著體力的消耗,食物和淡水也在減少,只有那臺笨重的相機成為我身上唯一嫌棄的負重,很想就此作別。而事實是,登頂山頭,朝日從山間呼之欲出,我與其他游客都興奮地拿出手機拍攝壯美之景(圖01),直到最后,相機也沒派上用場。
我在開羅生活的時間比在北京要久,若把她視為第二故鄉,毫不矯情。不管外人對埃及的評價如何,她在我心中就是一個充滿“生活氣息”的地方。來過埃及的朋友都知道,埃及人對于相機有著天生的敏感,或忌諱,或熱情,總之有點極端的程度。那么,一臺手機就是記錄埃及生活最好的工具,低調地拍攝,瀟灑地分享,讓人欲罷不能。
現在,我已經養成了在工作和生活中輪流使用單反相機和手機拍攝的習慣。對我而言,手機讓我對待攝影的態度更加活潑,在新聞現場也更加從容。無論在埃及,還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手機都是我的親密“備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