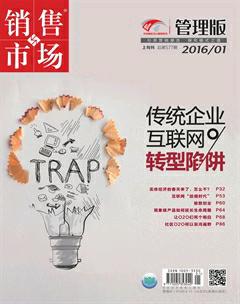供給側改革
近日在發改委調研時,李克強總理再次指出,要從“供需兩側發力,推進結構性改革”。事實上,從2015年11月起,在中央高層的講話中,“供給側改革”就成為一個高頻詞。如何解讀這一經濟術語?它的提出,體現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思路的何種變化?
彭元:真正需要的是“去政策性刺激”
去日本、德國、韓國、法國購物,不僅僅是為了買物質,而是購買一種先進文化體驗,而這些恰恰是我們這個制造業大國不能供給的東西。
供給側改革的目標是為了創造新的需求。土地、資本、普通勞動力是無差別的,但創新是需要社會環境才能有效實現的。只有配套的整體機制的改革,“雙創”才不會是無本之木,技術創新、文化創意才能從政治家的口號變成現實。這次供給側改革是背水一戰,已經沒有退路了。
其實,供給側改革真正需要的不是政策性刺激,恰恰是“去政策性刺激”。讓權力退出市場,讓市場主體歸位。
就像當年鄧公主導的改革,許多人把廣東、浙江的經濟成就歸功于改革的政策,事實上,真正的功勞,是重新獲得了經濟自由的人民。鄧公的功勞不在于經濟成就,而在于把經濟的自由還給了人民。
鄧沉飛:解決有效需求
從根本上講,供給側改革是解決有效需求,是更明晰的結構調整。供給側改革的重點是滿足需求,創造新需求,核心是推出更能滿足需求的好產品,解決的是供給與需求不匹配的問題。簡政放權、打破區域格局,讓現有企業松綁。
不能把供給側改革和結構性改革停留在概念和理論層面,炒概念救不了企業。供給側與需求側相對應,需求側有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三駕馬車決定短期經濟增長率。而供給側則有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四大要素,四大要素在充分配置條件下所實現的增長率即中長期潛在經濟增長率。而結構性改革旨在調整經濟結構,使要素實現最優配置,提升經濟增長的質量和數量。
劉春雄:中國不缺供給,缺的是有效供給
供給側改革一提出來,馬上有人說中國要搞供給學派,我不贊同這個觀點。我們先談供給學派,然后再談供給側改革。
供給學派與凱恩斯學派。經濟學的鼻祖是亞當·斯密,他認為應該讓“看不見的手”來調節經濟。后來經濟出了問題,就出現了凱恩斯學派。
20世紀70年代出現一種經濟現象——滯脹,滯脹有三大現象:經濟停滯、失業、通貨膨脹。這挑戰了所有經濟學,因為過去認為經濟停滯與通貨膨脹不可能同時存在,這是兩種不可能并存的現象。供給學派就是解決滯脹這個經濟怪物的。
滯脹,簡單地說就是經濟下滑,但物價卻上升。經濟下滑,以前經濟學家提出的辦法是增加刺激,中國過去也一直是這么干的,比如4萬億政策投資,是典型的凱恩斯主義。凱恩斯的邏輯是創造需求,然后增加供給。
供給學派則提出了一套完全相反的邏輯,即增加供給能夠創造需求。供給學派的兩個做法:一是減稅,二是減少政府干預。減稅的邏輯是:減稅—刺激經濟增長—增加就業——增加消費—刺激經濟增長,這個邏輯是成立的,減稅能夠刺激供給,帶動經濟發展。里根就是靠這一套解決美國滯脹問題的,因此供給學派一戰而勝。
而中國現在并沒有滯脹。
中國現在的問題是什么?中國現在的問題是:經濟下滑,就業增加,物價下降。也就是說,中國的問題不是滯脹,只滯不脹,不符合供給學派的適用條件。并且中國目前是供給過剩,并不存在供給不足的問題。
所以,中央一提出供給側改革,馬上有人提出中國要實行供給學派的政策,我有點看不懂。當然,也許是我修煉不夠,才看不懂。
最近總理又提出供給側改革與刺激需求并舉,如果真是實行供給學派,那不是十八反(中醫詞匯,即作用相反的兩味藥)嗎?
以下是對中國目前經濟現狀的幾個觀點,我很贊成,所以摘抄幾條:
第一,需求基本都已歸位,再刺激作用不大。次貸危機以來,出口從30%降到負增長,投資從30%降到10%,消費增長從20%降到10%左右,經濟增長從14%跌到7%,最慘烈的下跌過去了。即使再刺激,可能也很難有太大的效用,這叫邊際效用遞減,所以我們要轉向。這句話的意思很簡單,就是凱恩斯主義不行了,不能再搞類似4萬億政策。
第二,一方面需求不足,一方面醫療、教育、娛樂等大量需求得不到滿足。最有意思的是,“中國制造”滿足不了國內需求,中國人到美國買的襯衣是中國制造的,到日本買的馬桶蓋也是中國制造的,這是有效供給不足。能通過需求去解決這個問題嗎?顯然不能,那么要靠供給。
第三,我們正處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浪潮中,中國有可能實現彎道超車,這叫創新驅動,顯然靠需求也沒辦法實現。
第一是說刺激需求不行了,第二是說新的需求沒有滿足,第三是說新科技創造了新需求。
有些搞傳統經濟的人對“雙創”提出質疑,認為是瞎搞。這是帶著工業文明的思維想信息文明的事。
在供給與需求之間,還有一個商業,這個商業才是關鍵。中國不是供給不足,而是供給與需求結構性不對稱。
商業扭曲供給與需求,核心在哪里?自2000年以來,KA在扭曲這個問題,電商還在扭曲這個問題。
供給側改革,目前比較害怕的是落后產能,因為它們的存在,會加劇商業扭曲。所以,我認為供給側的改革,不是一視同仁,而是差別對待。
在宏觀與微觀上,我同意下列幾個做法:
一是新科技創造新需求,增加新供給。過去克林頓就是這么做的。
二是發展增值服務業,中國在經濟下滑過程中,就業問題不突出,就是服務業立了大功。隨著電商對商業中心的擠壓,服務業成本并沒有上升很快,服務業已經超過GDP的一半,這個領域一定要大鼓勵。
隨著C端電商份額到頂,B端電商增加,我認為商業扭曲供給與需求的現象會好得多。特別是跨境電商的出現,會帶動中國消費品升級。
孫明峰:再一味沖量就是撞墻自殺
凱恩斯的需求側是通過貨幣寬松實現消費增長,目前需求側改革模式已經無法解決經濟持續增長問題,導致過剩產能有增無減,如鋼鐵、煤炭等。
供給側改革是從生產方即供方角度提高產品技術含量,來滿足市場需求。淘汰過剩產能,加大創新型企業扶持力度。比如奶粉行業,國家通過提高生產技術門檻淘汰80%的奶粉品牌。
目前需求側改革不會停止腳步,貨幣適度寬松基調沒有變,但貨幣寬松的結果是消費在國外而不是國內。供給側改革的提出一定是兩個方面同時著力,就像央企整合一樣提升競爭力。
整體趨勢是去庫存,需求端的暗示就是放棄數量要質量,對企業而言就是減少銷量考核比重,提高利潤指標考核比重,當然這是對于有余糧的企業而言。再一味沖量就是撞墻自殺。
王巧貞:供給側改革帶給企業的機會
越簡單,越普世。
二戰后的德國一片廢墟,然而1950年年初,就開始了經濟上的起飛,到今天,德國已經成為歐洲第一大經濟體。而英國、法國這些戰勝國反倒經濟增長緩慢,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尚不能完全解決國民的基本溫飽問題。德國經濟的成功,轉折點就在于艾哈德在馬克與美元掛鉤后,馬上取消了市場管制。市場經濟的大手,成為德國經濟的唯一指揮棒。
目前中國經濟的弊端正在于大量無效供給。供給側出了問題,不該生產的東西生產得太多,而消費者需求的東西缺乏供給,供給與需求發生了扭曲。而這種扭曲,一定程度上是政府造成的,一方面,從優質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大幅收稅去扶持競爭力低下的企業,客觀上造成劣幣驅逐良幣;另一方面,稅負過重,導致本來具有活力的企業創新能力降低。
本屆政府提出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下,不得不正視現實,斷臂求生。關鍵在于,政府到底會以什么樣的方式去實現供給側改革,如何把握改革的方法及步驟。快則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慢則難以推動中國經濟快速提振。而富有遠見的企業家,自然知道如何去適應市場。
編輯:
王 玉 spellingqiu@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