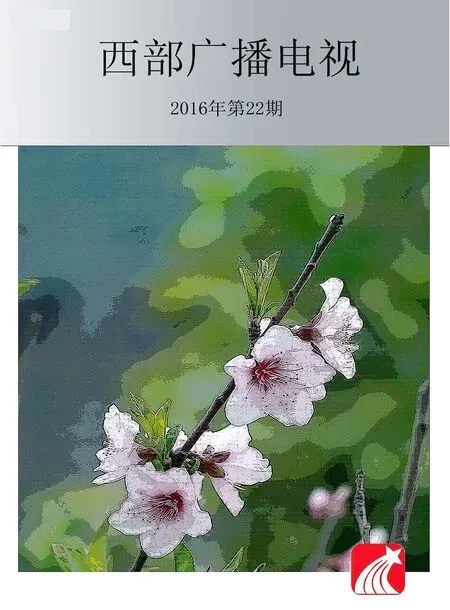廣播直播節目主持人語言表達問題淺析
劉 宇
(作者單位:哈爾濱鐵路局新聞媒體中心)
廣播直播節目主持人語言表達問題淺析
劉 宇
(作者單位:哈爾濱鐵路局新聞媒體中心)
隨著收聽習慣的改變,廣播節目的收聽人口增多,年齡跨度增大,廣播媒體的影響力逐漸擴大,國內廣播電臺迎來了十年的黃金發展期。各地電臺紛紛增加頻率、增辦節目,致使主持人隊伍不斷擴大,主持人在節目直播過程中的語言問題開始引起人們的關注。
廣播;主持人;語言表達
1 主持人直播用語問題
1.1 輿論導向偏差
語言作為主持人的工具,不僅直接反映主持人的個性和品質,還關系到其所在媒體的輿論導向。有一些主持人在節目中的隨意化傾向比較重,一些偏激觀點和偏離黨和政府方針、政策的語言間或出現,造成不良影響。渲染“亡命哲學”“頹廢哲學”;崇拜“升官發財”,追求“五子登科”,鼓吹“讀書無用”,質疑公平正義,扭曲醫患關系,大肆談論宗教問題。這些現象與我國一貫倡導的正確人生觀、價值觀相悖,降低了廣播電臺和廣播節目的檔次,影響了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有的還涉嫌違反、觸犯相關法律規定。
1.2 表達粗俗低劣
主持人的語言是口頭語,力求通俗但絕非粗俗,更不能低劣。日常生活中的口頭語言經過篩選、加工、提煉,最終形成的語言才是主持人應該使用的語言。對民間語言尤其是網絡語言的選擇性使用,是必不可少的凈化、純化的過程,包括舍棄其中不規范、不純潔的語言現象,努力使之更準確、順暢、健康而又不失生動和生命力。個別主持人為了追求所謂的節目效果,讓自己與“犀利哥”“快刀姐”的標簽相匹配,不惜犧牲語言的高雅與潔凈。
1.3 文字功底不深
在直播節目中,主持人口頭表達的重要程度絲毫不亞于平面媒體的書面表達,這就對主持人的文字功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直播節目中,主持人口中犯下的錯誤卻屢見不鮮。成語誤用濫用:某婚慶節目主持人幫情侶選婚宴酒店,“這天是大日子,喜宴多,酒店不好選,只能差強人意了”,“差強人意”的意思是“還能讓人滿意”,此處卻被誤用為不滿意。一檔教育節目主持人告誡一學生聽眾要學有所長,“學無建樹,身無長物,將來怎么在社會上立足呢?”,“長物”本意是“多余的東西”,被主持人誤用為“特長”。隨意制造詞匯:不知始于何時,軍人的妻子被稱為“軍嫂”并風靡全國,隨即“房嫂”“月嫂”“工嫂”“農嫂”甚至“地嫂”等詞匯蜂擁而至。這些“嫂”的提法本身就欠妥,生硬造出來的詞匯更是令人費解。不了解詞義想當然地去用:在某餐飲節目中,主持人說“你們店里的松鼠桂魚味道正宗,我們吃過一回還會再度光臨的”。“光臨”用于敬稱他人來訪以及賓客來到,用在自己身上則明顯不合適。
1.4 濫用網絡語言
網絡語言新鮮、生動,但不完全適用于廣播節目,有些還屬“三俗”范圍,應在抵制之列。“坑爹”一詞最早出現于網絡游戲魔獸世界,一般用于諷刺、嘲笑或吐槽不滿,在廣播節目中出現則顯大不敬;“屌絲”是中國網絡文化興盛后產生的諷刺用語,現在已被一些單位列入文明忌語當中,在個別節目中,仍有主持人用這個詞插科打諢;“翔”在網絡用語中作為“大便排泄物”的代稱,某交通臺主持人播報路況居然說“堵車堵成了翔”。“逗逼”“娘炮”“做人不能太李毅”等也間或被主持人提及。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已制定相關文件對此現象進行規范。
1.5 自身稱謂失當
主持人自身稱謂不當,會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節目的水準。某省臺婚慶類節目主持人在節目中稱自己是“委員長”,并引導甚至強迫參與節目的聽眾用這個專有名詞稱呼自己。委員長是政黨或政府高階官職名稱,在中國與日本的黨政組織中皆有名為“委員長”的職務。主持人稱自己為委員長,表面看是不嚴肅,實則是對這個問題的無知。某省會城市臺的一位主持人同時主持汽車和婚介兩檔節目。他在節目中自稱為舅舅,后來覺得不妥,又利用諧音自稱為“救救”。每當聽到有聽眾按照他的引導稱呼“救救”時,筆者很是為這樣的節目感到悲哀。另外一種情況是自稱為“哥”或“姐”。這樣的稱謂乍聽起來自然親切,但突出的是江湖氣、市井味兒,不適于大眾傳播平臺。
2 問題根源淺析
2.1 盲目崇洋,“脫口秀”泛濫
先是播音員搖身變成主持人,節目由“播”成“說”,而后又是男女主持“混搭”,“說”新聞、“評”事理,再后來就是插科打諢肆意蔓延。最終導致個別主持人“個人表現欲望”膨脹,“想什么說什么”,節目格調低下、內容失當。
2.2 廣播節目過度商業化
個別媒體將宗旨和責任拋在一邊,一味迎合某些受眾“三俗”收聽習慣,放棄高雅目標。
2.3 主持人選用標準降低
頻率多、節目多,主持人數量隨之增多,選人用人標準不但沒提高,反而有不斷降低的隱憂。主持人隊伍魚龍混雜,節目質量自然很難保證。
2.4 主持人責任意識和職業操守缺失
在工作中缺乏媒體人的社會責任感;把媒體公共平臺當成私下場合隨意交流;放棄對聽眾的正面輿論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