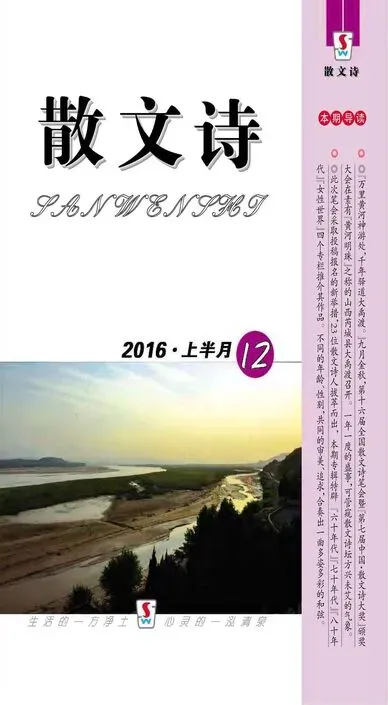蝴蝶
江蘇◎張作梗
蝴蝶
江蘇◎張作梗

在寫作中,我力爭謀求達到一種幾何學般的精確。
蝴蝶
你詢問我對蝴蝶的看法。語氣輕柔像一封情書。
要是我是莊子就好了,或者,是一只蝴蝶也行。可惜我兩者都不是。因此,我與蝴蝶永遠隔著一雙翅膀的距離。也就是說,無論我有怎樣的看法,并不能改變它的方向、顏色、出行時間和它所要駕馭的風的多寡。
頂多,我依稀聽見過它變成了一部悲情傳說的主角。它一分為二,被壓縮為愛情的標本。然而,多少年過去了,它依然在人世飛翔。與之交媾的死亡之夢,依然沒有誰能解析。
有時,它變作一只塵土,飛舞在山野草徑。它飛進眼里,磨損著我的眼球;粘在我的手上,像一粒老年斑;爾后,它飛離我的頭發,遠了,更遠了,消逝在群山透明的呼吸中。
你詢問我對蝴蝶的看法。在一只從書頁掉落的蝴蝶標本上,我答非所問地寫下如上文字——雨,在窗外下了一夜。
雪融
誰失去了誰?
萬物有如從夢中走出,毛茸茸的,慢慢,恢復了它們的本來面目。而有關
一場雪的甜蜜之憶,當最后只剩下這一灘冰冷的水,整個冬天,我們行經其上的腳印,而今都流進了哪一類植株之中?
消融,究竟是一種絕望的滲透,還是一次徹底的遺忘?
大雨。驅車:沿途佳境空置
雨水在玻璃的連接處畫出一條彈跳的虛線,仿佛雨水全是破碎的,全由破碎的云朵和原野構成。
你的到來不會比夜晚更遲。因為雨水是一個巨大的偽裝,早已為你的出場做好鋪墊。
此時,你若赴約,我就是你要兌現的諾言。你如果寫一首悲情詩,我就是你傾訴的對象。而倘若你魔術般把雨水撐開,變成一把油紙傘,我就是你身邊空缺的那個人。
擋風玻璃上,雨水分岔,向上飛跑。
雨刷器來來回回也擦不盡它們蝌蚪般浮游的頭顱。
你的出現不會比一場暴雨更突兀。因為夜晚降臨,萬物模糊又溫柔,
你的到來正好躬逢其盛,順理成章。
此時,在雨中馳行,除了把玻璃連接處那條幻影般的虛線當成唯一的方向,我找不到更好的導航儀。
沿途佳境空置,雨影疏斜,夜色闌珊。
兩個人的孤島
飛翔的孤島。沉淪的孤島。我們用頭顱趕路;騰出腳,去海水和云朵中嬉游。人世狂歡。我們用這鋪天蓋地的狂歡壘筑并加固我們的孤島。我們在這狂歡上飄蕩,克制又縱情。我們的孤島是另外一本臺歷,翻一頁,便是一次潮汐;翻一頁,便是又一個節日。
以其絕緣體般的封閉,我們把我們敞開,朝向世界。應和日月星辰的律動,我們制造出新的生長和律動。我們拒斥又吸納,孤單而浩瀚,無視風暴將我們的身體鍛打為兩截交纏扭動的閃電。
這人跡罕至之地。有多少片刻的消亡,便有多少漫長的沉醉。坐擁錦瑟,我從不吩咐和命令。我只負責享樂。
——愛是我們每日溫習的功課和唯一要做的事。海水濯足,你的裙裾寫滿盛夏紫羅蘭的日記。
海岸線一樣綿長的孤島。我們像一群候鳥,一次次穿過它——穿過時間的子午線。
睡眠深處的雨
雨,下了一夜。
閃電像是一只接觸不良的燈管,隔一會兒亮一下。在萬物慢慢收回它們警覺的影子前,我的睡眠比雨聲還深。
“下雨∕無疑是在過去發生的一件事”①引自博爾赫斯的詩歌《雨》;雨不是下在窗外,也沒有下在別處。它下在我的心上、聽覺上(死了的心和仍在塵世游蕩的聽覺);下在迷離之夢對這個世界的妥協或拒斥上。整夜,我的意識在泥濘中冒煙,雨水就要成為它的助燃劑。
一半的我還原為草本科目的水汽,氤氳在你的呼吸中;另外一半被階上冷雨沖進排水溝,流到我遙遠的肉身之外。
愈被遮蔽,窗外搖晃的路燈愈發顯得突兀、狐疑。好似一只枯葉蝶,我棲歇在夜色巨大的枝條上,連風也不能辨識。——你的晚禱和早誦,串成綠色之雨的火車皮,夢境般掠過我睡眠的窗口。
雨,下了一夜。
(張作梗本名張海清,1964年出生,湖北作協會員,現居江蘇揚州。作品散見《詩刊》《星星》《詩歌報》《揚子江》《詩選刊》等報刊,出版詩集2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