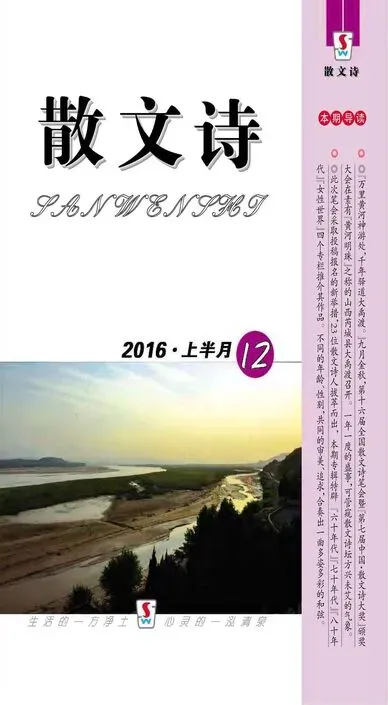祈禱
重慶◎徐庶
祈禱
重慶◎徐庶

詩歌是養心學,它把詩人從黑色影子中解脫出來。
祈禱
一朵蓮,在掌心端坐如佛。它被羞澀寵愛,四目禁閉。
如此,靜靜地綻開。如你我的中年,在波瀾不驚中,那么靜如處子。有嬌,不媚。
空即滿,它在睡意里醒著。
我明白,一旦被掌聲撐開,蓮花便成了別人的手掌,左三拍右四拍,在風中喪失矜持,喪失自己的語言和方向。
世間萬物,睜開眼睛的,卻并沒醒來。
比如水下那些游魚:脊背剛好低于水平線,低調地醒著,謙卑地活著,不貪戀一汪飽滿的江湖。
比如游進我們眼眶的思念:清醒的,竟是那些一閃而過看不到的……
所悟
風起。我才看見,那些矜持的樹木內心,藏著一道雷電之手。
往風的裂口里,有人伸進帶倒鉤的爪子。想要掏出什么?伸出一半,又悄悄縮了回去。如我們猶抱的琵琶,遮面,亦遮心。
風被風灌滿時,如同睽睽眾目被謊言灌滿,一樣安靜。
此時,燈火被月光灌滿。我才所悟:為何右手,不可一生緊握的是自己的左手。
我長父親6歲
雜草一年比一年年輕,父親也是這樣,笑笑,就把日月拋在了身后。
我比父親長得快:我45,長父親6歲。
每年,我為父親拔去頭上雜草,每拔掉一根,我的頭上就多了一根白發。
當我佝僂著一天天彎腰時,父親,還是那個39歲小伙,躲在畫框里,微笑。
去北海
在禪福寺,有人見佛就跪,額頭磕出朵朵蓮花。
“福田花雨”架上,一層又一層的“福”,被銅器壓得喘不過氣來。
祈愛情雨順的“福”,在風中,叮叮當當;祈官運亨通的“福”壓在最底層,不知善主求到了哪一級。
永安寺的羅漢,一個人笑出聲來,圓圓的銅皮肚,被信眾摸出了時間的油。
風
這是內蒙珠日河,這是馬群和風的故鄉。
跑來和馬群爭吃這片草地的,是風。我看到的,馬一直低頭,向青草贖罪也津津有味。
殊不知,蟄伏在草根的風是個負心郎,怎么也負不起,一個蹄掌深深淺淺的重托。
一些沙子命的人,夾在沙子中,沙子一樣沙沙沙漏下來。
他們卻不知道,自己已成了一股風。
縫月光
狗狗在前,穿著和孫孫一樣顏色的黃馬甲。爺只是一條活蹦亂跳的尾巴。
爺孫倆也曾是這樣的:孫孫引路,不緊不慢,踩落一地月光。
“別養啊,這是孫孫抱回來的!”爺這么自言自語。
狗狗鉆進電梯,爺跟著踏進去。仿佛兩顆紐扣,把被梯門撕裂的月光,縫了起來。
阿斗
花盆里,歪脖子樹脖子上似乎一直掛著,一顆看不見的秤砣。
它眼里:房子是扶不起來的阿斗,樹木是扶不起來的阿斗,河流是扶不起來的阿斗。飛鳥,也是扶不起來的阿斗。
(徐庶1971年出生,中國作協會員,魯迅文學院第29屆高研班學員,供職于重慶日報報業集團。作品散見《人民文學》《詩刊》《星星》《詩潮》《散文詩》等報刊。出版有詩集《骨簫》《紅愁》《夢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