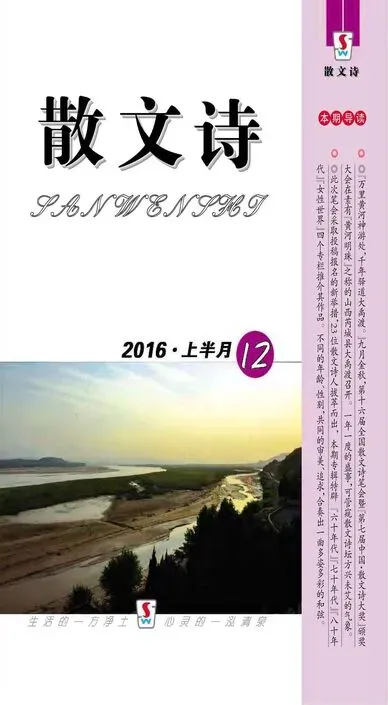生存者的氣息
河北◎曉岸
生存者的氣息
河北◎曉岸

以敬畏的姿態,傾聽心靈的指引。
點燃
我喜歡五月里漫天的氣息。那些野蠻的激情騷動著,樹皮因此脹裂。世界的子宮充溢著汁水。山道柔軟一折,纏住眾人的腳步,在色彩中迷惑眺望的人。
披著葉片和鳥羽的人來到風里。他說出的一切是如此強大而神奇。日光在他身后閃爍,他擅長技藝的手反復摩擦著結滿塵垢的鏡子。
大神到來了,仿佛呼聲圍攏在山谷。鷹群隨著沉默的人們遷徙到遠方,而蔚藍的翁泉河與結烈河相互纏繞。群山在紛亂的光線中微微搖動。
興安之神用鏡片點燃了這一時刻。那些不安而疼痛的人陷入睡夢;那些幸福而渴望的人睜開困惑的雙眼。所有祈求的手一同握緊下午的針葉,在離開之前和它們一樣變得寧靜。
大神點燃了自己無形的軀體。那些黑色的樹根、夜晚、紅色的巖石、云朵、倒流的河、神秘的鷹群的心臟,以及死亡灰暗的嘴唇,沒有語言,死亡將徹底毀掉自己。
在風中急速奔走的樹葉,帶著灼傷,蓋住大地憂慮的眼睛。大神點燃了秋天,點燃了五月和八月。
因為飛雪還在等待。
因為寒冷的巖頂和奔騰于寒流中的蒼狼,在這一時刻它們還在絕望地等待。
這是世界子宮里溫暖濕潤的一天。大神將放棄他不能把握的一切:
世界的意志和命運。
只有我在慌亂地書寫山中點燃的宿命。
因為灰燼是白色的,攪和著孤獨的血液重新形成骨頭。
它將結構成我們行走的肉體和無法命名的一切。
消失的雨:或回旋的低唱
薄暮時分,從山道上斜出的人影把你和這個世界劃分成兩個部分:明亮的西天,漸暗的群山。
手中的樹枝沾染著泥土和草汁的香味。和你擦肩而過的人那神秘的眼神變得晦暗。遠處是一片迷蒙的無聲的樹木、建筑和早出的星辰。
不必回憶過去的人與事:一個時代的興衰和個人的遭遇。傍晚的篝火,沉默的老人,煙縷的氣息,充滿小街上的五月松脂的芳香。
那突然消失的聲音:合唱的樹葉和跳舞的草。一個孩子在大人的背后被斧頭割傷。他蹣跚地奔跑、哭泣。五月的大地上,森林和群山傾斜。
一群人遠去。又一群人遠去。
櫟樹背對巖石支撐住黑色的葉子,它在夜鳥回來之前叫醒我回到人間。我是陌生的人。突兀的根穿過我的胸膛,那干燥的呼吸又一次失去律動。
現在我已遠離了這一切:泥濘的雨季,敲打窗子和樹枝的雨像早逝的情人。許多不能回去的記憶霉變,許多值得回憶的東西喪失。綠色的風聲跳過閃亮的葉尖。落下的雨水埋葬了生銹的工具。
如果你赤裸上身走出叢林,雨水將成為你的一部分。成為驕傲、姓名、血液和皮膚最敏感的一部分。成為今生揮之不去的痕跡。還有愛恨,充斥著人間的糾葛,像林地間靜止的松針,被輕輕地放下。而親人的悲歡和疼痛的理想像那拾不起來的散落林間的樹籽。
曲曲折折的四季。帶來的不是白雪和春水,而是五月漫天的雨絲。澆濕了篝火,和山地上奔跑在風中的紙鳶。
你把握住了么?
那山地上的人影將帶走你。不論你是誰:時光、星辰、蒼狼的化身、死去的草根還是夢想的結局——
生存者的氣息
樹木也許會感受到這樣的日子在逼近。
它們都散開,人群一次次蜂擁而過,在身后留下未燃盡的碳灰和潮濕的木塊。泥濘的轍跡像嘆息。扭曲著,重疊,覆蓋,在最后一天變得僵硬起來。
你一直在我身后,就像過往的生活。你深深的氣息讓我不能堅持——
……冬天從北邊圍過來。那里空曠的北方,青藍的蒼穹,鷹隼艱難地犁破沉重寒冷的空氣,升高,而后消失在群山之上。
你用手撫去我胸膛上的冰碴,俯下身,我像感謝生活一樣從此對死亡不再吃驚。點燃草枝把黑夜逼退,我平靜地面對你,像面對一次遠行。你的淚水如同暗紅的鐵汁落在我的心上……
我說過,一切都將重來。
在那里,白雪埋住白雪,眺望支撐眺望。
我瘋狂地劈開那些沉默的樹樁,一次次,我把自己推向危險的崖邊——
“你聽到了么?你握緊了么?”
——又是你。
當我把自己暴露在山林之中,把肉體懸掛在樺樹上,讓鐵器不斷地升溫,替代我的靈魂。
我一再張望,睜大眼睛忍住恐懼,用白雪緊緊捂住我冰冷的雙唇——
那沒有理由不能承受的輕與重。
那點滴的散亂的證據:那些不能行走的樹,巖石和陰郁的鉛云,干冷的風中折裂的鳥翅,你的影子……他們就像一個個傳說久久不能散去——
這是生活!
冬天緩慢地移動。群山迎接這盛大的死寂而虛無的光陰。我把自己裝進軀體里,允許他去揮霍,去放縱,去承擔和放棄。在麻櫟一樣粗糙的日子上放出血,讓它們散開,模仿樹枝返回枝頭的動作。
模仿你和你從未出現的眼神——
(曉岸本名代曉偉,1971年出生,黑龍江省作協會員。作品散見《星星》《詩刊》《詩潮》《北方文學》《詩林》《綠風》等刊物。現居河北承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