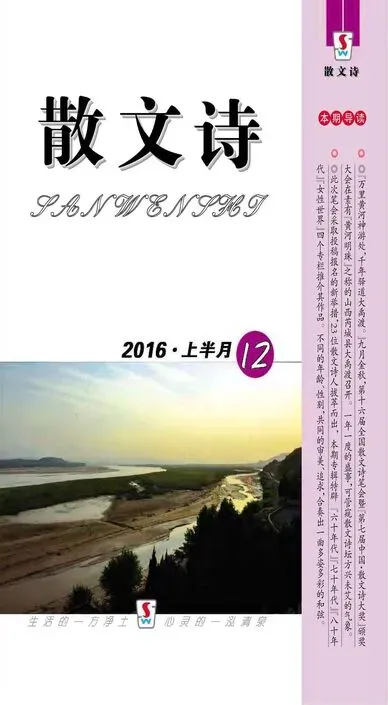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
甘肅◎王琰
從一座山到另一座山
甘肅◎王琰

詩歌如拉著輛上坡的板車,一刻也不能松手。
紅土尕莊
紅土尕莊是個靠山的村子,爺爺和奶奶住在一院順山勢修建的屋子里,我童年很多時候是爺爺和奶奶帶著我。不聽話時,奶奶會用一塊劈柴打屁股。而爺爺,把我放在柴房小屋的屋頂。我就在上面吹風,爺爺啊,我聽話呢。爺爺就會放我下來。我想念那風,清涼而柔和。紅土尕莊夾雜著童年,被我寫進文字——讀到這里,停下來重復再讀一遍的人,會不會是我失散的親人……
紅土尕莊據說出土過億萬年前的犀牛化石。我沒有見過犀牛,有一大片水洼地,我總在那里玩耍。水洼有狗魚,沒有鱗,狗魚躍起來像一枚舊錢幣。水洼里的狗魚,每天吃掉和自己體重相當的食物,偶爾襲擊蛙、鼠或野鴨,我懷疑,春天里的某一天,它們就會突然變成化石了?
天空中飄浮著楊樹或是柳樹的絨毛。紅土尕莊里住著一位陰陽先生。他為早逝的爺爺選定了墳地,在西山,一面長滿打碗花的山坡上。
陰陽先生的家總是靜悄悄的,偶爾出入的人神情異樣。我想象陰陽先生在安靜的院落里,研習線裝古書,推演著另外一件驚世駭俗的大事情,或許,他可以讓星星在暗中昭示著我回家的方向,讓離世過早的爺爺聽見紅土尕莊的讖語。
舟曲大峪溝
舟曲,藏語就是白龍江的意思。地圖上的舟曲地形狹長,一條潔白的哈達飄逸在岷迭大峽谷里。
盛裝的舟曲人不論男女,都戴著禮帽,帽子上插雄雞尾翎,有說是匈奴遺風。
大漠馬蹄,刀光劍影,好戰的匈奴人揮舞著狼旗追逐著風的蹤跡沖殺,又悄悄在風聲中隱匿,從此音訊全無。黑暗中只剩下一頂禮帽,像是某種宗教儀式的遺存。
舟曲大峪溝方圓幾十公里,有群山環繞,宜種麥屯田。
迎面隨便走過來一個人,怎么看都像是古代將軍的后裔。
高處行走,泉水濯足。天道呈祥,莊稼生長。那么,你還想從秋風中收獲什么呢?
水運處
白龍江畔的水運處,離村子很遠,有一座橋,橋旁有一掛長長的瀑布,匯入江水里。冬天,凍成一道銀河冰掛。我們常從橋頭下去,折了長長短短的冰柱子當冰棍吮吸,透心涼。
路與橋相接的地方,是坡,又帶了拐彎。于是常有不小心的車從這里跌入江水。
村子里的郵遞員呂效先就是騎著自行車從這里一直騎進了白龍江,那天他穿著一身新換的郵電綠的衣褲。
水運處是個專門運送木材的單位,從上游放入整方的木材,接下來就是等待。如同一封封投入郵筒的信。
打撈的時間即使用秒表把握得再精準,總有一些木材撈不回來了。
騎車子的呂效先,還有開車的王守孝,他們扎進白龍江,就如同丟失的信件,與這個世界從此失去了聯系。
白龍江時而安靜時而洶涌,奇怪的是,江水從來不會迷路。夜再黑,森林再多,赤足流過的江水,從不回頭追問緣由。
一輛卡車,拉著一堆貨、一群羊,車上還有幾個人。開車的人大概是睡著了,車子一頭撞進了白龍江。
有一些人獲救,傷勢嚴重。有一些貨物撈了上來,七零八落。唯獨車上一個小孩順流游去,奇跡般地從下游上了岸。
他穿著濕衣服回到家,告訴了大家車禍的來龍去脈。他的手臂只擦破了些皮,他的身體里像是藏著這條河流。只是,這小孩從那天之后從不再提起車禍。
白龍江知道這一切。白龍江像個大人物,背著手,走過來,一言不發。
木匠
迭部多樹木。我家院子里就長著很多樹。小時候,我覺得院子很大,院子里的水泥臺階很高。臺階上有一處印痕,大人們說,這是一只狼,深夜在未干透的水泥上踩下的爪印。所以,晚上不可以出門瘋玩。
那個印痕沒能嚇住我們,我們照舊在有月亮的夜晚出門瘋玩。
我從水泥臺階上摔下來,摔落一顆牙,埋在樹窩里。院子里有幾株石榴、幾株杮子,還有幾株花椒樹。牙長了出來,院子里又種下一株樹。
我每天梳著小辮,走出門,一只鳥巢,在樹上抬眼就能看見的地方。
等不到院子里的樹長大,我家已買了很多木頭做家具,說是兩個哥哥將來結婚用的家具都要準備好。
水渠柳是長在水渠邊嗎?一塊塊木頭推出長長卷曲的刨花,露出漂亮的紋理,嘩啦嘩啦,水渠柳水波蕩漾。
木匠埋頭干活,仿佛要把所有的木頭都推成刨花。我把自己埋進半房子的刨花和這芳香的氣味中,我默默地想,長大了,我要嫁給木匠,我要擁有一房子又一房子的刨花。
迭部
那一年,我們結伴去了迭部。在那之前,我一直孤獨得像落了單的鳥。黃昏沉靜而泛黃,棕色、金色勾邊,如燭火下祖母的臉,安寧、慈愛,就算我犯了什么錯,它也一定會包容我的。
迭部,神的大拇指摁出的一小塊山地,周圍山勢峭拔。吐蕃戍邊后裔繁衍生息,石頭高低錯落,有土的地方繡花般播下種子,小麥迎著秋風生長。
暮色中,彎月如一柄銹蝕的殘刀,正悄悄插上山梁。昨夜的花朵盛開在大地上。
一個男人在清晨攀上虎頭山的山崖,用一支鷹的翎吹出長長的嘯叫。太陽升起來了,男高音的太陽,在這里升起來了。
一匹匹馬兒在大地上奔跑,奔跑出:勒——勒是迭部民歌。
九層閣
九層閣,米拉日巴佛一個人修建的佛閣。修建過程中有人幫他,哪怕只是搬來一塊石頭,他也必須搬回原處。米拉日巴的九層閣在西藏,此九層閣非彼九層閣也。甘南米拉日巴九層閣是仿建的。
我們為叩佛而來,為米拉日巴的精神而來。
山坡上,矗立著高高的九層樓閣,沒有一層一層的檐牙翹角,整座建筑筆直地拔地而起,直沖云霄。
朝佛者抱著香燭、柏枝,往香爐里添加香火。彌漫的煙霧,籠罩著虔誠的信徒,時隱時現。佛閣四周的轉經通道,誦經的人用力撥動著經輪,轉了一圈又一圈,不停地轉。
米拉日巴在雪山上苦修九年,飲冰雪、食青草,身體膚色都變成了綠色,最終印證了“大手印”和“拙火定”密法。
九層閣大門響時,經筒還轉著,一個身體綠如青草的人,生來就是被供奉的。
此時,正值正午。
正午用來睡眠,用來誦經,用來講述。
一只麋鹿跑過九層閣,天空變陰。走下九層閣,院墻上一排排白色尖頂的佛塔。
高高的九層閣,每層前面的布幔都開一小窗,佛會不會透過它來看看外面的世界?
(王琰中國作協會員,魯迅文學院24期高研班學員,《蘭州晚報》副總編。作品散見《天涯》《散文》《詩刊》《星星》等報刊,出版有作品集6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