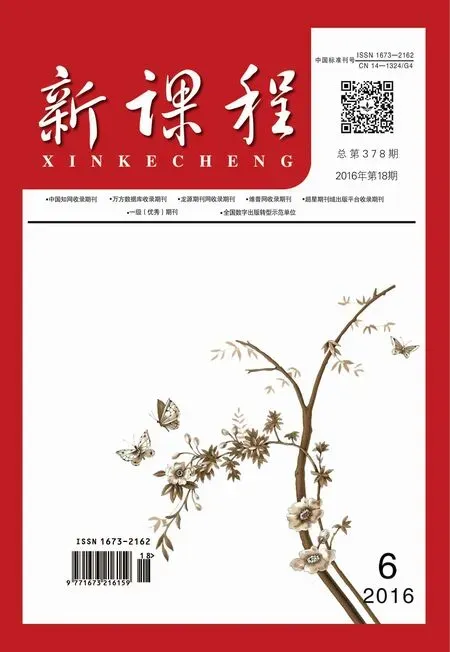論文學創作的民間立場
閆石(山西省文化廳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論文學創作的民間立場
閆石
(山西省文化廳文化政策研究中心)
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文學界,“民間”引起人們的廣泛關注。它從一個獨特視角,為文學批評和文學史研究注入了生機勃勃的理論活力,它的文化意識和文化價值深深觸動了知識分子對自身價值的思考。“民間”的存在無疑給知識分子精神發展、文學創作拓展了文化空間。
民間立場;創作;價值取向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一批新時期作家諸如余華、張煒和莫言等在小說創作上有共同的民間立場,同時又各具鮮明的特色,各自有著不同的價值取向和文學表達。所謂“民間立場”,可以理解為“民間”這種非權力形態也非知識分子精英文化形態的文化視界和空間,滲透在作家寫作的各方面,作家把自己融入民間,以講述老百姓故事的方式為出發點,表達對時代的認識,并從中確認理想的存在方式和價值取向。它是對“民間”的價值取向的尊重與認可,特別是民間價值取向與主流價值產生錯位甚至背離時,他們依然能從一些看似陳腐的精神資源中發掘出鮮活的生命與時代價值。可以說,民間立場是以“民間”為立足點和出發點的寫作姿態,在此基礎上,作家通過民間敘述,進一步體現自己的民間情懷和民間價值取向,并在作品中表現出民間的審美風格。作家的民間立場,從一定意義上來說就是人性的立場,是人道主義的立場。
“民間”首先是一個自由自在的客觀存在,是相對于政治空間和主流意識形態空間而存在的。在這里,人們的思想、觀念、道德、情感、人性等都處于相對自由和真實的狀態;人們的生產、生活、交往等活動大都出自自然本真的需求,相對來說沒有更多的顧忌和矯飾,這表現為淳樸自然的民俗民風,表現為人們樸實本真的性格。藝術創作的特性和特殊規律正需要這樣一個自在的生活空間和審美空間,這里蘊藏著豐富的藝術創作資源,蘊含著巨大的藝術創作的可能性。
首先,從創作題材上看,民間立場的作家都有著“走向民間”的共同眷戀:故土。如張煒和莫言都在鄉土的民間世界中出生長大,都對哺育自己成長的故土有著刻骨銘心的記憶,懷有深深的依戀。投入創作后,兩位作家源源不斷地將生活的經歷和體驗訴諸筆端。他們自覺地將故土設置為創作的背景,一次次地將人們帶入那片翠綠的葡萄園和火紅的高粱地。各自在家鄉的土地上,發掘著民間傳統文明在歷史、現實、時空中的生命力。
其次,從創作主題上看,此類作品都持有鮮明的民間立場。作家們都自覺從民間出發,從民間自由自在的人身上尋找發掘人的本性;或者把人放到民間話語中去考察,從而發現被遮掩的人性。作家還以民間的視角來審視歷史與現實,驅除了意識形態的蒙蔽,發現和構建了一個全新的民間歷史。
一、民間立場的文學創作對“人”的發現
著名文學批評家劉再復在《我國文學史上對人的三次發現》一文中指出:中國文學向來忽視“人”,人的價值被蔑視、被踐踏,以人為本的觀念始終沒有形成。“五四”以來我國現代文學直到當代文學不斷有新的思潮出現,這時,第一次人的發現出現了,這股思潮的變遷史大體上是人的觀念的變遷史,更具體地說,是人在文學中的地位的變遷史。
新時期文學伊始,出現了又一次“人的發現”,有歷史的反思、人的重新發現、文學形式的新探索三個特征,而中心思潮是對人的重新發現。這次人的發現本質上是五四運動人的發現的重復,但具有更深層次的發現。“五四”時期對人的肯定是求助社會,要求社會改變吃人的歷史,要求社會肯定人的價值,包括小人物的價值;而民間立場對人的發現,他們并不是求助社會,而是求助于己,求助自我。怎樣描寫人,怎樣對待人,真正的作家決不把他的人物當做工具,當做傀儡,而是把他當成一個人,當成一個和他自己一樣有著一定思想感情、獨立個性的人來看待的。他一定是充分尊重這個人的個性的,他可以通過自己的是非愛憎之感來描寫這個人物;他可以在他的描寫中表示他對這個人物的贊揚或是貶責,肯定或是否定;正像在生活中,他可以通過自己對一個人的評價來介紹這個人一樣。但他決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強加到他的人物身上去,迫使他的人物來屈從自己的意志。在生活中是如此,在作品中也是如此。
二、民間立場對歷史的重新認識
在中國當代,“革命歷史題材”一直是文學的重心所在。黃子平說:“‘革命歷史小說'是我對中國大陸1950至1970年生產的一大批作品的‘文學史'命名。這些作品在既定意識形態的規限內講述既定的歷史題材,以達成既定的意識形態目的。”可以說,這段敘述較為客觀地概括了革命意識形態對文學浸染和侵占的起因和過程。文學在一個特殊時代承擔了對它來說過于沉重的政治使命,而通過文學,主流意識形態也極為巧妙地完成了對大眾、對民間的侵占和改造。這種影響往往比想象的要深刻和深遠得多,它是滲透進人的血液和靈魂里的。然而人的意識的轉變是需要一個過程的,尤其當這種意識已經深入人心成為一種傳統的時候,即使社會發生深刻變革,主流意識形態發生深刻變遷,傳統的習慣意識還往往牢牢地控制著人們的心理高地。
歷史自有它的真相,只有有思想、有勇氣、目光銳利的作家才可能沖破意識形態的牢籠,也只有有見識的讀者才會跟隨作者去探尋發掘一個被遮蔽已久的歷史。而銳利的目光來自全新的視角,思想和勇氣來自民間的情懷。余華、張煒和莫言等就是具備這種目光和勇氣的作家。
歷史是由人來書寫的,要重新認識歷史,探尋歷史的本來面目,只有重新探尋人的內心,探問人的本性,才是重新解讀歷史的最好途徑。而要探究人的本性,最好的途徑就是回到自由自在的民間。民間立場的小說創作正是由此著手,開始對歷史進行解讀和重構的。
小說是寫人的,一部小說就是一部人的歷史,它總是通過寫人來傳達作者對現實或歷史的認知,或者說,小說中的人物承載著作者心目中的現實和歷史。作者通過對人物形象的塑造來呈現現實或歷史,表達自己的歷史觀和價值觀。余華、莫言等作家站在民間立場,在小說創作中塑造了一個個人性化的人物群像。與此同時,舊歷史的城墻土崩瓦解,一座全新的人的歷史在民間巍然聳立起來。
當然,顛覆、解構歷史并非藝術目的之所在,它只是手段而已,顛覆的目的在于重建。民間立場的小說對官方歷史的質疑,其實際上是從真實復雜的人性角度來還原立體化的歷史真貌,變歷史一元的話語權為包括民間在內的多元話語權,站在一個平民百姓的立場上書寫著自己眼中的歷史。
三、民間的當代價值
在中國20世紀的文學史上,知識分子與民間之間的關系可以描述為這樣幾種具有代表性的模式:(1)啟蒙與被啟蒙者。在世紀之初陳獨秀、胡適等人發動的新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是啟蒙者,大眾是啟蒙對象。(2)失衡狀態。政治意識形態砝碼的加入,打破了知識分子與大眾的關系。20世紀30年代出現的“大眾文藝”的論爭,知識分子與民間的關系出現了微妙的轉移,知識分子的啟蒙內容增添了政治的比重。(3)顛倒狀態。20世紀4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與民間之間的關系徹底顛倒過來,知識分子的啟蒙者身份喪失殆盡,逐漸淪為嘲諷和攻擊的對象,知識分子與民間產生了前所未有的緊張,這種關系模式持續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4)對話關系。20世紀90年代,韓少功、李銳等作家的“民間”不再是某種理論的強制性攤派,不再是某種冰冷的意識形態虛構,他們的民間就在身邊,他們走進民間、親歷民間;他們驚奇地意識到民間是文學不盡的資源,文學必須與民間保持不懈的對話。
審視事物的立場和視角發生轉變,就必定有新的發現和建樹。民間立場的寫作正是擺脫了主流意識形態的挾制,自覺從民間的視角來審視人和歷史,他們才發現真正的人和歷史。張煒《家族》中的人物個個是鮮活的,是有血有肉的,他們不同于一般革命歷史小說中呆板毫無靈性的人物。莫言《豐乳肥臀》的人物塑造也許時而帶有某些荒誕色彩,但它凸顯了真實的人性,所以這也是一種真實,甚至是更高層次的真實。余華的《活著》講述了人是為了活著而活著,而不是為活著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著。“活著”是一種張力,是一種希望,是承受不可承受的生命之重。這是一部闡釋“活著”的寓言,是一部描寫人生存鏡像的寓言。作家們都把筆下的人物回歸到人性和歷史的真實狀態,回歸到他們各自應有的“人”的位置上,從而使他們具有獨特的藝術魅力。《家族》中用細膩深刻的筆觸痛苦地反思歷史,《豐乳肥臀》用揮灑超脫的筆觸毫無顧忌地嘲笑著歷史,他們用不同的方式對歷史進行了重讀和重構。還有張煒的《九月寓言》《外省書》,莫言的《檀香刑》《生死疲勞》,余華的《許三觀賣血記》,這些代表作品都體現出一致的寫作立場和風格,不同程度地達到了相同的表現效果。
可見,“民間”的存在無疑給文學藝術的生成提供了豐富的資源和空間。作家如果自覺主動地與民間接近,與民間融合,在民間尋找文學創作的資源,在民間獲取文學創作的靈感,在民間尋找文學的根,那么他的創作就會給文學帶來新鮮的東西,他們的作品所表現和所承擔的,往往更是文學本身應該表現和承擔的東西,他的作品往往更接近文學本身。這是因為,民間的創作立場契合了文學的本質,契合了文學藝術創作的本質規律。可以說,民間的立場和方法不僅是一種創作態度和創作方法,對它的取舍更體現了作家對文學本質和藝術創作規律的理解和認識程度。
作家不同的生活經歷、不同的思想情感、不同的感受生活的方式、不同的藝術氣質以及不同的藝術創作理念,決定了作家創作的立場和方法。有的作家主動與民間接近,與民間融合,在民間尋找文學創作的資源,在民間獲取文學創作的靈感,在民間尋找文學的根,在創作中自覺或者不自覺地采取一種民間的立場。文學史和文學創作的事實證明,站在民間立場創作的作家,往往會給文學帶來新鮮的東西;他們的作品往往更接近文學本身,他們的作品所表現和所承擔的,往往更是文學本身應該表現和承擔的東西。選擇民間立場的作家,他們似乎跟真正的文學更接近,他們的作品往往更具備文學藝術應有的魅力。
在文學“邊緣化”的今天,被稱作“新民間寫作”的網絡文學卻如火如荼,而備受批評界關注的“底層寫作”的內在精神與“民間寫作”也是相通的。
文學不會消亡,它就像原野上的野草,只要有適宜的溫度、濕度和陽光就會蓬蓬勃勃地生長。
[1]朱光潛.西方美學史[M].北京:人民文學社,2003.
[2]李建軍.必要的反對[M].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5.
[3]林建法,徐連源.中國當代作家面面觀[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3.
[4]陳思和.雞鳴風雨[M].上海:學林出版社,1994-12.
[5]黃曼君.中國現代文學經典的誕生與延傳[J].中國社會科學,2004(3).
[6]王光東.民間與啟蒙關于九十年代民間爭鳴問題的思考[J].當代作家評論,2000(5).
[7]南帆.民間的意義[J].文藝爭鳴,1999(2).
·編輯薛直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