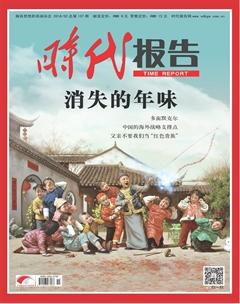陳大維:不愿在死亡來時(shí)悔意年輕
林迪


“衣服是一個(gè)有生命的個(gè)體,我希望有天它能遇到一個(gè)喜歡它的人,與它相處,善待它。”
“一個(gè)胡同、一間房子、一個(gè)人、一臺(tái)縫紉機(jī)、一個(gè)人臺(tái)、一臺(tái)電腦、一些布、很多亂七八糟的東西。”陳大維這樣描述自己租住的房子。
他的家看起來是生意不太好的那種裁縫店,陳大維在里面睡覺,也在里面制衣。為了增加點(diǎn)生活情調(diào),他在房間的角落擺上了一些花草和工藝品。
最近這個(gè)家的地址在網(wǎng)上公諸于眾。陳大維在一個(gè)網(wǎng)站上發(fā)了一條同城活動(dòng)招募,活動(dòng)的名字叫做“服飾設(shè)計(jì)私人培訓(xùn)”,他公開了自己的微信、電話、家庭住址和一個(gè)公眾號(hào)二維碼。
“你是想學(xué)做衣服嗎?”一旦有人加他微信,還沒等你開口說“您好”,他就會(huì)搶著打過來一行字,“歡迎來 Dave Chen 學(xué)做衣服。”不是自動(dòng)回復(fù)。
但是見了面,會(huì)發(fā)現(xiàn)他是個(gè)不太會(huì)說英語的人,甚至連中文也有些吃力,“我叫……那個(gè)……你叫我大維……就可以。”
“我就是個(gè)做衣服的”
2014年,陳大維從天津某二本師范大學(xué)的服裝設(shè)計(jì)專業(yè)畢業(yè)。現(xiàn)在他的日常工作是自己畫圖、設(shè)計(jì)、打版和上機(jī)制作衣服,這一點(diǎn)和裁縫不同,裁縫按照客人的需要工作,但陳大維只為自己而做。
也是在2014年,他開了一個(gè)微信公眾號(hào),宣告自己的原創(chuàng)品牌店成立。但是這個(gè)大學(xué)畢業(yè)才一年不到的年輕人既沒有固定客戶,也沒有發(fā)布成衣的渠道,更別提高級(jí)定制了。在他家里的一整支衣架上,掛滿了他自己設(shè)計(jì)的衣服,有大衣有裙子,卻沒有一件他打算拿去賣的。
“我不是設(shè)計(jì)師,我連縫紉工都不算。”陳大維不太好意思地扯了扯衣袖,“我就是個(gè)做衣服的”。
“做衣服”這三個(gè)字常常掛在陳大維的嘴上。對(duì)時(shí)裝行業(yè)熟悉的人大概都知道,《做衣服》也是日本時(shí)裝大師山本耀司的回憶錄書名,那本書從早年山本父親在二戰(zhàn)中的去世,講到他母親的裁縫店給他帶來的影響,再從他遠(yuǎn)赴巴黎開始自己的設(shè)計(jì)生涯講到和北野武等眾多海內(nèi)外藝術(shù)家跨界合作。光輝之下,不變的始終是他對(duì)服裝工匠式的執(zhí)著。這些內(nèi)容被精煉成一句話寫了在書的封帶上——以命相抵,制作服裝。
陳大維讀過這本生平流水賬式的書,那是他畢業(yè)后買的。“寫得太無聊了,”他強(qiáng)調(diào)道,“我不喜歡山本耀司,他的書也沒有啟發(fā)我什么。”
陳大維沒有山本耀司那樣開裁縫鋪的家人,他的父親做著小本生意,母親是主婦,偶爾也會(huì)務(wù)農(nóng)。大概唯一能與針線設(shè)計(jì)扯上關(guān)系的是他的家鄉(xiāng)甘肅慶陽最著名的香包。事實(shí)上,陳大維說他高考之前當(dāng)?shù)刈钣忻钠放凭褪敲捞厮拱钔?/p>
“那時(shí)候什么山本耀司啊,我連Gucci、Chanel都不知道。”高考時(shí),一心想去南方念書的他卻沒考上適合的學(xué)校,最后他選了天津的一個(gè)師范大學(xué)讀到了自己心愛的服裝設(shè)計(jì)專業(yè),“山本大哥是大學(xué)的理論課上學(xué)的”。
口上說著不喜歡山本耀司的陳大維,其實(shí)總有意無意地追隨那位大師的人生軌跡。山本在中學(xué)時(shí)一直沉迷于畫畫,在高中時(shí)每到周末就會(huì)去專業(yè)的繪畫教室學(xué)習(xí),陳大維也同樣如此;山本對(duì)他的母親有太深厚的感情,陳大維說自己對(duì)服裝的啟蒙是曾經(jīng)去過大城市見過世面的母親;而山本曾回憶自己第一次見到牛仔褲時(shí),覺得靛青色有說不出的優(yōu)雅,而牛仔也是陳大維最喜歡的布料。
但是陳大維沒有和山本一樣在畢業(yè)典禮上得到優(yōu)秀設(shè)計(jì)遠(yuǎn)藤獎(jiǎng),他的畢業(yè)作品因?yàn)榧舨寐度馓喽煌瑢W(xué)拒絕穿著,人們笑他是一朵“奇葩”。
“我覺得還好啊。”陳大維從隔間里的箱子底端翻出來那件畢業(yè)作品,他現(xiàn)在對(duì)于展示它依然感到自豪,那是一件牛仔吊帶背心,左側(cè)沒有封口也沒有拉鏈,就那樣任性地敞開著,“可能他們覺得不太好穿吧,其實(shí)我已經(jīng)很收斂了。”
臨近畢業(yè)季時(shí),陳大維來到北京尋找實(shí)習(xí)的機(jī)會(huì),他決定把衣服拿到一個(gè)開店的朋友那里去賣。但很快,他那些過于自我和偏執(zhí)的想法在殘酷的市場(chǎng)面前一敗涂地,衣服賣得很差,很快他就付不起當(dāng)時(shí)每月2400元的房租。
“后來我就不賣了,就自己做,想做什么做什么,一做就做了四五個(gè)月,感覺要自殺似的,特別糾結(jié)。”如今的陳大維說這些的時(shí)候,顯得很輕松,他的電腦里正悠悠地放著一首伴著古琴,唱詞哼哼唧唧的曲子。
他選擇了一條“小路”
他稀里糊涂地畢了業(yè)。這時(shí)候社會(huì)上的慣常想法是,一個(gè)學(xué)服裝的學(xué)生畢業(yè)了該去設(shè)計(jì)公司做助理,然后一步一步到設(shè)計(jì)師。
還有另一條路徑是,直接申請(qǐng)國外的設(shè)計(jì)院校,圣馬丁、帕森斯、倫敦服裝學(xué)院,讀完研再花個(gè)三五萬開個(gè)自己的工作室,從此直接坐上獨(dú)立設(shè)計(jì)師的位置。這是知乎上一位正在設(shè)計(jì)圈艱難生存的設(shè)計(jì)師給大學(xué)畢業(yè)的菜鳥支的招。
這位設(shè)計(jì)師沒忘提醒一句:“圣馬丁的導(dǎo)師在入學(xué)第一年就會(huì)說一句如雷貫耳的話:如果你沒有錢,不要學(xué)習(xí)時(shí)尚。”
很遺憾,陳大維沒有錢,而且他所認(rèn)識(shí)的圈子,都和他一樣是“窮鬼”。他的同學(xué)中百分之七八十都轉(zhuǎn)了行,或者去了服裝公司,幾乎沒有人像他這么執(zhí)拗地自己做衣服。
他不想放棄。畢業(yè)后的他去了北京雙井的一個(gè)工作室當(dāng)助理,那是一個(gè)叫做“YES”的服裝品牌,在淘寶上開著一個(gè)不大不小的網(wǎng)店。陳大維的工作是打雜,第一個(gè)月先剪布,第二個(gè)月還是剪布,第三個(gè)月是淘寶客服……這一晃悠就過去了四個(gè)月。
這段回憶讓陳大維頗為無奈,“原創(chuàng)設(shè)計(jì)師自己就是設(shè)計(jì)師,他們需要的只是打雜的。還好那時(shí)候我看到了一些東西,知道了工作室如何運(yùn)轉(zhuǎn)。”
天知道陳大維有多么憧憬自己也有一間工作室,YES是他見到的第一個(gè)世面,但是還不夠。他小心翼翼地藏起了內(nèi)心的小孤傲,決定去聽聽消費(fèi)者的喜好。
導(dǎo)購是個(gè)好主意。骨子里,他是喜歡和人交談的,只要和衣服相關(guān)就行。招導(dǎo)購的要求不高,初中畢業(yè)就可以,在這一行里,陳大維算是高素質(zhì)和高專業(yè)了。
他選擇了三個(gè)品牌——江南布衣、速寫和ZARA。“它們賣得可真好啊。我覺得這些都是我未來的客戶群,我得知道他們是怎么想的。”
陳大維講起客戶的故事時(shí),眼睛都亮了。那段日子打發(fā)了他長(zhǎng)久以來略顯孤僻的時(shí)光,品牌的門店是他唯一可以觸摸到整個(gè)時(shí)尚鏈條末端的通道,哪怕那是別人家的衣服、別人家的入賬,以及別人家的客人。
“我最喜歡的就是江南布衣,在那里待的時(shí)間也最久。我發(fā)現(xiàn)江南布衣,二三十歲的高個(gè)子年輕姑娘穿著可真好看,但是呢,她們只是試一試,常常不買。”陳大維分析起來頭頭是道,“我想一是年輕人購買力有限,二是年輕身材好啊,穿江南布衣好看,穿別人家也好看,江南布衣還很貴,價(jià)格上沒有優(yōu)勢(shì),所以最后買的都是中年人。”
在三里屯做了半年多導(dǎo)購,對(duì)顧客有了一定認(rèn)知后的陳大維卻有些沮喪,因?yàn)樗谝淮握媲械匾庾R(shí)到,原來他喜歡的東西真的讓市場(chǎng)挺難接受的。
其實(shí)真正刺傷他的并不是和世界背離的孤獨(dú)感,而是那顆實(shí)力還稱不上的野心。他第一次發(fā)現(xiàn)北京如此難以生存,對(duì)于這一點(diǎn),他遲遲不肯明說,而選擇用一種隱晦的方式表達(dá),“我可能從小智商就低吧,所以需要時(shí)間沉淀沉淀”。
于是他帶著全部家當(dāng)搬進(jìn)了現(xiàn)在這個(gè)帶著院子的小屋,當(dāng)作衣服工作室,開始沒日沒夜地做衣服。在北京這座寸土寸金的城市,陳大維覺得那窗前的院子是他的私人領(lǐng)地,在他瘋狂得幾天都不出門也不說話的時(shí)刻,給了他生命的希望。
但殘酷的是,這是一個(gè)高度依賴人脈的行業(yè),理想也需要財(cái)力的支持。英國設(shè)計(jì)師Stella McCartney從入學(xué)圣馬丁之日便受到極大關(guān)注,成立個(gè)人品牌后又一帆風(fēng)順地被LVMH收購。但發(fā)生在她身上的并不是一個(gè)白手起家的逆襲故事——Stella McCartney的父親是著名樂隊(duì)披頭士的成員Paul McCartney。
無論是大品牌小品牌,高端品牌還是高街品牌,設(shè)計(jì)師們紛紛尋找著金主和跨界的合作者,期望他們的點(diǎn)金之手,能夠助力品牌進(jìn)入更多人的尋常生活。
這也是陳大維的夢(mèng),但他離這個(gè)夢(mèng)是如此遙遠(yuǎn)。而他又是如此偏執(zhí),不肯一絲一毫地妥協(xié)。
“興許這就是我的命”
“我希望我的衣服成為一種基本的生活用品,而不是奢侈品。”這是陳大維的目標(biāo),關(guān)乎陳大維對(duì)衣服價(jià)值的理解。對(duì)此,他反復(fù)思量過很多回,為了驗(yàn)證這個(gè)目標(biāo),他還在朋友圈里開啟過一個(gè)贈(zèng)衣計(jì)劃,人數(shù)有限,“衣服是一個(gè)有生命的個(gè)體,我希望有天它能遇到一個(gè)喜歡它的人,與它相處,善待它”。
但這些都是倒貼錢的情懷,沒有任何現(xiàn)實(shí)的收益。為了生存,同時(shí)也為了支持自己的工作室運(yùn)轉(zhuǎn),陳大維只能在西單的實(shí)驗(yàn)二小接了一個(gè)工藝課的教學(xué),每周兩天,一個(gè)月工資2000元,加上私人培訓(xùn)課的收入,一個(gè)月能賺4000多,在刺骨的北京的冬天,這個(gè)年輕人勉強(qiáng)維持著生活。
賺來的錢除了房租,剩下的都被他拿來買了布料。戀舊的他常常回到天津母校旁邊的小白樓舊布料市場(chǎng),這個(gè)市場(chǎng)已經(jīng)存在了二十年,攤主多是大爺大媽。
“我喜歡這種老布料,在北京找不到,一定要去天津找。”陳大維說。買回了布料,他都屯在自己的房間內(nèi),像一個(gè)小山包,“買布的時(shí)候,我都沒想要做什么,就先買著。”
這份任性在朋友眼中挺“作”的。他的朋友張璐對(duì)此這樣評(píng)價(jià):“他對(duì)細(xì)節(jié)的要求挺高的,也許搞藝術(shù)的人就是這樣吧。大維和別人不一樣,他是個(gè)有想法的人,他不想和市面的衣服雷同,但是他的圈子比較小,沒有人幫他,所以一直也沒有賣出去。”
但“見過世面后”的陳大維覺得這是一種“顛覆”。他把貝多芬的一句名言當(dāng)做自己的座右銘——為了美,一切規(guī)則都可以顛覆。
現(xiàn)在的他越來越放棄規(guī)則,比如不拿西裝料子做西裝,而且絕對(duì)不用“黑白灰”三個(gè)無色彩傾向的顏色,他說“黑白灰”是山本耀司,他要探尋自己的風(fēng)格,絕對(duì)不抄別人的。
陳大維越來越像個(gè)設(shè)計(jì)師了,雖然他的衣服還沒有賣錢,但他已經(jīng)計(jì)劃好了未來。他要找到合適的合伙人,“服裝是一個(gè)工業(yè)化產(chǎn)品,自己一個(gè)人做下去,也看不見頭”,他想試著組建一個(gè)小的團(tuán)隊(duì)。最近在找適合做工作室的房子,一切都準(zhǔn)備就緒后,做一些市場(chǎng)化的成衣銷售。
現(xiàn)在的他一邊留心關(guān)注時(shí)尚行業(yè)的動(dòng)態(tài),一邊還在認(rèn)真地學(xué)習(xí)《日本女式成衣制版原理》一書,中國沒有自己的制版理論,大多是從日本引進(jìn)的,這本書是他實(shí)現(xiàn)夢(mèng)想的基礎(chǔ)。
陳大維在籌備著自己新的系列,“我感覺到我的代表作就要來了”,他說。
在微信朋友圈里他曾引用《紅高粱》中的一句話表明自己的心志:“我不管這路有多難走,我都沒有打算停下腳,興許這就是我的命。”問他為何執(zhí)著于這條路,他說:“畢竟我還年輕,我不想妥協(xié),我害怕在死的那一刻,恨自己沒有在年輕的時(shí)候?yàn)槔硐雸?jiān)持到底。”
- 時(shí)代報(bào)告的其它文章
- 要想成長(zhǎng),就必須改變
- 董國法小傳
- 海昏侯墓的“掘墓人”
- 回娘家
- 祖國高于一切
- 秘密出版《前西行漫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