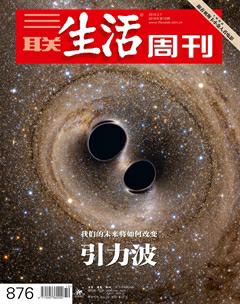經歷決定差異
維舟
在“9·11”恐怖襲擊事件之后,時任美國總統(tǒng)的小布什曾在公開場合脫口而出,宣稱眼下這場針對極端主義的斗爭是“新十字軍遠征”(New Crusade)。這番話別說是伊斯蘭世界聽來極不舒服,連西歐盟國的輿論也是一片嘩然。許多觀察家已注意到,“冷戰(zhàn)”結束之后“大西洋在變寬”,以往被遮掩的美歐之間的差異正在逐漸浮出水面,而這種差異一言以蔽之,即美國更為宗教化,而西歐更為世俗化。
小布什的話當然不是一時口誤,甚至也不止因為他本人是“再生基督徒”,那是美國在意識形態(tài)整體上的一個縮影。雖然憲法規(guī)定政教分離,但作為一個清教徒開創(chuàng)的國度,美國在立國精神上就長期貫徹著宗教精神——它想要成為《圣經》中所說的“山巔之城”,像燈塔一樣照耀和引領著世界上的其余人走向光明。美國在向西部擴張時提出的“天定命運”(Manifest Destiny)無疑也潛藏著“我才是承擔天命的選民”這類沖動。在美國第一次的海外擴張美西戰(zhàn)爭中,一位站在甲板上的美軍指揮官說出的話,就很像一百多年后小布什的口吻:“這是全能上帝的戰(zhàn)爭,我們只是他的代表。”
類似的話,在大多數歐洲人(尤其是西歐人)聽來,如果不是過時的愚蠢狂熱,就是厚顏無恥,差不多只能讓人聯(lián)想起中世紀的宗教戰(zhàn)爭,和現(xiàn)代社會格格不入。如今,歐洲精神的圣杯早已不歸教士階層把持,而由那些活躍在公共論壇、大學校園和媒體上的世俗知識分子看護。他們堅信,這一精神才是真正普世和更值得珍視的——這就是在伊拉克戰(zhàn)爭之后,哈貝馬斯和德里達等人鑒于美國的立場而針鋒相對提出的“核心歐洲”概念,強調歐洲的世俗主義、啟蒙思想與社會民主傳統(tǒng),走出一條有別于美國的獨立自主道路。
大西洋兩岸的這種差異不僅明顯,而且由于它造成了美歐之間的互相難以理解和信任,顯然也事關重大,當然值得為此專門寫一本書來探討這個問題。這甚至也不僅只是美歐之間的問題,因為一如《宗教美國,世俗歐洲》一書所言:“非常明顯的一點是:不同的宗教存在形態(tài),將會導致不同的世界觀視野、不同的思維方式,以及對于諸如經濟、政治、文化、哲學和宗教等一系列廣泛議題的不同理解視角的產生。”說到底,這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根本意識上的差異,而正是這決定了人們如何進行思考和采取行動。
美歐之間的這種分歧,至少要追溯到啟蒙運動的兩個不同版本。概言之,法國式的啟蒙運動具有鮮明的“反教權”性質,在像伏爾泰這樣的啟蒙運動領袖看來,“宗教”、“教士”、“中世紀”、“野蠻主義”這類名詞,并不是某種精確界定的中立概念,而是在針對基督教會時包含有強烈負面內涵的批判武器;相比起來,美國式的啟蒙運動卻并非要反教權——這主要可能是因為,它也沒有教權可以反對。最終的結果,歐洲發(fā)達地區(qū)如今幾乎僅有20%左右的年輕人還會不時去教堂,一位政治人物如果宣稱自己虔誠信教差不多是自殺之舉;而在美國,不僅信教者的比例可以達到歐洲國家的三四倍之高,而且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愿意投票給一個不信教的總統(tǒng)候選人。
或許是由于現(xiàn)代社會學的幾個主要奠基人,無論是涂爾干、韋伯、馬克思還是齊美爾,都是歐洲人,在以往人們的理解中,“現(xiàn)代化”通常都意味著世俗化,似乎宗教本身與現(xiàn)代城市生活之間存在著必然的不相容性。然而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事實表明這很可能只是一個假定——至少美國就是一個重大例外。
更有甚者,也許令不少人驚訝的是,就高度的世俗性而言,歐洲在現(xiàn)代世界是一個另類——也許唯一一個與歐洲較為近似的大國就是中國。和歐洲一樣,中國人也很少把“現(xiàn)代”和“宗教”聯(lián)系起來,人們腦海中對“現(xiàn)代生活”的第一反應,無論其畫面如何,大致都可歸入世俗圖景的類別,而“宗教”在很長時間里則被大多數中國人等同于“封建迷信活動”。在這一點上,中國人幾乎本能地理解那種地道的法國式觀念:現(xiàn)代意味著“從信仰中解放的自由”(Freedom from Belief),是掙脫了宗教束縛之后而獲得獨立性的生活領域,而不像美國那樣,“現(xiàn)代性”中仍可容納著宗教。雖然書中大膽預測“各個國家被整合進歐洲版圖的程度越高,其向世俗性靠攏的可能性就越大”,但作者毫無疑問遺漏了中國;而中國的現(xiàn)代性之所以如此世俗化,無疑和歐洲一樣,都源于其自身歷史道路的特殊性。
在這里,還潛藏著一個問題,那就是國家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性。雖然書中也約略提到一點,但還是秉持著社會學一貫的立場,在討論現(xiàn)代化歷程時更注重的是工業(yè)化、城市化這樣的社會發(fā)展進程,然而,國家很可能也是理解“宗教美國,世俗歐洲”這一本質差異的一把關鍵鑰匙。歐洲現(xiàn)代化進程幾乎無不與強大的國家政權建設同步,而中國的狀況之所以更接近于“世俗歐洲”,恐怕也是因為在中國傳統(tǒng)中有一個早熟的世俗政治。相比起來,美國的聯(lián)邦政府則眾所周知的長期虛弱,因而從搖籃到墳墓的一系列社會福利關懷大多都依靠社會自身救濟,歐洲的社會福利最早是由德國這樣的以國家力量強大著稱的國家推動起來的,這恐怕并非偶然,因為如果國家在福利關懷方面積極介入,那么在這一領域也就差不多無須宗教發(fā)揮作用了。
對美歐宗教生活演變軌跡的差異,本書提出了七種可能性解釋:教會-國家關系的不同、多元主義的競爭、對啟蒙運動的不同理解、不同類型的知識分子、文化上的差異以及如何看待這類差異,制度上的對比以及宗教組織與社會差異的幾個維度(尤其是階級和族群)在聯(lián)系方式上的不同。這些歸結到最后,都是走過的歷史道路太過不同。正如《民族主義:走向現(xiàn)代的五條道路》、《不由自主的資產階級》這樣的歷史社會學研究所表明的,不同社會的結構性差異,歸根結底都是在歷史時期所沉淀下來的。正如不同的人,哪怕是一母所生,但成年之后在個性表現(xiàn)上也會有諸多差異,這與其說是他們各自星盤和命運的不同,不如到他們從小到大的生活經歷中找原因,有時可能某一個特殊的事件就足夠改變他的一生——這一點上,美歐也是,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歐洲遭受的破壞特別慘烈,這本身就在戰(zhàn)后造成了許多人對上帝存在的幻滅感。
概括來說,如果美歐的差異在根本上是因為現(xiàn)代化進程中啟蒙運動的道路歧異,那么說起來,這在西方歷史上并非新鮮事:1054年東西方教會的分裂,可追溯至西羅馬帝國被蠻族滅亡給雙方帶來的結構性差異;16世紀的歐洲宗教改革則出現(xiàn)了南北方各守天主教和新教陣營的局面,這通常被歸結為羅馬帝國時代北歐一直沒有被征服這一歷史事實;而俄國走上獨特的道路,自然也是因為它最初擁抱東正教文明的緣故。實際上,如果順著這樣的思路想下來,海峽兩岸的某些差異不也是如此嗎?臺灣社會之所以保留著較多的傳統(tǒng)中國文化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沒有經歷“五四運動”的啟蒙和沖擊。在明白了這一點之后,我們理應對彼此的差異抱有更為寬容的理解。
(《宗教美國,世俗歐洲?——主題與變奏》,商務印書館2015年5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