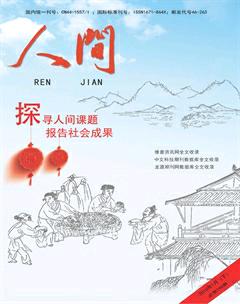攝影,現實還是虛假——從蘇珊·桑塔格《論攝影》談起
楊惠茗(西南民族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
?
攝影,現實還是虛假——從蘇珊·桑塔格《論攝影》談起
楊惠茗
(西南民族大學,四川 成都 610000)
摘要:在攝影日常化、大眾化的今天,在圖像無處不在、日益泛濫的當下,在影像大量復制、鋪天蓋地的當今,拍攝和收集照片就是保存和收集世界的想法成為人們的共識,人們對眼見的習以為然,并對圖像中的真實性深信不疑,將看到的一切不加分辨的接受下來,以為看見即是真實,表現即為現實,但事實上,攝影獨立為一個世界,影像世界脫離現實并背叛現實,我們看見的不是現實,而是陷入圖像世界帶來的虛幻的假象之中。本文試著分析攝影的現實性和虛假性之間的關系、視覺感官如何影響著觀看以及我們對攝影的認知這三個方面,從而說明攝影影像世界反映的并非現實而是虛假。
關鍵詞:攝影;現實;虛幻;藝術;理論
一、 柏拉圖的洞穴
柏拉圖有一個關于洞穴的著名寓言,寓言中的人們世代生活在洞穴之中,因為脖子和腳都被鎖住,無法動彈,他們只能看見眼前的墻壁,事物的影子通過他們身后的火焰投影在墻壁上,洞穴中的人以為這就是事物本身,以為投影在壁上的影像就是真實,柏拉圖認為,這個洞穴就是我們的世界。
存在于現實中的人們,所處的洞穴便是各自的肉體,這是有形的牢檻,從肉身之中形成的思想、認知、道德、精神等,便是無形的牢檻,人至始至終都只能從自身的世界出發去看待和解釋外在的世界,無論如何都只能依附于自身這個狹小的世界,從自身的角度來說,我們看見的并非現實,而是經過個人意識加工、扭曲、變形之后的帶有個人主觀色彩的現實。這樣看來,經攝影師選取拍攝下來的影像,就顯得更不現實,這是主觀意識后再主觀截取的過程,客觀的因素在這一過程中被層層過濾,以至最終隱而不見。蘇姍·桑塔格指出,“人類至今還無可救藥的留在柏拉圖的洞穴里,看不見真實,而只在真實的影像中陶醉。”其中“真實的影像”,就是攝影。追溯至攝影發明初始,攝影還不被大眾所認同,當達蓋爾銀版攝影法從法國傳入歐洲其他國家時,人們體驗到的大多是恐懼而非驚異,當時就有媒體對攝影法表示抗議,“要將浮動短暫的鏡像固定住是不可能的事,非但如此,單是想留住影像,就等于是在褻瀆神靈了。人類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創造的,而任何人類發明的機器都不能固定上帝的形象。”對信奉基督教的國家來說,這一言論無可厚非,但它暴露了當時的人對攝影的排斥與恐懼,在這種排斥與恐懼心理之下,是人類依舊活在柏拉圖的洞穴之中的隱喻,把人類的影像當成是不可辨駁的真理,而全然不知那只是光影的投影。然而人們對攝影術的恐懼便很快消散,攝影術的廣泛運用、影像的大量復制,人們對這一新奇事物的興趣和熱情催促著攝影相機和拍攝技巧的進化,并以為攝影停滯了瞬間,凝固了時間,記錄了世界,將一切可見之物化為影像,拍攝行為即捕捉世界,收集照片即收集世界。在人們看來,影像世界即為現實世界,照片反映的事實即為真實,就這樣,人們沉迷于復制世界的欲望中,卻不知已陷入“柏拉圖的洞穴”,并“在真實的影像中陶醉”。
柏拉圖的洞穴寓言對于沉默的記錄者——攝影來說,不失為一個恰當的暗喻,我們更愿意透過圖像來認識現實,而不是自身經歷過的反復日常,通過對圖像的觀看與收集,我們對赤裸的現實視而不見、充耳不聞,人們總是追求著美好快樂,悅目的影像代替了枯燥無味蒼白的現實,這是媒體和受眾兩廂情愿、協力合作的結果,媒體通過制作美觀絢麗的影像,讓觀眾以為這就是現實,從而吸引觀眾;大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引導著他們更傾向于媒體所展示的景象與畫面。攝影表現選定的現實,亦即展示經過選擇之后的特定現實,但這個特定的現實不再是客觀的真實的現實,而是成為寄托著攝影師記憶、情感的載體——表現著主觀和感性,也就是說,它的功能不在于觀賞,更在于感受。在這個特定現實中,圖像連接并構筑起了作者與觀者這兩者之間共同的世界。皮埃爾·布爾迪厄認為,“實際上,攝影捕獲的只是任意選擇下的現實的一個方面而已,因而它只是攝取某個摹本的一個方面;在客體的全部特質中,所保留下來的只是某一瞬間、某一視角下呈現的視覺特質。”猶如白紙上的一滴墨跡,若目光僅停留在墨點上,就只會注意到墨點而忽略到周圍的白色,對攝影的選取也是一樣,攝影是攝影師在特定地點、特定時間、特定意識之下的拍攝行為,是片面化的行為,是轉瞬之間發生的事,或者說,拍攝這件事是片段化的刻意的選取的,且只對那個瞬間有意義,因此,倘若將它視為反映現實的鏡面,就顯得不可靠了。
二、視覺之經驗
通過觀看照片,人們了解到了未曾到達過的地方,瞥見了更為寬廣的世界;通過拍攝照片,人們對于現實的經驗有了更直觀的認知。照片彌補了人們對未踏足之地的缺憾,豐富了人們的視覺經驗,對觀者來說,攝影以及影像縮短了他們與現實世界的距離,填補了他們對未知之地的想象力,不管是躬身經驗,還是認知能力,抑或者是視野范圍。
蘇珊?桑塔格對影像視覺經驗有如下看法: “攝影以一系列隨意的碎片來概括現實——一種無窮地誘人、強烈地簡化對待世界的方式。”攝影作為認識世界、傳遞經驗的方式,通過抽樣的、偶然的與某個現實片段相遇,再將這一片段化的現實簡化處理之后傳遞給他人,他人再形成關于這一碎片現實的片段經驗,攝影影像簡化了人們獲取視覺經驗的路徑,通過具體直觀的形式獲得認知經驗,拉近了與外在世界的心理距離,但攝影影像的這一便利性卻造成人們在面對真實時產生的失落,這其中既有圖像影像美化過度的原因,人們按圖索驥的對比圖像與現實,然而修改過后的圖像影像猶如化妝過后的人一般,再與原初的模樣對比時,差距之大可想而知,自然免不了失落,并且攝影圖像放緩了人們對現實的接受和反應速度,“照片異化了人的感受力”。美化后的圖像降低了人們對平淡無奇現實的接受和容忍能力,并助長了人們對美的感受力,將美作為感受的對象并排除感受以外的事物,人們不是在感受真實的現實而是在感受粉飾后的照片。即使現實表現出不輸于影像中的景象,人們的態度也多半是把它與圖像作比。對攝影影像的依賴和信任,以至于人們很難對現實做出客觀純粹的評價,在影像泛濫的今天,幾乎一切現實都逃脫不了被圖像化的命運,人們習慣了圖像中的現實,對真實的現實不屑一顧,這樣,真正的現實便在人們的眼中消失不見了。
拍照,這一凝固住事物瞬間的視覺性挽留行為,如今被用來當做把握現實經驗的方式,出行即為拍照,拍照強化實感,唯有如此,依賴圖像而認識外物的人們才能感受并體驗到現實的影像化,才能留有經驗過的實證。但拍照同時也是在簡化和模式化經驗,人們以拍照作為實際體驗參與過的物證,將所有經驗托付給相機,相機再輸出圖像到電腦,大眾的過往經驗淪為張張圖像,圖像不僅扣留了現實,也滯留了記憶,阻隔了人們對現實的直接感受,相機代替視覺,我們躲在鏡頭后面窺視現實世界,因此,也可以說我們不再裸眼直視現實,而是在鏡頭之后觀察相機截取的現實。已然預感到攝影在不久將大眾化的蘇珊·桑塔格指出,“我們對情景的感受,如今要由相機的干預來道出……如果形容說,人們患上了攝影強迫癥,大概是不會錯的:把經驗本身變成一種觀看方式。最終,擁有一次經驗等同于給這一次經驗拍攝一張照片。”
三、認知之誤解
盡管攝影來源于現實、取材于現實,但攝影影像并不有助于我們認識這個現實世界。
萬物在各類鏡頭以各類角度下捕捉,電子數碼相機的方便快捷性讓照相變得更快速簡易,世界在按下快門的當下凝固在方寸之間,遍布各地的主題各異的攝影展、不計其數的紛繁蕪雜的攝影集、借由互聯網的開放共享,使得獲取照片輕而易舉,充裕的照片在無限制彌漫下,人們不禁慶幸,正因為攝影,我們才對這個世界有更多的認識和了解。
事實上,攝影對于提升我們的認知作用甚微,一張照片僅僅是呈現它自己,且觀者多是以娛樂的態度觀看圖像,很大的情況是,它與觀者的現實生活相差甚遠,這就進一步加深了人們所面對的現實和圖像上事物的差距,如此,圖像相比現實,就顯得虛幻不真實,如此與各自面臨的現實不相關的圖像,再加上人們多以純粹娛樂的立場,攝影對人們的認知并不能產生多大的助益。桑塔格對攝影之于認知的作用的看法也并非肯定,她認為:“拍照時那種令人尷尬的不費力,相機產生的結果所具有的那種不可避免的、即使有時是無意的權威,表明攝影對于認知,其作用是非常微弱的。”攝影表現的現實并非現實的本質,若僅僅是全盤接受攝影所展現的世界來認識世界,并不會出錯,但若這樣來看待,就無法理解了,所謂理解就是并不只是停留在表象,不把浮于表面的世界當作真實的世界來接受,而是思考表象之下的世界的真相。雖然圖像填充我們未曾經歷過的生活的空白,但其表露的現實往往冰山一角——隱匿多于顯現。一方面是攝影師總是以某個特定的目的拍攝特定的事物,排除了其他不相關之物;一方面是事物總是以大致整體的狀態進入我們的視野,細節隱藏在整體之中,不易被察覺。我們的理解需經過時間的過渡,需經過言語的敘述、需以求知之心加以驅策,才能實現。
對照片的闡釋不同,對照片的認知也不同。媒體出于何種目的何種角度對一張照片做出何種解釋,將會左右觀者對這張照片的理解和認知。對照片的闡釋,倚賴如何制造效果、如何操作文字、如何引導方向、觀者如何接受,既可成全真相也可編織謊言,一張照片,可具有無數種意義,既可一本正經,作為證據,也可存心歪曲,予以誹謗。從這個意義上來看,攝影并非給予現實的圖像,而是提供可進行多詮釋的現實,這些現實因解讀的方向、各自的經驗等差異,或多或少都反映了真實。攝影集或是期刊圖書中的圖像,不乏是經過處理修整后展現的樣貌,照片是客觀的,主觀的總是人類,照片本無真相,真相是附加的。“照片本身不能解釋任何事物,卻不倦地邀請你去推論、猜測和幻想。”一張照片僅是展現,是空白,是無,但是存在引申、認知、觀點。另外,當我們在觀看一張圖像時,我們的大腦總是傾向于選擇已做出的現成的文字解釋,而不是主動自覺的對圖像以及文字進行重新判斷、思考,這就造成了我們在觀看一張圖像時是以他者的觀點和角度來看待而非我們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因為不假思索的接受,我們以為這就是事實,以為圍繞圖像的文字描述就是這張圖片的唯一詮釋,如此,既是對圖像的多樣解讀誘導了我們的看法,也是我們放棄了對其他可能存在的意義進行重置的機會。
參考文獻
[1]蘇珊·桑塔格《論攝影》M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8.1
中圖分類號:G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864X(2016)01-024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