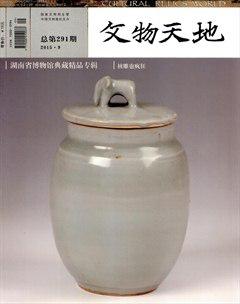長沙窯瓷題文雜識



一、題詩源于岳州窯
以詩文飾瓷以往均認為出自長沙窯,然從新近出土并流于民間的資料看,這種說法須予更正。據了解,湘陰縣城曾出土一件青瓷碗,內底貼塑一鳥,碗內下腹有戳印團花紋,上腹飾兩組復線弦紋,兩組弦紋之問劃有小方格紋,方格內填有刻寫的五言詩一首:“市朝非我志,山水得余情。琴逐啼鳥口,酒共落花傾。”(圖一)另一南京城家在該市區工地上也采集到一塊類似碗形殘片(圖二),內底印團花、忍冬紋,腹部同樣飾兩組復線弦紋,弦紋之間以短豎隔成小方格,方格中刻詩文:“醉一口(席、簾)詩若無此二。”另,長沙李吳先生本人收集到一殘片,釉色偏褐,下腹近底印團花及忍冬紋,口沿以同樣方法刻詩,惜字僅存“歌陽春”三字(圖三)。南朝詩人吳邁遠有詩《陽春歌》,其中有“宋玉歌陽春,巴人長嘆息”之句。唐李白也有樂府詩《陽春歌》。前兩件標本的文字都提到酒、孵等意境,可見此碗的功能與酒有關,當為酒碗、酒盞。這些詩文當與唐代興起的酒文化有關。如果說長沙窯與岳州窯有諸多淵源,這便是其中之一。同樣,長沙窯瓷器上的題詩、警句箴言絕大部分題寫于茶具、酒具的壺、碗(盞)上(李建毛:《長沙窯與唐代茶酒》,《茶酒:長沙窯瓷與詩書畫結合的媒介》,湖南省博物館第一、三期,岳麓書社2004、2006年)。由此也可看出岳州窯與長沙窯之間的傳承關系,同時也可看出唐代商品經濟發展后,伴隨市井文化悄然興起的茶酒文化。有趣的是,唐代酒文化的興盛比茶文化早半拍,從唐詩中可見看出,初唐便有許多飲酒、品酒的詩文,據統計,《全唐詩》中直接與酒相關的詩篇約12000余首,幾占總數的22%,時間上貫穿唐代始終。而關于飲茶的詩出現稍晚,《中國古代茶濤選》(錢時霖選注:《中國古代茶詩選》,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中所選茶詩的作者年代,最早為8世紀,茶詩的流行是茶文化興起的重要標志。從時間排序可見,岳州窯刻詩時只流行酒文化,而茶文化的興起正與長沙窯的鼎盛時間對應,也就是說長沙窯處于茶酒文化并行的時代。從書寫方式看,岳州窯題詩為刻劃,先在將干未干的胎上劃刻寫,再施釉覆蓋,字跡通過釉的深淺變化得以識讀。而長沙窯作為彩瓷窯,則是在潔白的化妝卜上,以毛筆蘸彩書寫,再罩上透明青釉,形成較強的色差對比,非常醒目。而且字體也跳出岳州窯的蠅頭小楷,變為揮灑自如的楷、隸、行、草等書,書寫部位不再同于碗的內口沿,而是位于器物最為醒目的部位,器形也不再拘泥于碗盞,有碟、壺、枕等物。問題在于,瓷器題文現象為何最早出現于既非政治中心、對非經濟中心的湖南地區所在窯址,這值得深思。
二、書寫人身份
關于長沙窯瓷器上題寫詩文的書者,筆者也曾做過一些推論,認為是唐科舉制實行后社會上山現大批未能通過科舉入仕的學郎,經歷安史之亂,大量衣冠南遷,部分貴族豪強南遷后失去原有的土地和財產成為破落戶而轉謀他職,長沙窯題文作為新興的職業未嘗不會受到這些略通文墨且處境欠佳的人所關注。然從敦煌文書可知,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一些大都市出現專門抄書的職業書手,抄書后須對抄本進行三次校對,當今出版此的三校制恐由此而來。如敦煌文書伯P3278號《金剛經》殘卷末尾就有這樣的題記(轉引自:方廣鋁、許培玲《敦煌遺書中的佛教文獻及其價值》,《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
上元三年(676年)九月十六日書手程君度寫
用紙十二張
裝潢手解集
初校群書手敬誨
再校群書手敬誨
三校群書手敬誨
詳閱 太原寺大德神符
詳閱 太原寺大德 嘉尚
詳閱 太原寺主 慧立
詳閱 太原寺上座道成
判官司農寺上林署令李德
使朝散大夫守尚舍奉御閻玄道
這些佛經在長安由寫經坊抄出,類似題記在敦煌遺書中亦甚多,共有三十多號。一些書手不僅抄寫,有時也負責繪畫,如四川博物院藏的敦煌絹畫,其中一幅為開寶二年(969年)千手千眼觀音像,主尊上方兩側各繪一童子,榜題均為“持花化現童子”,發愿文書有“清信弟子節度押衙知上司院書手張定成,奉為故慈父及兄,發于弘愿,彩會尊容”(董華鋒、林玉:《四川博物院藏兩件敦煌絹畫》,《文物》2014年第1期)。也知當時官府內設有書手這類職位。由于民間需求的增長,民間也當有書手之業,長沙窯瓷器題文無疑出自民間“書手”,繪畫也同樣出自他們之筆。有意思的是他們書寫時,仍保留當時官方書手的范式,據徐俊先生研究發現,敦煌文書在抄寫過程中校塒時發現文字序顛倒時,往往在字右側或右上側打勾(√),如敦煌遺書寫卷《佛說十王經》上的修改符號(紅色箭頭處)(圖四),表示該字應與前一字對調字序。羅振玉編纂的《鳴沙石佚書正續編》中的《太公家教》中“日月雖明,不照盆覆之下”(圖五),原文本是“不照覆盆之下”,但盆覆二字倒序,故在覆字旁打“√”。而長沙窯也如此,如長沙市博物館藏的“鼓價”,上書:“大中拾年拾日叁造鼓價”(圖六),當是“拾叁日”誤書為“拾日叁”,故在“叁”字的右上方打“√”標識。此外,一藏家所收藏的長沙窯瓷上題七言詩:“造得家書經兩月,無人為我送歸將。欲憑鴻雁寄將去,雪重天寒雁不飛。”(圖七)“歸將”二字顛倒,故在“將”右上方打“√”。另一藏家所藏詩文壺上題:“白玉非為寶,千金我不須。意千念張紙,心存萬卷書。”(圖八)該詩在長沙窯瓷上發現多件,但此壺在書寫上“念千”二字倒序,故“念”右側打“√”。類似現象還有“上有千年鳥,下有百年人。丈夫具紙筆,一世(世壹)不求人”。
三、與敦煌文書的關系
1.詩歌寫本
長沙窯瓷器上許多詩文是全唐詩中未收錄的,但在敦煌文書中卻可找到同樣或相似寫本。據徐俊先生統計,長沙窯題詩在敦煌抄本中有11首之多。
這些相同的詩中,勸學詩占較大的分量,如“白玉非為寶,千金我不須。意念千張紙,心仔萬卷書”,在敦煌文書寫本中多次見到,如國家圖書館之典籍博物館展示的敦煌佚書之學郎詩中便有“白玉非為寶,黃金我未須。意在千張紙,心存萬卷書。”另敦煌佚書伯_六二二:“白玉非為寶,黃金我未須。口竟干張數,心存萬卷書。”又伯三四四一:“白玉雖未寶,黃金我未雖。心在千章至,意在萬卷書。”(同卷有“大中七年十一月二卜六口學生判官高英建寫記”題記。幾種寫本略有區別,概輾轉抄寫所致。中國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藏敦煌遺書》15號背6雜寫也有“白玉非為報”,當是習書人對“白玉非為寶”的誤抄(方廣鋁主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圖書館藏敦煌遺書》第139頁,臺灣臺北,2013年)。長沙窯題詩“天地平如水,王道自然開。家中無學子(士),官從何處來”。也在敦煌文書中見到類似寫本,如敦煌遺書北八三一七(玉字九一):“高門出貴子,好木出良在。丈夫不學聞,觀從何處來。”又斯六一四:“高門出貴子,好木不良才。男兒不學門(下缺)”。又見于吐魯番阿斯塔那三六三號唐墓出土卜天壽寫本:“高門出己子,好木出良才。交口學敏去,三公河處來。”
長沙窯題詩:“竹林青郁郁,鴻雁北向飛。今日是假日,早放學郎歸。”也有“望林心憂傷,鵲雁北向飛。今日是佳節,早盼學郎歸”。該詩見于敦煌遺書伯二六二二:“竹林清郁郁,伯鳥取天飛。今照是我口,且放學生郎歸。”吐魯番阿斯塔那三六三號唐墓出土卜天壽抄《論語》附詩:“寫書今日了,先生莫咸池。明朝是賈日,早放學生歸。”據唐《假寧令》,唐代假期有節日和假日兩種,元日(春節)、冬至節放假各七天,降圣節(老子誕日)、佛誕日各放假一天,“千秋節”(帝王生日)放假三天,還有清明節、中秋節等節假。此外,庸代實行為“九口馳驅一日閑”的旬休制,元稹有詩云:“朝十還句休,豪家得春賜。”官員休假時,學郎也相應休假。長沙窯題詩中也有學郎習字詩,如“夕夕多長夜,一一二更初。田心思遠路(客),門口問征(貞)夫”,敦煌遺書伯三五九七:“日口昌樓望,山山出沒云。田心思遠客,門口問貞人。”(張錫厚:《敦煌本唐集研究》。斯三八三五亦載此類離合體詩,參見徐俊:《敦煌詩集殘卷輯考》811頁,中華書局,2000年)“天明日月奣,立月己三龍。言身一寸謝,千里送金鍾。”(圖九)這些拆字組合詩,是學郎經常玩的文字游戲,前首詩每句的前兩字組成第三字,后首詩每句的末字由前三字組合而成,該詩每句末字組成“奣龍謝鍾”,有趣的是1990年2月,內蒙古托縣曾出土一枚遼民俗錢,正面刻有“奣龍謝鍾”字樣的楷書,背鐫草書“家國永安”,長沙窯勸學詩還有“上有千年鳥,下有白年人。丈夫具紙筆,一世不求人”。有些家訓詩則與寫本中《王梵志詩》中的勸教詩相似,或格式相同。“客人莫直人,直如主人嗔。打門三五下,自有出來人。”便與3656號《王梵志詩》相關:“主人相屈至,客莫先入門。若是尊人處,臨時自打門。親家會賓客,在席有尊卑。諸人未下籬,不得在前據。親還同席坐,知卑莫上頭。忽然人怪責,可不眾中羞。尊人立莫坐,賜坐莫背人。罇(蹲)坐無方便,席上被人嗔。尊人葑客飲,卓立莫東西。”
有些題詩在敦煌遺書中還可以找到多個類似寫本,如長沙窯題詩:“春水春池滿,春時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哢春聲。”(圖十)在敦煌遺書中,有伯三五九七“春日春風動,春來春草生。春人飲春酒,春鳥弄春聲”,又如日本北三井一〇二(025-14-20):“春日春風動,春山春水流。春人飲春酒,春棒打春牛。”
敦煌文書的許多內容都可以看出宗教世俗化的過程,長沙窯的一些題詩,在敦煌文書中也可看出由一些佛家偈語演變而來,而這種演變也可反映宗教世俗化的轉變過程。如佛家偈語:“身生智未生,智生身已老。身恨智生遲,智恨身生早。”在長沙窯題詩中則變為:“君生我未生,我生君已老。君恨我生遲,我恨君生早。”(圖十一)成為許多人津津樂道的老少戀情詩。
2.警句箴言
長沙窯瓷除題有大量詩文外,也有相當數量的警句箴言。其內容主要有兩類,一是勸人如何為人處世,教人做人的道德準則;二是基于人性本惡的世界觀,反映世態炎涼的警句,教人“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這些箴言警句部分出自于《太公家教》,如“蓬生麻中,不扶自直”(圖十二),“屋漏不蓋,損于梁柱”,“懸鉤之魚,悔不忍饑”(圖十三),“羅網之鳥,悔不高飛”(圖十四),“日月雖明,不能盆覆之下”等。《太公家教》是唐宋之際廣為流行的童蒙讀物,敦煌文書遺存的各種抄本,多出自學郎之手,如斯497卷末題記“學生呂康三讀誦記”,斯1163卷末題記“永口寺學仕郎如順進自手書記”,們2825卷末題記“學士宋文顯讀,安文德寫”,伯2933卷未題記“沙州敦煌郡學士郎兼高行軍除解口太學博士宋英達”,伯3569卷末題記“蓮臺寺學士索威建記”,伯3764卷末題記“學士郎張會平時寫記之”等等(《鳴沙石室佚書》影印出版。轉引自汪泛舟:《<太公家教>考》,《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據劉安志先生考汪,《太公家教》成書于“唐朝前朝,時間當在公元7世紀下半葉,8世紀則廣泛傳播于全國各地”(劉安志:《<太公家教>成書年代新探——以吐魯番出土文書為中心》,《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3期)。至少在9世紀《太公家教》在敦煌出現多個寫本,而與敦煌相隔萬里之遙的長沙也非常流行。可見當時文化傳播普及之快之廣。不過因抄寫原因,長沙窯瓷與敦煌寫本個別有所不同,如《太公家教》是“屋漏不覆,損于梁柱”,覆與蓋意思相近,經常連用。另如“吞鉤之魚,悔不忍饑”,有“懸”與“吞”之別。
有些則出自敦煌文書巾的佛經。如“小人之淺志;道者,君子之深識”,而其原話出自《真言要決》,“故言名利者是小人淺志。談至道者是君子深識。是以小人用名利為宗。君子以道德為主。故孔子云。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真言要決》卷一)可見瓷上所題因抄本原因,缺“利者”二字,也因此引起學者們此句的誤讀(陽光的味道:《 <中華彩瓷第一窯——唐代長沙銅管窯實錄>一書中的錯誤芻議》)。有的出自儒家經典,如“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圖十五),則出于《孝經》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三者備矣,然后能守其宗廟。”“雁有行列之次”出自《儀禮》注曰:“以雁為贄,取其有行列之次。”漢代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雁行有序。”南朝丘遲《與陳伯之書》:“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明朱國禎《涌幢小品·雁塔》:“塔乃咸陽慈恩寺西浮圖院也。沙門玄奘先起五層。永徽中,武后與王公合錢重加營造,至七層,四周有纏腰。唐新進士同榜,題名塔上,有行次之列。唐韋、杜、裴、柳之家,兄弟同登,亦有雁行之列。故名‘雁塔。”而“慈烏反哺之念”,“羊申跪乳之志”,“牛懷舐犢之恩”,出自《敦煌變文集》中《胡秋變文》:“臣又聞:慈烏有返哺之報恩,羊羔有跪母酬謝,牛懷舐犢之情,母子寧不眷戀?”不過受書寫面積的局限,原文提倡“孝”德比喻的排比句,被拆分成單句分別題寫在單件器物上,這種形式的變化可看作為紙寫本到瓷寫本的轉化。瓷器題寫只能將紙寫本中最動人、最經典的語句摘下,省略原文中作為鋪墊和輔助的句子。有的警句也取自敦煌其他文獻,如“忍辱成端政(正)”,就出自王梵志詩:“忍辱成端正,多嗔作毒蛇。”(《全唐補逸》卷二)
也有部分警句箴言與后世成書的《增廣賢文》,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異。如“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已(幾)人”,“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增廣賢文》為“一生一世,草木一春”,也見于《西游記》“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富從升合起,貧因不計來”(《增廣賢文》為“貧從不計來”)。“家中無學子,官從何處來”(《增廣賢文》為“家巾無才子”)。可知在成書之前,這些諺語已廣為流行。
“古人車馬不謝,今人寸草須酬”(此句出自《論語·公冶長》“愿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有錢冰亦熱,無錢火亦寒”,這些句了反映當時商品經濟發展,世人越來越功利,人心不古的社會現實。
如前所述,敦煌遺書寫本多出自學郎之手,其中包含不少勸學詩、家訓詩、《太公家教》等佚文,同樣長沙窯詩文有豐富的家訓、蒙學內容,反映唐代社會對蒙學的重視,說明家訓不再是單個家庭內的私事,已變為社會行為,凸顯民間對教化的重視。敦煌文書上不少抄錄的詩文見于長沙窯,且許多不見于《全唐詩》,令人困惑的是,敦煌與長沙窯又相隔甚遠,這些詩文為什么會如此雷同,除了這些詩文或許當時普及甚廣之外,也或是因安史之亂,人口大量南遷,西北陸路絲綢之路逐漸蕭條,沿路居民及商戶大量內遷所致。
四、名物
長沙窯瓷中除題寫詩文、警句箴言外,也有些廣告語,還有一些題寫器物名及其功用,是唐代名物研究的重要資料。據統計,長沙窯題寫盂子、瓶(飲瓶、油瓶、茶瓶)、注子、小口、盞(茶盞子、酒盞)、碗、盒(油合、茶合)(圖十六)、櫬子(魚櫬子)、槌子、印子、撲滿子、錢胡子、杓子等十余種。
長沙窯同一種器物往往有不同名稱,如碗,或稱之為碗、盞、盂子,出土器物書有“茶埦”“茶盞子”(圖十七)、“酒盞”“湖南道石渚草市盂子有明(名)樊家記”等,黑石號出水青瓷碗也有底部墨書“盂子”的(圖十八)(長沙窯編輯委員會:《長沙窯》作品卷(貳),303頁,湖南美術出版社,2004年)。這種現象的出現,或因長沙窯工由湖南當地居民及北方遷來的各地窯工組成,各自保留原來區域的方言習慣,也或因為長沙窯銷售面極廣,小同稱呼是以訂銷者所在語言而題寫。《方言》:“盂,宋楚魏之間或謂之盌。碗謂之盂,或謂之銚銳。碗謂之棹,盂謂之柯。海岱東齊北燕之間或謂之﨎。”(楊雄《方言》卷五)《說文》:碗,“小盂也。”張舜徽《說文解字約注》:“盂與碗實一物。”又“頷,械,盞,頭,閜,啲,頹,桮也。秦晉之郊謂之頷。自關而東趙魏之間曰椷,或曰盞,或曰頭。其大者謂之閜。吳越之間曰啲,齊右平原以東或謂之頹。桮,其通語也。”可見當時盂、盞、杯、碗有時通用。而盂是唐代比較流行的稱呼,唐詩中比較常見,各地俗稱有所小同。
撲滿是長沙窯瓷中較常見的產品。漢人劉歆<西京雜記》卷五有記載:“撲滿者,以土為器,以蓄錢具,其有入竅而無出竅,滿則撲之。”唐末僧人齊己《撲滿子》云:“只愛滿我腹,爭知滿害身。到頭須撲破,卻散與他人。”最近新發現的一件撲滿上書有“……林寺之……,施者善愿合家平安。撲滿子”題文(圖十九)。瓷上的撲滿子與齊己詩互為佐證,可見當時這種物名為撲滿子。“林寺”之前字殘,僅剩“辶”旁的底部,聯想到長沙另一藏家所藏的樸滿上有“潭州準造,道林寺幕(募)主施……”等銘文,可知殘字當也是“道”,此產品也為道林寺所訂燒。道林寺位于長沙岳麓山,唐代香火頗旺,歐陽詢曾為道林題寫匾額“道林之寺”,杜甫撰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當地生產當地用,可見“撲滿子”長沙地區流行稱呼,而長沙窯另一撲滿則刻有另一名稱,“李有錢不得,此是錢胡子也”(圖二十),說明撲滿另有一名稱——錢胡子。錢胡子的稱呼,不見于文獻,或是某一地域的方言。
唐李匡義《資暇集·注子偏提》:“元和初,酌酒猶用樽杓……居無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蓋、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貴人惡其名同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目之曰偏提。”從文獻看,因權臣鄭注人品之故,酒壺有由注子到偏提的演變過程。但長沙窯瓷中這兩種器形都存在,并不存在這種演變關系。長沙窯壺中最常見是執壺,前有短流,后有執鋬,當系文獻中“去柄這系”的“偏提”,而在長沙窯中這種壺被稱之為“瓶”,如“此是飲瓶,不得別用”“張家茶坊,三文壹平(瓶)”“油瓶伍文”(圖二十一)。另一種壺無鋬,肩部裝有橫柄,流細長,與橫柄成90度直角(圖二十二),附蓋,這便是《資暇集》中所說的“注子”,與長沙窯瓷的稱呼相同,長沙窯址中出土數量較多的這種橫柄壺,柄上印有“趙注子”“趙家注子”銘。從器形關系看,長沙窯執壺出現較早,并伴隨長沙窯始終,并非由“注子”(橫柄壺)演變而來,而是源于岳州窯的盤口瓶。而“注子”(橫柄壺)確如文獻所述,蓋、嘴、柄皆具,造型處于唐向宋的轉變期,器形趨向秀美,流細長,至宋后這種壺形基本不見。《資暇集》提到的杓,在長沙窯也有發現,一杓殘件上書“酒家杓子”。
長沙窯瓷中有種白名為“櫬子”的碟子(圖二十三)。按《說文》:“櫬,棺也。”《小爾雅》:“空棺謂之櫬,有尸謂之柩”。很明顯,櫬為棺材之意,并無“碟”之意。其實,櫬為櫬之簡化,古時櫬與櫬當為兩字,各有其意。從實物看,櫬顯然與碟相通。古字中同一器物,往往有木、金、土旁,與其材質相對應,如長沙窯碗中寫成土、木旁者,碟為漢時流行漆器,常為“木”旁。但碟中的“世”寫成“立”,當與太宗李世民之避諱有關。“櫬”為碟,不僅長沙窯如此之稱,之后的衡州窯也是如此。衡州窯的碗、碟、盤的圈足較高,底心常印“高足盤”“高足埦”“高足櫬”(圖二十四)銘文,可見碟寫成櫬,在湖南地區曾流行一段時間。這種高足盤碟,應與高從誨盤踞荊南時器尚高足有關,朱琰《陶說》卷六《說器中·唐器》之“高足碗(原注:十國南平器)”條記:“周羽沖《三楚新錄》:高從誨時,荊南瓷器皆高足,公私競置用之,謂之高足碗。”窯址出土元和三年印模,側面陰刻“元和i年正月卅日造此印子田工宰記”。可知當時這種印模稱為“印子”(圖二十五)。
從上述諸多物名看,唐代口語中對器物稱呼,常在器名之后加“子”字,便成為瓶子、盞子、印子、撲滿子、盂子、櫬子、注子等,在詩文及其他文獻中也可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