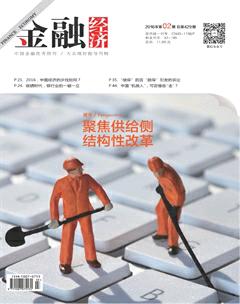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解決哪些問題?
陳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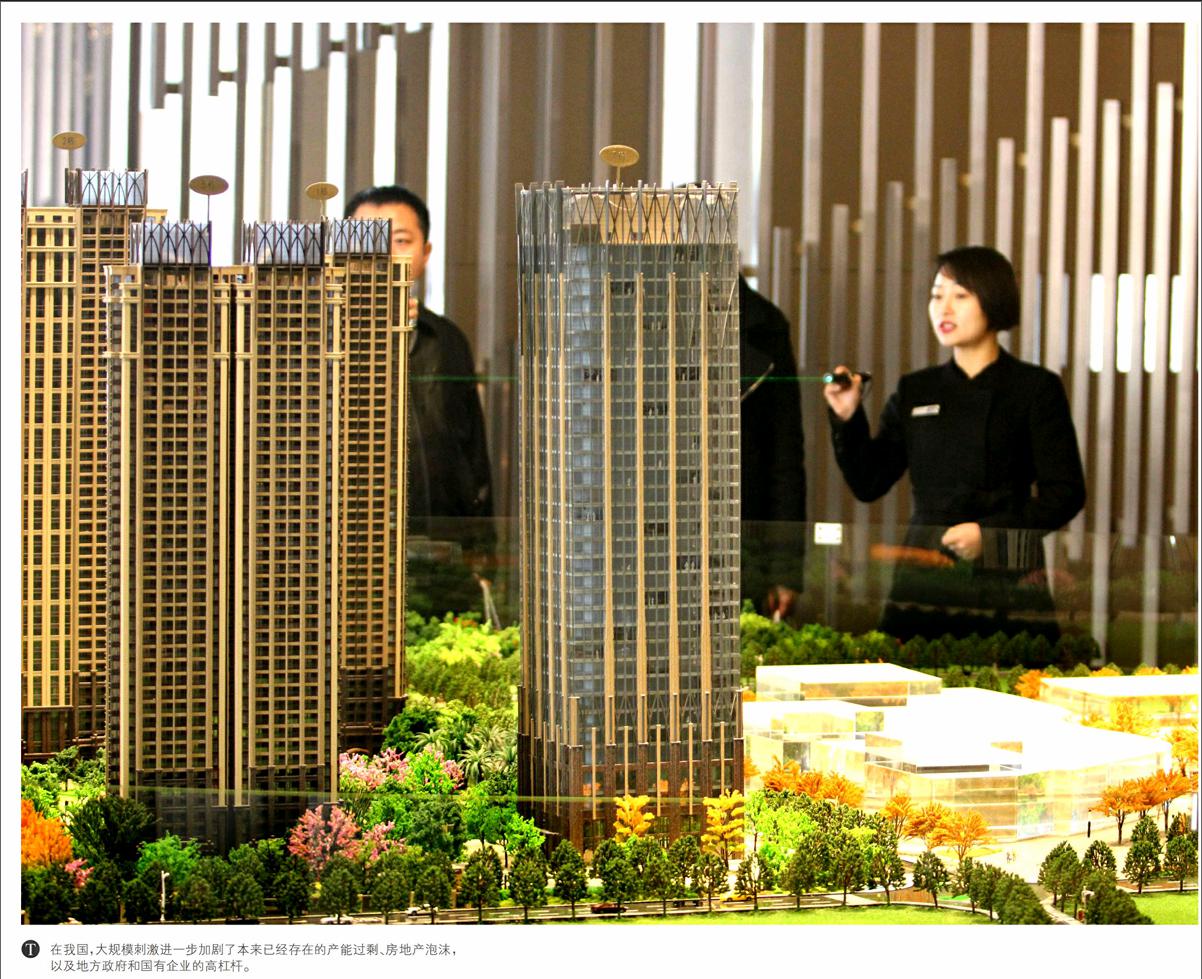
需求不足要求擴張和刺激,產能過剩要求收縮和抑制,但二者同時存在,該怎么辦呢?
美國金融危機爆發后,托馬斯·弗里德曼(《世界是平的》的作者)在《紐約時報》撰寫專欄文章《罕見的不確定》,他當時就斷言,無論是在美國還是歐洲,宏觀經濟都需要經歷一些大的結構性修復才能回到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結構性修復與結構性改革基本同義。修復什么?修復結構性矛盾。諸如,美國虛擬經濟過度膨脹的矛盾,歐洲主權債務居高不下的矛盾。然而,由于需求沖擊來勢洶洶,各國政府一如慣常,采取了寬松乃至極度寬松的總需求管理政策,即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大規模刺激經濟,以期走出危機。一方面,這場危機波及之廣泛,影響之深重,超出了人們的預期;另一方面,存在于各經濟體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均系長期累積,非一時能夠調整,所以,各種政策工具都未能達到預想的效果,不得不反復使用,造成短期政策長期化的基本事實,其后果是政策效應不斷減弱,并造成了一系列新的矛盾,如增長持續低迷。
在我國,大規模刺激進一步加劇了本來已經存在的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以及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的高杠桿。簡言之,總需求管理的空間日益狹小,總供給管理的迫切性日益彰顯,這就是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基本背景。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應對這一輪經濟增長下行的正確對策,又是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唯一藥方。
那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并能夠解決哪些中國經濟問題呢?
需要并能夠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
首先,需要并能夠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問題。經濟學家比較一致地認為,導致這一輪經濟增長下行,結構性因素是主要的,甚至有經濟學家認為,完全是結構性因素造成的。所謂結構性因素,在這里,主要是指產能過剩。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和國有企業高杠桿的背后,也都是產能過剩。正因為產能過剩,致使需求側主要動力——投資的增速大幅度下降;與此同時,外需持續不振,另一駕“馬車”——出口的增速也大不如前,致使經濟增長進入較長時期的下行。當產能過剩和需求不足同時存在,事情的難辦就有點像上個世紀70年代西方國家出現的“滯脹”,需求不足要求擴張和刺激,產能過剩要求收縮和抑制,但二者同時存在,該怎么辦呢?此時,比較可行的辦法,一是通過供給側的改善,創造新需求或轉化潛在需求。不過,中國目前還有大量阻礙供給側動力形成和發揮作用的體制性、政策性障礙,所以,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才能激發和產生供給側動力,即技術進步、人力資本和企業家精神,以保持經濟的可持續增長;二是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擴大投資和消費需求,以走出兩難的困境。特別需要指出,就我國當下而言,因為政府的負債水平已經高企,積極財政政策的工具選擇應較多地考慮減稅,并從結構性減稅到普遍性減稅。
供給側動力及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來源,是現代增長理論。凱恩斯革命后,經濟學的最重要發展之一,就是現代增長理論。現代增長理論以探討經濟增長源泉為使命,同時將經濟學動態化、長期化。現代增長理論揭示的增長源泉,或者說增長動力即供給側動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一,內生于經濟體系內部的技術進步。經濟學家索洛首先指出了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經濟學家羅默進一步指出,由于經濟體系內部存在著激勵,所以技術進步是內生的,由此產生了內生增長理論。其二,如果從要素投入角度觀察現代經濟增長,人們發現,人力資本既替代勞動,也替代物質資本,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最重要投入要素。經濟學家舒爾茨指出了人力資本投資的主要途徑:健康、教育和培訓等。其三,經濟學家熊彼特則將創新等同于企業家精神,并將其作為供給創造需求的主要動力。在經濟學的視角,熊彼特創新是要素及生產條件組合的革命性變化,其深處是技術進步驅動。企業家在這里的關鍵性作用,是作為技術創新成果產業化的組織者。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文化創意的成果,都是企業家主導的產業化過程的投入要素。那么,企業家精神又來之于哪里?唯一的答案是,來自于不斷試錯的創業創新過程。較好的環境,較多的機會,將提高試錯的激勵和成功率。
需要并能夠解決對接需求和供給的問題
其次,需要并能夠解決對接需求和供給的問題。也就是說,通過供給創新,滿足現實需求,轉化潛在需求,并且,創造新的需求。當前,中國經濟的一個突出的內在矛盾是,在嚴重的產能過剩存在的同時,并存著有效供給不足的問題。在經濟學看來,供給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生產,二是成本。在中國,目前比較普遍存在的生產問題,是質量問題、效率問題、安全問題,乃至誠信問題。不解決這些問題,供給滿足需求就將遇到障礙。這就是中國老百姓的需求要么到海外去實現,要么被抑制的原因。什么是現階段中國的成本問題?現在提出的“降成本”,其空間主要在哪里?當然,企業自身無時不刻都要通過優化配置和加強管理降低生產成本、管理成本等,但就現時的宏觀情形而言,“降成本”主要指降低企業面對的、過高的融資成本、運輸成本、用電成本和稅務成本等,這些成本的降低,主要責任在政府,在政府推動全面深化改革。由此可見,無論在生產的問題中,還是在成本的問題中,都既有技術的問題,也有制度的問題。技術的問題要通過創新來解決,制度的問題則要通過深化改革,一如上述“降成本”的問題。降了成本,就是降了價格,就會帶來更大的需求滿足和實現。
長期以來,在討論經濟增長,以及決定經濟增長的動力時,人們總會糾結于需求與供給這一對關系,具體地說,就是市場需求導向,企業供給創新,孰為主導?其實,在現實經濟生活中,二者有著各自發生作用的條件和領域,并隨著條件的變化而變化。在需求導向和供給創新的關系上,需求導向是比較純粹的市場決定,供給創新則是一個創業者、企業家不斷試錯的過程性活動。在完全競爭、信息對稱的假設下,市場和企業本質上是等同的,但是,這兩個假設都已經被放松,不完全競爭、信息不對稱是經濟活動的常態。作為市場經濟主體的企業和企業家,不僅成為經濟研究和分析的基本對象,而且是現實經濟活動的決定性力量。
在市場經濟國家,過去很長時間,需求導向是經濟增長、產業發展的主要路徑,它的優點是比較可靠,缺點是有滯后效應。然而,在現今社會,需求表現出兩個顯著特征:其一,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常態,中國也不例外。其二,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需求更多地表現為潛在需求,也就是說,在消費者的購買行為中,越來越多的需求是由他們的潛在需求轉化而來的。上述兩個特征表明,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企業,要想在這一格局的競爭中取勝,不僅要著眼于現實需求,更要通過供給創新的不斷試錯,滿足現實需求,創造新的需求,并將潛在需求轉化為現實需求。誰在這個創造和轉化中得到先機,誰就能得到更大的市場份額,進而獲得更大的競爭優勢。所以,考慮到動態的技術進步和企業家精神,并考慮到需求導向的缺陷,那么,供給創新就成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我們轉型發展的必然選擇。
需要并能夠解決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
再次,需要并能夠解決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發展方式轉變,首先是發展理念的轉變。《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倡導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完整地闡述了發展方式轉變的方向和要求。在操作層面,重點則是結構調整、動力轉換。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中國經濟“新常態”有三個特點:中高速增長、結構調整和動力轉換。前者是經濟活動的結果,后二者是轉變發展方式的核心。
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視角,結構調整和動力轉化都要進入到更深層次、更具體的對象。例如,結構調整要從去庫存、去產能,到去僵尸企業,這才是一場真正的攻堅戰。惟其如此,結構調整才能見到成效;又如,動力轉換要從不斷提高投入要素的質量入手,提高勞動力、資本和創新成果的質量,由此才能提高產出的質量。所謂提高勞動力的質量,就是將勞動力在更大范圍、更高層次轉化為人力資本,使他們能夠從事創業創新、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文化創意的工作,并都取得積極的成果;所謂提高資本的質量,就是優化土地、自然資源與產業資本的配置,提高它們的利用效率,并使它們更多地轉向新興產業和高科技產業。所謂提高創新成果的質量,就是要更加專注于內在技術創新的創業,尤其是原創技術的發明和產業化。這是增長動力中的動力,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于這個動力中的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