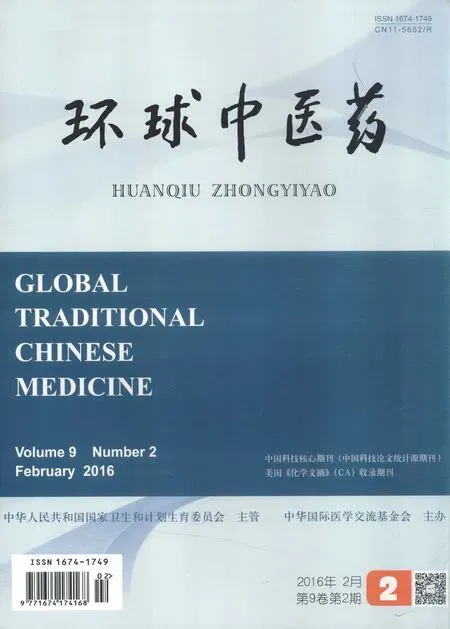從《未刻本葉氏醫案》淺談葉天士治咳經驗
劉柳青 劉果
北京中醫藥大學臨床醫學院(中日友好醫院)[劉柳青(碩士研究生)];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溫病教研室(劉果)
?
從《未刻本葉氏醫案》淺談葉天士治咳經驗
劉柳青劉果
北京中醫藥大學臨床醫學院(中日友好醫院)[劉柳青(碩士研究生)];北京中醫藥大學基礎醫學院溫病教研室(劉果)
【摘要】葉天士門人所錄的《未刻本葉氏醫案》載有大量治咳醫案,這些醫案體現了針對不同病證特點而采取的多樣化的治法:對陽虛咳嗽,主以溫腎,佐以化飲、降逆;對陰虛咳嗽,主以滋養不同臟腑陰液;對于外感咳嗽,則主以散寒祛風或疏散風熱,兼用養陰、理氣等法。葉天士治療咳嗽,辨證精準而細致,治法靈活而貼切,其經驗值得當今臨床醫生學習。
【關鍵詞】葉天士;未刻本葉氏醫案;咳
葉天士,名桂,號香巖,為清代著名醫家,不僅對溫病學有巨大貢獻,于內科雜病亦有頗高造詣。然其平生診務繁忙,著作不多,《未刻本葉氏醫案》系其門人周仲升侍診時所錄,被程門雪先生贊為“未經修飾”之“渾金璞玉”。其案雖簡,所涉病種亦不多,然恰可窺見葉天士對某一病癥的診治經驗。其中治咳逆醫案數量甚多,且治法多端,故摘取其中數案加以分析,嘗試總結葉天士辨證、制方思路,以冀對臨床有所裨益。
1陽虛咳嗽
陽虛咳嗽,主要指以下焦陽虛為總病機的咳嗽。下焦陽虛,溫化無權,氣化失司,水飲聚而成邪。水邪變動不拘,或停于體內而成鼓脹,或溢于肌膚而成水腫,或上泛凌心而有心悸,或上逆射肺而致咳嗽。而下焦陽衰時,虛陽浮越,可形成沖氣上擾,使肺氣宣降失常,亦可致咳。在《未刻本葉氏醫案》中,上述兩種情況俱可見到,雖均以下焦陽虛為基本病機,但治療思路卻有區別。
1.1陽虛水泛
陽傷飲逆,咳嗽腹膨。
真武湯[1]
患者主要表現為咳嗽、氣逆,腹部膨隆,為水飲停聚腹部、濁陰上泛致咳。結合用藥,可以推測,飲邪泛溢緣于陽虛溫化失司。經云:“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故水飲為病,與脾、肺、膀胱關系密切,治療需從此處著眼。
此案以仲景真武湯溫陽利水,以炮附子振奮腎陽助膀胱氣化,生姜溫散水氣、溫肺化飲,白術健脾燥濕,固中土而制飲邪,茯苓甘以健脾,淡以滲濕,借滲降之勢平潛水飲逆氣,芍藥利小便、去水氣,與茯苓相合,“收攝迷漫渙散之陰氣,復歸于下”[2],則治水降逆之功畢矣。
柯琴論少陰病篇真武湯證曰:“為有水氣,是立真武湯本意……實由坎中之無陽……法當壯元陽以消陰翳,逐留垢以清水源,因立此湯。”[3]又論太陽病篇證見“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而用真武湯之條文,曰:“坎陽外亡而腎水凌心耳……凡水從火發,腎火上炎,水邪因得上侵……”[3]此論所言真武湯證之特點,與本案陽虛水泛、飲邪上逆之病機甚為契合。由此可見,對于此種咳嗽,可考慮使用真武湯溫陽化飲,利水降逆。《未刻本葉氏醫案》中另有咳喘一案“陽微陰濁泛逆”[1],亦用真武湯,并點明病機為陽虛濁陰上泛,可為佐證。
1.2虛陽上沖
嗽逆,沖氣不納,形浮。
茯苓桂枝北五味炙甘草[1]
患者主要表現為咳嗽、氣逆,形體浮腫,為水飲泛溢肌膚、氣逆上沖致咳的癥狀。下焦陽虛,一則溫化無權,不能制水;二則虛陽上越,形成沖氣,挾水氣上逆而致咳。故治療此類咳嗽當降沖氣、攝虛陽、制水飲。
此案用仲景桂苓五味甘草湯,方出《金匱要略·痰飲咳嗽病脈證并治第十二》,本為體虛支飲咳嗽病人服小青龍湯后發生沖氣而設。原文中,患者水飲為病故服用小青龍湯,但因體虛不耐辛散,出現“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沖胸咽,其面翕熱如醉狀”等表現。寸沉為有水,尺微為下焦陽虛,陽虛四末不溫故手足厥逆,虛陽上越、影響沖脈,故有逆氣上沖之感及面熱色紅、虛陽浮越之象。此時雖有飲邪,因虛陽已動,亦不可再用辛散復擾沖脈、動其沖氣,而應斂氣平沖。故以茯苓淡滲利濕、引氣下行;桂枝平沖降逆,二者共“伐腎邪”“抑沖氣使之下行”;五味子斂肺止咳,收攝浮陽;甘草培土治水,“土厚則陰火自伏”[4],則虛陽可降,沖氣可平,肺氣可收。諸藥相合,治療下焦陽虛、支飲上盛、沖氣上逆之咳嗽。
葉天士運用桂苓五味甘草湯治療虛陽上沖作咳非此一例,且能根據患者陽虛程度調整用藥。另一案“脈細如絲,形神尪羸,嗽而氣逆。下焦陽氣頗衰,最慮喘脫。延至春和日暖,始可無虞”[1],則在此方基礎上加制附子、胡桃肉。案中雖未明言水飲之象,然既用苓桂劑,推測當有飲邪為患;且此人下焦陽氣甚衰,形體羸弱,陰陽俱虛,虛陽不僅上沖,更有外越而成喘脫之險,遂于桂苓五味甘草湯制水斂氣平沖之余更加補腎助陽之力:制附子溫腎助陽,破水飲濁邪結聚,直入下焦以助氣化,益火之源而消陰翳;胡桃肉性溫質潤,培補右腎元陽,既可“通命門”[5]、填下焦,引浮陽下納,又能“化虛痰……暖水臟”[6]而溫散飲邪。諸藥相合,則寒飲得化,虛陽得攝,沖氣得平。
2陰虛咳嗽
下焦陽氣衰弱,攝納無權,濁陰上泛,虛陽浮越,可以引起咳喘;若下焦陰精不足,涵陽無力,下焦陰火上沖,亦能引起嗽逆。
2.1肺腎陰虛
嗽而脈數,臟陰虧矣,金水同治。第參之色脈,恐延損怯。
熟地甜北參麥冬茯神川石斛天冬[1]
既言“臟陰虧矣”,必是有陰傷見證;數為熱,當是腎水不足,虛熱內生,上灼肺臟,而有咳嗽。日久則陰液漸耗而有傷及天年陰精之虞,故當金水同治,急用甘涼濡潤之品以救臟陰。
方用熟地壯腎水,大補真陰不足;石斛“輕清和緩……能退火養陰除煩,清肺下氣”[7],既有清潤降氣治咳之功,又有養胃清肺、培土生金之意;茯神益氣健脾,寧心安神,既可斡旋中焦,調節氣機以復肺氣宣降,又可健運脾氣以防陰藥呆滯,而其甘淡性平,益氣無動陽擾亂氣機之憂,健脾無溫燥耗傷陰液之弊,對于氣機上逆、陰血耗傷的陰虛咳嗽患者,較其他健脾藥更為合適;又以北沙參、麥冬養陰清肺、益胃生津、除煩清心;天冬在上可苦寒清降上逆之虛熱,在下可甘寒滋養匱乏之腎水,兼顧陰虛與虛熱。全方諸藥相合,主以甘寒濡潤之品養肺腎陰液,輔以苦寒清熱降火,而不忘健運中焦以調氣機,寧心安神以定神志。藥味雖少,卻兼顧各方。
熟地、石斛、茯神是葉天士常用配伍,多用于陰虛病癥,根據具體情況的不同,配合使用的藥物可有變動,但總不離甘寒養陰、甘苦寒清熱除煩、甘淡平健脾之法,常用配伍藥物有北沙參、麥冬、知母、天冬、穞豆皮、扁豆等。另有多則陰虛咳嗽醫案,對“真元頗虧,內熱咳嗆”[1]“下虛氣逆,作咳內熱”[1]的患者,用藥均基本遵循這一思路。
2.2肝腎不足
咳嗽失血,左脈弦數,少陰頗虧、厥陽不潛使然。
熟地茯神山藥牡蠣川斛湘蓮[1]
脈數為熱,弦為肝陽上亢,又有少陰不足,故其病位在肺,根源在腎,又與肝相關。肺為嬌臟,常為肝木所侮,木擊金鳴,肝氣上沖可致肺氣上逆而咳;水不涵木,肝火上炎,又可木火刑金,灼傷肺陰,而致咯血。此種咳嗽,緣于腎水不足,一則水不生金而肺陰耗竭,二則水不涵木而肝陽不潛。因此,治療時需補腎、潤肺、平肝三法并舉。
組方上,用熟地黃、石斛補腎水、養肺陰、清虛熱;茯神、山藥平補氣陰;更加蓮子甘平之品,兼有澀性,健脾固腎之余可“安靖上下君相火邪”[5],有和中而交通上下之功[8],以助攝虛火、降氣逆;又有牡蠣“肝腎血分之藥”[5],既有介類潛陽之功,又可“解喉痹咳嗽”[7]。茯神、山藥、石斛、蓮子補益脾胃氣陰,可培土生金而養肺;而“脾氣散精,上歸于肺”,脾胃健運則養陰之品無滋膩之弊則可入肺。山藥、蓮子、牡蠣俱有收斂澀精之功,與填補腎水之劑合用,使腎水真陰得以補益而無外泄之虞,生金涵木之功得以發揮。而茯神、蓮子、牡蠣均可安神,葉天士嘗有“久病以寢食為要,不必汲汲論病[9]”之論,如此等陰分匱乏又見失血、虛陽擾動的病人,夜晚往往煩熱難眠,夜寐愈差,陰精愈弱,其病愈重。若能以安神之品令其安然入睡,夜間精血方能自生,于其病亦有益處。重視安神助眠,乃葉天士治療久病頑癥的重要思路之一。
3外感咳嗽
3.1寒閉衛陽
衛陽怫郁,形冷咳嗽。
苦杏仁大桂枝生姜炙甘草天花粉大棗[1]
該患者外感寒邪,肌表陽氣為寒邪所郁,故而怕冷、咳嗽。肺外合皮毛,寒邪束表,則肺氣閉郁、宣降失常。肺為水之上源,又主一身之氣,肺氣不暢,則氣滯水停,飲邪聚而成痰;肺氣閉郁,日久化熱,熱可煉液為痰,又可灼傷津液。由于葉天士業醫江南,此地常有濕熱之邪,南人既多內濕為患,又因天氣炎熱而陰液不足、虛熱內生。因此,外感寒邪之咳嗽常伴痰熱,故治以辛溫解表加清熱化痰生津之法。
此方可看做由桂枝加厚樸杏子湯化裁而來。以桂枝溫散肌表寒邪,杏仁宣肺止咳;因無喘憋脹滿,故去厚樸下氣除滿之品;以清熱生津排膿之天花粉代芍藥,則是考慮到肺衛閉郁繼發的痰熱、津傷,癥見有痰、口干者尤宜。
以桂枝湯加杏仁為基礎進行加減可視為葉天士治療感寒咳嗽之常法。在“形寒咳嗽脈小[1]”案中也使用上述藥物。《臨證指南醫案》咳嗽門中,證屬感寒咳嗽者亦多用此法,并加以靈活化裁,如口渴加天花粉,痰濕為患加薏苡仁等[9]。
3.2溫邪作咳
案一:溫邪侵于肺衛,作之咳嗽。
杏仁桑葉川貝母花粉黃芩南沙參[1]
案二:脈細澀,咳嗽三月不愈,溫邪伏于肺衛使然,漸延陰損勞怯。
玉竹桑葉花粉川貝南參梨肉[1]
《未刻本葉氏醫案》中有大量言及“溫邪”“溫侵”的病例,用藥雖不盡相同,其法卻大致相通。由溫邪導致的咳嗽情況復雜,有偏于溫邪盛的,有偏于肺陰虛的,有偏陰于虛陽亢的,有偏于衛不固的,有偏于肺氣逆的,有偏于肺體傷的,有集中在肺衛局部的,有涉及全身整體的。雖都是溫邪侵襲肺衛,因素體稟賦不同,感邪輕重不同,病程長短不同,病情轉歸不同,就診時的情況就會千變萬化。如果不能準確把握病人刻下特點,一味辛涼解表、養陰潤肺,恐怕會貽誤時機。
兩案在病程上即有長短的區別。案一“溫邪侵于肺衛”,此時表邪為重,陰傷較輕,以桑葉、黃芩、天花粉疏散風熱、清肺泄火;杏仁、南沙參清肺化痰、宣降肺氣以止咳,南沙參、川貝清熱化痰,與桑葉、天花粉同用又可生津養陰潤肺。全方以散溫邪、清肺熱為主,兼以暢達氣機,佐以益肺氣、養肺體,攻補兼顧,又以祛邪為主。案二則陰虛之象明顯,兼有余邪未盡,故棄前方黃芩之苦燥,加玉竹養陰兼以祛邪,仿古人葳蕤湯之意,并用梨肉清肺潤燥,養陰化痰,使全方攻補兼施而偏于扶正,與患者久病陰虛、伏邪未凈之病機正相契合。
由于溫邪咳嗽病情表現多樣,因此葉天士用方選藥亦變化多端,但總是與患者病機緊密相扣。若溫邪偏盛,邪氣不解,束于肌表者,可用玉竹、桑葉、薄荷、連翹透邪于外,如“溫邪咳嗽”[1]案;邪伏深處、外達受阻者,藥用射干、浙貝母、梔子清瀉于里,如“溫邪郁于肺衛,咳嗽音嘶”[1]案;亦可二者結合,內清外透。祛邪時亦應配合杏仁、桔梗、南沙參等通利肺氣之品,一可復肺氣宣肅而止咳平喘;二可暢達氣機以助祛邪。
陰傷甚者,可參考葉天士治秋燥之法。其中,桑葉、沙參、天花粉、玉竹四味運用最繁,川貝母、杏仁、甘草使用亦多,其他如蔗漿、梨汁、麥冬等生津藥及連翹、綠豆皮之類,每相機參用一二味[10]。除此以外,玄參、石斛亦可根據熱盛傷陰程度斟酌使用。
其他隨癥加減,有痰者,養陰之余加入川貝母、天花粉、橘紅、梨肉、南沙參等化痰之品;素來內熱較盛、肝膽火旺,或見有少陽郁熱之象如弦脈者,可加黃芩、青蒿;咽痛音嘶者,加射干[10]、薄荷利咽。
除此以外,亦須慮及患者病史,如“溫邪作咳形寒,曾失血,宜用輕藥”[1]案,患者雖有外邪束表惡寒之象,卻有失血史,故不用辛散燥烈之品解除肌表閉郁,恐動其血,而僅以桑葉、橘紅此等輕清透邪之品以防動血。一代大家葉天士辨證之細致、用藥之精準、思慮之周全,于此可見一斑。
綜上,從《未刻本葉氏醫案》記載的咳嗽病案中,可以窺見葉天士先生治療咳嗽的部分辨證思維和用藥特點:(1)下焦陽虛者,若有飲邪上泛,可用真武湯;若是虛陽沖氣上逆,可用桂苓五味甘草湯,酌情加附子、胡桃肉。(2)下焦陰虛者,常用熟地黃、石斛、茯神培補下焦、兼顧中焦,并不忘安心神、助睡眠以養精血;證屬肺腎陰虛者,可加入清燥潤肺之品;證屬肝腎陰虛者,則加入養肝、平肝之物。(3)外感邪氣者,若是寒邪束表,治以辛溫解表合清熱生津化痰之法,常用桂枝、生姜、杏仁、天花粉、甘草、大棗;若是溫邪襲肺,則需辨明正邪偏盛,祛邪既可用疏散風熱辛涼之品,也不避用清熱瀉火苦寒之物,扶正主以甘寒養陰,同時注意宣降肺氣、暢通氣機。把握病機細致而準確,遣藥制方巧妙而周全,先賢臨證心法,吾輩后學當仔細體會。
參考文獻
[1]清·葉天士.未刻本葉氏醫案[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63:2-41.
[2]民國·張山雷.本草正義[M].太原:山西科學技術出版社,2013:174.
[3]清·柯琴.傷寒來蘇集[M].3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139,140.
[4]王玉興.金匱要略三家注[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3:190-191.
[5]清·汪昂.本草備要[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5:169,171,242.
[6]清·王孟英.隨息居飲食譜[M].南京: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3:77-78.
[7]明·張介賓.景岳全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7:1237,1264.
[8]清·黃宮繡.本草求真[M].3版.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72.
[9]清·葉天士.臨證指南醫案[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8:86,49.
[10]柴中元.溫病求真——葉天士、吳鞠通溫病學說研究[M].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12:349,306.
(本文編輯: 董歷華)
(收稿日期:2015-10-06)
【中圖分類號】R256.11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6.02.013
作者簡介:劉柳青(1992- ),女,2015級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醫婦科。E-mail:ahhfllq@163.com通訊作者: 劉果(1979- ),博士,講師。研究方向:中醫溫病名家學術思想發掘與整理。E-mail:liuguo980131@163.com
基金項目:北京中醫藥大學教育科研課題(XJY15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