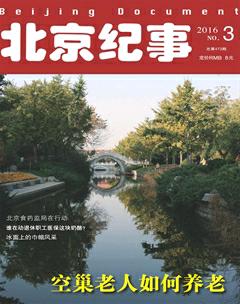空巢老人如何養老
張乃堅


著名電影演員于洋老師,今年已年過八旬,說實話,我們是看著于洋老師的電影長大的一代人。通過電視臺采訪,我才知道,于洋老師竟是典型的“空巢老人”。兒子年僅44歲離他而去,女兒移民美國。于洋老師對著觀眾說:“你們不知道,人老了,生活會多么艱難。但是,我要當英雄,不做狗熊!”話音剛落,掌聲雷動。人們在感動之余,可曾考慮過,這話語的背后,隱含著多少不易啊。據報道,2012年2月24日,北京市西城區東經路居民樓內,一名七旬的獨居老人被子女發現死于家中。急救人員趕到時,老人的尸體已出現腐敗現象。網友呼吁“空巢老人”現象應受到更多關注。有數據顯示,北京市老年人口已超過300萬人,這其中約一半是空巢老人。另據老齡委披露,我國大中城市老年空巢家庭率已達70%……
“空巢老人”大量產生于“50后”
筆者在《北京紀事》2015年第10期上,寫了一篇文章,叫《京城尋找養老院》,其中談到了黃如水先生(化名)。黃如水,男,60歲,典型的“50后”,離異,無子女。最近,筆者就“空巢老人”問題,再一次采訪了他。
某國際養生公館,即便白天,館內也是燈火輝煌。公館原先是4星級飯店,改為“養生公館”后,依舊保持著舊日飯店的氣派。
老黃快言快語地說:“ 首先,應當搞清楚‘空巢老人的定義。根據百度百科的解釋,‘空巢老人一般是指子女離家后的中老年人。這是一個既籠統又簡單的解釋,缺乏分類和系統性。從大城市的現狀看,結婚后,愿意與父母同住的年輕人越來越少,幾乎形成了一種新常態——有子女,不同居,子女常回家看看。實際上,真正需要社會救助的并非新常態下的空巢老人,而是真正意義上的空巢老人。什么叫真正意義上的空巢老人呢?個人的理解是:一、壓根兒就沒接過婚的獨身者。二、丁克夫婦,夫妻倆商議好不要孩子。三、失獨家庭,喪失掉獨生子女的老人。四、離異家庭,子女跟了一方,另一方沒有再婚處于獨居狀態。五、子女移居海外,有的獲綠卡,有的加入了外國國籍,父母留在國內,身邊無其他子女照看者。六、子女離開原籍工作,老家的父母長年無人照看者。實際上,這些人才是真正意義上的‘空巢老人,才是真正需要社會救助的群體。如果按此推斷,社會上空巢老人的數量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龐大。有一個現象值得一提,在空巢老人的群體中,的確不乏社會精英人士,隨便就能舉出許多許多,比如,已故日本影帝高倉健(獨身),已故產科名醫林巧稚(獨身),已故著名京劇演員李和增夫婦(無子),已故著名評劇皇后白玉霜(獨身),活著的有慈善家李春平先生、歌唱家郭蘭英女士、影星劉曉慶女士……您可以打開百度隨便調查一下,數量肯定是十分驚人的。
“空巢老人大量產生于50后,年齡段在60歲上下的群體中空巢老人的數量特別多。相比之下,40后和30后,也就是現在七八十歲的人群中空巢老人的數量,遠沒有50后那么多。此狀況的形成是有其歷史原因。40后和30后的‘適婚期并沒有趕上‘計劃生育,那個年齡段的老人,家里一般都有兩三個子女。50后則不同,他們的‘適婚期,趕上‘計劃生育政策的嚴格執行。現在,60歲上下的‘初老人群,如果有孩子的話,家里大多是獨生子女。在北京市,家長把孩子送出去留學太普遍了,當然不是所有的孩子,的確有許多孩子‘黃鶴一去不復返,留下家里的老人無人照顧。前些天,老同學聚會,一聊才發現,有三分之一的老同學將孩子送去國外。同學中有離婚的有獨身的,鬢角斑白的我們竟半數是空巢老人。
“不是危言聳聽,將來‘空巢老人的數量還會增多。現在網上不是盛傳中國11大光棍職業嗎?別笑,包括你們記者和編輯都榜上有名。再加上男女比例嚴重失調,若干年后,據專家預測許多男士會娶不到老婆!所以,網絡上才有了‘收入低可合娶的流行語。這些人到了老年,怎么辦?說實話,我們必須為此做好充分的精神準備,將來的老年化社會,搞不好,很可能就是一個以空巢老人為主導的老年化社會。現在,政府已經放開了‘二胎政策,實際上,也是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空巢老人之生存狀況
談到空巢老人的生存狀況,筆者將其歸納成三種。一、部分空巢老人忙于重組家庭,如轉型成功,就不是空巢老人了。二、一部分空巢老人住進了養老機構。三、大部分空巢老人依舊死守著居家養老的模式不變。
“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這是漢樂府里的詩句,代表了中國人的生活態度。中國自古就不提倡獨身主義,孔子講男人“三十而立”,這個“立”字,據國學研究者曲黎敏女士的解釋,首先不是“立業”,而是獨立生活,娶妻生子的意思。《詩經》曰:“執子之手,與子偕老”,這句千古不朽的名句,幾乎成了全世界華人的理想追求。您到中老年婚介所轉轉,生意火爆得非比尋常。說實話,這部分老人處于彷徨中,是依靠機構養老,還是居家養老,完全取決于最后的黃昏戀。
第二部分空巢老人放棄居家養老的想法,毅然決然地住進了養老機構,老黃就是其中的一員。老黃告訴筆者說,他現在的生活非常愜意。公館條件很好,大廳內有銀行提款機,樓內有24小時醫護站。只要老人身體不適,在家里按下救急按鈕,馬上就會出現護士小姐親切的聲音:“您需要幫助嗎?”999救護車停在門口,一旦發生情況,馬上就會把您送進大醫院。公館的地下室還設有康復中心,如此條件,實非居家養老者所能享有。難怪乎,最近新聞報道,北大著名教授錢理群老先生賣房住進養老機構,按老先生的話講:“我是適合養老院生活的。”有人給做飯,有專業小時工和醫護人員提供服務,老先生每天安安靜靜寫上幾千字的文稿,寧靜致遠,再創輝煌。隨著時間的推移,會有越來越多步入老年的社會精英住進養老機構,從而推動社會養老機構的向前發展。
第三部分空巢老人是居家養老型。從國情來看,這部分老人占絕大多數。以北京市來說,住進養老機構的“空巢老人”并非主流,占不到“空巢老人”數的30%。絕大多數“空巢老人”還是居住在家里,子女在國外的,逢年過節打個電話;結婚成家的,常回家看看;身體好的,雇個小時工;身體不好的,雇個保姆……守著老宅,日子就這么過。但是,問題多多。
老黃的母親,今年94歲,身體尚好,和保姆生活。街道對老人很照顧,專門為高齡老人安裝了“急救鈴”,有事按鈴,人家會上門服務。倒不是老黃不愿意與母親同住,父親的遺囑說得明白,房子留給老太太,兒女必須搬出去住,不能影響老人生活,常回家看看,即可。老黃住得遠,叮囑母親,有事按急救鈴,千萬別把病耽誤了。一次,保姆休息,黃母身體不適,馬上按鈴,還真就接通了街道。黃母要求街道給她叫輛救護車,幫助她上醫院。街道工作人員卻說,必須有子女在場,他們才能上門服務。事后,老黃找到街道,說子女在場還找你們干什么?按急救鈴的目的,就是子女不在家,尋求你們幫助的!老太太要沒兒沒女,不就死在家里了嗎?工作人員卻面露難色,說以前類似的情況確實發生過問題。不能說對方就是“碰瓷”或“無理取鬧”,可的確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很大難度。再比如,我們在社區辦了老人飯桌,來的絕大多數倒不是老人。“飯桌”是承包的,人家要盈利,不能硬性規定只招待老人。現在是有些老人染了頭發不像老人,有些中年人生活壓力太大,顯老。讓我們如何甄別?總不能全出示身份證吧。再者說,現在60歲是老人,還是65歲是老人,社會上還存在爭議,政府不是也在探討延遲退休問題嗎?實際上,基層工作很難做,當然,我們需要改進工作,但這需要一定的時間,畢竟老年化社會來得太快太快。聽罷,老黃無語。
養老機構經營上存在空檔
按老黃的話講,養生公館約等于養老院。養生公館里住的絕大多數是老年人不假,但是,您年輕人非要來湊熱鬧,交了錢,也可以居住。至少在九華山莊,入住是沒有年齡限制的。實際上,住養生公館跟住飯店的感覺也差不太多,只是入住者老年人居多而已。說起來,養老院這個詞,似乎太陳舊太過時了。現如今,社會上許多老年人不愛聽“老”字。就以老黃為例吧,老黃說,他曾與超市門口的小伙子紅過臉。小伙子推銷商品,見著老黃,張口閉口“大爺,大爺”地稱呼。老黃卻怒目道:“我有這么老嗎?”而老黃每次去權金城洗浴,服務員都親切地稱呼他:“黃哥好!”聽罷,老黃的心里比喝了蜜還甜呢,為了這一句“黃哥”,他沒少在店里購買消費卡。此乃社會習俗微妙之變化,于是乎,絕大多數養老院都起名為“養生公館”。個別超前意識的養老院干脆就起名為“健康智慧生態谷”,聽上去和“兒童樂園”的名字也差不太多,這就是與時俱進。
老黃跟我說,公館一到節假日,來訪的人非常多。食堂里的桌椅都不夠用,一家占一張桌,老人被兒孫圍著,其樂融融。但是,也有一些老人,孤孤單單,很少有人來探望他們,平時也不愿與人交往。公館里有許多業余組織,如游泳隊、乒乓球隊、舞蹈隊等,這些人很少參加,公館和旅行社聯袂組團旅游,更難見到他們的身影。原因并不復雜,大家伙湊一塊兒,最愛聊的無非是“您家孩子如何如何,我家孩子如何如何……”而這恰恰正是空巢老人的軟肋。他們大都避免談論這個話題,也不愿意讓別人知道自己的“底細”。因此,他們寧愿將自己封閉起來,或者只愿意和境遇相仿的人交朋友。
其實,老黃本人就是典型的空巢老人——60歲,50后,離異,無子女。老黃說,很難統計出公館里有多少像他這樣的人,身邊的老楊和老李跟他情況類似,幾個人經常在一起。老楊和妻子年輕時當過職業運動員,一位打排球,一位打籃球,大高個,儀表堂堂。但他倆卻沒有孩子,是典型的“丁克夫婦”。
電視臺曾經采訪過丁克夫婦不要孩子的原因,夫妻倆的回答非常直率:“養一個孩子防老,需要幾十年的精力和物質投入。而需要兒女照顧的時間也許很短,劃不來,不如兩個人享受生活。”前幾天,看“非誠勿擾”,有位精英男士,某網絡公司總監,擇偶的條件就是不生孩子不買房子,只做“丁克夫婦”。如此個性的人物,竟有六分之一的女士為他留了燈。據場上老師介紹,這叫“鐵丁”。還有一種叫“鐵狗”,就是只養狗,不養孩子。真不知是對是錯,不養孩子,到老了怎么辦?兩個人還好辦,先走了一位,剩下的可就孤獨了。看來,空巢老人的后備軍大有人在,這不能不引起社會的廣泛關注。
老李夫婦也是典型的空巢老人,就一個兒子,留學英國,加入了英籍。“好嘛,就一個兒子,還給英國作貢獻了。”我常和他們開玩笑。“兒子是不會回來了,等他退了休,我們還在嗎?兒子讓我們去,我們不去,不懂英語,吃也吃不慣。我們決定留在國內,哪兒也不去……”這是老李的原話。筆者認為,像老李夫婦這樣的家庭,在京城并不算太罕見。
雖然住進了養生公館,三個人的心里并不十分踏實。按老黃的話講,現在的養生公館適合于健康老人居住,一旦生病,那些沒兒沒女的空巢老人處境依舊十分尷尬。就拿老黃現在居住的公館來說吧,館內設有24小時醫護站,999救護車就停在公館的大門口。老人一旦出事,可謂救助及時,萬無一失。可是,問題來了。公館現在只負責將老人送進醫院,接下來,馬上聯系家屬,然后,人家就撤了。護士站就那么倆人,哪兒能就為您一人服務啊。問題是,那些沒有家屬照看的老人如何處置?對此,尚無相應的應急措施和規定。目前,絕大多數養老機構依舊死抱著有事聯系家屬的慣例辦事,而對于“孤獨老人”的經營缺乏足夠的考慮。而這個問題不解決,顯然不能夠滿足真正的空巢老人的養老需求,實乃經營上的空檔,是一塊尚待開墾的處女地。
市場里缺少“專門店”
前些日子,老黃參觀了位于北京和天津之間的卓達太陽城。據介紹,卓達太陽城是民政部門指定的養老示范基地,建筑和環境自不待言,就說人家房間的智能化,看罷,您不服都不行。房間里帶著監控,兒女通過手機就能觀察到父母的情況;老人往床上一躺,智能床墊能為您檢查身體;如廁也不閑著,儀器可以自動做出尿檢……足不出戶,屋子里儼然就是半拉小診所,我想發達國家的養老機構也不過如此吧。可當老黃問及,如果老人沒有兒女或兒女在國外,你們怎么辦?對方感到有些茫然。老黃認為,養老市場里“百貨商店”和“超市”太多,少的是“專門店”。基本上可以這么說,沒有一家養老機構是專門針對空巢老人的。
實際上,“專門店”的作用不容小視。就像您買照相機,蘇寧電器里有,為什么攝影發燒友還要跑到五棵松攝影城轉轉呢?因為,五棵松攝影城是專門賣相機的,不賣電冰箱。“專賣店”的特點是,只為一部分消費群體服務,與百貨商店和超市相比,“專賣店”在某一項產品的經營上,一定會做得更為專業和精當。當然,并不是說養老機構里就沒有“專門店”,比如說,位于昌平的某半公立養老機構,規模不大,據說只接受85歲以上的老人,就屬于“專門店”性質,只是這樣的“專門店”數量并不太多。
老黃是行動派,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給養老機構的高管寫信或直接跑養老機構,到處宣傳他的“專門店”企劃,忙得不亦樂乎。老黃所謂的“專門店”,是指建立一家只接收6類空巢老人的養老機構。按老黃的話講,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同等命運的人聚在一起,容易找到共同語言。管理者針對這一群體老人的特點,便于提供各項專門服務,諸如過生日沒親人,機構組織大家為你過。機構建立“慈善基金會”,老人過世后,鼓勵將錢捐給基金會,基金會為你料理后事,余下的錢可作公共積累。專門化的養老機構也便于與社會志愿者組織溝通,甚至可以得到國際慈善組織的關注和支援。想法不錯,但是做起來并非那么容易。
老黃說,首先,新成立的養老機構數量不多,成立一家養老機構絕非易事,需要各級政府的審批。而老的養老機構已經有了自己的經營模式,你讓它改弦更張,幾乎不可能。其次,老黃心中的“專門店”需要一定的檔次,不是任意一家養老院都可以辦到的。老黃曾經聯系過一家規模很小的鄉村養老院,老板是東北人,為人豪爽。聽罷老黃的想法,他大腿一拍,豎起大拇指說:“兄弟,您的想法太猛了,您負責招人,我給您回扣。我給你們養老送終,去世后,錢存在我這兒,放心吧,我跑不了!”可老黃覺得這家企業收費雖然極低,但條件太過簡陋,怎么看都有大車店的感覺。好在老黃聯系到一家中型企業,企業的老總是“海歸”,人很好,留學加拿大,碩士,業內有一定的名氣。現如今經營旅游度假村,買賣做得風生水起不說,近期,準備同時進軍養老地產。看來,老黃的努力沒有白費,他終于找到了一線希望。
空巢老人要當英雄不做狗熊
還是于洋老師的那句話“我要當英雄,不做狗熊”,這句話太經典了,足以成為空巢老人的座右銘。社會理應關注空巢老人問題,為他們的養老提供種種便利。同時,空巢老人本身更應該自強自立,勇敢地面對流金歲月、身體的衰老,甚至勇敢地面對死亡。
老黃對我說,他的戶籍是在北京太陽城,開發商曾經計劃在院里的東北角,也就是醫院后身,建一座“臨終堂”。其實,這是一件極利民的好事情。太陽城打出的旗號就是提供“一條龍全程式養老服務”,臨終堂顯然是服務的最后一環。老人在醫院歸天,在臨終堂辦個告別儀式。創意是沒有問題的,卻遭到院里不少老人的反對。他們認為,在院內建臨終堂不吉利,好端端的社區里擺著雪白的花圈,飄出哭聲和哀樂,容易引發老人的聯想。因此,至今臨終堂也沒有建,一塊空地留在那里,長滿了衰草。老黃說,不管部分老人的反對與否,臨終堂最終肯定會建,老年人意識的轉變需要一定的時間。在養老社區可不可以建臨終堂,這個問題值得社會人士商榷。筆者認為,死亡并不可怕,所謂的“紅白喜事”,“紅”是婚禮,“白”是葬禮,都是人生的“喜事”,佛教管它叫“涅”。老黃說,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更不應該害怕那一天的到來,說白了,不管您害怕與否,那一天總會到來。我們要當英雄,不要做狗熊,有什么可怕的!特別是空巢老人,兒女不在身邊或干脆沒有兒女,機構幫您料理后事,應心存感激才是。實際上,就此問題,老黃詢問過空巢老人,他們百分之百贊同在養老社區里建臨終堂。其中一位甚至說,可以預先留下一部分錢給臨終堂,去世后,不給街坊鄰居和社會添麻煩。不知道這叫不叫英雄行為,反正,那位老人的社會責任感值得肯定。
實際上,關鍵不是死亡,而是活在當下,有意義地活好每一天,這才是空巢老人應當思考的問題。九華山莊養生公館的老人自發創作了一本文集,叫《九華人》,其中一首詩寫道:“人只要活著,就要成長,即使沒人重視,也要努力成長。許多眼睛,都藏在你看不見的地方。”老黃說,他就是這樣一只眼睛,見證了老人在公館里的生活。老黃不止一次對身邊的老人說,你們不是在養老,比上班的白領還忙呢。忙繪畫的、忙舞蹈的、忙音樂的……有些老人走路都爭分奪秒,畢竟余下的時間有限,每一個人都在向生命的極限挑戰。到院子里看看,練太極的、跳廣場舞的、打網球的……追求健康和長壽也是一種成長,漢字中寫法最多的一個字就是“壽”字。見過書法家寫的《萬壽字圖》,說實話,任何一個漢字都沒有“壽”字牛,能寫出萬種形態,足見古人對“壽”的重視。
采訪結束的時候,老黃最后說,空巢老人不必擔心,當孝道從家庭走向社會,當新生代創業者關注起養老事業,當機器人等高科技產品開始服務于老齡化社會,當空巢老人有意義地活好每一天,“路”自然也就出現了。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