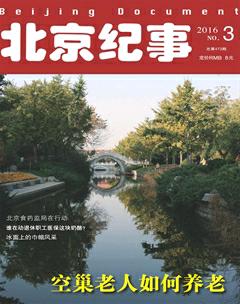張嘉佳:我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我很普通
那子


張嘉佳,作家,一個有著文藝才情的80后男人。從大二開始,他就一直在南京、上海、北京的各個電視欄目晃蕩著,他在那些文字里恣意揮灑著自己的才情,33個睡前故事,暖心,很容易打動人,而且有“治愈”功能。他的書籍《從你的全世界路過》《讓我留在你身邊》都創下了不俗的銷量。現在,他自編自導,正全力打造自己的電影《擺渡人》。就算拍攝現場忙到無暇睡覺吃飯,面對我們的采訪,他依然回答得很走心,這種敬業的態度讓人感動。同時也證明,張嘉佳不僅有才情,還有人情。
這是我的第一部作品,必須堅持
7月9日,張嘉佳首任導演的電影《擺渡人》開機。他坦言,此前覺得不就是拍個電影嘛,順其自然就可以。但是真正開機的那天,當梁朝偉站在鏡頭前的那一刻,他突然知道了什么是緊張。
除了緊張,還有另外一個字——累!可以說拍這部電影是張嘉佳人生最辛苦的階段。“如果是別人的電影,我根本無法堅持下來。但因為是我的第一部作品,我必須堅持。”張嘉佳說。
記者:《擺渡人》對你的意義是什么?
張嘉佳:《擺渡人》對我最大的意義就是讓王家衛知道了我,并且帶我走上導演之路。
記者:據說劇本寫了40稿,這是一個怎樣的過程?
張嘉佳:我6月8日進組時,這部電影劇本已經寫了30多稿,7月9日開機前一個月,又寫了9稿;開機到現在,繼續加了三稿。正常電影劇本3萬字,而《擺渡人》的劇本至今已經累積70萬字。一直傳聞王家衛拍電影沒有劇本,事實是,他不是沒有劇本,而是劇本概念太宏大,不是探討人物情節,而是探討人的一生。當然,這只是我初期的領悟,到了后來,我知道自己太幼稚,他的劇本不是探討人的一生,而是探討人物一生的幾種可能。
記者:《擺渡人》講述的是什么?你想通過這個故事傳遞什么?
張嘉佳:《擺渡人》中,女主角“小玉”喜歡畫家“馬力”,明知對方并不喜歡自己,也樂于付出,傾盡全力幫忙,在燈光下擁抱對方的影子。“他在岸這邊落水了,我要把他送到河那岸去。河那岸有別人在等他,不是我,我是擺渡人。”王家衛看中的正是“擺渡人”這樣一個意向,并由此重新發展出更加豐富的故事和人物關系。
擺渡人很多人理解為備胎,其實不是的。因為人人都在渡河,也都在擺渡。這是所有人必經的河流。你的河流,我的河流,或許永不并流。尊重每一份感情,因為它們可以發生,就是了不起的事情。我喜歡擺渡人的最后一句話,我們都會上岸,陽光萬里,鮮花沿路開放。
記者:首任導演,最大的挑戰是什么?樂趣是什么?
張嘉佳:第一次當導演,演員里那么多大咖,還有很多高難度甚至高危險性的拍攝,對我來說就是最大的挑戰。
雖然有這么多的大牌,但無論是多么高難度甚至高危險性的拍攝都沒有人拒絕,都很配合。我越來越愛梁朝偉,跟他說什么,他都張大那雙電眼,嘴巴成O形說:哦好。簡直太迷人了,成熟與童真并具。
記者:請評價一下王家衛,并談談你們相識的細節。
張嘉佳:首先王家衛對我來說肯定是偶像,我看的遍數最多的電影就是《東邪西毒》。高中看的,在租碟店發現一個武打片,打得一塌糊涂,很激動,借回去看。回家一放,看不懂啊,為什么啊?明明打得很厲害怎么看不懂呢?大學一遍遍看,就此被導演拐帶成了文藝青年。《重慶森林》《花樣年華》《2046》都喜歡。梁朝偉的盲武士,張國榮的歐陽鋒,喜歡得不得了。張曼玉在窗沿的獨白,“我最好的時候,你卻不在我身邊”,至今還會在腦海里回放。
第一次見面是在上海的一家酒吧,穿什么不記得了,不過導演沒戴墨鏡。第一句也不記得了,只記得差點撲上去親他。當時導演說,你故事里有適合梁朝偉演的嗎?我說,就算沒有編也要編一個出來。
我是一個具備寫字天賦的普通人
張嘉佳被稱為“微博上最會講故事的人”,對這個稱號,他說他不介意一切評價和稱呼。如果是褒義的,他會感謝;如果是貶義的,他會看不見。
張嘉佳只對喜歡負責,他很高興自己是被這個世界需要的,很高興自己能夠提供那么一點點微弱的東西。
對于自己,張嘉佳說:我最特殊的地方,就在于我很普通,我是一個具備寫文字天賦的普通人,過自己喜歡的生活,回報喜歡自己的人。
記者:好故事的標準是什么?如何講好故事?
張嘉佳:在技術層面劇本和小說是兩個領域的技巧,恰好我都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所以講起故事來和別的作家有所不同,節奏更快,更注重人物設定,更強調嚴格的三段式敘述,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回饋吧。這是技巧層面的,其實我私下覺得,可能更多是因為我在堅持一個講述的概念——我說的一定是我自己真這么認為的。寫作對我來說,一直是件私人的事情,不因為他人喜歡而改變,也不因為他人厭惡而退卻。寫作,意味著我與這個世界正在對話。
記者:在你的故事中,哪些人物有原型?哪些是你自己的影子?
張嘉佳:故事都有原型。是朋友們和自己的故事,打碎了,重新梳理的,拼接到一個完整的人身上。一定是自己的真實寫照,而且零碎投射到了每一個主人公身上。自己在小說中客串,所以才叫作“從你的全世界路過”。我把這本書當作一張專輯,幾年來的人生全部打散了,依次刻錄、鑲嵌,這本書其實呈現的就是我的世界觀。我33歲生日之后,就想要把最近幾年的經歷寫出來。可是我又不想寫自傳,寫成好多塊之后,它就零零散散地變成這么一些每個獨自成篇的故事。
記者:如何從一個作家轉型成為編劇?
張嘉佳:這個其實我不太好回答,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在我出《全世界》這本書之前已經寫過電影《刀見笑》了。只是我做事比較隨性,沒啥太集中的目的。電視、小說、編劇一直陸陸續續做著,不太追求勇攀高峰什么的。頹廢文青做得好好的,突然做娛樂節目去了。電視做得好好的,突然寫劇本去了。《刀見笑》被金馬獎提名最佳改編劇本,可惜沒拿到,導演監制安慰我,明年再來,結果第二年我研究美食去了。
記者:幸福是什么?
張嘉佳:努力做到忠于自己吧。
日前,張嘉佳正式成立“時間海”公司,簽約并培養年輕寫作者。從作家向出版人轉型的他坦言:“‘時間海這家公司,就是想找到對的人,一起做好的事。”
(編輯·麻雯)
mawen214@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