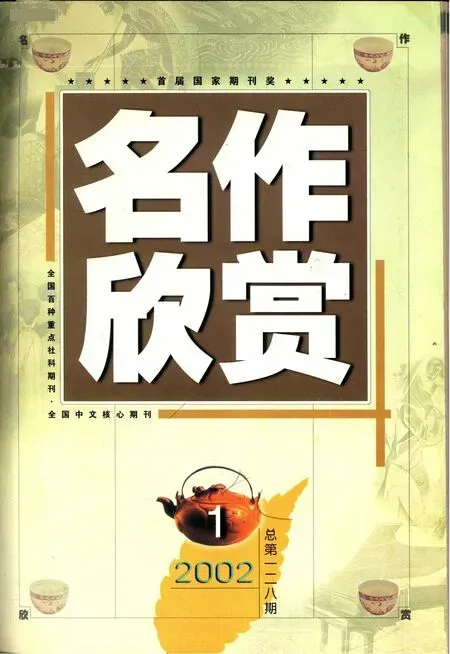現代早期中國思想中的“第三世界”
上海 王曉明
?
現代早期中國思想中的“第三世界”
上海王曉明
摘要:大約在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讀書人階層就已經開始形成“中國需要一場革命”的共識,然而孫中山、劉師培、梁啟超等人對于革命的論述又是不盡相同的。但“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無疑是他們的共識。中國是“第三世界”,這一意識在改造中國的同時,又催生出對于中國與世界關系的思考。但在中國,要堅持“第三世界”的視野和思路,又是非常困難的。
關鍵詞:中國革命第三世界孫中山劉師培梁啟超
1955年周恩來在萬隆會議(Asian-American Conference)上強調亞洲和非洲人民有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共同經驗和要求;1974年毛澤東在會見贊比亞總統時提出“三個世界”的判斷,說日本以外的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都屬于“第三世界”。
如果只是以這兩個事件為標志,就很容易得出這樣的判斷:在中國,這一種今天很多人習慣于用“第三世界”這個詞來概括的、強調“發展中國家”有與發達資本主義世界不同的共同的歷史經驗,因而應當開拓自己的革命/進步道路①的思想,主要是上世紀40年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
實際情況當然不是這樣。在現代早期(1880—1940)的中國,這一思想已經發展得相當完備,進而推動了一系列對后世影響深遠的社會實踐。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有關“第三世界”的論述,其實只是延續了現代早期的這一思想,有些時候,還延續得相當粗糙和膚淺。
限于篇幅,這里只粗略地介紹有關現代早期中國“第三世界”思想的兩個方面的論述:一個是“如何理解世界革命”,另一個是“如何創造新的中國”。限于篇幅,本文不能較為全面地介紹這兩方面的論述,只能選當時流行的兩個思想概念,來勾勒這兩方面論述的大致輪廓:一個是“中國革命”,另一個是“農國”。
大約在20世紀初,中國的讀書人階層(當時中國社會的主流階層),至少是其活躍部分,已經開始形成這樣的共識:中國需要一場革命。因此,“革命”及其派生詞“中國革命”,開始成為流行詞。
中國革命的基本內容是什么?它和其他國家的革命是什么關系?1905年,中國第一個規模較大的革命黨——國民黨——的創始人孫中山,在日本發表了一套影響深遠的論述②,大致的意思是這樣的:
世界各地的情況不同,社會進步的道路也就不同:“夫繕群之道,與群俱進,而擇別取舍,惟其最宜。此群之歷史既與彼群殊,則所以掖而近之之階級,不無后先進止之別。”因此,中國革命與歐美資本主義發達地區的革命不同,重點不是反資本主義,而是反帝國主義和反專制,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族殘之,外邦逼之,民主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慮積重難返者(指資本主義——作者注),中國獨受病未深,而去之易。”也因此,中國革命不能跟著歐美式的革命走,要開辟自己的革命路線。正因為是走自己的路,中國革命反而可能同時完成兩個任務:一是反對帝國主義,爭取民族解放;二是控制資本主義,避免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地區那樣的社會矛盾。孫中山認為:“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后發現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于一役。還視歐美,彼且瞠乎后也。”
三年以后的1908年,持無政府主義立場的劉師培,又從另一個角度解釋“中國革命”及其與世界革命的關系:中國革命是一場以農民為主體、以官僚地主土地所有制(田主之制)為主要革命對象的“農民革命”③。他特別強調,之所以這么理解中國革命,是因為中國的社會實情:“中國大資本家仍以田主占多數,田主之制覆,則資本階級之大半亦因之覆”,“中國人民仍以農民占多數”,“中國政府之財政仍以地租為大宗”,“農民者有團結之性者也……含有無政府主義者也……保存共產制者也”。雖然用了一堆西式概念,他實際表達的,卻是一般人對于當時中國社會常識性的理解。
正是根據對這些近乎常識、表達得也很粗糙的理念的理解,劉師培提出了一條其后半個世紀(不只是中國)的許多革命方案(包括毛澤東式的方案)都不同程度地沿用過的革命路線:在亞洲這樣的農業國家里,以“農民革命”為橋梁,進入世界革命(他稱之為“無政府革命”)。
1921年,老資格的革命家梁啟超再次討論中國革命(他稱之為“社會主義運動”)“與歐美最不相同之一點”及其全球意義:中國的資本主義還沒有怎么發達,就已經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禍害的最后集中地了。他說:“吾國國內,未曾夢見工業革命之作何狀!而世界工業革命之禍殃,乃以我為最后之尾閭。”他這么說的依據,同樣是基于對中國和全球實際狀況的認識,例如中國國內資本主義的不發達,以及帝國主義/資本主義創造的全球結構的不平衡。他說:“所謂階級者,非自國內縱分,而自國際上橫分。”雖然他沒有像20世紀50年代以后的毛澤東那樣,在“國際資產階級”和“國際勞工階級”這兩大世界之間,多劃分出一個“中間”部分,但那種將“階級”之類概念運用于把握全球情勢的思路,已經非常清晰。他由此估計:“在稍遠之將來,必有全世界資本家以中國為逋逃藪之一日。而中國勞動階級最后之戰勝,即為全世界資本主義根株斷滅、全世界互助社會根本確立之時。”④身為大陸中國人,今天重讀梁啟超寫于差不多一百年前的這個估計,很難不感慨萬分。
了解中國現代思想史的人都知道,以上三位論者,在政治、思想和人生道路上,都是明顯不同的。但是,當闡釋什么是“中國革命”的時候,他們卻凸顯出一個明顯的共同之處:他們都認為中國這樣的資本主義不發達地區的革命,和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地區的革命,是互相聯系、相互支援的;但他們都更強調,由于歷史和現實條件的不同,這兩類革命的主要內容,是有重大不同的。他們因此都認為,中國革命,以及其他地區的類似革命,應該在思想、動力、對象、政治路線、行動模式等方面,都開創了適合自己的道路。最后,他們也都堅持,那種要把在歐美式社會革命中發展起來的理論拿到中國來教條式地指導革命的做法,是不合適、弊大于利的。⑤
在現代早期,將這一套共識表達得最為清晰的,是施存統發表于1928年的長篇名文《中國革命底理論問題》。此文在一開頭就說,中國的各派革命者,在如下認識上是意見一致、“沒有什么大的不同”的:“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世界革命包含兩個部分,一是西方的無產階級革命,二是東方的民族革命,而中國革命是后者“最重要的根本的部分”。但是,“追究到這一部分究竟是什么性質,在世界革命中有沒有其獨立的地位,意見便不一樣了”。文章概括得非常準,分歧的焦點正在這里:如果中國革命——以及整個東方的革命——與西方的革命有不同的性質,那接下來的一切就都應該不同,不能照著西方的路子走。
作者逐條列出他對中國革命的理解:“出發點”“社會基礎”“革命勢力”“革命對象”“根本理論”和“革命政黨”……限于篇幅,這里不做具體介紹,只引出他的主要結論:“中國革命是一個——帶有社會主義性的國民革命,適合中國革命的主義是一個——革命的三民主義……”也就是說,中國革命是與歐美的革命根本不同的。
施存統是中共早期的重要成員,后來加入國民黨,成為該黨左派的重要論者。他這篇長文的基本內容,有相當廣泛的代表性。就“三民主義”這一路向的思想論述來說,它不但可以代表胡漢民那樣的左翼思路,也與戴季陶式的右翼思路,共享一些社會判斷的基本前提。而在20世紀20年代,“三民主義”式的社會認識和政治訴求,是構成了大多數革命者的思想底色的,即便一些屬于中共或其他規模較小的政治組織的人,其基本的思想意識,實際都還是“三民主義”式的,盡管他們自己不一定承認。⑥
有意思的是,在施存統概括的這一分歧焦點上,當時站在上述論者對面的,恰恰是一批共產黨的思想家,尤其是那些有意識運用馬克思、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式的理論的年輕人。他們依據對當時全球資本主義的認識,根本否認中國革命有什么特殊性質,或者雖然承認中國革命有自己的特點,但認為這只是較為次要,或者只是初步階段的特點。⑦因此,在論述中國(東方)革命與西方革命的關系的時候,他們總是走到這樣的結論:前者只是后者的初級階段或從屬于后者,后者才代表了整個世界革命的核心或關鍵。毛澤東寫于1940年的名文《新民主主義論》,就依據源出于斯大林的“中國革命必須分為兩個步驟”的思路,明確得出結論:中國(東方)的革命不是與西方的革命(此時這個革命已經被認為是以蘇俄為中心)一起構成世界革命,而是本身成為西方的革命的一部分,因為西方的革命正體現了世界革命的方向。⑧
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第三世界”的視野/思想最可貴的一點,就在于不盲從那些主要依據歐美式的社會歷史經驗而形成的革命理論,而要從本地的歷史、社會和現實狀況出發,開拓自己的思想和社會解放道路,并由此互相啟發和結合,形成與西方式革命不同,但可以互相支援的,范圍更廣闊的視野、思想和行動空間。地處美蘇兩大集團空間之外的萬隆,在1955年成為亞非會議的舉辦地,印尼總統蘇加諾致開幕詞的時候,之所以強調這是第一個有色人種的洲際會議,萬隆會議之后,之所以更進一步形成了以“不結盟”為旗號的全球運動,都是凸顯了“第三世界”論述/實踐的這一個特點。
從這個角度看,現代早期的那些自覺地從實際國情出發、探究中國(東方)革命的特別性質的論述,雖然各不相同,卻合力形成了中國人的相當穩定的“第三世界”的思想視野,反倒是一些被歐蘇版本的革命理論捆住了手腳的論述,明顯欠缺“第三世界”的意識。
1924年孫中山說,中國革命的目的并非只是建立一個共和政權,而是要“改造中國”⑨。這是現代早期幾乎所有革命派別的共同認識。因此,一旦形成了“第三世界”的視野,就自然會在如何改造中國的方案設計中,發展出各種富于啟發性的思路,20世紀20年代中期由老資格的革命思想家章士釗首倡的“農國”論,就是其一。
作為一種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整體構想,章士釗說,“農國”的關鍵在于“農”的精神,要以這個精神立國。⑩這是與“工”相對的一種精神,其核心意思是兩條:第一,家里有多少米,就煮多少飯,不要想著把別人家的米也搶來,煮成自家的飯。用他的話說,就是“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而不攫國外之利益以資挹注”。第二,煮飯是為了全家人吃,而不是廚師自己賺錢,因此,重要的是全家老小都有的吃,可以有人吃得多一點,但差別一定不能大。用他的話說,就是“取義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遠”。
“工”的精神和以此造就的“工國”,則是完全相反。他認為:“其人民生計,不以己國之利源為范圍,所有作業專向世界商場權子母(即投入/產出——作者注)之利,不以取備國民服用為原則,因之資產集中,貧富懸殊,國內有勞資兩級,相對如寇仇……”他特別強調,“農”“工”之別的關鍵,在于你是不是要去搶別人的米,即“以財源是否在于本國為斷,由此勘入,思過半矣”?。一種與站在發達資本主義地區把握世界的眼光明顯不同于現代被壓迫民族的視野,也即“第三世界”的視野,在這里凸顯得非常清楚。
正是沿著這樣的思路,從1910年到40年代,一系列更為具體的社會進步的主張和構想,相繼成形。
其中有晏陽初式的“農村運動”的主張:視上海那樣的都市和西式學校教育為病態之物,因此號召城市知識青年大批下鄉,與八千萬農村青年一起奮斗,在鄉村創造真正的“現代化”——他稱之為“民族再造”——的基礎12;也有梁漱溟那樣的“鄉村建設”的構想:以“復興農村”為起點,從鄉村開始構造新的社會組織,以此重建中國社會,從根本上結束中國因為“文化失調”而四散崩壞的局面13;還有費孝通式的“鄉村工業”道路的設計:既然“在現代工業世界中,中國是一名后進者,中國有條件避免前人犯過的錯誤”,就應該從“恢復農村企業”開始,開辟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鄉村工業”的道路,“以合作為原則來發展小型工廠……防止生產資料所有權的集中”14;更有潘光旦那樣的“鄉土的史地教育”15的方案:根據“鄉村是本,城市為末”的原則,發展聚焦于本地歷史/地理的系統教育,培養青年人熟悉和熱愛鄉土的能力和情感,以此打破有為青年紛紛“輕去其鄉”的失衡局面……
這些都不只是寫在紙上的方案,更是以各種方式、在大小不同的范圍內展開的改造現實的行動。例如,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的將近十年間,單是投入晏陽初或梁漱溟式的鄉村建設運動的知識青年(大部分都是在城市接受西式教育),就達十萬人次。即便在各種條件都極為艱苦的抗戰時期,這個運動依然在西南地區堅持下來。它是到了20世紀50年代,才被中共領導的以“統購統銷”和“人民公社”為主要內容的鄉村改造所取代。但到20世紀90年代,隨著“人民公社”制度的廢除和“三農”困境的蔓延,類似的鄉村建設運動又再度復興,并且與經歷了西式現代化社會巨變以后的更大范圍的反思相結合,開始形成在廣闊的歷史和社會框架內重構人類——不僅是中國的——生活前景的思想的可能。
即使從上述這個例子也可以看出,“第三世界”的視野和思想,是如何在一百多年的中國現代歷史,尤其是其早期階段中,激發和落實為各種社會運動和群體實踐的,雖屢受打擊,仍以各種思想火種和社會遺存的形式,留存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中。
需要說明的是:至少在整個現代早期,大多數中國的革命思想家,都是把“中國”和“世界”16聯系在一起考慮的,他們改造中國的許多具體的構想和方案,常常都從屬于他們對整個人類未來的宏觀理想。因此,現代早期中國思想中的“第三世界”意識,并不只是落實為改造中國的具體方案,也同時催生出對于中國與世界其他地區如何交往的理想,甚至發展出對于整個人類生活乃至更大范圍的未來的理想。
比如,就在強調中國革命的獨特性質的同時,一種“中國不能變成歐美式的帝國主義強權”的警告也持續出現。1907年章太炎說,中國人要實現自己的民族主義理想,就必須去幫助其他被壓迫的民族獲得解放,但誰要是借此牟取中國自己的利益,就是犯了不能赦免的死罪,即“有……假為援手,藉以開疆者,著之法律,有誅無赦”17!1924年,孫中山演講“民族主義”的時候,也一再告誡,以后中國強大了,絕對不能學西方列強,“也去滅人國家”,蹈其覆轍……18
對內對外,中國世界,唯其從這些不同的方面,都長出了打破強勢力量與流行理論的束縛,依實情與己力去開創新天下的理想,我們才可以說,現代早期的中國思想中,真是有“第三世界”的意識。
但是,在中國,要堅持“第三世界”的視野和思路,又是非常困難的。極多的障礙和打擊接踵而來,其中最難克服和抵抗的是這么兩項:思想能力本身的薄弱;嚴酷現實的逼迫。
現代世界的一大可怕之處,就是形成了知識/文化生產向西方一面倒的畸形結構。現代中國人自不例外,也被推進了這個結構,于是一方面深陷難以用西方知識切實把握的現實,另一方面又日益喪失傳統智慧的支援,在這兩面夾攻之下,“第三世界”式的意識就很不容易成長,尤其是在概念和原理的發育上,進展緩慢,以致在大多數時候,這些本來內含了豐富的發展可能的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停留在粗糙甚至初步的階段上,不成體系。19
當然,更大的打擊還是來自于嚴峻現實的逼迫。黑暗越是濃厚,企望“根本解決”、不惜以暴易暴的沖動就越強烈,追求快速起效的功利意識,就很容易壓倒那些一點一滴、需要長時段才能顯出效果的治本之策。一旦這樣的短視氣氛彌漫開來,那些邏輯強勁、目標明快的西式流行理論,憑借其已經形成的精神和物質實力(例如蘇俄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影響力),自然就會占得上風,令那些本來就范圍廣闊、輪廓不全的“第三世界”情懷,更顯得好高騖遠,不切實際。那些批評“農國”論的人舉出的一條最有力的理由,就是:“人家已經靠工的精神發展得如此強大,打上門來,你不趕緊仿效,也把自己搞強大,怎么對付得了!”在20世紀各種革命路線的競爭當中,以“革命黨—黨軍—黨國”為核心的路線之所以脫穎而出,獨領風騷,更說明嚴峻現實對于現代中國人革命意識結構的影響是多么深刻:政治功利主義,穩穩占據了革命意識的中心位置。20
不用說,大半個世紀之前中國人的“第三世界”意識在兩面夾攻之下步履維艱的困境,今天依然在整個世界范圍內繼續。在中國,直到六十年以后,“萬隆精神”才被當作重要的話題得到關注,這本身就表明了“第三世界”意識所遭遇的困境,在今天的中國是如何強固。當然,終于記起了“萬隆精神”,總是一個進步:風沙可以一時抹除行者的腳印,甚至掩埋整條道路,但只要有人記起了,甚至接著走起來了,這斷了的路就有可能再次伸向遠方。
①這道路既是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也是文化的和知識的。
②孫文:《民報發刊詞》。
③劉師培:《無政府革命與農民革命》。
④梁啟超:《復張東蓀書論社會主義運動》。
⑤這方面劉師培有所不同,在20世紀第一個十年晚期之前,他曾熱衷于用西式概念來描述中國的現實,并相信類似無政府主義這樣的思想是適合用來推動中國革命的。
⑥之所以形成如此的思想局面,原因很多:當時規模最大的革命黨——國民黨——以三民主義為指導思想;與譬如馬克思主義或無政府主義相比,三民主義的論述相對空洞,因而其核心概念的涵蓋面反而較寬;在當時的思想激進、傾向或投身革命的人士中,懂外文或能出國留學者僅是少數,等等。
⑦相較而言,這些論述當中,從托洛茨基派的理論視角展開的論述是最有新意的,例如“資本主義落后國”這樣的概念的提出。
⑧20世紀20年代中期,孫中山為了爭取蘇聯援助而修改三民主義論述的時候,也部分贊同過類似的說法。
⑨孫中山:《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10有意思的是,當時就“農國”問題與章士釗論戰的人當中,相當一部分人不理會章士釗對他所謂“農國”的這一解釋,而簡單地判定他就是要“以農立國”。
11章士釗:《農國辨》。
12晏陽初:《農村運動的使命》。
13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
14費孝通:《江村經濟》。
15潘光旦:《說鄉土教育》。
16在整個現代早期,許多中國思想家筆下的這個“世界”,并不是只包括人類的,甚至常常也不是以人類為中心的。
17章太炎:《五無論》。
18孫中山:《民族主義第六講》。
19三民主義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隨著20世紀20年代晚期各種西方現代思想較大規模、也較為系統地傳入中國,類似三民主義這樣基本上是“土生”的表述粗糙的思想,對日益習慣于西式哲學/理論形態的城市知識青年的吸引力,就明顯弱化。
20連魯迅這樣頭腦清醒的人,也因為憤恨于專制統治的殘暴,而多次感嘆“改革最快的還是火與劍”。
作者:王曉明,上海大學文化研究系、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思想、文學研究和當代文化分析。
編輯:張勇耀mzxszyy@126.com
經典重讀Class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