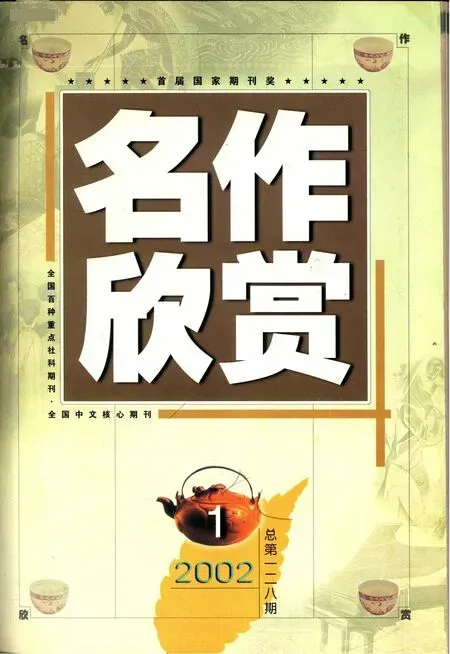精神自由與審美自信——高相國山水藝術的啟示
山西 劉淳
?
精神自由與審美自信——高相國山水藝術的啟示
山西 劉淳
20世紀中國山水畫壇的平靜,首先是被伴隨辛亥革命而興起的新文化運動徹底打破的。康有為、梁啟超、陳獨秀和蔡元培等文化維新人士在批判和抨擊中國傳統文化的同時,一致將目光對準了中國傳統繪畫,倡導革中國畫的命,用西方的寫實精神改造傳統中國畫。但由于他們缺乏專業眼光,立足點多數不在藝術發展與變革,而只是一味革命,故不無偏頗過激之弊。但對于當時的中國畫壇,無疑是一塊巨石投入平靜的水面而引起的爆炸式翻滾。1949年以后,國家全面投入社會主義建設,中國畫作為媒材也被納入到新的國家意識表達中,歌頌祖國大好河山、贊美社會主義新氣象等,成為這一時期的創作主題,并在以后的三十年中成為謳歌和贊美社會主義中國的主要宣傳工具之一。改革與開放再一次打破了三十年的沉寂,20世紀80年代中葉,李小山高呼“中國畫已經走向窮途末路了”,對一個多世紀以來中國畫在創作上的得與失進行了無情抨擊,就此引發了20世紀以來最為熱烈的中國畫及水墨問題的大討論。在歷時三年的討論中,畫壇那些往昔德高望重的大家一個個被驚醒,他們和眾多的年輕人一同,置身于此,加入到這場曠日持久的論戰中。如今,中國畫是否窮途末路已無人關心,李小山當年震耳欲聾的聲音早已消失,那些當年讓人眼睛發熱的文字靜靜地躲藏在漸漸發黃的書籍里。但是,無論怎么說,這場發生在中國畫壇上的大論戰激發了那些具有反思傾向的藝術家的創作激情和向傳統挑戰的欲望,他們的內心曾被一層厚厚的油布緊緊包裹,恰在李小山的挑戰和呼喊聲中得以釋放。重要的是,他們獲得了對藝術,以及作為水墨的中國畫的重新理解和認識。
對中國畫的重新認識,是作為人的精神自由和思想解放為主體得以展開的,不是單純為了水墨的緣故而進行的。對于革新者的水墨,時代總是顯得滯后;而革新者的水墨傳達和表現的,也總是有那些道義者為之吶喊和辯護——所辯護者,充分肯定并贊同對藝術自由精神的激賞。如果,在人類所有的生存方式中,藝術不能帶給人視覺、觀念和認識上的發展與變化,那么藝術作為思維創造的手段與對象的存在將何以成立?
這個時代,如果沒有銳意進取,沒有敢為天下先的膽魄和氣度,何以改革積弊深久的問題?對水墨問題的思考與討論,同樣是時代的反映。
一個有追求的藝術家,必須是在中國藝術發展的歷史長河中,尋找自己生存的基本點和可能性。藝術家高相國在過去四十多年的藝術道路上,以堅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以及趨向自由的選擇意識和創新精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和語言方式,走出了一條屬于自己的藝術之路。綜觀高相國四十多年的藝術歷程,我發現,從萌芽狀態到今日探索,是一個完整的過程,一路走來,盡管坎坷卻陽光燦爛。可以說,高相國的藝術,是一個探索、追求和創新的歷程,盡管艱難曲折,卻一路高歌猛進。
當今中國畫壇熱鬧非凡,“名家”遍地開花,“精品”處處皆是,可謂“群星”斗艷。而高相國的山水藝術,是在擺脫傳統束縛和大膽求新的疾風暴雨中走向新的開始,并給我們以深刻的啟示。在我看來,中國繪畫史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部文人畫發展的歷史,從唐宋到明清的杰出藝術家,幾乎都是有學問的人,王維、蘇東坡、董其昌、“四王”以及齊白石和黃賓虹無一例外。從這個角度說,我們研究高相國,就必須將他放在中國山水畫發展與變革的歷史背景中展開,因為,他的作品中體現出一個勇于探索的藝術家的睿智與膽魄。這一點,不是所有藝術家都具備的。改革開放三十年,由于認識的偏見、視野的局限,以及思想和觀念的滯后,導致許多畫家成為十足的匠人,甚至是三流四流的江湖藝人。
高相國不同,他的山水藝術蘊藏著隨處可見的文化資源,文學、哲學、美學、宗教甚至其他學科,都成為他尋找出路時補充體力的重要營養。所以,高相國視野上的拓展,與他在上述的資源比較中獲得了理性的判斷。還有,對中國民間美術的了解和認識以及廣收博納,都在他過去幾十年的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埋下了種子,尤其是黃土地與黑土地,使他在追求人格完美和獨立、藝術探索和創新,以及文化和精神上,都成為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在長期的積累中,獲得了精神的自由和審美的自信。
應該說,中國山水畫走的是一條精英文化之路,如果文化上出現貧血,必然導致藝術品質的蒼白。在高相國的探索中,我感受到藝術家的思考遠大于動筆。這一點,對于一位具有探索精神和創新勇氣的藝術家來說,是何等重要,因為新時代要求所有的藝術家必須有新的文化學養。
高相國的山水藝術展現出一個當代藝術家悲壯慷慨、激揚蹈厲的陽剛氣概,還有玄遠、放任、曠達與超越的意蘊。在藝術家的筆下,技藝已經轉換為一種表現手段,轉換成一種藝術語言,他以大筆無痕抒寫大象無形、大美無顏、大音希聲之境界,展現出一種天地人化一、道物我通悟的境象精神,這樣的創作狀態,是一種理性的超越,也是大道境界的可視展現。所有這一切,得益于高相國的大筆墨、大胸襟、大氣概和大修養,這是一種真真切切的大道精神。
藝術史需要不斷地進行鏈接,否則就會出現斷裂。而鏈接需要長度和寬度,如果一部藝術史只有其長度而缺少寬度,久之必將枯竭。高相國敏銳地發現了這個問題,因此他在自己的探索與實踐中,必須擺脫傳統的約束和捆綁。需要強調的是,一個有歷史責任感的藝術家,不是傳統的守望者,而是一個時代的開拓者和創造者。我們從他的山水藝術中很容易發現,他沒有滿足現有文房四寶所提供的便利,而是在宣紙上不斷探索實踐,直接摸索出屬于自己的方式,最大能量地將筆、墨的自由發揮到極限。這其中有偶然也有控制,由此形成了獨特的視覺效果和明顯的個人風格。
筆墨是中國畫的底線,也是中國畫發展中最大的障礙。高相國沒有被傳統筆墨捆綁,他總是以簡約而概括的線游走于宣紙,每一根線條、每一筆頓挫都變成藝術家對世界的感受,變成藝術家生命的印痕,靈動中透露出堅強不屈的生命張力。筆和墨,在高相國的畫面上不再是單一的結構或組成畫面的因素,而是生命的載體,這一點,就與傳統“文人畫”和那些所謂的“新文人畫”拉開了距離。
高相國非常注重山水畫語境的拓展。以往,我們崇尚山水畫的逸趣,將逸品當作山水畫的最高境界,高相國的作品自覺取舍了宋元以來繁多的山水畫皴法程式,他是在以一種反傳統的方式在呈現自己心中的山水。他用生命寫出的山水,不僅創造出新的山水圖式,重要的是,打破了以往山水畫的敘事性和逃逸現實的倫理意義。這是藝術家高相國在探索和追求上達到的高度。
欣賞好的山水作品,獲得的心理滿足和愉悅難以言表。“至美”之境乃美中太極,“其大無外,其小無內”,高相國山水藝術的超拔、冷逸和蒼美,是他生命體驗的外化。寫到此,我想起了《金剛經》中有這樣一段話:“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這幾句話,可以看作是藝術家高相國對待藝術態度的徹底表白。“無人相”即作品無他人之痕跡,“無眾生相”即作品不落入藝術尋常的習見或俗套中,“無壽者相”即作品不以樣式追攀古人便自視高古。在這當中,“無我相”則是最具氣魄和膽量的根本話語。我想說的是,高相國以其繪畫“無我相”切入山水創作之本質,實有蹄簽擯落的意味。他從“觀古,觀土,觀洋,觀我”的方式入手,出手而為“不古,不土,不洋,不我”之境界。
在當今物質至上、功利盛行的社會環境中,高相國的作品不屬于時尚之類,不如那些批量生產的“中國符號”在市場上大行其道,但高相國的作品自有其“道”。我所說的“道”,就是人的生存尊嚴,包括對自然的親切和對生命的敬畏。尤其是“法道自然”,是藝術家對自然的體驗過程中生發的廣闊、靈動、生生不息的精神空間——對于高相國,這是一種永無止境的“綿延”和“生命沖動”,更是對有限空間的突破與超越。高相國的山水藝術,是領略了“道法自然”之后的創造,因此畫面上就有了生命的境界,同時,也創造了具有歷史感的世界。正如楊天佑先生對他的評價:“在繪畫中,打動人的力量并不是精確地復制自然的形態,而是畫家對大自然深沉的感受。”
今天,我們應該對“當代水墨”這個詞匯有一個正確的理解和認識。“當代”在這里是一種變化,是一種新的表現,它契合于當今的視覺感受——甚至,還有一個參照的水墨歷史語境。如果沒有后一種關系,我們無法言說“當代水墨”。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需要將傳統水墨放在“當代”語境中思考、思辨和質疑。真正的當代水墨是一種精神象征,是一種生命意志的頑強表現——它是對所有不能忍受的文化保守、文化偏見和文化惡俗的抵抗。當代水墨就是對水墨頑疾進行一場觀念的革命和媒介的再造,最后,以水墨的陌生化來完成水墨在當代的壯行與革命。從這個層面上說,高相國山水藝術具有強烈的當代意識,對傳統的質疑與再思考,強調生命的感受與再創造,對社會變革的真實記錄,尤其是藝術家通過作品捍衛藝術自身的獨立性和批判性,挑戰傳統審美習俗,體現了藝術家的精神和勇氣——我以為,這就是當代藝術的本質。
無論是李小山的“窮途末路”,還是吳冠中的“筆墨等于零”,我們終于走出了水墨是一個畫種的狹隘、封閉的死路,開始了一種水墨既是一種文化,又是一種媒介的全新發展。這其中,高相國以自身的實踐和思考完成了從“水墨畫”到“水墨”的認識轉變及觀念轉變,從而進入當代藝術的表現范疇和創新的高度。
最后我想說的是,藝術家高相國的水墨揭示了現代文明的痕跡,涵蓋了中國元素和符號以及語言的選擇和推進,在黑白交響中揭示了音樂般的變調與置換——這是他的風格與創造。文化的生長、發展和碰撞,最后成為一種新的語言,重要的是,它重新定義了感知,并重新探尋自我存在的本質,那就是永遠關注當下,努力重建揭示世界的真實。
作者:劉淳,資深美術批評家、藝術策展人。
編輯:趙際灤chubanjiluan@sina.com
讀書論道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