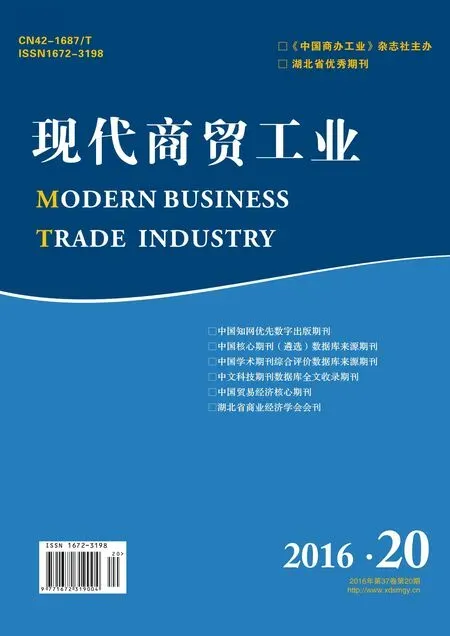制度理論視角下企業國際化優勢詮釋
徐明霞
(鄭州輕工業學院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00)
1 引言
企業國際化擴張的優勢來源是什么?這是國際商務領域和企業戰略管理領域一直關注的問題。以發達國家的企業為研究對象,企業國際化的優勢來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8世紀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的“絕對優勢說”以及19世紀大衛·李嘉圖的“比較優勢說”,之后先后出現了壟斷優勢理論、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內部化理論、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范式)等。隨著發展中國家企業國際化進程的加快,國際商務領域以發展中國家的企業為研究對象繼續探索企業國際化的優勢來源,又產生了小規模技術理論、局部技術變動理論、技術創新產業升級理論。以上所有用以解釋企業國際化優勢的理論中,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即OLI范式成為主流,是解釋企業國際化價值增值活動的有力理論工具。
然而,隨著新興經濟體國家如中國、印度的企業國際化進程越來越快,學術界針對“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的國際化優勢是什么?”這一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部分學者認為OLI范式能夠解釋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國際化的優勢(Lau et al.,2010;Zhang et al.,2010),還有一部分學者認為需要新的或至少擴展現有理論來解釋其優勢來源(Alon et al.,2011;Peng,2012)。制度理論學派的學者們認為,制度理論對制度轉型條件下的企業行為有著獨特的解釋能力和預測能力,尤其對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的國際化行為有著重要作用。因此,本文嘗試從制度理論的視角剖析企業國際化尤其是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的國際化優勢問題,預期有新的發現和貢獻。
2 制度理論
企業戰略管理領域和國際商務領域引入制度理論,主要是用以分析制度因素對企業行為的影響,即制度環境與企業組織的互動關系(Peng,2008)。從宏觀層面來看,制度理論主要用以分析國家層面的制度因素對本國企業和外來跨國公司的行為影響;而從微觀層面來看,制度理論主要用以解釋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子公司如何獲取母公司內部的合法性以及東道國制度環境下的合法性。
Scott從社會學視角定義了制度,將制度分為管制制度、規范制度和認知制度(Scott,2001)。管制制度來源于具有法律權威的法律法規,以及政策制定機構(國家和地方政府)所頒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等;規范制度包含類似于規則、規定、準則和行為規范的因素,既包括社會規范,也包括各種職業標準或專業標準(DiMaggio et al.,1983);認知制度來源于個體或集體對外部真實世界的認知和理解,也構成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DiMaggio,Powell,1991)。North從經濟學視角對制度進行了定義,認為制度是經濟社會的游戲規則,是為了組織人際互動而人為設計的約束條件(North,1990)。制度可以分為正式制度(憲法、法律和規則等)和非正式制度(行為規范、慣例、行為準則等),這些制度構成完整的制度體系,共同形成了一定的“游戲規則”,組織必須遵循這些“合法性”,以追求和實現資源配置目標(North,1994;2005)。社會學和經濟學對制度的定義本質上是一致的,管制制度相似于正式制度,規范和認知制度與非正式制度相對應。基于制度理論的視角,現有研究多數探討了“合法性”機制對企業行為的影響。為了尋求“合法性”,組織會出現趨同性,甚至會出現“制度化”的組織(Meyer et al.,1977)。導致組織趨同性與組織“制度化”的機制有三種:強制機制、模仿機制和社會規范機制。當企業的行為符合內外部制度環境的“合法性”時,企業即擁有“合法性”優勢,也可以形成企業國際化優勢的重要來源。
3 制度理論對企業國際化優勢的解釋
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的國際化行為受到制度因素的影響較大,包括母國和東道國的各種激勵體制和法律制度影響。針對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的國際化行為,Dunning對OLI范式進行了修正,提出將制度理論融入OLI范式的構想(Dunning,2008)。按照這種理論邏輯,結合制度理論的內涵,下文將詳細闡述制度理論如何實現對企業國際化優勢的解釋。
3.1 制度所有權優勢
制度所有權優勢(Oi)即企業所擁有的制度優勢,包括內部合法性和外部合法性制度優勢。內部合法性制度優勢指企業內部的規章制度和管理機制、信念、價值觀等,也稱“企業文化”;外部合法性制度優勢指企業所嵌入的外部制度環境(母國和東道國),也包括社會信念、價值觀念等。制度所有權優勢可以給企業帶來競爭優勢,且可以從母國、東道國兩個角度來解釋企業的國際化優勢。
制度所有權優勢之所以能夠形成企業的國際化優勢,是由于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可轉移性和“外溢性”。例如,企業一旦在一個國家獲取“合法性”,便可以把這種企業實踐復制至其他國家:當企業內部形成的組織架構、管理模式、激勵機制、專業實踐、質量管理、環境管理等構成自身的競爭優勢時,企業會把這種優勢復制至其在國外的子公司或分支機構,同時保證了企業集團內部的合法性。當企業在與母國的制度環境博弈中形成外部合法性時,即企業行為符合政府頒布的法律法規、行業規范以及社會認知時,也會形成企業的競爭優勢,企業在進入國外市場經營時便會把在母國獲取的這種外部合法性機制應用到異國的制度環境中,以獲得在東道國的制度優勢。
3.2 制度區位優勢
制度區位優勢(Li)包括某一國家或地區在財產權、法律規則、社會基礎設施等正式制度因素方面具有的優勢,以及在社會資本(如社會公民之間的合作關系網絡、公民規范)等非正式制度方面的優勢。
企業國際化的制度區位優勢依賴于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時所選擇的東道國或地區的要素優勢。Rodrik等把某一國家或地區的區位優勢分為三類:一是地理因素,如氣候、自然資源和交通運輸成本等;二是經濟模式和開放程度;三是制度因素,如法律規則、激勵機制、財產權、社會基礎設施等,其中制度因素的影響高于其它兩個方面(Rodrik et al.,2002)。當企業進入東道國經營時,企業的制度區位優勢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東道國的各種法律法規、規則、慣例等正式制度環境相當完善,且政府頒布的各種法律和優惠政策對外來企業形成引力,這些正式制度能夠正向影響外來企業的產品范圍和地域范圍,使得外來企業形成在這一國家或地區的獨特制度區位優勢;二是企業的運營管理符合東道國的非正式制度,如企業形象和社會責任吻合東道國的社會道德規范,企業的各種宣傳推廣活動能夠被東道國的民族傳統,不與當地的宗教信仰沖突,不觸及當地的民間團體利益等,企業獲得來自于非正式制度的“合法性”。當企業主動利用制度環境獲得東道國制度優勢時,就具備了在這一國家或地區經營的制度區位優勢。
3.3 制度內部化優勢
制度內部化優勢(Ii)主要來源于企業的內部合法性機制,指企業內部的各種契約、關系網絡等形成的正式制度約束所帶來的優勢,以及內部組織成員之間的信任關系、員工內疚感、羞恥感等非正式制度約束所帶來的優勢。
企業的制度內部化優勢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企業內部各種契約、關系網絡能夠形成較好的約束機制,使得企業通過內部協調來獲得的中間產品、信息、技術、營銷技術的交易成本和協調成本較低,低于通過外部市場獲得時,企業就會利用這種制度內部化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建立分支機構將這些產品、信息、技術內部化,而非市場協議來獲得。二是企業內部組織成員之間的信任關系、員工內疚感、羞恥感等非正式制度的約束機制給企業帶來的制度內部化優勢,例如,即便是企業內部的信任機制使得委托代理人的成本低于外部市場交易的成本時,代理人也會因這種信任關系而繼續留任企業,給企業創造效益。
制度理論對企業國際化優勢的解釋,或者說制度理論對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的有益補充見表1,制度理論融入OLI范式增強了OLI范式的解釋力度和范圍,能夠較好地解釋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企業國際化行為。

表1 制度理論對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的補充
資料來源:作者結合Dunning和Lundan(2008)的研究整理。
4 制度理論對企業國際化優勢解釋的研究展望
雖然將制度理論引入OLI范式是重要的理論貢獻,但是在探討企業國際化優勢的來源時,圍繞制度因素如何融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還存在一些可以討論的問題。
第一,制度所有權優勢(Oi)是否歸屬于資產所有權優勢(Oa)的問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企業所擁有的“合法性”制度優勢,也是企業的一種重要資產,因為制度所有權優勢(Oi)中企業特定的信念、價值觀、規章制度機制等本身就是企業的資產組成部分。有沒有必要將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中的所有權優勢(O)拆分出制度所有權優勢(Oi)仍然需要進一步探討。
第二,制度所有權優勢(Oi)的可轉移性問題。制度所有權優勢(Oi)中的制度實踐(內部“合法性”優勢),包括鑲嵌于組織內部的組織架構、管理模式、激勵機制、工作實踐、質量管理以及環境管理等都可以實現轉移。但是企業所擁有的符合母國制度環境要求(外部“合法性”)的實踐卻是不可以轉移的。關于制度所有權優勢(Oi)的可轉移性問題也需要進一步地研究。
第三,將制度理論引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在解釋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時,應注意必須要結合國家特定優勢來分析。國家特定優勢也是企業國際化的重要優勢來源,但是由于國家特定優勢的難以轉移性,大多數文獻在討論企業國際化優勢的來源時僅重點強調了企業特定優勢。例如,中國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都很好地運用了要素優勢、相關配套產業優勢等國家特定優勢,并且能夠在國家特定優勢的基礎上逐步建立起企業特定優勢。將國家特定優勢與加入制度因素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一起來解釋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將會有重要的研究意義和發現。
5 結語
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企業國際化問題已成為國際商務理論與戰略管理領域的重要研究議題,但是關于新興經濟體國家企業的國際化優勢來源問題目前的研究較少,部分學者已嘗試從國家特定優勢進行解釋,或者是從國家層面的制度因素進行解釋。本文在解釋制度理論的基礎上,將制度理論融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OLI),并進行了詳細的闡述和解析,但圍繞制度因素如何融入國際生產折衷理論需要進一步探討和研究,以期較好的完善和補充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同時挖掘更有意義的研究發現。
[1] Lau,C.,Ngo,H.,Yiu,D.W.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of Chinese firms[J].Chinese Management Studies,2010,4(3):258-272.
[2] Zhang.J.,Ebbers,H.Why half of China’s overseas acquisitions could not be completed[J].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2010,39(2):101-131.
[3] Alon,I.,Child,J.,Li,S.,McIntyre,J.R.Globalization of Chinese firms:theoretical universalism or particularism[J].Management Organization Review,2011,7(2):191-200.
[4] Peng,M.W.The global strategy of emerging multinationals from China[J].Global Strategy Journal,2012,2(2):97-107.
[5] Peng,M.W.,Wang,D.Y.L., Jiang,Y.An institution-based view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rategy:a focus on emerging economies[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2008,(39):920-936.
[6] DiMaggio,Paul J.,Walter W. Powell.The iron cage revisited: Institutional iso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3,48(2):147-160.
[7] North D.C.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change[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8] Meyer,John W.,Brian Rowan.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77,83(2):340-363.
[9] Dunning J.H.,Lundan S. M..Institutions and the OLI paradigm of th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J].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8,(25):573-593.
[10] Scott W. R.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2nd ed.)[M].CA:Sage Publications,2001.
[11] 單寶.中國企業跨國并購的策略選擇及其啟示-基于中海油跨國并購案例的研究[J].寧夏社會科學,2006(4):3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