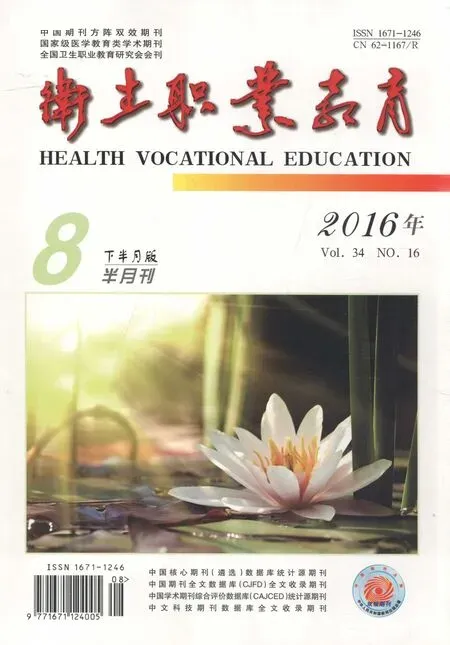轉化醫學在肝膽外科研究生臨床教學中的應用
隋承軍,李巧梅,張敏峰,楊甲梅
(第二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上海 200438)
轉化醫學在肝膽外科研究生臨床教學中的應用
隋承軍,李巧梅,張敏峰,楊甲梅
(第二軍醫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院,上海 200438)
轉化醫學是連接基礎與臨床的橋梁,其興起和發展可極大地推動肝膽外科的發展。肝膽外科研究生是未來轉化醫學的工作者,目前的研究生臨床教學模式已不能滿足轉化醫學的要求。在臨床教學中,通過引用肝膽外科典型的轉化醫學實例,采用以病例為引導聯合以問題為基礎的模式,加強對研究生論文寫作能力的培養,讓研究生積極參與標本庫的建立等,強化肝膽外科轉化醫學的理念,有助于肝膽外科研究生在工作中更好地理解并積極實踐轉化醫學,使更多的基礎研究成果快速有效地向臨床轉化,造福于人類。
轉化醫學;肝膽外科;臨床教學;研究生
轉化醫學(translational medicine)是近年來醫學研究中出現的新概念,指快速有效地將生物醫學基礎研究的最新成果轉向臨床應用,并及時把臨床應用的實際情況再反饋給實驗室,以此完善相關的基礎研究并進一步開展新研究的雙向過程[1]。其核心是打破基礎醫學和臨床醫學之間的屏障,使基礎研究成果能及時為臨床應用,而臨床實踐中急需解決的問題能及時反饋給基礎研究者,引導其研究方向,最終使患者受益[2]。轉化醫學的興起和發展加速了外科臨床的進程,在肝膽外科領域,諸如分子靶向治療、腹腔鏡技術及醫學影像技術等的應用,都極大地推動了肝膽外科的發展。在轉化醫學時代,如何更好地對臨床研究生進行培養,使其更加適應未來的醫學模式,需要教學醫院的臨床教師進行改革和創新。本文對如何在肝膽外科臨床教學中應用轉化醫學及促進肝膽外科創新型后備人才的培養進行了探討,現介紹如下。
1 轉化醫學的概念及發展現狀
轉化醫學的概念最早出現于1996年《Lancet》雜志上的一篇論文[3],又稱為轉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是指從實驗室到臨床和從臨床到實驗室的雙向研究體系,其內容包括將基礎醫學取得的成就應用于臨床疾病的診治和預防以及根據來自臨床醫師的觀點和假設設計基礎研究實驗并加以檢測和驗證。2003年Zerhouni在《NIH Roadmap》中正式明確了轉化醫學的概念[4],其核心是將醫學生物學基礎研究成果迅速有效地轉化為可在臨床實際應用的理論、技術、方法和藥物。轉化醫學成為生物醫學領域發展的新方向,美國及歐洲一些發達國家紛紛制訂了轉化醫學發展戰略,設立轉化醫學基金,建立轉化醫學研究中心,開展轉化醫學研究模式[5-7]。
我國政府機構、科研院所、大學、醫院以及廣大科研工作者對轉化醫學也高度重視。2007年,國家衛生部提出了“健康中國2020”戰略規劃,提出了包括基礎、臨床、預防等10個轉化整合,設立生物醫學技術臨床轉化專項基金,成立多家臨床醫學轉化中心,開展重大疾病轉化醫學研究,啟動了生物樣本庫建設[8-9]。我校于2012年4月與中科院聯手,建立了第二軍醫大學轉化醫學研究院,在人才培養、轉化醫學研究等方面開展深入合作,努力打造符合生物醫藥產業發展方向的轉化醫學研究平臺,以促進生物醫藥產業的發展。我國的轉化醫學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這就需要大量的轉化醫學人才作為支撐,因此轉化醫學人才的培養和醫學教學模式的改革勢在必行。
2 轉化醫學與肝膽外科的聯系
肝膽外科的發展離不開基礎科學研究的新理論、新成果,而轉化醫學就是要使基礎科學成果能及時為肝膽外科臨床所用,同時將臨床實踐中需要解決的問題及時反饋,從而引導基礎研究。在肝臟外科中,轉化醫學研究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成果:如對肝臟解剖學的深入研究大大促進了肝臟外科的發展。肝臟結構復雜,血供豐富,曾一度被認為是腹部外科的一大手術“禁區”。我院的吳孟超院士在我國最早對肝臟解剖進行了深入研究,根據肝臟鑄型標本,提出了肝臟的功能性劃分,即“五葉四段法”,用于指導臨床肝臟切除,使肝臟手術成為常規手術,并且使活體肝移植特別是肝段移植成為可能。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在分子水平上對腫瘤病因學理解的加深,在肝癌治療領域出現了索拉非尼這種多靶點的信號轉導抑制劑,既可阻斷Raf激酶信號傳導通路而直接抑制腫瘤細胞增殖,又可抑制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而阻斷腫瘤新生血管的生成,間接抑制腫瘤生長。索拉非尼的發現經歷了從基礎到臨床的過程,通過基礎研究、藥物開發和醫學實踐三者的整合,為其治療肝癌提供了有力證據。醫學影像學的迅速發展使得肝臟外科醫生具有了更多的檢查、治療手段,如術前可以通過三維CT掃描顯示病變的立體結構,通過CT血管造影(CTA)展現肝臟血管系統的走行與病變部位的關系,做到更加精準地切除肝臟,大大降低了手術風險,減少了出血。而PET-CT的出現,則可使醫生在術前就能明確腫瘤的良惡性以及有無其他部位的轉移,為手術方式的選擇提供了更加直接的依據。醫療器械的發展也使肝臟外科手術變得更加安全,如水刀、超聲刀(CUSA)、結扎束高能電刀、無血解剖刀等外科器械的發明,大大減少了手術的出血量;最新的達芬奇手術機器人的出現,則使肝膽外科手術變得更加精準及安全。以上這些從基礎研究到臨床的轉化,很好地促進和加快了肝臟外科研究向更高水平邁進,實現新的飛躍。
3 將轉化醫學理念引入肝膽外科研究生臨床教學中的必要性
3.1肝膽外科研究生是未來的轉化醫學工作者
肝膽外科涉及的基礎和臨床知識范圍非常廣,基礎科研人員往往缺乏臨床專業知識,而臨床肝膽外科醫生也對基礎科研缺乏了解。基礎科研人員不重視研究成果解決實際問題的可行性;而臨床醫生不關心最新的科研進展,只滿足于臨床看病,這種實驗與臨床脫節的現象很普遍。因此,培養肝膽外科研究生成為未來轉化醫學工作者對于肝膽外科的發展有著關鍵性的作用。
3.2有利于整合資源,以建立肝膽外科轉化醫學研究平臺
通過臨床工作建立并完善臨床病例、標本數據庫,整合患者疾病危險因素、臨床診斷、生存和預后等臨床資料,建立具有完整患者資料的開放式轉化醫學研究平臺。利用這一平臺,能夠對實驗室發現的和運用生物信息學技術發現的生物標志物進行快速鑒定和評估,真正實現轉化醫學的目的。肝膽外科領域對肝癌及膽管癌的研究,只有整合生物技術、計算機科學、生物信息學以及臨床外科學等多學科知識,才能揭示環境、生活方式、遺傳等因素對惡性腫瘤的影響。從研究生進入臨床開始,就對其強化轉化醫學的理念,可使其在未來的工作中將臨床資料的收集、整理貫穿整個職業生涯。
3.3有利于提高科研基金的利用率
目前,研究生在進行科研選題時主要是以導師的基金項目為主,這些項目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和實用性。對研究生強化轉化醫學的理念,可使其在選題時更多地考慮到研究成果是否有利于轉化,從而被臨床所用,以解決實際問題,而不是單純地為了實驗而實驗、為了發表文章而做實驗,不考慮其實際的應用價值。這樣有利于提高科研基金的利用價值,并且能鼓勵科研人員和臨床外科醫生進行雙向交流,共同承擔轉化醫學相關課題項目。我國人口眾多,臨床病例資料豐富,如果將這些資料優勢轉化為服務患者的優勢,那么轉化醫學的成果必將成為解決人民健康問題的有效方法。
4 轉化醫學在肝膽外科研究生臨床教學中的具體實施
4.1研究生導師自身需要強化轉化醫學的理念
對研究生導師而言,實現轉化醫學模式必須改變傳統的臨床科研思維方法,應及時掌握發展迅速的高新技術,并指導研究生將其融入到研究項目中。在教學工作中,研究生導師應堅持基礎研究與臨床工作相結合,從臨床反饋中發現問題、提煉課題,以尋找疾病診斷、治療的新方法。研究生導師需要學會熟練應用互聯網平臺及資源,并指導學生使用醫學文獻數據庫,通過檢索網絡信息資源、查找現代醫學知識及現代科學技術手段,掌握基礎研究與臨床實際問題相結合的最新進展。
4.2在教學中引用肝膽外科典型的轉化醫學實例
在肝膽外科診治技術的發展中,轉化醫學發揮了重要作用。在研究生的臨床教學中,帶教教師應增加肝膽外科疾病診斷與治療方面關于轉化醫學的內容,培養學生的轉化醫學意識。例如肝癌的早期診斷一直是肝臟疾病診斷中的重點和難點,效率不高。研究發現,腫瘤發生發展的過程中自身會表達或產生特異性分子,在疾病早期,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篩選、鑒定,最終發展為診斷試劑并用于腫瘤的早期篩查、臨床診斷、療效評估和預后判斷。腫瘤分子標記物的研究與轉化則是當代轉化醫學的重要體現,血清甲胎蛋白(AFP)是世界上應用最成功的肝癌診斷標記物,但由于AFP的敏感度和特異度并不是很理想(分別為41%~65%和80%~94%),從而極大地限制了AFP的應用。以親和層析為原理,可以從總AFP中分離出肝癌特異性甲胎蛋白(AFP-L3)。研究發現,AFP-L3只能由肝癌細胞產生,占總AFP的10%左右,其定量臨床資料顯示,AFP-L3對肝癌的特異度>95%,若AFP-L3測得值占總AFP的10%以上,就可以考慮惡變可能,因此臨床上可以將AFP-L3作為肝癌鑒別診斷指標。磷脂酰肌醇蛋白聚糖-3(GPC-3)是一種癌胚抗原,因其能在早期肝癌組織中檢測到且特異性高表達而備受關注。免疫組化方法檢測顯示,肝癌中GPC-3敏感度為72%,特異度達100%[10]。并且研究發現,GPC-3與AFP無明顯相關性(P>0.05),二者聯合應用,檢測肝癌的敏感度可達72%,因此將GPC-3作為AFP的補充,會大幅度提高早期肝癌診斷的準確率。人異常凝血酶原(DCP)又稱維生素K缺乏或拮抗劑Ⅱ誘導的蛋白(PIVKA-Ⅱ),在肝臟合成后釋放入血,生物學上不具凝血酶活性。Liebman等研究者[11]最早于1984年發現,PIVKA-Ⅱ在90%的肝癌患者中升高,且具有較高的診斷特異性。PIVKA-Ⅱ產生機制可能與患者肝臟維生素K代謝異常、γ-羧基凝血酶原轉錄后表達異常和過多的凝血酶原前體產生有關[12]。AFP主要來源于胎兒肝細胞,當成人肝細胞發生癌變后,部分肝細胞會恢復產生這種蛋白的能力。PIVKA-Ⅱ和AFP二者的產生途徑不同,兩者在血清中的含量是相對獨立的,因此,分別測定有助于肝癌的診斷,特別是聯合檢測可提高肝癌檢出的敏感度。肝癌分子診斷標志物的不斷完善就是“從基礎到臨床”,在臨床上發現不足,再回到基礎研究的典型轉化醫學案例。
4.3臨床教學多采用以病例為引導聯合以問題為基礎的模式
以病例為引導(CBS)聯合以問題為基礎(PBL)的模式要求以學生為主體、以問題為中心,臨床教師通過真實病例對學生進行引導和啟示,讓學生將所學理論知識應用于臨床實踐中,帶著問題去問病史、查體、查閱資料和分析思考,找出診治中的問題并尋找解決方法。這樣可以充分調動學生主動學習的積極性,對學生的臨床綜合能力和創新思維具有促進作用。例如,通過對臨床上不能明確診斷是否為肝癌病例的具體分析,可以引導學生對肝癌的診斷方法,包括腫瘤標志物、增強CT、MRI、MRCP、PET-CT、組織活檢等的全面認識,學生自己可進一步去查找每種方法的具體應用,在下次對類似病例進行討論時,教師可以根據學生掌握的情況來講解每種方法的優缺點和存在的問題,加深學生的印象。在臨床教學中,提出臨床急需解決的問題讓學生深入思考,啟發、鼓勵和指導學生檢索相關文獻資料,可以培養學生逐步形成轉化醫學理念及行為模式。
4.4加強對研究生論文寫作能力的培養
在轉化醫學理念指導下,研究生在臨床發現問題,通過設計課題進而解決問題,最終的研究成果要以論文的形式發表出來。因此,論文寫作能力也是將研究生培養成為轉化醫學人才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導師應在研究生對實驗原始數據進行整理分析時便對其進行指導,結合臨床實際展開討論,盡早發現遺漏的重要數據,及時收集補全。要對論文反復修改,爭取使研究生的論文可以發表在SCI收錄的期刊上。在畢業答辯之前,組織科室的專家、科研人員擔任評委,讓研究生進行預答辯,進一步查漏補缺,提高研究生的答辯通過率。在此過程中,研究生的思維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得到了鍛煉,逐漸具備了較高的學術論文寫作能力。
4.5讓研究生積極參與臨床病例資料和標本庫的建立工作
人類基因組計劃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對疾病機制的研究,發現了大量與疾病診斷、治療相關的候選基因和蛋白,這些都離不開標本數據庫的建立。轉化醫學研究平臺順利運行的重要條件同樣也是擁有充足的標本資源。這些資源包括腫瘤及癌旁組織、血清、血漿、尿液以及石蠟包埋后的組織蠟塊,每一種標本都需要建立專門的標本庫,實現專人管理。研究生在臨床工作和學習中,可參與收集臨床病例和標本數據庫資料,包括完整的病史、輔助檢查、治療方式和出院后隨訪等。資料和數據庫可隨時提供符合科研設計需要的標本,實現病例資料、標本庫等信息的互通,這對于篩選腫瘤標志物、治療和預后評估有著重要意義。我院在肝癌標本庫的建立方面已經進行了多年,目前已經建立了世界最大的肝癌標本庫,可為肝癌領域的轉化醫學研究提供大量的標本。在標本庫的建立過程中,研究生也積極參與其中,做了大量的貢獻。
5 結語
轉化醫學已經成為醫學研究領域一個新的關注點,作為一種新理念,轉化醫學在基礎研究和臨床實踐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同時也對醫學教育和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轉化醫學的實踐已經使肝膽外科領域獲得了巨大的發展,但肝臟疾病(特別是肝硬化、肝癌等)仍是人類健康的巨大威脅,在肝膽外科研究生的臨床教學中強化轉化醫學的概念,有助于這些未來的醫學人才在工作中更好地理解并積極實踐轉化醫學的理念,使更多的基礎研究成果快速有效地向臨床轉化,從而造福于人類。
[1]Wehling M.Translational medicine:science or wishful thinking?[J].J Transl Med,2008,6(1):31-34.
[2]洪琪,郭進,劉媛,等.轉化醫學:新世紀醫學發展新動力[J].醫學教育探索,2009,8(3):339-341.
[3]Geraghty J.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J]. Lancet,1996,348(9025):422.
[4]Zerhouni E.The NIH Roadmap[J].Science,2003(302):63-72.
[5]EditoriaI.Human capital in translational research[J].Nat Rev Drug Discov,2008,7(6):461.
[6]Wadman M.Harvard turns to matchmaking to speed translational research[J].Nat med,2008,14(7):697.
[7]Ablin RJ,ZengYX.The excellence i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award 2006-07[J].J Transl Med,2007(5):40.
[8]張鵬,秦嶺.轉化醫學:基礎醫學與臨床醫學實踐的橋梁[J].實用醫學雜志,2010,26(18):3277-3279.
[9]徐幻,劉玉秀,楊國斌,等.轉化醫學:從理念到實踐[J].中華全科醫學,2010,13(8):2536-2538.
[10]Wang XY,Degos F,Dabois S,et al.Glypican-3 expression in hepatoce-Hular tumors:diagnostic value for preneoplastic lesions and hepatocelular carcinomas[J].Human Parhol,2006,37(11):1435-1441.
[11]Liebman HA,Furie BC,Tong MJ,et al.Des-gamma-carboxy(abnormal)prothrombin as a serum marker of primary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J].N Engl J Med,1984,310(22):1427-1431.
[12]Inagaki Tang,Makuuchi M.Clinical and molecular insights into the hepatocellular carcinoma tumour marker des-y-carboxyprothrombin[J].Liver Int,2011,31(1):22-35.■
G420
A
1671-1246(2016)16-0007-04
上海市科委醫學引導項目(134119a7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