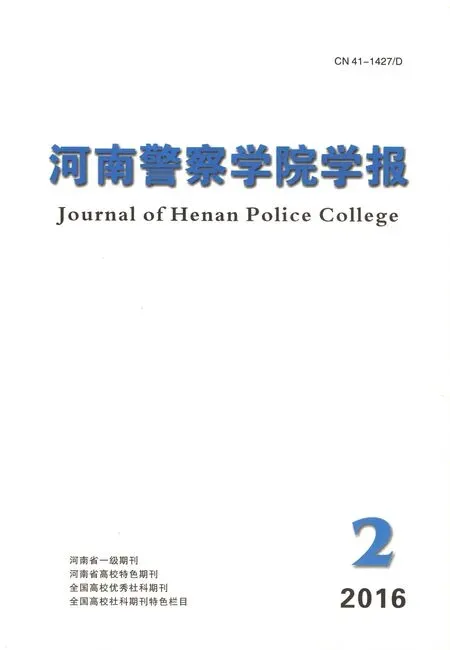主觀惡性新界說
李永升,馮文杰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重慶401120)
主觀惡性新界說
李永升,馮文杰
(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重慶401120)
近現代刑法學的發展史是一部苦苦追尋貫通犯罪與刑罰合理聯系的探尋史,行為主義刑法學派、行為人主義刑法學派、人格主義刑法學派的界說均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在靜止的犯罪與變化的刑罰之間,必然有一個呈時空變化狀的因素方能將二者合理貫通始終,該任務的完成者不是靜止著的客觀罪行,也不是靜止著的主觀罪過,更不是隸屬于心理學概念上的虛無縹緲的人格態度,以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蔑視與對抗態度作為自身內核的主觀惡性成為當仁不讓的中介載體。這個主觀惡性堅持由行為作為其征表的可靠載體,犯罪行為成為其進入刑法學評價范圍的絕對牽引力,而罪前、罪后可以表明犯罪人主觀惡性輕重程度的因素也依附于主觀惡性進入刑法學的評價范圍。
刑法學派;主觀惡性;主觀罪過;人身危險性;社會危害性
一、問題的提出
摒棄以主觀歸罪與罪刑擅斷為特征的中世紀刑法而弘揚行為主義刑法的客觀主義刑法學派在刑法學的發展史上大放異彩,“無行為則無犯罪,無行為則無刑罰”是其立足之本。深受實證主義思潮影響的主觀主義刑法學派認識到刑罰預防犯罪作用的實現必須依托于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矯正之上,而提出注重犯罪人以及潛在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及其矯正的行為人主義刑法,“無人身危險性則無犯罪,無人身危險性則無刑罰”是其扛鼎之基。在刑罰運作的理念上,預防犯罪固然可以成為刑罰的目的,這一適應社會化及其良性發展的刑罰目的使得僅僅以公正懲罰犯罪人為刑罰目的的客觀主義刑法學派認識到其理論的不足,從而不斷吸收主觀主義刑法學派的優長點。現代刑法學奠基于客觀主義刑法學派與主觀主義刑法學派的理性發展及其對抗之上。犯罪與刑罰構成了刑法學的兩大主體,二者的關系在傳統的刑由罪使以及新近提出的罪由刑使的關系理念下仍然顯得撲朔迷離,犯罪與刑罰應該由哪一中介因素連接貫通方才可以顯示出刑法學建構的科學性與可感性,是一個令刑法學者揮之不去的問題,依附于犯罪構成的主觀惡性是這一課題的合理答案。
二、刑事責任、人格無法承載貫通犯罪與刑罰的橋梁功能
我國刑法學界通說認為在犯罪與刑罰之間起合理橋梁作用的便是刑事責任,其認為這是對包含了刑罰個別化因素的《刑法》第五條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合理闡述[1]31,只有應當受到刑罰懲罰的行為才能夠稱為犯罪行為,包含了非刑罰處罰措施的刑事責任的承擔在某些情形下,使人無法從其外在處罰方式上聯想到刑罰的承擔,進而也無法聯想到這種受到非刑罰處罰的行為確屬犯罪行為。陳忠林教授提出“主觀罪過是犯罪構成的核心”,“主觀罪過是刑事責任的唯一根據”[2],人格刑法學的強勢崛起佐證了這一學說的合理之處。將主觀罪過作為犯罪構成的核心、將主觀罪過作為刑事責任的唯一根據的主張固然有其閃耀的合理之處,但仍然無法解釋刑罰在量刑、行刑階段的具體量刑技術、減刑、假釋等制度運作法理,且主觀罪過作為一個犯罪構成的核心要件有其局限之處,至少從語義上無法被延伸到罪前、罪后的量刑情節考量之上。
總體而言,人格刑法學認為刑法規制的重點應轉向具有犯罪危險性人格的犯罪人本身,其犯罪危險性人格以實施法定犯罪行為為征表[3]。犯罪危險性人格與人身危險性都與危險性有一種天然的近親關系,在刑罰可罰根據視域下而言,二者的發展及其相互替代都是一種預測主義思維的濫觴惡果。人格在心理學家的定義中五花八門,至少不下于60種定義。心理學家從不同側面以及不同方法對人格定義作出的研究各異,有的側重于獨特性、有的側重于穩定性、有的側重于傾向性、有的側重于綜合性、有的側重于特定情境性,根本沒有一個統一性的概念界定以及重點傾向。
有學者基于人格心理學的發展提出:“犯罪行為與犯罪人格并重、以犯罪行為與犯罪人格二元因素定罪與量刑機制的刑法觀。”[4]將心理學家爭吵不休的無統一性概念界定的人格導入定罪、量刑領域只會致使“混亂的更加混亂,清晰的被混亂化而混亂化。”只有清晰地觀察人格中的哪些內容可以為刑法學的發展作出貢獻,哪些內容不宜于導入刑法學的建構中,方得以撩開人格的詭異面紗,透過其清晰的面容洗盡刑法學的鉛華。并非人格中的所有內容都具有刑法意義,人格態度而非人格才應是刑法學的關注重點。這種人格態度在陳忠林教授看來便是指,行為人對社會基本價值的敵視、蔑視、漠視的情感態度[5]。社會基本價值仍然顯得有一定的模糊性,使得我們無從捉摸什么樣的價值是社會基本價值,什么主體界定的價值才是社會基本價值,德國法西斯主義下的權威主義與社會基本價值相聯系的重大惡果不得不使我們引以為戒。總之,人格概念的模糊性與縹緲性使得其無法成為貫通犯罪與刑罰的橋梁。
三、主觀惡性概念解析
貫通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奧秘的主觀惡性的合理確切內涵是什么以及它是怎樣貫通犯罪與刑罰之間的奧秘,這些問題的合理解答不得不從對主觀惡性的歷史嬗變以及當代刑法含義的一般解析中找尋。
(一)主觀惡性的內涵嬗變解析
作為當代刑法學領域重要基本范疇的主觀惡性的含義已與其千年之前的含義大相徑庭。“惡性”一詞淵源于作為倫理學基本概念的“惡”,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首先將“惡”作為倫理學的基本概念加以闡述,其認為“沒有人有意追求邪惡的東西或者他認為是邪惡的東西,趨惡避善不是人的本性。”[6]其將“惡”在與善的對應關系中界定為對某個行為或事件的否定評價,它更多的是與人性相聯系,卻并非是對某個違背道德正義行為所作的評判。亞里士多德將惡與犯罪相聯系,其認為奸淫、謀殺、偷盜等行為本身便是惡,皆應當受到道德的譴責,皆應當負擔道德譴責的責任[7]。古羅馬法學家進一步將惡性引入刑法學中,以“自體惡”與“禁止惡”兩分理論將某些即使法律未作規定的不法行為,認定為違背倫理道德而應予譴責的行為。以主觀歸罪為特征的中世紀則將惡性在刑法學中的應用非理性化,這在基督教的格言“行為無罪、除非內心邪惡”[8]中可見一斑,致使主觀惡性的注重被當下的刑法學界作為主觀歸罪的變種。
(二)關于主觀惡性刑法內涵學說的理性解析
現代心理學已經證明故意與過失的區分成為合理的考量,案外情節成為判定行為人刑罰有無及其輕重必須考量的重要因素,行刑階段刑罰的變化更加重視早已脫離于犯罪之外的個人因素,現代刑法學的種種制度設置以及配套制度設置都證明了行為人的主觀惡性的考量不僅成為合理的厘定,而且成為必需的厘定。我國刑法學界對于主觀惡性內涵的界定大致有四種說辭,第一種觀點認為,主觀惡性是指犯罪人因其犯罪所應受到的道德譴責[9]。質言之,這種觀點將主觀惡性限定于犯罪者所應得到的道德譴責,但道德譴責的界定仍未指出主觀惡性的確切以及可以考量的內涵到底是什么。第二種觀點認為:“主觀惡性是指人對現實的破壞態度及與之相適應的行為方式上的反社會心理特征。”[10]質言之,這種觀點將主觀惡性界定為行為人因其行為所應得到的否定的心理態度評價,這種觀點將主觀惡性的界定延伸到反社會心理特征是其可取之處,但并未進一步指出反對的是什么社會的什么樣的心理特征。第三種觀點認為,主觀惡性是指行為人以其罪前、罪中、罪后的行為所表現出來的惡劣思想品質[11]。質言之,這種觀點將主觀惡性界定為惡劣思想品質,且將罪前與罪后情節也作為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輕重考量的依據,但罪前與罪后情節并不會一概加重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輕重程度,這是其定義所忽略之處。第四種觀點認為,主觀惡性的考量主要是從對社會的惡意的動機出發對犯罪行為所作出的道德評價[12]。但僅僅將主觀惡性的考量局限于對社會的惡意動機之上,與現代刑法學上刑罰有無及其輕重的考量因素不符,局限性甚為明顯。
(三)主觀惡性是犯罪人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蔑視與對抗態度
貝卡里亞認為:“罪孽的輕重取決于叵測的內心墮落的程度,除了借助啟迪之外,凡胎俗人是不可能了解它的,因而,怎么能以此作為懲罰犯罪的依據呢?”[13]中世紀刑法容易以罪刑擅斷的不當方法去考量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輕重,從而決定行為人刑罰輕重程度,這是以貝卡里亞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反對中世紀刑法的濃墨理由。值得深思的是,以行為人的主觀惡性輕重程度為依據決定刑罰的輕重程度配置是否是一個值得追求的正當、合理目標呢?毫無疑問,這是一個正當而又合理的目標,從我國刑法所確立的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可見一斑。如果因為追求正當目的的方法不當而斷然否定所追求的正當目的本身,顯然是不合理的。
人的本性決定了人注定要形成共同體[14],每一個個體的總和及其交往組成了每一個個體賴以生存與發展的社會,“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15]。質言之,社會的維持與良性發展是每一個個體生存與發展的堅強后盾,一切刑罰方式與方法的制定、適用與執行都是為了社會化的維持與良性發展。“在法和‘政府’提出的任務中,維護和平和秩序……刑罰作為法制的制裁,其發展與這項任務是密切相聯系的。”[16]依托于已然犯罪及案外情節的運用,考量出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的消長,從而在刑罰制定、適用與執行中作出有針對性的應變,都是為了準確而公正地配置犯罪人的刑罰,從而為社會化的維持與良性發展作出貢獻。主觀惡性指的是,犯罪人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蔑視與對抗態度。對于主觀惡性刑法內涵的這個界定可以合理貫通犯罪與刑罰的連接,使得固定的犯罪與順勢而變的刑罰形成一個合理的對照關系。一言以蔽之,犯罪決定刑罰的有無,即是犯罪背后凸顯的主觀惡性決定行為人應當受到應有的刑罰懲罰,罪前、罪后情節成為考量行為人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蔑視與對抗程度加重與減輕的必需因素,這也符合刑罰裁量原則的實踐運用法則。
四、主觀惡性與相關概念關系解析
(一)主觀惡性與主觀罪過關系解析
主觀罪過屬于犯罪主觀方面的重大內容,是一切犯罪構成都必然具備的主觀要件,其內容包含犯罪故意與犯罪過失[1]111。沒有主觀罪過便不構成犯罪,即使為了正當防衛權限的行使以及共同犯罪等問題的解決而構造出主觀不法與客觀不法的二元不法模式,也無法否認客觀層面的犯罪仍舊不是犯罪。犯罪行為是行為人主觀罪過(不法意圖)的展開,沒有犯罪行為的主觀罪過不應當也不能夠納入刑法學的評價視野之內,這便與主觀歸罪以及嚴格責任劃清了界限。主觀惡性代表著行為人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蔑視與對抗態度,它必然淵源于主觀罪過,但又不局限于主觀罪過。質言之,主觀惡性是主觀罪過的上位概念,主觀惡性這一含攝行為人罪前、罪中、罪后行為表現的概念呈時空變化狀,而主觀罪過只能顯現于行為人行為時的主觀心理態度。
(二)主觀惡性與人身危險性關系解析
我國刑法學界對人身危險性內涵的界定大致有三種代表性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人身危險性指的是行為人對社會造成侵害的可能性[17];第二種觀點認為,人身危險性指的是行為人初次犯罪的可能性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的統一[18];第三種觀點認為,人身危險性指的是犯罪人存在的對社會所造成的潛在威脅[19]。國內學界對人身危險性內涵的界定是在初犯可能性與再犯可能性之間徘徊,毋庸置疑,在犯罪學意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內涵與刑法學意義上的人身危險性內涵必然存在著角度不同下的界定不同。不同學科視野下以及不同學者思維下的人身危險性內涵的不同界定并不妨礙將人身危險性與主觀惡性的關系作一合理的分析。人身危險性的預測可以服務于犯罪學視野下的犯罪預防舉措的制定,但其不應當存在于刑法學領域,更不應當存在于刑罰學領域。側重于研究行為人人身危險性的新派被界定為犯罪學更為適宜,包含社會政策等犯罪預防的措施不局限于刑罰,刑罰甚至不是最好的犯罪預防措施。因此,在犯罪預防的視野下研究人身危險性以制定刑罰之外的社會政策等措施,毫無疑問是具有正當性與合理性的。
現代科學證明了某些心理傾向在某些情況下可以得到準確預測,但仍然有大量的人的心理傾向無法得到準確的預測,現代科學不應自負到可以將一個無法準確預測的人身危險性運用到刑法學中。“現代性內在地是指向未來的,它以如此方式去指向‘未來’,以至于‘未來’的形象本身成了反事實的模型。”[20]對未來的不合理預測不僅僅是對行為人定罪量刑的不公平,也是對吹噓人身危險性超級功能的絕大諷刺。在關乎公眾重大人身權利的刑罰學領域內引入一個無法準確考量的人身危險性因素,不僅是不具有正當性的,而且也是不可能的。質言之,“脫離已然行為預測‘潛在犯罪人’的預防論是對國民法秩序主體地位的否定”[21],建立在預測主義之上的人身危險性考量無法在刑罰運作中獲得正當地位。主觀惡性的程度輕重與人身危險性是一個無法一一對應的概念,從已然行為中可以推出行為人暫時的主觀惡性的程度輕重,卻無法推出人身危險性的程度輕重,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人身危險性的評估依賴于行為人實施具體犯罪行為或客觀層面的犯罪行為后的未來犯罪可能性,而主觀惡性的輕重程度評估卻是不依賴于未來行為的實施。
(三)主觀惡性與社會危害性關系解析
我國刑法學界通說將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視為犯罪的本質特征,其將社會危害性界定為行為對刑法所保護的社會關系造成或可能造成一定損害的特性,其將犯罪客體、行為的手段及其造成的結果、時間、地點、行為人的情況及其主觀因素作為社會危害性輕重程度的衡量因素[1]50。我國傳統觀點大多認為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顯現于主觀見之于客觀的犯罪的種種因素,有學者甚至于提出社會危害性包括客觀的社會危害性與主觀的社會危害性,前者指由犯罪人的犯罪行為所帶來的犯罪后果以及由此對社會造成的實際危害;后者指犯罪人主觀心理上的反社會性和再犯可能性[22]。這種觀點本不僅僅是對犯罪的誤解,也是對社會危害性本身的誤解,其脫離了犯罪的客觀與主觀界定,對于犯罪的界定必須堅持主客觀相統一,且統一于主觀的原則。再犯可能性這一人身危險性所包含的內容無法在認定社會危害性輕重程度上獲得正當地位,其預測主義的建構思維是無法與追求精確的刑法學相契合的。
犯罪行為是對犯罪人主觀惡性的表現,通過犯罪行為至少可以認定出犯罪人具有值得刑罰懲罰的主觀惡性,主觀罪過的具體確定也可以助益于犯罪人主觀惡性程度輕重的準確考量。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一種社會屬性意義上的評價,僅僅從行為的自然屬性層面無法認定行為是否為犯罪行為,必須通過社會層面的檢驗方得以認定行為的價值屬性。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行為必然具有的社會屬性,主觀罪過不同下的行為所體現的主觀惡性不同,社會危害性也不相同。一言以蔽之,犯罪的社會危害性與犯罪人的主觀惡性在罪中情節認定階段是呈相同方向增減的,而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的考量不局限于罪中情節的認定,在罪前、罪后階段同樣存在著不得不認真對待的考量情節。
五、主觀惡性在刑法學中的功能解析
(一)主觀惡性在定罪中的功能解析
現代刑法學的基本原則便是責任主義,“無責任無犯罪,無責任無刑罰”是責任主義的基本觀點,這個責任的有無便立足于行為人主觀罪過的有無。一般而言,只有能夠對行為人的主觀心理進行非難可能性,才能夠認定行為人對其行為應當負有責任。現代刑法學對于主觀罪過內涵的分析便遵從認識因素與意志因素的結合原則,故意的實質內涵便是,行為人只有在認識到其行為可能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結果,而去故意追求或者放任這樣嚴重社會危害性結果的發生;過失的實質內涵便是,行為人應當預見到或者已經預見到其行為可能會造成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結果,而沒有在意志上采取合理的措施,致使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結果發生;在故意與過失的建構上凸顯了行為人主觀心理上的非難可能性,也是責任主義的具體展開。犯罪構成理論只是學者對刑法條文的抽象概括,這樣的抽象概括難免掛一漏萬,認定犯罪的唯一根據仍然是刑法條文。作為對刑法條文抽象概括的犯罪構成的核心要件便是主觀要件,主觀要件的認定決定了犯罪客觀要件的認定,繼而決定著犯罪客體的認定。犯罪實質上是行為人主觀惡性的展開,換句話說,犯罪凸顯的是行為人的值得被刑罰懲罰的主觀惡性,這個主觀惡性是指行為人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蔑視與對抗態度。
行為人的行為之所以應當受到刑罰懲罰,在于其主觀心理支配下的行為達到了應受刑罰懲罰的社會危害性,這種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的背后凸顯出行為人的主觀惡性達到了應受刑罰懲罰的主觀惡性。重罪重刑、輕罪輕刑的背后凸顯的是重惡重罰、輕惡輕罰,這是罪刑相適應原則的可靠解讀。沒有以行為作為征表依據的主觀惡性是難以把握而又無法準確把握的,在刑法學的視野下,不存在沒有行為的應受刑罰懲罰的主觀惡性。
(二)主觀惡性在量刑、行刑中的功能解析
德日刑法條文均明確規定了刑罰的裁量應當根據犯罪人的責任原則,我國《刑法》第六十一條規定:“對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立法的有關規定判處。”由此觀之,我國刑罰裁量的基本依據內涵豐富,不僅僅包括罪中情節的裁量,也包括罪前、罪后情節的裁量,這與德日刑罰裁量必須考慮行為人罪前、罪后因素的原則相一致。罪前情節中的犯罪人社會經歷、生活環境、表現情況等因素,犯罪動機、方法、結果、社會影響等罪中因素,罪后情節中的犯罪人態度等因素,皆成為合理考量行為人刑罰有無、輕重及其變更的正當因素,這個合理考量的實質內涵便是對犯罪人主觀惡性的考量。結合我國刑法中的刑罰裁量需要結合的事實依據與法律依據,行刑過程中的刑罰執行方式變更以及刑罰懲罰量的變更等制度措施,凸顯了主觀惡性在包含了行刑階段刑罰裁量的廣義上的量刑的決定地位。對行為人主觀惡性這一動態因素的考察成為實現罪刑相適應的考量依據,多重的主觀惡性決定了多重的刑罰,多輕的主觀惡性決定了多輕的刑罰。
當犯罪人在罪前的成長經歷以及生活表現等因素可以依附于犯罪人的主觀惡性時,這種罪前因素必然影響犯罪人的主觀惡性輕重裁量;當犯罪人在罪后的認罪態度以及罪后表現也可以依附于犯罪人的主觀惡性時,這種罪后因素也必然影響犯罪人的主觀惡性輕重裁量;在這些合理裁量的基礎上,行為人的刑罰必然會出現與之主觀惡性相對應的增減以及變更,以求得動態發展中的罪刑相適應。主觀惡性在量刑中的功能定位在我國刑罰裁量制度的設置中表現得淋漓盡致,如累犯、慣犯等一般會增加犯罪人的刑罰量,坦白、自首、立功等一般會減少犯罪人的刑罰量,緩刑的條件設置正是依賴于犯罪人主觀惡性的輕微考量。這種刑罰裁量制度的合理正當性便在于,其正視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的合理考量因素,正視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無法僅僅從犯罪行為以及主觀罪過中準確而全面地解析出,正視真正的罪刑相適應只能從動態中予以把握。
我國刑罰制度在犯罪人被執行刑罰階段中也有針對犯罪人主觀惡性變化的應對制度,假釋、減輕制度的基本條件的設置正是著眼于犯罪人主觀惡性的消長。《刑法》第七十八條規定犯罪分子在立功或重大立功下應當依法被減刑,犯罪人的立功或者重大立功恰恰體現其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積極態度。換句話說,犯罪人的立功或者重大立功體現了其主觀惡性較之犯罪時的主觀惡性的降低,這正是法院可以并且需要降低其刑罰量的合理正當依據所在。《刑法》第八十一條規定犯罪分子的假釋條件,諸如認真遵守監規、接受教育改造及其悔改表現都是表明犯罪人在受到監獄改造情形后的主觀惡性程度的降低,如果刑罰制度不正視這一變化著的主觀惡性則顯得僵硬扭曲,正是犯罪人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積極態度使得其獲得了刑罰變更或者降低的正當合理性。在行刑階段的減刑、假釋等刑罰變更制度正視了犯罪人的主觀惡性的降低,是實現真正的罪刑相適應的可靠路徑。
(三)主觀惡性是犯罪人應當承擔刑罰的唯一正當根據
犯罪與刑罰作為刑法學的兩個基本主體,在“刑事責任”一詞的映襯下顯得舉步維艱,甚至愈來愈有犯罪與刑事責任成為刑法學的兩個基本主體的意味,刑罰學貌似成為依附于刑事責任的下位概念。犯罪與刑罰是流傳于公眾間的古老而深刻的懲罰觀念,刑事責任不宜替代刑罰成為犯罪的應然后果,只有應當受到刑罰懲罰的行為才能夠稱為犯罪行為,我國《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了予以訓誡或責令賠禮道歉、具結悔過等非刑罰處罰措施的刑事責任承擔方式,幾乎所有刑法學者都會否定應受刑事責任懲罰的行為是犯罪行為的觀點。質在于,承受刑罰懲罰是行為人入罪的充分條件,承受非刑罰懲罰則無法推定出行為人的入罪與否。主觀惡性與犯罪、刑事責任的相互關系在國內學者的解說中有一定程度上的缺陷,如有學者認為:“以主觀惡性為刑事責任的根據,既能夠反映犯罪的實質,又能夠說明犯罪與刑事責任的關系。”[23]刑事責任本身便是貫通犯罪與刑罰所提出的一個中國特色概念,其是為了實現刑罰個別化而納入人身危險性等預防論因素的特色載體,中國刑法對刑事責任的定位并不在于刑罰相似甚至相等層面,而在于貫通犯罪與刑罰層面。
作為語言學上的考察,刑事責任本身是與刑罰所相似,在特定語境下甚至可以等同的概念,將刑事責任作為貫通犯罪與刑罰的中介橋梁并不合適。行為入罪的前提便是行為在社會屬性上應當被評價為應受刑罰懲罰性,即使犯罪人最后得到的是免予刑罰處罰后果,但這個免予刑罰處罰卻恰恰證實了行為人的行為當屬犯罪無疑。由此觀之,主觀惡性作為貫通犯罪與刑罰的依據并不依附于刑事責任,而是對刑事責任(刑罰)有無、輕重及其變更依據的合理考量,刑事責任本身便是一個無法自己將自己闡述完整的概念。行為人罪前因素、罪中因素、罪后因素所凸顯的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態度是主觀惡性的實質內涵,其決定著刑罰的有無、輕重及其變更。大致而言,有什么樣的主觀惡性,便應當有什么樣的刑罰,主觀惡性呈現什么樣的變化,刑罰也應當隨之呈同方向的變化。[24]由犯罪的時空性展現出犯罪人主觀惡性的時空性,進而合理的刑罰也應隨之展現時空性的對應。
六、結論
近現代刑法學的發展史是一部苦苦追尋貫通犯罪與刑罰合理聯系的探尋史,無論是堅持行為乃犯罪之基的行為主義刑法學派,還是堅持人身危險性為犯罪之質的行為人主義刑法學派,抑或是晚近崛起的堅持反社會的人格態度為犯罪之本的人格主義刑法學派,均存在著或多或少的問題。在靜止的犯罪與變化的刑罰之間必然有一個呈時空變化狀的因素方能夠予以將二者合理貫通始終,這個任務的完成者不是靜止著的客觀罪行,也不是靜止著的主觀罪過,更不是隸屬于心理學概念上的虛無縹緲的人格態度,以對社會化的維持及其良性發展的蔑視與對抗態度作為自身內核的主觀惡性成為當仁不讓的中介載體。這個主觀惡性堅持由行為作為其征表的可靠載體,犯罪行為成為其進入刑法學評價范圍的絕對牽引力,而罪前、罪后可以表明犯罪人主觀惡性的輕重程度的因素也依附于主觀惡性進入刑法學的評價范圍。主觀惡性是行為人應當承擔刑罰的唯一正當依據,“無主觀惡性則無犯罪,無主觀惡性則無刑罰”應當成為新時期刑法學堅持與努力開拓的原則。
[1]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2]陳忠林.刑法散得集[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269-277.
[3]張文.行為刑法危機與人格刑法構想[J].井岡山大學學報,2014(5):8.
[4]張文,劉艷紅.人格刑法學理論之推進與重建[J].浙江社會科學,2004(1):117.
[5]賀洪波.論主觀罪過與人格態度的視角差異[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2(11):48.
[6][美]梯利.西方哲學史[M].葛力,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54.
[7]陳興良.主觀惡性論[J].中國社會科學,1992(2):166.
[8]儲槐植.美國刑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80.
[9]邱興隆.罪與罰演講錄[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0:77.
[10]青鋒.罪與罰的思考[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67.
[11]胡學相,黃祥青.論主觀惡性[J].政治與法律,1993 (4):27.
[12]卜安淳.犯罪惡性探析[J].政法論壇,2000(1):41.
[13][意]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2:79.
[14][古羅馬]西塞羅.論法律[M].王煥生,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8.
[15][法]讓-雅克·盧梭.社會契約論[M].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4.
[16][德]H.科殷.法哲學[M].林榮遠,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118.
[17]劉勇.犯罪基本特征新論[A].改革與法制建設——北京大學九十周年校慶法學論文集[C].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9:540.
[18]陳興良.刑法哲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136.
[19]邱興隆,許章潤.刑罰學[M].北京:群眾出版社,1988: 259.
[20][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M].田禾,譯.江蘇:譯林出版社,2000:155.
[21]高艷東.刑罰可罰根據語境中預防論的否定與再生[J].中外法學,2006(6):67.
[22]王勇.關于犯罪的社會危害性[J].社會科學,1984(3): 65.
[23]梅傳強.論刑事責任的根據[J].政法學刊,2004(2):19.
[24]許玉秀.當代刑法思潮[M].北京: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4.
(責任編輯:芮 強)
New Theory of Subjective Evil
LI Yong-sheng,FENG Wen-jie
(Law School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Chongqing 401120,China)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riminal law is a quest to explore the reasonable relations between crime and punishment.Behaviorism criminal law school,actor criminal law school and personalism criminal law school have their own problems respectively.Between stationary crime and changing punishment there must be a factor of time and space which can reasonably balance the both.This factor can not be either the still significant objective crime or stationary subjective guilt,or even the personalism belonging to the illusory psychology concept.Subjective evil,with its contempt and confrontation attitude for social maintenanc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can be this factor.The subjective evil manifests with behaviors and can be evaluated with criminal’s before-crime and after-crime attitude.
criminal law school;subjective evil;subjective sin;personal danger;social harmfulness
D924
:A
:1008-2433(2016)02-0078-07
2015-12-21
中央財政支持地方高校建設項目“特殊群體權利保護與犯罪預防研究創新團隊”的研究成果,西南政法大學法學院2015級研究生科研創新項目“主觀惡性新界說”的研究成果,“西南政法大學科研創新項目”(FXYYB2015125)的研究成果。
李永升(1964—),男,安徽懷寧人,西南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博士后合作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刑法學、犯罪學;馮文杰(1991—),男,河南項城人,西南政法大學2014級刑法學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外刑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