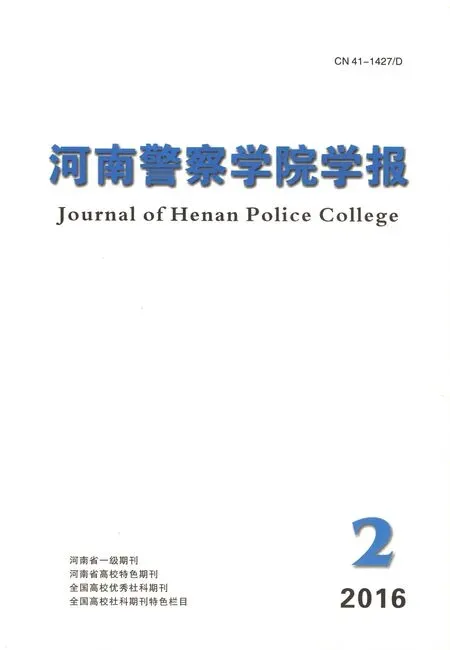行賄犯罪疑難問題解析
胡增瑞,盧勤忠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200042)
行賄犯罪疑難問題解析
胡增瑞,盧勤忠
(華東政法大學,上海200042)
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的界分是司法實踐中的難點,兩罪的區分應遵循意志屬性—資金來源—利益歸屬的進路來判斷。從立法沿革及司法實踐來看,行賄罪不正當利益要件不可或缺,且其外延呈不斷擴大的趨勢。無論在主動行賄還是在被索賄的情況下,“謀取不正當利益”都是主觀要素而不是客觀要素,被勒索而給予財物的也應當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要素才可能構成行賄罪。經濟行賄只能發生在平等的經濟往來中而不是在經濟管理過程中,且不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構成要件,但要以違反國家規定為構成要件。
行賄罪;單位行賄罪;“謀取不正當利益”;主觀要素
司法實務中,對于行賄犯罪的打擊明顯少于作為其對合犯的受賄犯罪。雖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不能不說對于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的界定困難是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之一。對于不正當利益的界定以及其在犯罪構成要件中的歸類也同樣影響著行賄罪的認定。與此同時,經濟行賄與普通行賄在司法實務中的混亂適用甚至是被虛置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司法實務中對行賄罪的認定困難。
一、行賄犯罪的主體:單位與個人的界分
一般而言,行賄罪的主體是個人而非單位是非常明確的,因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明確規定了單位行賄罪,而《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規定的是行賄罪。然而在司法實踐中,無論是在立案偵查、審查逮捕、提起公訴抑或是審判階段,對于行賄罪,審查重點及難點之一首先是對其主體的審查,即行賄行為究竟是單位行為還是個人行為,因為不同主體實施相同的行為,可能涉及此罪與彼罪,甚至罪與非罪的問題。①因為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的入罪標準不同,個人行賄入罪數額標準是1萬元,單位行賄入罪數額標準是20萬元。通常區分行賄主體難度并不大。根據刑法規定,個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的為行賄,單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行賄的是單位行賄。但實踐中,單位法定代表人、實際控制人或是一人公司的負責人行賄,這時的單位行為和個人行為以及利益歸屬經常難以區分,不僅司法實踐中處理方法不一,刑法理論對此也存在較大爭議。概括起來[1],對于兩者的區分,有職務關聯區分說,②該說認為,單位中自然人的行賄是否與自己的職務相關聯,是區分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的一個條件。對于此說,并無本質不同的意見,只是在職務關聯的程度及范圍上存在爭議。張明楷教授認為,“單位犯罪一般表現為為本單位謀取非法利益或者以單位名義為本單位全體成員或多數成員謀取非法利益的行為”。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第四版),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39頁。但也有觀點認為對于單位從業人員為本單位謀取不正當利益而實施違法犯罪行為,如果單位沒有制定預防制度或實施必要的防范措施以防止他們實施這些行為,在規定單位犯罪的前提下,單位應當承擔刑事責任。參見李希慧,杜國強著:《貪污賄賂罪研究》,知識產權出版社2004年版,第332-333頁。行賄名義區分說,③該說認為,是以個人名義還是以單位名義行賄,是區分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的一個標準,即以個人名義行賄的肯定不能認定為單位行賄罪;以單位名義行賄的,肯定不能認定為行賄罪。參見呂天奇著:《賄賂罪的理論與實踐》,光明日報出版社2007年版,第227頁。但是在司法實踐中,行賄人與受賄人往往是心照不宣,行賄人行賄時根本就不提是以誰的名義,按此標準,顯然無法作出區分。賄賂權屬區分說,①該說認為,在判斷單位行賄意志整體性問題上,一個重要的表現就是賄賂資金從單位賬簿上支出。具體參見竇大勇:《單位行賄罪的司法認定》,載《民營科技》2010年第10期。但是,對于“夫妻公司”,“父子公司”而言,行賄人可能會認為公司的錢就是自己的錢,自己的錢也是公司的錢,形成了公司財物和個人財物混同而不分的情況,按上述標準,也很難區分賄賂資金來源。利益歸屬區分說。②該說有直接而明確的法律依據,即《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規定的,“因行賄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依照行賄罪的規定處罰。疑問之處在于違法所得是直接歸屬個人還是包括間接歸屬個人;既有歸屬單位的,也有歸屬個人的,該如何處理。有人認為,如果個人利益與單位利益有依存關系,則認定為單位行賄罪。參見林亞剛主編:《貪污賄賂罪疑難問題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248頁。也有人認為對這種情況原則上應當按照個人行賄和單位行賄分別處理,對個人認定行賄罪,對單位認定單位行賄罪。參見肖中華著:《貪污賄賂罪疑難解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頁。無論何種觀點,單獨適用的話都不能簡單明了地解決行賄與單位行賄的區分問題,以下試舉例予以說明。
例1:李某是某土石方公司法定代表人,該公司的股東是李某及其妻子王某。王某從不過問公司的事情,都是由李某一人負責業務及財務等工作。某日,李某為了能承接蘇州市某區國有某城投公司土方工程,在工程招標前,找到城投公司的主管人員張某,希望其多多關照,日后將重謝。后在張某的幫助下,李某順利承接了該公司價值人民幣500萬元的土石方工程。在李某公司陸續收到上述工程款后,李某將部分工程款轉入自己的銀行卡上,并從中取出人民幣15萬元送給張某。某區檢察院在初查過程的討論中對于李某的行為是單位行賄還是個人行賄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李某雖然是土方公司法定代表人,但是該公司實質上是李某個人所有,其作出行賄的決定也是其個人所為,并沒有與其他股東商量,不能代表單位意志,其行賄款也是從自己銀行卡支出,是為謀取個人利益,構成行賄罪;另一種意見則認為,李某是該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個人的意志也可代表單位的意志,其行賄是為了讓公司承接到工程,利益是歸屬于該公司的,雖然工程款最終轉到了自己的銀行卡上,但也不能否認行賄利益首先歸屬單位的事實。因此,李某的行為是單位行賄,但是因為行賄數額沒有達到單位行賄罪的立案標準,因此李某不構成犯罪。
筆者認為,根據上述任何一種學說,都不能單獨適用例1而得出正確結論。對于職務關聯說而言,李某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雖然沒有與另外一個股東,即其妻子共同商量行賄一事,但是公司實質上由其一人負責經營,其妻子僅僅是該公司為了滿足公司法的相關要求而作為一名掛名股東而已。李某本人的行為,既可以代表公司,也可以說是其個人的行為,因此,依據職務關聯區分說是無法區分是個人行賄還是單位行賄的。行賄名義區分說在本案中同樣是難以適用的。李某送錢給張某的時候,僅說是感謝其的關照,而并沒有說是關照自己還是關照自己的公司。實際上僅這一句話也就足夠了,對方足以心領神會。對李某來說,關照自己就是關照公司,同理關照公司也就是關照自己。至于賄賂權屬說,這15萬元應當是李某公司的財物呢,還是李某個人的財物呢,區分實屬不易。實踐中,與此類似,有些公司可能根本就沒有完整的財務記錄,或者公司法定代表人個人財物和公司財物混同,要想區分清楚行為人是用屬于誰的財物來行賄,根本不可能。按照利益歸屬說,本案中行賄的利益首先歸屬于李某的公司,進而又歸屬于李某個人,也可以說行賄的利益直接歸屬于李某的公司,間接歸屬于李某。那么《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因行賄取得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的”是否包含間接歸屬個人的情況呢?對此不無爭議。
例2:王某是某知名制藥公司的銷售人員,為提高個人業績,多得年終獎金,便個人出資購買2萬元購物卡送給某醫院藥房主任,請其在藥品招標采購時關照自己。后王某如愿以償,向該醫院銷售了200萬元的藥品,并在年終因該筆銷售獲得了10萬元的獎勵。王某行賄的行為是否屬于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呢?筆者認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違法所得歸個人所有”應當可以包括利益間接歸屬個人所有的情況,否則可能放縱例2中的行為,并且也不會置單位行賄罪于虛置的境地,畢竟兩者立案標準不同,法定刑亦差異巨大。
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本質上是個人犯罪和單位犯罪的關系。根據刑法分則的立法例,其本應當歸入同一條文,適用相同的法定刑,只需另外規定對單位犯行賄罪的判處罰金即可。但是,刑法為了突出打擊行賄罪,將兩者分別規定,并對二者配置了差異巨大的法定刑,致使本該并無實質意義的區分在實踐中變得疑難而且復雜。筆者認為,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的區分應當堅持以下三個步驟:首先看意志屬性。出于個人意志行賄的是行賄罪;出于單位意志行賄的是單位行賄罪。當意志屬性無法區分,例如上述例1和例2中的情況,意志重合的情況下應當接下來考察資金來源。其次看行賄資金來源,對于資金來源要從實質上把握,而不能只看表面。實踐中,有的行賄人用自己身邊的備用金來行賄,表面看起來備用金不是公司的財物,實際上可能是行賄人每年定期以各種名目從單位賬上支出,放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如此情況,仍應作為單位資金看待。最后看利益歸屬。利益歸屬應當堅持利益直接歸屬和利益間接歸屬均可適用《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二款的規定,否則就留給了犯罪嫌疑人巨大的規避空間,從而不當縮小了打擊面;同時,也與司法解釋不斷擴大“不正當利益”范疇進而擴大打擊行賄罪的目的背道而馳。
根據上述三個原則來分析前述例1。李某的行賄意志既可以看成是李某個人的,也可以看成是李某公司的;對于用以行賄的15萬元,表面看起來是李某個人卡上的錢,實際上來源于單位所直接獲得的不正當利益,因而是來源于單位的;而行賄的利益直接歸屬于單位,間接歸屬于李某個人。因此,李某的行為是單位行賄。因行賄額未達到人民幣20萬元的標準,李某不構成犯罪。同樣以上述步驟來分析例2。王某行賄的意志不是單位意志,而是個人意志。王某是個人出資購買購物卡行賄的。王某最終間接獲得了10萬元的不正當利益。因此王某構成行賄罪。可見,在行賄罪和單位行賄罪沒有統一立法前,將《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利益歸屬個人理解為既可以直接歸屬于個人,又可以間接歸屬于個人,可以嚴密法網,不會遺漏類似對例2中王某的行為的打擊,還可以契合當前嚴打腐敗的需要。
二、不正當利益的規定:限縮與擴大之爭
1979年刑法規定只要是行賄或者是介紹賄賂,不論什么原因,一律構成犯罪。①該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款規定,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或者介紹賄賂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在實踐中不免打擊了一些目的正當的行賄,擴大了打擊面,如為了要回貨款而被逼無奈的行賄。為了適應司法實踐中的新情況,最高人民法院與最高人民檢察院于1985年發布的《關于當前辦理經濟犯罪案件中具體應用法律的若干問題的解答(試行)》(以下簡稱《解答》)中首次將謀取非法利益作為行賄罪的構成要件要素,適當地限縮了行賄罪的成立范圍。②在《解答》中關于行賄罪和介紹賄賂罪的問題中指出“個人為謀取非法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或介紹賄賂的,應按照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三款追究刑事責任”。但是,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關于懲治貪污賄賂罪補充規定》(以下簡稱《補充規定》)又通過用“為謀取不正當利益”③《補充規定》第七條規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國家工作人員、集體經濟組織工作人員或者其他從事公務的人員以財物的,是行賄罪。”替換了司法解釋中的“為謀取非法利益”,變相地擴大了行賄罪的成立范圍,因為不正當利益的外延比非法利益的外延要寬得多。此后,在新刑法的修訂過程中,圍繞何為不正當利益又不斷形成新的爭議。
198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刑法修改小組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交的《修改刑法研究報告》中就指出:調查中大部分人認為行賄罪和介紹賄賂罪不能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限定條件。原因在于:首先,行賄罪的危害性在于嚴重腐蝕國家工作人員,無論其是否以謀取正當或不正當利益為目的,這種危害性都不會因此而有所不同;其次,實踐中不正當利益與正當利益有時難以區分,造成適用混亂;最后,作為對向犯的行賄與受賄,沒有理由只打擊受賄行為而放縱行賄行為[2]2639。與最高人民檢察院呼吁取消行賄罪的“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構成要件不同,在刑法修訂過程中,最高人民法院卻一直主張應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明確規定為行賄罪的構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刑法分則修改的若干問題(草稿)》中認為,“鑒于目前社會風氣敗壞,不少人為了合法利益也不得不行賄,故不能對一切行賄行為都以行賄罪論,必須在行賄罪前邊加上‘為非法利益’而行賄這一限制內容”[2]2641。1997年修訂刑法最終采納了折中意見,既沒有將謀取利益的范圍縮小為非法利益,也沒有不當地擴大到正當利益,而是吸收了《補充規定》中的相關內容,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規定為行賄罪的構成要件之一,暫時平息了“兩高”的爭議。
然而,司法實踐中隨之而來的問題出現了,如何理解與準確界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其是主觀要件還是客觀要件?對此刑法理論界與司法實務中爭議較大。為此,1999年3月4日,“兩高”聯合頒發的《關于在辦理受賄犯罪大要案的同時要嚴肅查處嚴重行賄犯罪分子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首次明確了不正當利益的內涵。①《通知》第2條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謀取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利益,以及要求國家工作人員或者有關單位提供違反法律、法規、國家政策和國務院各部門規章規定的幫助或者方便條件。”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在商業往來活動中,賄賂之風愈演愈烈。為遏制這種勢頭,2008年11月20日,“兩高”出臺的《關于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又顯著擴大了前述《通知》對不正當利益的界定,為擴大打擊行賄犯罪的范圍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據。②《意見》第9條規定:“在行賄犯罪中,‘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行賄人謀取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或者政策規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對方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
2012年12月26日,“兩高”在《關于辦理行賄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中繼承了前述《意見》中對于不正當利益界定的同時,又在第12條第2款中再一次擴大了不正當利益的范疇,③增加規定“違背公平、公正原則,在經濟、組織人事管理等活動中,謀取競爭優勢的,應當認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首次將在相關領域謀取競爭優勢的行為視為謀取不正當利益。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中提到,“將明確地方立法權限和范圍,依法賦予設區的市地方立法權”。在此之前,只有較大的市而不是設區的市才有最低一級的地方立法權。隨著《決定》的出臺,可以預見的是擁有立法權的地方政府將大大增加,地方政府規章的數量無疑也會大大增加,“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外延肯定會在司法實踐中進一步擴大,為當前的反腐敗形勢再添一把力。
梳理“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立法及司法沿革可以發現,在行賄罪中,“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要件從無到有,期間雖有爭執,但隨著各種腐敗犯罪情況的不斷出現,為嚴控腐敗形勢,“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這一要件的內涵與外延又不斷擴大,增大了其犯罪構成的涵攝面。在可預見的將來,在目前反腐敗的高壓態勢下,行賄罪“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要件決不會取消,反而會不斷擴張其外延,以擴大行賄罪的適用范圍。這既符合我國的國情,也是當前高壓反腐的刑事政策需要。
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主觀要素還是客觀要素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行賄罪的主觀要素還是客觀要素,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分歧較大,一種觀點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行賄犯罪的主觀目的,而且行賄犯罪是指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目的為其特別構成要件的犯罪,是目的犯[3]。持同樣觀點的論者認為,“為謀取”一語明顯屬于主觀目的的范疇。《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款是該條第一款的補充性規定,同樣也應當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主觀要件;同時,從犯罪構成的角度來看,《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是行賄罪的基本犯罪構成,第三款的規定是行賄罪的修正犯罪構成,“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在這兩款規定中之犯罪構成中的地位是一致的,都屬于其主觀方面的要件[4]。第二種觀點認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既是主觀要件又是客觀要件。如張明楷教授認為,如果認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主觀要素,則當行為人已經獲取不正當利益后,為了不正當利益酬謝國家工作人員,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時,就會被排除在行賄罪之外。如果將“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解釋為既可能是主觀要素,也可能是客觀要素,該種行為才可認定為行賄罪”[5]。
筆者認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主觀要件要素,但其屬于行賄罪的動機,而不是行賄罪的目的。犯罪目的是行為人希望通過犯罪行為達到某種危害結果的心理活動,它反映要達到某種愿望的意志。而犯罪動機則是推動或者促使犯罪人實施犯罪行為的內心起因(內在推動力量)。行賄者的目的是要收買國家工作人員,而動機可能是多種多樣的[6]。行賄者首先產生行賄動機,這個動機既可能是“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也可能是為謀取正當利益,如為按期拿到工程款,行為人在上述動機的驅使下進而采用金錢或其他財物收買的方式拉攏腐蝕國家工作人員,目的就是收買國家工作人員,客觀上形成了錢權交易,侵害了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不可收買性。同時,筆者認為,張明楷教授用以證實其“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也屬于客觀要素的觀點的案例④2009年9月的一天,被告人許某受他人委托替他人辦理房屋所有權證過戶手續,為少繳納契稅及相關滯納金等費用,找到時任平頂山市房產管理局政策法規科科長兼平頂山市房地產產權產籍監理所負責人、黨支部書記的吳某某,吳某某利用其職權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條件,給相關人員打招呼,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事后,許某向吳某某行賄人民幣6萬元。河南省郟縣人民法院(2010)郟刑初字第9號刑事判決書認定被告人許某犯行賄罪,判處有期徒刑2年,緩刑2年。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上),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2版,第394頁。恰恰證實了該要件屬于主觀要素。該案中,被告人許某事先對國家工作人員有請托,請托的內容是“少繳契稅及相關滯納金等費用”,該請托顯然是違反相關法律法規規定的。受請托國家工作人員接受請托后,為許某謀取了不正當利益,事后,許某送錢給國家工作人員表示感謝。該案中,許某只是在謀取到了不正當利益之后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但其事前對該國家工作人員已經進行了“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請托,其謀取不正當利益的動機很明確,只是事成之后給予財物罷了,其實質仍是以錢買權。
值得注意的是《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不是行賄”的內涵。根據該款規定,從邏輯上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的,獲得不正當利益的,是行賄。”①司法實踐中也持同樣看法,如1999年8月6日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第(五)項中規定“因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已獲得不正當利益的,以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是否構成行賄罪取決于是否實際獲得不正當利益這一客觀結果,如果不考慮主觀方面的話,得出這樣結論顯然是一種客觀歸罪,與我國刑法理論與實踐認定犯罪所堅持的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相違背。主觀上有犯罪的故意,客觀上實施了犯罪的行為,只是因為客觀原因而未得逞,這更符合我國刑法理論關于犯罪未遂的規定,而不是不構成犯罪。因此,對《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只能理解為是該條第一款規定的例外規定,而不是補充規定,其應當符合第一款規定的基本內容,即“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但因為客觀方面存在些許不同,即“被勒索而給予財物而不是主動給予”,同時“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所以排除了犯罪構成。如此規定依據何在?筆者認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款規定的內涵應當是:“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而被勒索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本應構成行賄罪,但畢竟是被勒索給予財物而不是主動給予,同時又沒有獲得不正當利益,使得行為人的主觀惡性及客觀危害性均顯著降低,沒有達到嚴重的社會危害性程度,符合《刑法》第十三條但書的規定,不認為是行賄罪。所以,可以認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三款規定暗含了“為謀取不正當利益”是主觀要件要素而不是客觀要件要素的意思。
四、謀取不正當利益:能否適用經濟行賄
一般認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的是經濟行賄,也就是經濟往來中發生的行賄行為,而不是行政管理過程中發生的行賄行為。經濟往來的范疇是什么,司法實踐中其實并不容易準確界定。以袁某行賄案為例(例3):被告人袁某系國家注冊建筑師。2010年5月,其通過同學沈某某(泰州市路燈管理處主任,另案處理)的介紹,與負責拆遷安置房開發建設的泰州市海陵房產開發公司經理劉某某(國家工作人員,另案處理)相識,并委托沈巧龍向劉某某索要其使用的銀行卡號,于2010年6月14日向該卡存入人民幣4000元,同年9月18日向該卡存入人民幣20000元,又于2011年3月12日向該卡存入人民幣100000元,總計人民幣124000元。在劉某某的幫助下,未經招標程序,被告人袁某以掛靠單位同濟大學建筑設計研究院(集團)有限公司的名義承攬了泰州市迎春東路安置小區海曙頤園的規劃設計項目[7]。檢察機關以行賄罪(經濟行賄)提出公訴得到法院的認可(從判決書中法院同意檢察院看法可以推斷出來)。法院認為:“被告人袁某在經濟往來中,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行賄罪。公訴機關起訴指控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罪名成立,予以支持。”在本案中,檢法兩家均認為未經招投標而因行賄直接承攬設計工程的行為屬于在“經濟往來”中。如此一來,那《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二款將被虛置。到底該如何界定“經濟往來”?一種意見認為,經濟往來活動包括生產、經營的各種活動,既包括國家經濟管理活動,又包括國家工作人員參與的直接的經濟交往活動[8]。另一種意見認為,經濟往來活動只限于行為人代表本單位與外單位或個人從事經濟交往活動,也即限于平等民事主體之間的交往,不包括行為人代表單位所進行的經濟管理活動,凡是行為人在履行經濟管理職能過程中收受或者索取賄賂的,都不算是經濟受賄行為[9]。筆者同意第二種觀點。如果經濟往來既包括經濟管理活動,又包括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交往活動,那么《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區分設置第一款和第二款就變得幾乎毫無意義了。國家工作人員從事經濟管理活動,其本質上和國家工作人員從事行政管理活動并無實質差別,都是一種行使公權力的管理活動,是國家工作人員行為公務性的體現。而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交往,體現的是一種平等關系,而不是一種管理與被管理的不平等關系。《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二款規定的是經濟往來中的回扣、手續費,而不是經濟管理中以回扣、手續費名義出現的行賄和受賄。因為回扣本身只產生于商品貿易流通過程中的買賣雙方,手續費、辛苦費、勞務費等則是因一定的勞務關系,由接受勞務的一方支付給提供勞務的一方的報酬。主要產生于推銷商品、采購原料、聯系企業經營有關業務等活動中。實踐中,在銀行信貸、發包工程及工程驗收、決算等過程中以所謂回扣、手續費名義出現的行賄受賄問題,雖然打著回扣、手續費的招牌,但嚴格說來,因其具有經濟管理的內容與特征,不應屬于經濟行賄范疇,只能屬于一般行賄范疇[10]。因此,在例3中,袁某為了直接得到設計工程,多次給予具有將工程以何種形式進行發包決定權的劉某某以財物,這顯然不能當成是經濟往來過程中給予財物,而是屬于經濟管理過程中給予財物。在此過程中行賄罪的認定應當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而非第二款的規定。因此,在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管理活動過程中行賄的應適用《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而在國家工作人員實施的平等經濟交往過程中行賄的,應當適用該條第二款的規定。
那么《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條第一款明確要求要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要素,該條第二款因為對此沒有明確規定,是否也要求具備這樣的要素呢?刑法理論中,一種觀點認為,經濟行賄的構成要件也應當包括“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其是行賄罪的必備要件[4]。另一種觀點認為,經濟行賄并不要求以“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為要件。經濟行賄具備行賄罪的特殊構成要件體系,從邏輯角度看具備獨立的存在價值,也不像一般行賄行為發生在社會生活領域而是發生在經濟往來環節[11]。也有論者認為,經濟行賄是行賄罪的一種特殊形式。只要行為人實施了給予國家工作人員以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的就屬于行賄,不要求“為謀取不正當利益”作為構罪要件[10]。司法實踐中上述規定給司法實務者造成巨大的困擾,同時也是司法實務中的一個難點。筆者認為,理論與實務中對此問題糾結的根源在于一是沒有深刻理解“經濟往來”的內涵,二是沒有認真研究法條規定中“謀取不正當利益”與“違反國家規定”的異同。如前所論,只有在嚴格區分行賄犯罪中社會管理、經濟管理與經濟往來的具體類別歸屬的前提下,討論“謀取不正當利益”是否屬于普通行賄與經濟行賄的構成要件才具有針對性。實際上,經濟行賄的構成要件要求比普通行賄應當更嚴。因為,從立法本意來看,犯罪構成要件寬嚴的決定性因素是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社會危害性大,則構成要件要求寬;社會危害性小,則構成要件要求嚴。普通行賄發生在雙方不平等的社會及經濟管理過程中,在這種情形下行賄人處于相對更弱勢的地位;而經濟行賄發生在雙方平等交往的經濟活動中,在這種情形下行賄人處于相對較平等的地位。處于相對弱勢地位的行賄人要求要具備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才構成行賄罪,那么處于相對平等地位的行賄人不更應當具備這樣的要件嗎?按此邏輯,經濟行賄中也應當具有謀取不正當利益的目的。
但實際上,根據前文對“不正當利益”的分析可以發現,其外延其實相當豐富,并且呈不斷擴大趨勢。①根據《解釋》規定,“‘謀取不正當利益’,是指行賄人謀取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或者政策規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對方違反法律、法規、規章、政策、行業規范的規定提供幫助或者方便條件。違背公平、公正原則,在經濟、組織人事管理等活動中,謀取競爭優勢的,應當認定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與此同時,經濟行賄中“國家規定”的內涵相比“不正當利益”要嚴格得多。②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準確理解和適用刑法中“國家規定”的有關問題的通知》(法發〔2011〕155號)中規定,“根據刑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刑法中的‘國家規定’是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的法律和決定,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規定的行政措施、發布的決定和命令。其中,‘國務院規定的行政措施’應當由國務院決定,通常以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制發文件的形式加以規定。以國務院辦公廳名義制發的文件,符合以下條件的,亦應視為刑法中的‘國家規定’:(1)有明確的法律依據或者同相關行政法規不相抵觸;(2)經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通過或者經國務院批準;(3)在國務院公報上公開發布。”對比上述規定同樣可以發現,經濟行賄的構成要件要求比普通行賄的要求要嚴格得多。糾結于經濟行賄是否要以謀取不正當利益為要件并無實際意義,它不是一個“有”或者“無”的問題,而是由刑法在不同層面作出了不同的安排,即在經濟行賄中,只要證明行賄人違反哪一個具體的“國家的規定”,并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回扣、手續費,就足以認定其構成行賄罪,而不需要證明其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五、結語
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的區分應遵循意志屬性—資金來源—利益歸屬的進路來判斷,個人決定進行行賄,資金也來源于個人的,行賄利益也是歸屬于個人的,才可認定為行賄罪。從立法沿革及司法實踐來看,不正當利益外延呈不斷擴大的趨勢,這也是契合了當前高壓反腐的要求。行賄罪中,謀取不正當利益是主觀要素不是客觀要素,被勒索而給予財物的也應當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的主觀要素才可能構成行賄罪,否則不構成犯罪。經濟行賄發生在平等主體的經濟往來過程中,而不是在經濟管理過程中,并且其構成要件之一為違反國家規定而非為謀取不正當利益。
[1]董桂文.行賄罪與單位行賄罪界限之司法認定[J].人民檢察,2013(12):30.
[2]高銘暄,趙秉志.新中國刑法立法文獻資料總覽(下)[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8.
[3]趙秉志.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分則篇(六)[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62.
[4]趙翀.行賄罪中“謀取不正當利益”之要件[J].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5(2):102.
[5]張明楷.刑法分則的解釋原理(上)[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394.
[6]盧勤忠.“謀取私利”是行賄罪的目的嗎?[J].法學,1990(4):20.
[7](2011)興刑初字第304號[J].人民司法·案例,2012 (4):66.
[8]王作富.刑法分則實務研究[M].北京: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1981.
[9]楊興國.貪污賄賂罪法律與司法解釋應用問題解釋[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216.
[10]郭晉濤.論行賄罪中的“為謀取不正當利益”[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0(6):33.
[11]金永華,解杰.行賄犯罪“為謀取不正當利益”要件刑法適用疑難問題研究[J].人民檢察,2011(2):20.
(責任編輯:劉 芳)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of Bribery Crime
HU Zeng-rui,LU Qiu-zhon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Shanghai 200042,China)
The boundary of bribery and corporate bribery is the difficulty in judicial practice.We need to follow the order of will attribute-the source of funds-attribution of interests when distinguishing these two crimes.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egislative evolution and judicial practice,the illegitimate interests is an indespensable element of the crime of bribery,and its extension is constantly expanding.No matter in active bribery or extortion bribery case,to seek illegitimate interests is subjective factor rather than objective factor.Those who are blackmailed to give properties shall also be subject to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of illegitimate interests that may constitute the crime of bribery.Economic bribery can only occur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transaction,but no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anagement,and its constitutive element is the viol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state but not to seek illegitimate interests.
bribery;corporate bribery;to seek illegitimate interests;subjective factor
D924
:A
:1008-2433(2016)02-0110-07
2016-02-06
胡增瑞(1979—),男,安徽固鎮人,華東政法大學2013級刑法學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經濟刑法;盧勤忠(1965—),男,浙江上虞人,華東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經濟刑法、刑事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