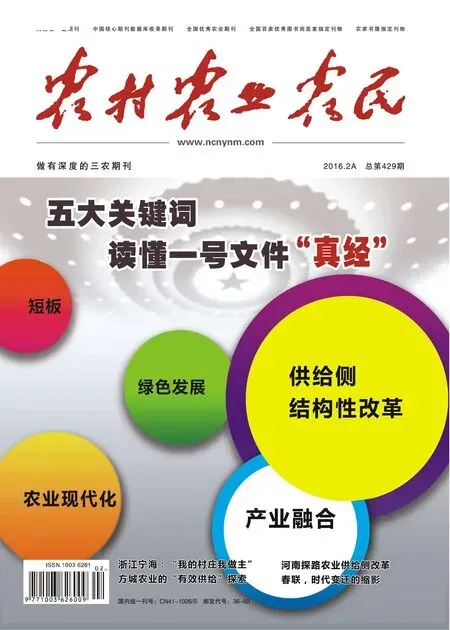考問農業新業態的成長困惑
李松
?
考問農業新業態的成長困惑
李松

發展休閑農業,有利于延伸農業產業鏈,推動一二三產業良性互動
當下,都市休閑農業等各類農業新業態正茁壯成長。但在其成長過程中,隨著與資本、勞力、土地等要素日益緊密結合,一些政策困惑也表現了出來:有的都市農業項目無法取得用地指標,打起了土地政策“擦邊球”;有的農業補貼政策“落地”效果不佳;有的農業項目在土地上積累了大量固定資產,卻無法成為有效抵押物……改革思維下,如何應對農業新業態的成長困惑?
都市農業缺用地指標,“擦邊球”怪相頻現
山前綠樹成蔭、景觀廊道、亭臺水榭繞湖而建,景色宜人;山腳下占地1畝多的花卉植物區呈現鄉村民居風格,古色古香,配套主題餐廳,可供游客用餐、娛樂;山上400多畝林地栽種楊梅、櫻花等,可供采摘、觀賞……重慶某區一農業觀光園建于2012年,業主累計投入3000多萬元,以特色效益農業為基礎,配套發展休閑旅游。
經過多年投入,項目已成熟。但業主張天新(化名)坦言,自己心里總是不踏實,原因就在于觀光園以臨時生產用房和農業附屬設施建設的名義,搞起了主題餐廳和住房,打了用地政策“擦邊球”。
張天新說:“流轉之前,觀光園的地大多是撂荒的,由于流轉租金比較高,農戶默認了我們修房的行為,但是土地流轉有期限,農地改變用途也違規。合同一到期,農民要求原貌歸還土地該怎么辦?土地執法部門來查處,要求拆掉房屋,又該怎么辦?”
相比以農業附屬設施的名義直接建房,有的項目做法更“巧妙”些。在重慶某農家樂,有10多座木質“農家旅舍”環湖而建,建筑物離地一兩米,使用鋼架作支撐。農家樂負責人說:“之所以要挑空建房,就是因為政策規定農業用地不能改變用途和性質,農旅配套又必須建接待設施。權衡政策邊界和現實需求,離地挑高建木房風險較小。如果政府來查,我們拆房、復墾的成本也低些。”
都市觀光農業項目用地“擦邊球”問題多發,既與項目投入不規范、踩用地紅線有關,也有一些合理的建設用地需求無法得到滿足,迫使不少人選擇“繞著政策走”。
“發揮農業休閑、觀光、旅游功能,延長產業鏈,建設配套用房和設施有客觀需求。但農業建設用地管控嚴格,觸碰紅線,風險很大。”重慶兩江藝龍實業發展公司流轉了2000多畝土地,發展花卉苗木和有機農產品。總經理尹詩麟說:“公司曾打算依托有機農產品種植,發展采摘體驗、觀光旅游項目,農產品附加值能大幅提升,就因為用地指標沒法落地,配套設施建不了,最后不得不放棄。”
大戶補貼政策難“落地”,固定投資變“死資產”
都市觀光農業成長需要用地指標,規模化糧食生產則需要政府補貼扶持。在重慶,不少農民反映,種糧大戶補貼在“落地”時有不少問題。
為了穩定糧食生產、抵消成本上漲對種糧的不利影響,近年來重慶實施種糧大戶補貼,規模50畝至100畝的,每畝補貼160元;100畝以上的,每畝補貼230元。在基層,大戶補貼卻遭遇散戶分利的現實尷尬:流轉出土地的農民雖不種糧,卻也要求比照其他種糧農民所能享受的農資補貼、糧食直補等,分享大戶補貼資金。
“這些年國家出臺不少補貼政策,種糧農民打心眼里歡迎。可補貼是按承包面積,補給土地承包者,并非我們這些實際耕作人。”梁平縣種糧大戶胡永剛說,村里農民把土地轉包給我們,除了能收取租金外,補貼款還要切一塊返還給農民。不種糧的能得到150元/畝,種糧的只有10元/畝,這對我們這些堅持務農的人積極性多少有些挫傷。
“惠農政策實施的效果,既取決于政府資金投入的力度和范圍,又受到農民之間利益關系和農地權利關系的影響。例如,在土地流轉中,雖然土地使用、經營權轉給了大戶,但散戶農民依然保有土地承包權,在農村契約約束力不強的背景下,如果大戶不能滿足散戶的利益訴求,散戶就很可能收回土地。”重慶墊江縣農委副主任劉寶凡說,政府要求“誰種糧誰得補貼”,基層落實難度很大。在土地流轉過程中,轉入土地的大戶和散戶之間實際上存在著利益博弈,大戶要租到土地,通常要以返還部分補貼資金為前提。
除了涉農補貼外,現行的一些農村金融政策也不利于農業新業態成長。例如,隨著各地土地流轉加快,農業生產配套建設了越來越多的附屬設施和生產管理用房,然而由于沒有明晰的產權,這些“沉淀”在土地上的資產,已引起農業大戶普遍擔憂。
重慶江津現代農業園區從2008年建設以來,已入駐農業龍頭企業超過50家,形成了優質糧油、晚熟柑橘、花卉苗木等特色產業。“一方面農業發展缺資金,另一方面即便有資金投入,也難以獲得保障,無法融資循環,成了‘死資產’。”談到農業項目的融資瓶頸,園區管委會劉玉鐘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府也想了不少“土辦法”,例如根據鄉村道路、水利設施、林木、農業生產配套設施等不同投資項目,區級涉農部門可以給企業出具投資證明,以降低銀行貸款門檻。即便有這些措施,金融機構仍不認可農業投資形成的固定資產是有效抵押物,融資依然困難。
優化政策框架,打破尷尬現狀
現階段農村土地、金融、補貼等政策事關現代農業持續、健康發展,政策調整、優化“牽一發而動全身”。在業內人士看來,要解決農業新業態成長中的這些政策困惑,需要立足農業、農村發展現實狀況,分類施策,對癥下藥。
以農村土地建設利用為例,應該出臺專門的政策文件,一方面凸顯政策的“規范和引導”作用,堅持紅線思維,設定耕地保護、產業準入、環境保護、農民利益分配等底線,農業項目建設遵循產業發展規劃要求,明確經營方向;另一方面,劃定一定比例的土地利用指標,專門用于滿足現代農業的發展需求。
同時,隨著現代農業發展,農業固定資產投入必定越來越大,相關產權的明晰需要決策者通盤考慮。據了解,為了推動農村固定資產明晰權屬,重慶、山東等地政府部門已開始試點探索給投資業主頒發相關的產權證明,確定資產投資額度、面積、有效期限等產權屬性。但這些規定是國家層面相關法律、政策并未作出調整背景下作出的,屬于地方政府自發探索行為,有的不規范、不完善。
業內人士認為,目前正在推進的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既應該明確土地本身的權屬關系,也應明晰附著在土地上的固定資產的權屬關系,通過制度創新和政策調整,進一步回答農業附屬設施和生產管理用房等固定資產如何確權、如何進行價值評估和能否進行抵押融資等問題,以真正穩定農業生產關系,促進現代農業發展。
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