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寧海:“我的村莊我做主”
李玥
?
浙江寧海:“我的村莊我做主”
李玥

浙江省寧海縣紀(jì)委工作人員向當(dāng)?shù)卮迕褓浰汀秾幒?h村級權(quán)力清單36條》宣傳畫冊
每月第一個星期二早飯后,浙江省寧海縣大陳村村民陳先良,都會穿上那身老式藍(lán)呢子中山裝,系好風(fēng)紀(jì)扣,趕到村里的祠堂開會。
這是他晚年最期待的生活。
就在這一次次會議上,74歲的陳先良就大陳村的河堤整治表過態(tài),也為“美麗庭院”建設(shè)提出過意見。村里100畝海塘的招標(biāo),陳先良把每一個步驟都摸得一清二楚。只要是村里的事兒,他和村里的成年人,都有資格參與決策監(jiān)督。
“我年輕的時候就盼著,人民當(dāng)家做主,村里的事能讓老百姓湊一起討論。”這個冬天的一個上午,陳先良端坐在村子的祠堂里,戴著老花鏡讀報紙。
他是村里的文化人,當(dāng)過兵,教過書。即便這樣的人,在2014年之前,他從來沒享受過參與村里決策的政治待遇。
終于在前年,寧海縣推行的一項政策,讓他的角色有了重大改變。
老村里的新變化
大陳村的祠堂,就在村子中心。這個陳氏家族的精神寄托之地,也是大陳村的政治中心,村委會就設(shè)在祠堂里。
不過在2014年之前,陳先良,這個陳氏家族中的文化人,也很少踏足這里。村干部和村民就隔著一道門,可在他心中,如同大陳村到寧海縣城的距離。
“幾年前,村民可不愛往村委會跑。”陳先良搖著頭,用手點著桌子,“見到村干部,都躲著走的。”
現(xiàn)在完全不一樣了。祠堂成為他和老街坊每天都會去的地方。冬天,他總是喜歡到祠堂外曬曬太陽,瞇起眼睛看看村里的公示欄。也有村民在這里玩會兒麻將,一邊扔出“西風(fēng)”,一邊念叨兩句村子里的新動向。
這個變化,源于寧海縣在2014年推出的《寧海縣村級權(quán)力清單36條》,并建立了社情民意發(fā)現(xiàn)機制、群眾訴求辦理機制、權(quán)力監(jiān)督約束機制和干部作風(fēng)保障機制“四位一體”的基層治理體系。
這份權(quán)力清單,包含村集體民主管理事項方面的19項權(quán)力和村集體便民服務(wù)事項方面的17項權(quán)力。每一項都有詳盡的流程設(shè)置。
比如對于村級重大事項就規(guī)定了“五議決策法”,凡涉及村集體和村民利益的多項重大事項,當(dāng)由村黨組織提議,接著兩委聯(lián)席會議商議,后交黨員大會審議,待村民代表會議決議后,留足3天公示時間,兩委會組織實施決議。
這些內(nèi)容,陳先良背得滾瓜爛熟。在寧海的每一個村子,關(guān)于36條的宣傳隨處可見。祠堂門前的電線桿上,就有36條的宣傳標(biāo)語;36條的漫畫,也出現(xiàn)在村里主干道兩側(cè)的墻上。
有了這份權(quán)力清單,陳先良發(fā)現(xiàn)了村里的很多變化。
當(dāng)了一輩子老師,這位老人從不求人,但他知道“規(guī)矩”。過去,在村子里想辦點事得到處跑,提著禮品哈著腰求村干部,還不一定辦得成。而現(xiàn)在,村干部甚至?xí)祥T服務(wù),就連村子里出不去門的殘疾人,辦事也順當(dāng)了。
說話間,村干部進(jìn)進(jìn)出出,碰見陳先良,都會點個頭打個招呼,念叨兩句公示欄里的新項目。
村民代表也受村民歡迎了。一旦有村民代表參加村里的討論,散會后,他們總會被大伙兒圍住。“這是大伙自己選出來的,他的話我們都信”。
當(dāng)然,陳先良本人及其他村民,也能按流程,參與到村里重大事項的決策中。比如,村里的水環(huán)境整治工程,陳先良就在祠堂門口和村干部討論過。祠堂里新修的戲臺,村干部也吸收了村民對戲臺裝飾的建議。
還有一些變化是直觀可見的,比如村里的衛(wèi)生。
即使在前些年,村里也很難找出一個干凈的地方。多年前,陳先良的兒子結(jié)婚時,村里根本找不出能舉辦宴席的地方。桌子就架在垃圾上,豬晃晃悠悠拱過來,驚得外村的賓客壓根兒坐不住。現(xiàn)在,大陳村的每條街道都打掃得干干凈凈。
這樣的變化,也出現(xiàn)在寧海的海頭村。
海頭村村官陳彥伶,曾細(xì)細(xì)地在海頭村3.5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走了一遍,最終寫了一份關(guān)于海頭村最近兩年來變化的報告。在她的報告中,海頭村的公共衛(wèi)生是重頭。村里的7個公共廁所,即使在夏天,也聞不到太多異味。這些變化,陳彥伶歸功于36條:“所有事都按規(guī)矩辦,哪怕是打掃公共廁所這這件小事,村里當(dāng)然越來越好了。”
還有一些從數(shù)字可見的變化。據(jù)寧海縣紀(jì)委工作人員介紹,去年,寧海縣新增上訪為零。他還表示,自從36條推行以來,干群關(guān)系發(fā)生了很大變化。現(xiàn)在跑到上級部門反映村干部問題的村民多了,但都是老問題。
把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交給村民
陳先良所期盼的“人民當(dāng)家做主”,其實早有寧海縣力洋鎮(zhèn)的村民就體會到了。
2014年年初,寧海縣剛剛推出36條時,力洋鎮(zhèn)紀(jì)委書記徐建岳便申請在該鎮(zhèn)做試點。
徐建岳還清楚地記得,該鎮(zhèn)力洋村活動中心建設(shè)工程的每一個細(xì)節(jié)。
早在幾年前,力洋村就開始醞釀修建活動中心。這是10年來最大的村級工程,造價625萬元,村干部猶猶豫豫,誰都不敢拍板。2014年,村里決定按照36條來走一趟,先用五議決策法征得村民同意,再依照工程流程圖實行招投標(biāo)管理。
“這意味著,把知情權(quán)、參與權(quán)、監(jiān)督權(quán)交給村民。”在徐建岳心里,這是場實驗。
這一年,因為這項工程,村里破天荒召開了一次村民代表大會。200多號人擠在一起,他們將代表力洋村的3000名村民對設(shè)計方案的意見。
在縣里工作的村民代表也特意請了假趕來參會,“想看看到底是干啥”。
正值夏天,可在那間大會議室里,200多人,絲毫沒有一點熱烈的氣氛。有村民小聲嘀咕:“一直以為都是村干部說了算,我們坐在一起能討論出來個啥?”在他們的印象中,活動中心修成啥樣,理應(yīng)由村干部決定。
村里的老人,也有不少參會的。盡管村干部見了他們,也會客氣地打個招呼,可在這間會議室,這些老人的目光始終落在村干部身上。
終于,在村干部的鼓勵下,有村民打破沉默,嘗試著表達(dá)顧慮:“設(shè)計方案這么專業(yè),我們也看不懂,找我們商量沒啥用。”
發(fā)問一出,村干部特意請來的設(shè)計師登場,開始闡述設(shè)計方案。
整個過程十分安靜。設(shè)計師闡述完,征求村民代表的意見,現(xiàn)場的村民沒人應(yīng)聲,交頭接耳商量著。
幾分鐘后,又有一名村民發(fā)問:“為什么要修消防通道?如果是國家規(guī)定必須建的話,那這個錢是村里出還是國家出?”在這場不斷有專業(yè)術(shù)語蹦出的設(shè)計方案陳述中,“消防通道”是村民最清楚的名詞之一。
沉默一打破,后面的問題就源源不斷。比如,活動中心的選址,村干部把選擇權(quán)完全交給村民。
“當(dāng)然建在村子中心。”年長的村民希望活動中心就建在家門口,平日里散散步就能到達(dá)。
村里的年輕人可不這么想:“辦大活動肯定有不少人開車出行,村子中心都是老宅子,壓根兒沒有停車的地方,還是建在新區(qū)方便”。
綜合村民的意見,活動中心最終選址在村子中心。為滿足停車需要,又專門在設(shè)計方案里增加了地下停車場。
“這會有點意思。”坐在后排的那些出門在外的年輕人,放下手機,抬起了頭。
“雖然是村干部,但權(quán)力不是你們的,意見應(yīng)該聽我們的。”會議結(jié)束后,有年輕人這樣說。
此后,力洋村關(guān)于活動中心的修建,又展開了為期一年多的討論。等動工時,村民發(fā)現(xiàn),不管是活動中心的選址,還是戲臺的朝向,都由他們做主。
有了這個開頭,徐建岳松了一口氣,他認(rèn)定,36條可以繼續(xù)推行。剩下的就是照葫蘆畫瓢了。
依照36條,海頭村村民否定了村干部購買餐廚垃圾生化機的提議。村里重點打造的菊花種植基地,當(dāng)初在選擇種植對象時,完全按程序交給村民決定。
“至少讓村民知道,這個不是暗箱操作。即使村民有爭議,即使需要花幾倍的時間,即使他們并非都能聽懂,我們也要公開。”徐建岳說。
你的村莊也是我的村莊
經(jīng)過一年“訓(xùn)練”,陳先良早已熟悉這套議事流程。這正是他一生所企盼的。
年輕的時候,陳先良是中學(xué)里的語文老師。站在講臺上,他常一字一頓地講“人民當(dāng)家做主”。可回到村里,他就感受到落差。自己站在講臺上所講的,很難在現(xiàn)實中得到印證。
20年前,大陳村對外承包100畝海塘。因價格低、承包期限長,村民紛紛找到村干部申請承包海塘。在陳先良的記憶里,村干部直接拍板,海塘就包出去了。“什么時候包?誰能承包?年限是多少?這些村民通通不知情”。
向來都是村干部說了算,村民們敢怒不敢言。海塘剛承包出去的那段時間,他總感覺“悶得慌”。覺得外面天氣陰沉沉,特別壓抑,吃完飯也懶得散步了。
“真是垂頭喪氣啊,就跟打了敗仗一樣。你想想,在家里,你沒有話語權(quán),說了不算,這村莊還是你的嗎?住得能舒服嗎?”陳先良低頭整了整帽子,“那跟現(xiàn)在怎么比啊?沒法比。”
那時,他在學(xué)校里講“人民當(dāng)家做主”時,總感覺有些荒唐。
直到2014年,他才重新審視了這幾個字的含義。讓他改變看法的,還是這100畝海塘。
這一年,大陳村嚴(yán)格按照36條規(guī)定的招標(biāo)流程,重新對外發(fā)包海塘。其中一個環(huán)節(jié),就是經(jīng)由陳先良參加的黨員大會的審議。
“信息都上網(wǎng)了,在電腦上還怎么作假啊。”說這話時,陳先良眼神放光。他用食指關(guān)節(jié)輕輕敲擊桌子,笑出了聲。
最終承包海塘的不是寧海縣人,價格高出本村人的投標(biāo)價。這讓陳先良很高興:“集體經(jīng)濟(jì)嘛,當(dāng)然是價錢越高我們越開心啦。”
這一件事兒,讓這名曾經(jīng)的人民教師,終于找到了當(dāng)家做主的感覺,他也開始關(guān)注村子里的大小事務(wù)。
村子里的一些人,也有了與陳先良一樣的轉(zhuǎn)變。陳先良注意到,就在祠堂門口的兩只石獅子旁,參與討論村里事務(wù)的人員構(gòu)成發(fā)生了變化。
剛開始,只有村干部會站在祠堂門口那兩只石獅子旁交談。慢慢地,一些黨員和村民代表也會圍在石獅子兩側(cè),議論村里的事兒。再往后,村民有事沒事就會聚在石獅子前,站著、坐著、聊著、閑逛著。河道治理、污水處理、道路改造工程,全是大家討論的內(nèi)容。
“這時候不分什么代表啊、村干部啊這些,你的村子也是我的村子,商量的都是家里的事。”從村民代表那聽聽開會討論的情況,像圍住一個說書人,能持續(xù)整整一上午。
這樣的景象,在寧海別的村子里也能看到。幾乎每個村子,都有聊天長廊。村子里的很多重大事務(wù),都是在這個長廊里討論出來的。這也正應(yīng)了寧海的一句老話,“六眼無私”,意思是6只眼睛看到的、多個人見證的,就很難出現(xiàn)作弊的事兒。
陳先良一直記得祖祖輩輩傳下來的老規(guī)矩,因此他對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格外重視。
又一個周二,村里的黨員會議就要在祠堂召開。陳先良照例穿上那身老式藍(lán)呢子中山裝,系好風(fēng)紀(jì)扣。他雙手交叉背在身后,走路略有蹣跚,在邁進(jìn)祠堂里的那幾步,陳先良特意挺直了歷經(jīng)74年的腰板。
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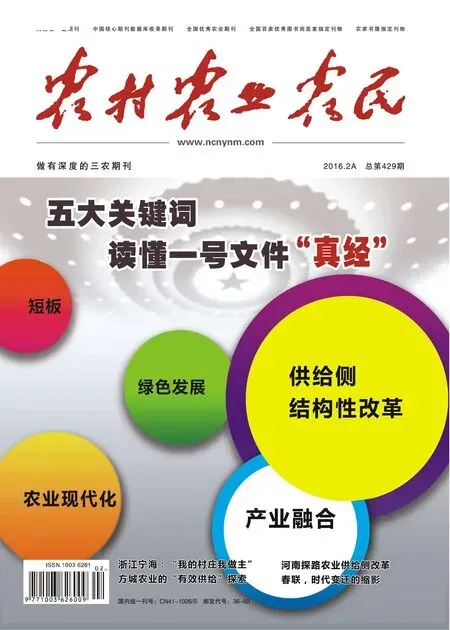 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2016年3期
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2016年3期
- 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農(nóng)民的其它文章
- 以新理念培厚農(nóng)業(yè)土壤
- 用新理念破解新難題
- 在貝加爾湖畔慢慢老去
- 方城農(nóng)業(yè)的“有效供給”探索
- 我國農(nóng)業(yè)保險開啟黃金年代
- 小鳥摘枇杷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