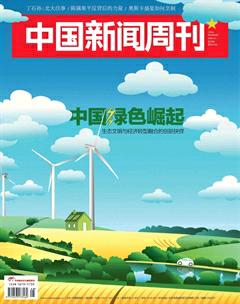小傘兵可安好
曹紅蓓
林紫心理機構北京
中心副主任咨詢師
前一陣美國的中國小留學生凌霸案宣判,引發了人們對降落傘少年的精神健康的關注。之所以叫他們降落傘少年,最初是指那些小留學生,少不經事的年紀,背著父母打包好的夢想,被空投在異國他鄉的土地上。父母盼著他們就此生根發芽,結出果實,而所有的過程,都將在父母的視野之外,悄然發生。
降落傘少年在心理上會遇到什么?首先是更嚴峻的身份認同的挑戰。12-17歲青春期少年最大的心理發展任務,就是自我身份的認同,即回答“我是誰”的問題,包括:我是哪里人?我是男的女的?我是窮人還是富人?我漂亮嗎強壯嗎?我有沒有擅長的東西?我是受歡迎還是不受歡迎?等等這類的具體問題。發展心理學的研究顯示,青春期少年每天要回答的自我認同問題多達幾十種,心里的小情緒經常像坐過山車一樣起起落落,為了回答這些問題忙不過來,而且每一回的答案經常是相左的。
不過別擔心,如果環境穩定,一切如是發展,在少年心中,所有這些疑問隨著時間的推移終究會塵埃落定,水落石出。這是正常的情況,如果你想給正常的情況制造干擾,增加難度,你可以大舉改變少年的生長環境,比如把他空投到異國他鄉。
也許你會想,異國他鄉除了語言改變,別的不是都更容易了嗎,在中國這種復雜的環境中都沒問題,出了國到那些更規矩祥和的地方還有什么不能適應的?很多人都會低估語言的意義,對改變語言的憂傷視而不見。語言其實是人類最核心的心理構件之一。很多智力優異的人就是學不好外語,其實是個心理和文化選擇的問題。改變語言本身是讓少年更加懵懂的第一大挑戰,同時,環境的變化,也讓上面那些所有必須要回答的身份認同問題,被攪得更亂。
除了環境改變造成青春期身份認同的更大挑戰以外,社會支持變少,又使所有的困難雪上加霜。社會支持是個心理學概念,有點像我們日常說的關系網、親友團,但更偏重情感方面。降落傘少年一個人輕身而去,父母本人不僅只能留在視頻,他們能幫助少年們搞定的具體事情也大幅縮水,比如這次凌霸案里的父母想用錢平事的企圖落空。
降落傘少年要面對的心理困難,是每個小留學生都要面對的。然而并非所有的小留學生都是降落傘少年。仍有至少一名父母陪讀的之外,也有很多的小留學生不能說只是被父母空投到異國他鄉,他們的求學路,更多是自己一步步走過來;他們的背包里,除了父母的錢和夢想,裝的主要還是自己的志趣和能力。90年代出國留學,都得有全獎,就像早年買房的錢都要自己掙一樣,幾乎沒有家庭有空投孩子的財力。等到獲得出國的機會,人也大了,力也長了,自己的斤兩自己知道,出了國也沒那么容易懵懂。現如今,仍有部分真正有能力和志趣的小留學生。當他們克服了比在國內更大的困難終于完成自我身份認同的時候,他們會是更加開闊和有彈性的人。
降落傘少年不僅出現在小留學生群體里,一些超齡的降落傘少年在國內也能看得到,《老炮兒》里的小飛就是。他爸是南方的大員,他經常降落在北京的夜三環,飆車、闖禍,懵懂得不行。心理咨詢業在國內方興未艾,一些出得起高額咨詢費長期咨詢的年輕人里,能看到一些降落傘少年的典型故事:畢業于京外高校,應屆就被空投到了北京人人眼饞的大國企里,有編制,有戶口,有房,有車,從不用跟人合租,可以夜夜笙歌不息,日日海外代購,經常在爸爸給買的車里以淚洗面,在裝修講究的房里用頭撞墻,上班如同上刑,最重要的,特別難愛,他們不清楚到底是誰在愛里,自己究竟有什么可愛之處以及別人為什么愛他們。比這些再普通一點的家庭,父母做生意掙了些家底的,把孩子空投到北京的國際學校里就接著忙去了,結果這些小傘兵和差不多背景的青春期懵懂們同病相憐地在一起,過了一些風云激蕩的殘酷生涯,最后留下幾個刺青,成功地丟了自己。
從一般意義上講,自己從產道爬出來比剖宮產要好。要想孩子登山,幫他修臺階永遠比直接把他投放到山頂要好,如果他完全不知道來時路,一旦山頂不舒服,可能就會跳崖。所以無論是到北京還是到紐約,能不采取空投就不采取空投,且要在18歲之前盡到監護的責任。實在空投擋不住,那也要提前不斷訓練他,清楚區分哪些是他自己的,哪些是他老爸的,千萬不要跟孩子說:我的就是你的,你的就是我的,連你也是我的。他是你的孩子,他更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