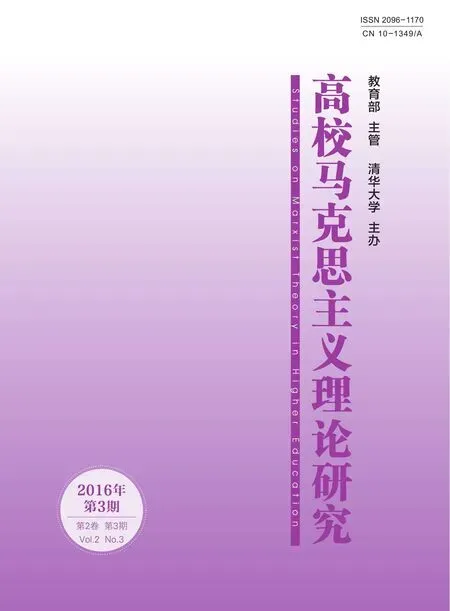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鄒廣文
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思想及其時代意義
鄒廣文
[內容提要] 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作為其所創立的唯物史觀的重要組成部分,集中表達了如下內涵:市場經濟、工業文明和資產階級是人類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助推器,而人類世界歷史實踐所產生的精神成果將是“世界的文學”的形成,世界歷史的未來圖景是共產主義。當代中國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思想的時代回應,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
馬克思;恩格斯;世界歷史;普遍交往;命運共同體
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作為其唯物史觀的有機組成部分,在其思想體系中居于重要地位。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高度概括了人類由大工業和普遍交往所開創的各個國家和民族走向“一體化”的歷史時代,從而揭示了人類歷史的整體性和有機性。今天,人類全球化的發展圖景日益清晰,全世界各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呈現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統一格局。在此時代情勢下,認真領會和解讀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對于我們分析人類社會發展歷史、把握經濟全球化發展動向并有效破解全球化難題,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馬克思對于世界歷史思想的首次完整表述,見于1845年秋季至1846年夏季其與恩格斯合作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在馬克思看來,世界歷史不是通常的、歷史學意義上的世界史即整個人類歷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和國家通過普遍交往而進入相互依存的狀態,進而使世界整體化發展的歷史。而這種世界歷史的呈現是與近代以來資本主義登上人類歷史舞臺相關聯的。馬克思用“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1]541這一命題表征了這一人類歷史趨勢。在之后撰寫的《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更進一步指出,世界歷史并不是各個民族歷史的簡單相加,而是世界各個民族相互依賴、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所形成的歷史整體。任何一個民族或地區的發展都是世界整體的有機組成部分,其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受到世界歷史的影響;與之相對應,各個民族或國家的發展又深刻影響著世界歷史的發展。
我們知道,在馬克思恩格斯之前,系統地對世界歷史觀念進行闡發的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他在其《法哲學原理》和《歷史哲學》中指出,歷史并不是雜亂無章的偶然性堆積,歷史在其演化中存在著內在的規律性,沖破狹窄的地域范圍,由民族歷史匯成世界歷史就是其中的規律之一。黑格爾認為世界歷史是“理性”“精神”的展開和實現。理性統治了世界,世界歷史的本原和基礎是“客觀精神”,“客觀精神”是世界的主宰,世界歷史則是這個絕對終極目的的實現和體現。由于這種體現,這一絕對終極目的就從內部世界不僅過渡到自然界現象,而且過渡到精神界現象,亦即過渡到世界歷史的現象。馬克思恩格斯認為,黑格爾的世界歷史理論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是用虛構出來的“精神”來解釋世界歷史,因而當然不能正確解釋世界歷史。在克服和批判黑格爾唯心史觀的同時,馬克思恩格斯繼承了黑格爾世界歷史理論的合理內核,即歷史發展的世界性和規律性思想,認為世界歷史是人類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人類歷史的發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民族歷史向世界歷史的演變并不是絕對精神的運動,而是現實的社會生產力推動的結果。
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突出表達了以下基本邏輯內涵。
第一,市場經濟與工業文明是人類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助推器。
馬克思認為,自近代以來,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產力獲得了普遍的發展。以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為標志,人類在全球范圍內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人種大交換與物種大交換,人類活動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和障礙,形成全球范圍內各民族之間全面的互相往來和互相依賴的趨勢和過程,從此徹底改變了世界的面貌。“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2]35世界歷史的形成要以生產力、分工和交往的發展為物質基礎,代表先進生產力的現代工業的建立已成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關的問題。“工業的歷史和工業的已經生成的對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開了的關于人的本質力量的書,是感性地擺在我們面前的人的心理學。”[1]192馬克思認為,前資本主義的歷史都是狹隘地域性的民族歷史,只有隨著生產力、分工和交往的高度發展以及大工業的出現,人類活動才開始突破地域等的限制,世界歷史才開始形成,這是一種客觀歷史規律和趨勢:“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不是‘自我意識’、世界精神或者某個形而上學幽靈的某種純粹的抽象行動,而是完全物質的、可以通過經驗證明的行動,每一個過著實際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個人都可以證明這種行動。”[1]541工業化大生產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用機器的操作代替了人工勞動,也就是說,人類勞動的各種代替物日益增多,效力日益增大,工業化生產使人類社會實現了歷史上的劃時代飛躍:“自從蒸汽和新的工具機把舊的工場手工業變成大工業以后,在資產階級領導下造成的生產力,就以前所未聞的速度和前所未聞的規模發展起來了。”[3]隨著每一個國家和民族進入世界歷史,每一個人也都改變了原先那種孤立隔絕的生存狀態,進入發展的同步時空,和世界市場緊密地聯系著。大工業和市場改變了每一個人的生活,也改變了每一個人,使大家趨向更多的共同性,這就使狹隘的地域性的個人為世界歷史性的、真正普遍的個人所代替了。因此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大工業和世界市場首次開創了世界歷史,開創了全球化發展的歷史。
第二,資產階級在人類走向世界歷史的實踐中扮演了雙重角色。
馬克思恩格斯基于歷史與價值的雙重視角,對資產階級在人類走向世界歷史的實踐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精當分析。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站在歷史主義立場,充分肯定了資產階級在推進世界歷史形成過程中所起的決定性作用,認為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到過非常革命的作用,尤其是在促進生產力發展、推進工業化大生產方面所起的作用:“資產階級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治中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2]36作為新時代生產力的代表,資產階級挖掉了工業腳下的民族基礎,民族性發展須納入世界的一體化格局之中。尤其是世界市場的開辟,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資產階級通過發揮其革命作用,確立了新的生產關系,并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用現代大工業替代工場手工業甚至封建行會的經營方式,使得生產成本急劇下降,創造了顛覆世界的生產力。在某種意義上講,資產階級促進了技術進步,提高了社會生活水平,這是資產階級最主要的歷史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馬克思恩格斯也從人文關懷的視角,對于資產階級在開辟世界市場過程中的種種野蠻血腥行為進行了價值控訴。馬克思恩格斯把19世紀德國浪漫主義對于資產階級的美學批判轉變為意識形態批判和政治經濟學批判,認為貪婪是資本主義的本性,“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4]。“資產階級撕下了罩在家庭關系上的含情脈脈的面紗,把這種關系變成了純粹的金錢關系。”[2]34馬克思看到資本主義雖然在其殖民地摧毀了舊的社會結構,帶來一定程度的現代化,但卻也給殖民地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世界上少數人的發展是以犧牲絕大多數人的發展為代價的,因此指出資本主義的殖民統治是一種“海盜式的侵略”,其中充滿著血腥與殘酷。在《不列顛在印度統治的未來結果》一文中,馬克思清醒地指出:“在印度人自己還沒有強大到能夠完全擺脫英國的枷鎖以前,印度人是不會收獲到不列顛資產階級在他們中間播下的新的社會因素所結的果實的。”[2]690另外,馬克思強調資本主義在全球一體化的推進過程中,客觀上造成了世界呈現“中心-外圍”結構體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們不想滅亡的話——采用資產階級的生產方式。……一句話,它按照自己的面貌為自己創造出一個世界。……正像它使農村從屬于城市一樣,它使未開化和半開化的國家從屬于文明的國家,使農民的民族從屬于資產階級的民族,使東方從屬于西方”[2]35-36。這個龐大的體系是以西方發達國家為中心,以東方和其他落后地區為邊緣;以現代化城市為中心,以自然形成的城市和鄉村為邊緣;以大多數資本家為中心,以廣大的工人和勞動人民為邊緣的。結果是,一方面,處于中心的社會和國家控制著世界市場,斂取絕大部分的產品附加值,掠奪巨大的財富;而另一方面,處于外圍或更邊緣的國家則深受中心國家的剝削和控制,不但分享不到世界一體化所帶來的好處,反而日益貧困,導致其地位更加邊緣化。
第三,人類世界歷史實踐所產生的精神成果,將是“世界的文學”的形成。
馬克思恩格斯認為,生產力迅速發展,與此相適應,在人們的社會文化生活領域,它將促成世界性的文化交流與文明進步:“過去那種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給自足和閉關自守狀態,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來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賴所代替了。物質的生產是如此,精神的生產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產品成了公共的財產。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為不可能,于是由許多種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學形成了一種世界的文學。”[2]35馬克思恩格斯這里所講的“世界的文學”不是一個純文學概念,而是一個包括文學、藝術、哲學、科學等在內的廣義文化概念,它根植于工業生產和世界貿易等全球化物質基礎上的現實和必然。它的現實意義在于剔除了民族間的隔閡,克服了本民族的局限性,達成互通互利,把各民族創造的精神產品變成世界各民族都能共同欣賞的公共文化產品。“各個相互影響的活動范圍在這個發展進程中越是擴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由于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間的分工消滅得越是徹底,歷史也就越是成為世界歷史。”[1]540-541市場經濟與工業文明使現在的社會成為實質意義上的“人類”社會。在此之前,諸多孤立發展的人們并不具有現實“人類性”,而世界歷史的現實呈現則使每個人的行為都成為人類社會體系中的一個有機環節,使每個民族、國家的發展都匯入了人類發展歷史的洪流中來,彼此不可分割,于是每個民族甚至每個人的發展、發明都會迅速傳遍全球,這就避免了隔絕狀態下人們所走的歷史彎路,加速了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馬克思恩格斯特別強調,置身于世界一體化的發展之外,處在封閉狹隘地域的人是不可能獲得真正解放的,“每一個單個人的解放的程度是與歷史完全轉變為世界歷史的程度一致的”[1]541。世界歷史所呈現的“現代性”實踐,開啟了人類的普遍性交往時代,相應帶來了人們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革,并以其特定的方式打破了從前的一切秩序,每個人都在親身經歷并感受著與世界歷史的直接聯系。
第四,世界歷史的未來圖景是共產主義。
共產主義是馬克思恩格斯畢生為之奮斗的理想。但在他們看來,共產主義作為一項世界歷史性的偉大事業,需要在世界歷史中完成,“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就像共產主義——它的事業——只有作為‘世界歷史性的’的存在才有可能實現一樣”[1]539。共產主義是世界歷史性的事業,共產主義不能作為某種地域性的東西而存在,因此絕不能把共產主義狹隘化、民族化,理解為孤立的地域性的存在。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指出,無產階級是推進共產主義事業的主體,是在世界歷史范圍內普遍存在的階級,無產階級的世界性決定了它所肩負的共產主義事業的世界性,所以交往的任何擴大都會消滅地域性的共產主義而達成普遍的世界交往。對于未來人類社會的發展圖景,馬克思恩格斯曾經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用“共同體”(Gemeinschaft)或“聯合體”(Assoziation)等相關概念作了表達,意指一種揚棄了階級對立的共產主義社會理想。真正意義的世界歷史乃是全人類獲得徹底解放的歷史。這就是說,人類在沒有消滅私有制、消滅階級、消滅勞動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義的世界歷史的。因此,世界歷史的形成是與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即實現共產主義緊緊聯系在一起的。總之,無產階級只有在世界歷史意義上才能存在,與之相應,共產主義事業作為一種“世界歷史性的共同活動”[1]542,只有在世界歷史未來圖景的意義上才能真正凸顯其深邃的歷史內涵。
今天,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時間跨越,馬克思恩格斯所闡發的世界歷史圖景更為真切地呈現于我們的社會生活中,經濟全球化貫穿于世界各個國家與民族的社會發展實踐。尤其對于致力于改革開放、走向世界的中國來說,領會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就顯得更加意味深長:中國的改革開放需要在更廣闊的世界時空中展開,因為一個民族不走向世界、融入世界歷史,就難以擺脫封閉和僵化的格局,就不能借鑒世界發展的成果。中華民族只有積極主動地融入世界歷史大潮,才有可能引領世界歷史,進而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
現如今,人類的文明進入到了一個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和文明間交往日益密切的新的發展階段。2013年3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傳遞了對人類文明未來走向的中國判斷:“這個世界,各國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類生活在同一個地球村里,生活在歷史和現實交匯的同一個時空里,越來越成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運共同體。”[5]2015年9月,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習近平更是明確地向世界各國呼吁:“為了和平,我們要牢固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6]據不完全統計,從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在各種場合對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強調達60余次,這一方面表現了當代中國領導人的世界情懷,同時也清晰地向世界傳遞了這樣一個信息:人類文明是一個有機的整體,未來世界各國只有通過進一步推進不同文化形態間的交流互鑒,人類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
顯然,習近平同志對未來人類文明將走向“命運共同體”的判斷,與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性。眾所周知,現時代發展的突出特點是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化多樣化和社會信息化。特別是隨著資本的全球擴張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出現了一系列全球性問題,如糧食安全、資源短缺、氣候變化、網絡攻擊、人口爆炸、環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國犯罪,等等。這些問題的出現及其造成的影響是全球性的,而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有賴于全世界各國的通力合作。面對這一時代情勢,我們亟待呼喚和培育一種以應對人類共同挑戰為目的的全球價值觀,并逐步獲得國際共識。習近平同志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體現了對中國與世界互動發展特征的清晰認識和把握。和平與發展是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不變的價值訴求,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同志對“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作出了多角度的闡釋:從“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判斷,到“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的感言;從“牢固樹立命運共同體意識”的號召,到“讓命運共同體意識在周邊國家落地生根”的部署;從“共筑亞太夢想”的呼吁,到“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方案的提出。我們從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的核心價值訴求——堅持求同存異、和而不同,努力把握人類利益和價值的通約性,在國與國關系中尋找最大公約數。
理論是時代的心聲。立足現時代的問題與挑戰,重溫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歷史思想,我們或許能夠從中感悟出別樣的時代意義。
第一,要樹立極限意識,致力于人與自然和諧關系的全球共建。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學者沃德和杜博斯主編的著作《只有一個地球》問世,書名如警世之鐘,在旁征博引、絲絲入扣的論證中表達著強烈的憂患意識: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不同人群,共同擁有唯一的地球,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極限意識”。的確,不同的人群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可以有貧富之別,可以占有不同份額的資源,但今天的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有一點是平等的,即我們只有同一個地球。人類要生存,社會要發展,就必須擁有一個能與人類長期和諧共處的自然環境。告別盲目的發展狀態,共同建立起一種全球性的生態文明,這是保證人類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基礎。因此,未來人類的實踐行為必須自覺關注現代生態文明的重建,展示人類文明發展的真正意蘊。
第二,要注意守護文化的多樣性,在文化的一元與多元之間找到平衡和張力。文化多樣性問題是伴隨著全球化與現代性的歷史節奏凸顯于我們的時代生活中的。本來,文化多樣性是世界的“原生態”,但是今天的全球化卻加劇了不同文化系統之間的緊張,使得人類文化多樣性面臨嚴重威脅。現代性的一元邏輯日益成為改變人們日常生活的發展要素,高效率、標準化、整齊劃一取代了文化的個性化追求,人類文化發展的多樣性被消弭。文化發展的實際情形常常是強勢文化對于弱勢文化采取了“文化霸權”或“文化殖民”,并將自己的文化價值觀強加于對方。今天,人類作為命運共同體,必須倡導文化多樣性,這種文化多樣性既是對文化個性與特殊性的表達,也是人類共同文化品質的展示,正所謂“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只有尊重文化多樣性,尊重文化的獨立性、異質性和完整性,我們才能深切感受到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
第三,要堅持合作共贏原則,合力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文明。不可否認,在當今世界,仍然存在著不同的國家利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識形態以及不同的社會制度的分歧和對立,冷戰思維還時不時充斥于國際關系中。但是不管怎樣,我們是命運共同體,只有超越冷戰思維、零和博弈和各種偏見的藩籬,超越種族、文化、國家與意識形態的界限,讓共同利益壓倒分歧對立,作出和平共處、有序競爭以及合作共贏的明智選擇,世界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從這一價值訴求來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不啻為推動世界和平與發展給出了一個理智可行的行動方案。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建構過程,也是人類新文明和世界新秩序的生成過程。要實現這一歷史使命,絕非一日之功,更難憑一國之力,需要各國持續不斷地共同努力。正如習近平所強調的,不管今后國際風云如何變幻,我們都要始終如一地高舉“人類命運共同體”這面旗幟,都要全力以赴地引導國際社會與我們相向而行,共同推動這個歷史進程。
第四,要努力培育人類世界歷史實踐的中國經驗。當代中國所堅持和奉行的和平發展道路,是一條促進不同文明開放包容、交流互鑒,推動各國相互尊重、合作共贏,推動世界共享和平、共同發展的道路。中國人民致力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追求的不僅是中國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國人民共同的福祉,只要有利于增強這一福祉,不管什么樣的文化要素,我們都可以吸收,都可以包容。置身于這樣一個世界大變局的發展時代,從容步入世界舞臺中心的中國,沒有理由不向世界貢獻出人類世界歷史實踐的中國經驗。從這個角度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提出,就集中體現了對當今復雜多變的國際局勢及未來時代發展的中國判斷,展現了應對當前挑戰、加強全球治理、開創人類美好明天的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隨著當代中國的和平崛起,中國在世界未來發展中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倡導包容性的多邊主義外交理念,建構更加開放、公正和有效的世界秩序,這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和目標。由世界大國走向世界強國,不僅僅意味著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長,還意味著責任意識的增強,需要我們為人類未來的世界歷史發展實踐提出更多的中國方案、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為國際社會提供更多的公共產品,要更加積極有為地促進世界的和諧發展、共同發展與可持續發展。
[1]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48.
[4] 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5] 習近平.順應時代前進潮流促進世界和平發展——在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的演講[N].人民日報,2013-03-24(2).
[6]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N].人民日報,2015-09-03(2).
(編輯:李成旺)
鄒廣文,哲學博士,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