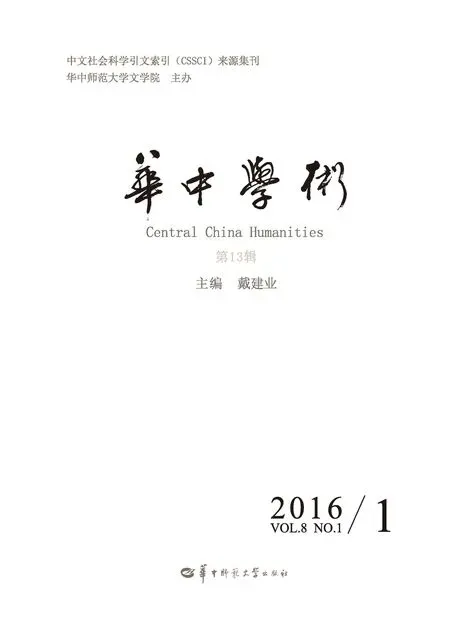阿寄事跡考論
張世敏
(上饒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江西上饒,334001)
?
阿寄事跡考論
張世敏
(上饒師范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江西上饒,334001)
內容摘要:義仆阿寄的故事在明清兩代廣為流傳,按文獻類別可分為文集、小說、史志三支,故事的源頭不是寧稼雨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所說的文言小說《阿寄傳》,而是《田叔禾小集》中的《阿寄》一文。阿寄故事正好發生、流傳于明初禁奴與明末奴變之間,通過對文獻進行解讀,可知在禁奴與奴變之間,還有一個過渡時期。在過渡期,士大夫階層一方面繞過禁奴政令,已默認了庶民蓄奴的事實;另一方面在主奴關系松動甚至主奴秩序顛倒時,士大夫希望通過樹立道德榜樣來維系奴仆忠于主人的關系。各種文獻中的阿寄故事承載著士大夫們重構主仆關系的理想。
關鍵詞:阿寄;田汝成;禁奴;奴變
阿寄是明代嚴州府淳安縣徐家的奴仆,同時也是一位販漆商人,五十多歲后,以十二兩白銀作為資本,為寡婦主母掙得巨萬資產。從其身份來看,阿寄在明代是不折不扣的小人物;然而,這位小人物的傳記被《明史》、《浙江通志》等史志文獻與《田叔禾小集》、《明文海》、《焚書》等集部文獻收錄,故事在《續說郛》、《五朝小說大觀》、《舊小說》、《醒世恒言》、《無聲戲》等小說中廣為傳揚。一位小人物被明清兩代士人普遍關注,是值得我們關注的文化現象;在明代商品經濟繁榮的社會背景下,阿寄具有奴仆與商人雙重身份,是研究明代商品經濟與封建政治相互沖突難得的樣本。本文將對阿寄故事的源流進行考證,并在此基礎上,通過阿寄故事這一獨特視角,對明代社會中的奴仆現象進行論述。
一、阿寄事跡源流考
明清記錄、敷演阿寄事跡的文獻數量較多,文集、筆記小說、通俗小說、地方志、正史等文體均記述了其事跡,這些支流應當有一個共同的源頭。其源頭在哪里,各個支流之間又是什么關系,是需要我們探討的兩個問題。
(一)阿寄故事的源頭
對于阿寄故事的源頭,學界至今未做嚴密的考證,僅寧稼雨在《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中略有提及,該書介紹道:《阿寄傳》,“明代傳奇小說。未見著錄。現有《續說郛》、《五朝小說大觀》本等《明史》、《浙江通志》、《嚴州府志》等均據以立傳”[1]。據此論述,阿寄傳的源頭是一部稱為《阿寄傳》的文言小說,且未見之前文獻著錄。這一觀點看起來似乎是持之有據的,乾隆《浙江通志》中阿寄本傳開篇便交代傳記資料來源于“田汝成《阿寄傳》”[2]。明代《吳興備志》施奶婆傳后,有作者董斯張的按語云:“范蔚宗傳李次公,近世田叔禾傳阿寄。施奶婆者,不可為萬世人臣法哉?”[3]李贄《焚書》在收錄《阿寄傳》時,也明確指出:“錢塘田豫陽汝成有《阿寄傳》。”[4]這些文獻都將阿寄故事的源頭,指向田汝成的《阿寄傳》。因此,寧氏關于《阿寄傳》故事源頭的結論還可商榷。
第一,從版本上看,《續說郛》中的《阿寄傳》并非現在可見到的阿寄故事的最早版本。寧氏認為作為阿寄故事源頭的文言小說《阿寄傳》未見著錄,最早見之于《續說郛》。《續說郛》的作者陶珽生于萬歷元年,主要生活于萬歷年間,因此,《說郛傳》的成書當在萬歷或萬歷之后,離阿寄故事發生時的嘉靖已有較長時間。事實上,早在嘉靖年間,田汝成《田叔禾小集》便收錄了阿寄傳記,篇名為《阿寄》,與《續說郛》的阿寄故事內容高度一致,可視為同一故事的不同版本。《田叔禾小集》刊刻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是“汝成晚年令其子藝蘅所編,凡詩文三百六十九首,五十以后所作,均不在是焉”[5]。《田叔禾小集》在編定時作者還在世,且五十歲后的作品不收錄,說明其中的《阿寄》相比其他能見到的版本要早。《田叔禾小集》是在田汝成授意之下,由其子編定的,因此,該集中所收《阿寄》當更加可靠。
第二,從文體與內容上看,記述阿寄故事的文章在明清時期一般都被視為散文而非小說。阿寄之文有兩個版本,一個版本題名為《阿寄》,另一個版本題名為《阿寄傳》,通過比對可發現,兩者之間內容高度一致,僅有細小差別。題名《阿寄》的版本最早見于《田叔禾小集》卷六,全文如下:
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別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二牛,季寡婦得阿寄。阿寄年五十余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踉蹌老仆,乃費我藜羮!”阿寄嘆曰:“噫!主謂我力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悉簪珥之屬,得銀一十二兩畀寄。寄則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立致矣。”又二十年而致產數萬金,為寡婦嫁三女,婚兩郎,赍聘皆千金。又延師教兩郎,既皆輸粟為太學生,而寡婦則阜然財雄一邑矣。頃之,阿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馬牛之報盡矣。”出衴中二楮,則家計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言訖而終。徐氏諸孫或疑寄私蓄者,竊啟其篋,無寸絲粒粟之儲焉,一嫗一兒,僅敝缊掩體而已。嗚呼!阿寄之事,予蓋聞之俞鳴和云。夫臣之于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于父也,有骨肉之愛。然垂纓曳綬者,或不諱為盜臣五都之豪。為父行賈,匿良獻苦否,且德色也。乃阿寄村鄙之民,衰邁之叟,相嫠人撫髫種而株守薄業,戶祚彫落,溝壑在念,非素聞《詩》、《禮》之風,心激寵榮之慕也。乃肯畢心殫力,昌振镃基,公爾忘私,斃而后已。是豈尋常所可及哉!鳴和又曰:“阿寄老矣,見徐氏之族,雖幼必拜。騎而遇諸途,必控勒將數百武以為常。見主母不睇視,女使雖幼,非傳言不離立也。”若然,即縉紳讀書明禮義者何以加諸。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6]
此文收入《明文海》卷四百三,題名《阿寄》;收入《文章辨體匯選》卷五百三十七,題名《阿寄傳》。還有《焚書》卷五所錄《阿寄傳》。各種文獻中的《阿寄傳》與《阿寄》之間的差異,僅在于“仲得二牛”作“仲得一牛”。明代各種阿寄傳記之間雖然高度相似,但也存在規律性的差別,即題為《阿寄》者都作“仲得二牛”,題為《阿寄傳》者都作“仲得一牛”。無論是《阿寄》還是《阿寄傳》,都被收入別集或總集中,由此可知,阿寄的傳記在明清時期大多被視為傳記散文。即使阿寄故事后來被《續說郛》等小說集收錄,題名《阿寄傳》,然其內容也與之前作為散文存在的《阿寄傳》完全一致。小說《阿寄傳》完全可視為散文《阿寄傳》變換文體之后的改頭換面。
第三,從史志編撰原則上來看,正史與方志在修撰時一般不會取材于筆記小說。正史與地方志作為官修史書,特別注重內容的真實可信,即使是明清兩代地方志良莠不齊,其真實性頗受懷疑,甚至被等同于筆記小說,被稱為清言叢書[7],但很難找到正史與地方志取材于筆記小說的記錄。而正史、地方志取材于文集的記述很是常見,章學誠在《文史通義》中記道:“國史不得已,而下取于家譜志狀、文集記述,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8]“傳狀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譜牒,一家之史也;部府縣志,一國之史也;綜紀一朝,天下之史也……所屬之中,家修其譜,人撰其傳志狀述,必呈其副……銘金刻石,紀事摛辭,必摩其本,而藏之于科可也。”[9]章學誠所論,說明文集記述、家乘譜牒、地方志、正史,都具有史的性質,材料可以相互為用。由此可見,即使內容完全一樣,作為文人傳記的《阿寄傳》可以被正史與地方志采用,但作為筆記小說的《阿寄傳》則不大可能被正史與地方志采用。
綜上所述,阿寄故事的源頭只能是田汝成為阿寄所作傳記,寧氏所言《明史》與方志據小說為阿寄立傳之說不確。
(二)阿寄故事的流別
記述、敷演阿寄故事的明清文獻種類較多,導致阿寄故事形成了幾個支流,有以文人傳記為代表的文集一脈,有以筆記小說、通俗小說為代表的小說一脈,有以正史、地方志為代表的史志一脈。阿寄故事的不同的流別之間關系密切。
文集中的阿寄傳記是其他各個流別的源頭,是其他兩類文獻記述與敷演的基礎。在田汝成《田叔禾小集》之后,李贄《焚書》收錄了《阿寄傳》并對故事做了評述,《明文海》、《文章辨體匯選》則分別收錄了阿寄傳記,這說明明清文人對阿寄故事有持久的關注。
筆記小說《阿寄傳》,內容與散文《阿寄傳》并沒有實質性差異,只是文體歸類時對文體的理解有分歧而已。通俗小說《醒世恒言》中的《徐老仆義憤成家》,與田汝成的《阿寄》之間有直接的淵源關系。《徐老仆義憤成家》相對《阿寄》來說,故事更加具體,故事發生的地點具體到了村子,徐家三兄弟的姓名,寡婦的姓氏,以及阿寄經商的經過等,都有詳細記載,但故事梗概卻與《阿寄》完全一致,阿寄經商的本錢都是十二兩。
《明史》、《浙江通志》以及《嚴州府志》等正史與地方志為阿寄所立之傳,完全以田汝成《阿寄》作為底本縮略而成。以《明史·阿寄傳》為例,傳云:
阿寄者,淳安徐氏仆也。徐氏昆弟析產而居,伯得一馬,仲得一牛,季寡婦得阿寄,時年五十余矣。寡婦泣曰:“馬則乘,牛則耕,老仆何益。”寄嘆曰:“主謂我不若牛馬耶!”乃畫策營生,示可用狀。寡婦盡脫簪珥,得白金十二兩畀寄。寄入山販漆,期年而三倍其息。謂寡婦曰:“主無憂,富可致矣。”歷二十年,積資巨萬,為寡婦嫁三女,婚二子,赍聘皆千金。又延師教二子,輸粟為太學生。自是,寡婦財雄一邑。及寄病且死,謂寡婦曰:“老奴牛馬之報盡矣。”出枕中二籍,則家巨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兩郎君,可世守也。”既歿,或疑其有私,竊啟其篋,無一金蓄,所遺一嫗一兒,僅敝缊掩體而已。[10]
通過對比可發現,《明史·阿寄傳》除了做過將“阿寄年五十余矣”改成“時年五十余矣”等改動之外,相對于田汝成的《阿寄》,沒有幾個字是創作的,可以說是“縮而不作”。《浙江通志》與《嚴州府志》中的阿寄傳也大抵類于《明史》。
通過對阿寄故事的流別進行梳理可以發現,文集中的阿寄傳記自成一脈,是小說、史志這兩個流別的文獻源頭。小說中的阿寄故事是對文集傳記的敷演,史志中的阿寄傳記則是對文集傳記的節錄。文集中的阿寄傳記通過小說的敷演成故事而在普通大眾之間傳播,通過史志的收錄而被主流意識形態接受,進而對整個社會產生更大的影響。
二、阿寄與明代奴仆
阿寄是一位典型的義仆,其故事在明清兩代廣為傳揚,文集、筆記小說、通俗小說、正史、地方志等不同種類的文獻,都記載了他的事跡,有的還對其事跡進行了評論,這為我們從不同視角審視阿寄形象提供了文獻依據。在明代奴仆史上,有兩個關鍵詞,一是明代前期的禁奴,一是明代后期的奴變。田汝成主要生活在嘉靖年間,其文集《田叔禾小集》也成書于嘉靖年間,阿寄之事是田汝成耳聞之時事,據此可知《阿寄傳》當作于嘉靖年間。從現存的眾多文獻可知,阿寄是士大夫階層為了特定目的樹立的義仆形象,故事又正好發生在明前期禁奴與明后期奴變的轉折點上,因此,阿寄為我們研究明代奴仆史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一)禁奴與士人對庶民蓄奴的接受
明朝建立后,下層出身的朱元璋在一定范圍內推行了禁奴政策。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頒布詔令,規定“士庶之家毋收養閹豎,其功臣不在此例”[11]。蓄奴的特權被限定在功臣這一很小的范圍內。洪武三十五年(1382)頒布的《大明律》也規定:“若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12]按照《大明律》規定,蓄奴的資格稍稍放寬,只要是非庶民的一般官員,蓄奴也不違法,但朱元璋禁奴詔令的基本精神在《大明律》中得到了延續。上述詔令與法令,在明初得到了不折不扣的執行,為此,牛建強論道:“朱元璋在推行各項政令的過程中,使用鐵腕,令到即行。可以肯定,其限制庶民使用奴婢的政策在當時是產生了實際效果的。”[13]
與明初相比,明中期的禁奴情況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蓄奴法令在民間被全面突破,自弘治、正德開始,“追求奢華消費的取向已成為全國帶有明顯整體性特征的普遍現象”,“明代中后期奴仆現象的大量化和普遍化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14]。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找到足夠的證據證明,即使是到了嘉靖年間,庶民蓄奴依然未被官方正式接受。嘉靖年間擔任過刑部郎中的雷夢麟為限制庶民蓄奴,再次強調“若庶民之家存養奴婢者,杖一百,即放從良”[15]。通過對比,可以發現庶民蓄奴的普遍性與禁止庶民蓄奴的法令之間,已經存在矛盾沖突。相對于政府近乎頑固地維護《大明律》禁止庶民蓄奴的政令,夾在政府與庶民之間的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態度更能代表當時社會對于庶民蓄奴的接受程度。
根據阿寄的故事資料,可知阿寄是庶民所蓄之奴。前面所引各類記述阿寄故事的傳記、小說等都出自士大夫之手,從這些文獻的字里行間,我們可以發現士大夫對庶民蓄奴的態度。田汝誠《阿寄》一文在記述阿寄之事時,說阿寄是“淳安徐氏仆也”,阿寄臨死之時說道:“老奴馬牛之報盡矣。”文中直言阿寄的奴仆身份,與官方文件中所載明代士庶在買賣奴仆時,往往“皆不書為奴為婢,而曰義男義女”[16]有著很大的差別。不僅如此,田汝誠還把阿寄與主人的關系,比作君臣、父子關系,在傳末發表議論,說道:“夫臣之于君也,有爵祿之榮;子之于父也,有骨肉之愛……移此心也以奉其君親,雖謂之大忠純孝可也。”細味田汝誠之論,徐氏蓄奴,阿寄為主盡忠似與君臣、父子關系一樣理所當然,沒有什么不妥之處。《元明事類鈔》以及馮夢龍《徐老仆義憤成家》等文獻在記述阿寄之事時,同樣也對阿寄的奴仆身份直言不諱。這說明在庶民蓄奴已成為常態的明代中晚期,士大夫已接受了這種現實,與政府維護《大明律》禁止庶民蓄奴之間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受文人傳記的影響,《吳興備志》、《浙江通志》、《嚴州府志》等史志在撰寫阿寄的傳記時,也對阿寄的奴仆身份直言不諱,這說明士大夫漠視《大明律》禁奴條款的心態,已蔓延到主流意識形態,明初的禁奴令,到了明中期之后,已成一紙具文。
(二)奴變與理想的主仆關系
蓄奴在明中期以后成為普遍現象,奴仆的人數便會積累達到一定的規模。按照民間的約定俗成,奴仆在賣身時,“即立身契,終身不敢雁行立”,“子孫累世,不得脫籍”[17]。在奴仆與主人矛盾的推動下,發生奴變便成為順理成章的事。對于明代奴變,早在20世紀初就有不少學者注意到,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謝國楨的《明季奴變考》,吳晗的《明代的奴隸和奴變》,傅衣凌的《明季奴變史料拾補》等。根據這些研究成果可知,奴變在明代晚期頻繁發生。
實際上,早在明中期,自上而下都發生了奴變,《萬歷野獲編》卷十八“宮婢肆逆”條載:“嘉靖壬寅年,宮婢相結行弒,用繩系上喉,翻布塞上口。”[18]身為九五之尊的皇帝,也身陷奴變之險境。宮門之外,除了有奴變之外,由于商品經濟的快速發展,奴仆通過經商完成了資本的積累,因此,很多奴仆在經濟上已能夠與主人抗衡,或者在經濟實力上凌駕于主人之上,原來奴仆依附于主人的關系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被沖破。主要生活在嘉靖與萬歷年間的管志道對此現象曾有過激烈抨擊,他說:“近乃有起家巨萬之豪仆聯姻士流,多挾富而欺其主;亦有奮跡賢科之義孫通名仕籍,則挾貴而卑其主。”[19]奴仆傲主到明末更是變本加厲,顧炎武曾言:仆人一旦得勢,“則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于出處語默,無一不受其節制,有甘于毀名喪節而不顧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20]。
在明中期以后自上到下奴仆鉗制主人甚至發生奴變的社會大背景下,構建理想的主仆關系,是士大夫階層必須面對與思考的問題。阿寄作為一名仆人,其故事在文集、小說、史志廣為記述傳揚,實際上承載著士大夫階層重構主仆關系的理想。各類與阿寄故事相關的文獻,大部分在講述故事時會夾雜著對主仆關系的議論。例如:
李卓吾曰:“父子天性也。子而逆天,天性何在?夫兒尚不知有父母,尚不念昔者乳哺顧復之恩矣,而奴反能致孝以事其主。然則其天定者雖奴亦自可托,而況友朋!雖奴亦能致孝,而況父子!彼所謂天性者,不過測度之語;所謂讀書知孝弟者,不過一時無可奈何之辭耳。奴與主何親也?奴于書何嘗識一字也?是故吾獨于奴焉三嘆,是故不敢名之為奴,而直曰我以上人。且不但我以上人也,彼其視我正如奴矣。”[21]
馮夢龍曰:“為奴一日主人身。情恩同父子,名分等君臣。主若虐奴非正道,奴如欺主傷倫。能為義仆是良民。盛衰無改節,史冊可傳神……勸諭那世間為奴仆的,也學這般盡心盡力幫家做活,傳個美名;莫學那樣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的,被人唾罵。”[22]
李漁曰:“我道單百順所行之事,當與嘉靖年間之徐阿寄一樣流芳。”[23]
前文所引田汝成《阿寄》及以上議論性文字說明,明清兩代的文人士大夫們把主仆之間的關系,與君臣、父子之間的關系相互比照,奴仆忠于主人,就像臣子忠于君王,子女孝順父母一樣,是理所當然之事。在奴仆“背恩反噬,尾大不掉”習以為常的明代中后期,對主人忠而忘私的阿寄,被士大夫們樹立成踐行奴仆道德的標桿,李贄說阿寄是自己“以上人”,“彼其視我正如奴”,不是要否定阿寄的奴仆身份,而是要從道德上將阿寄無限抬高。《嚴州府志》、《浙江通志》以及《明史》中的阿寄本傳中,雖然未在傳中對阿寄之事有所評議,但史志收錄阿寄傳記本身就是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阿寄無言的肯定,也是最高的肯定。可以說,阿寄事跡之所以廣為傳揚,是因為奴變頻發、奴仆傲主成為常態的明代中后期,亟須一位道德上的奴仆標桿。明清兩代文人在書寫阿寄故事時,實際上包含著文人們重構主仆關系的理想。
三、結語
阿寄是明代具有代表性的義仆,士大夫階層以及史志的編撰者為樹立典范,使得其故事在文集、小說以及史志中廣為傳揚,其故事在傳播中相應地形成了文集、小說與史志三個分支。此前,小說領域的學者寧稼雨在編撰《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阿寄”條目時,將史志中阿寄故事的源頭追溯到文言小說《阿寄傳》,不僅有違史志編撰傳統,也與文獻相抵牾。事實上,明清兩代所有記述阿寄故事的文獻,其源頭都可以追溯到《田叔禾小集》中的《阿寄》一文。
阿寄故事發生在嘉靖前后,多種文獻中的阿寄形象,實際上是士大夫樹立的奴仆道德典范。在明代奴仆史上,明初的關鍵詞是禁奴,明末的關鍵詞是奴變。從阿寄故事這個視角來觀察明代奴仆史,可知在禁奴與奴變之間,還有一個過渡期。在過渡期,士大夫階層一方面繞過禁奴政令,已默認庶民蓄奴的事實;另一方面在主奴關系松動甚至主奴秩序顛倒的社會大背景下,士大夫希望通過樹立道德榜樣來維系奴仆忠于主人的關系。各種文獻中的阿寄故事承載著士大夫們重構主仆關系的理想。
?本文系江西省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文學商品化與明代傳記文學新變研究”【14WX23】的階段性成果。
注釋:
[1]石昌渝:《中國古代小說總目·文言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頁。
[2](清)稽曾筠:《阿寄傳》,乾隆《浙江通志》卷一百八十九,《四庫全書》本。
[3](明)董斯張:《笄祎徴第六》,《吳興備志》卷十三,嘉業堂刊本。
[4](明)李贄:《阿寄傳》,《焚書》卷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94頁。
[5](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1583頁。
[6](明)田汝成:《阿寄》,《田叔禾小集》卷六,《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7](清)章學誠:《方志立三書議》,《文史通義》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73頁。
[8](清)章學誠:《方志立三書議》,《文史通義》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73頁。
[9](清)章學誠:《州縣請立志科議》,《文史通義》卷六,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588頁。
[10](清)張廷玉:《阿寄傳》,《明史》卷二百九十七,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第7615~7616頁。
[11](明)夏原吉等:《明太祖實錄》卷七三,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第1352頁。
[12](清)薛允升:《立嫡子違法》,《唐明律合編》卷十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277頁。
[13]牛建強:《明代奴仆與社會》,《史學月刊》,2002年第4期,第98~107頁。
[14]牛建強:《明代奴仆與社會》,《史學月刊》,2002年第4期,第98~107頁。
[15](明)雷夢麟:《人戶以籍為定》,《讀律瑣言》卷四,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22頁。
[16](清)薛允升:《良賤相毆》,《唐明律合編》卷二十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年,第595~596頁。
[17]佚名:《研堂見聞雜記》,臺北:大通書局,1987年,第30頁。
[18](明)沈德符:《宮婢肆逆》,《萬歷野獲編》卷十八,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469頁。
[19](明)管志道:《分別官民家奴婢義男因以春秋之法正主仆議》,《從先維俗議》卷二,《太昆先哲遺書》本。
[20](明)顧炎武:《奴仆》,《日知錄》卷十三,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767頁。
[21](明)李贄:《阿寄傳》,《焚書》卷五,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第594~595頁。
[22](明)馮夢龍:《徐老仆義憤成家》,《醒世恒言》卷三十五,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第722、726頁。
[23](清)李漁:《兒孫棄骸骨僮仆奔喪》,《無聲戲》第十一回,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20頁。
主持人語 這里披載的四篇論文,都不是所謂的宏觀研究,而是扎扎實實地針對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有相當成就和影響的作家與作品展開的研究。四篇論文所涉問題各不相同,論述風格也因人而異,其觀點雖不能說都是可以讓學界同仁認同或接受,但都能持之有據地成一家之言。這也許就是這四篇論文最可寶貴的品格。
武漢大學陳國恩教授的《世紀焦慮與歷史邏輯——林語堂論中國文化的幾點啟示》一文,是陳教授提供給紀念林語堂先生誕辰12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該論文以較為新穎和獨到的視角——世紀焦慮與歷史邏輯,著重論述了林語堂對于中國文化既批判又肯定的復雜內容,較為有力地辨析了林語堂以西方文化肯定中國文化的意義、價值以及所留存的缺憾。其觀點,都是從材料而出,所以,具有相當強勁的說服力。更為可貴的是,作者還由此闡述了林語堂論中國文化的觀點對于今天我們弘揚傳統文化的啟示性意義,從而拓展了自己對一個具體對象研究的意義,也當然顯示了作者論文的現實意義與價值。
作為青年學者的云南師大孫淑芳與中南民族大學楊潔梅的論文,則很直接地顯示了青年研究者的風格——敢于嘗試,勇于創新。孫淑芳的論文選擇了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界公認的較為繁難的跨藝術的格局來研究魯迅《故事新編》中的油滑與戲劇的關系,其框架及格局都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所列舉和分析的事例不僅具有相當的說服力,而且也較為新穎。可以說是為學界從戲劇的角度來透視魯迅《故事新編》中的油滑問題提供了自己的一家之言。楊潔梅論沈從文《邊城》的論文,其中的一些觀點也許學界同仁不一定認為是作者的創建,但作者在論述問題過程中所顯示出來的才氣,卻是不能否認的,至少作為主持人,我是很直觀地感受到了的,也十分欣賞。這也就是為什么我欣然將該文在此披載的重要原因。
許祖華的論文是一篇細讀經典的論文,其細讀所選擇的角度是話語與修辭,其中對魯迅《傷逝》所采用的兩種修辭手法的分析,雖不能說已經盡善盡美,但也經受得起相應的推敲,有些觀點雖為一家之言,但也言之成理。(許祖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