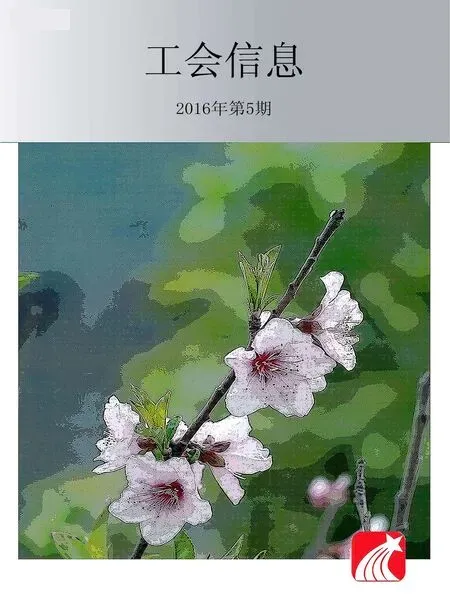一個院士眼中的生老病死
中國工程院院士 秦伯益 口述 健康時報記者葉正興 整理
一個院士眼中的生老病死
中國工程院院士 秦伯益 口述 健康時報記者葉正興 整理
精彩閱讀
■“病人是醫生的衣食父母,醫生是病人的救命恩人”,這兩句話沿用上千年,本義沒錯。然而,現在卻常常容易引起誤會,病人誤以為“我是你的父母,你該關照我”,醫生認為“我是你的恩人,你應該感恩”,如果大家彼此這樣要求,醫患關系就好不了了。歸其根本,關鍵還是我們的基礎教育有問題。
■我不刻意養生,但健康狀況不錯,目前可以用八個字來概括:清楚、通暢、不高、不大。清楚,頭腦眼睛耳朵感官清楚;通暢,呼吸道和兩便(大小便)通暢;不高,血壓血脂血糖不高;不大,前列腺和肝脾不大。我的各種化驗結果,直到今年都還正常,一輩子沒有住過醫院。
■我很欣賞廣東省委老書記任仲夷的樂觀態度。60多歲時,一只眼睛瞎了,他說我照樣“一目了然”;過了幾年,耳朵聾了,他說我“偏聽了”但 “不偏信”。又再過幾年,膽囊不行,摘了,他說我渾身是膽了,照樣大膽改革;到了80多歲時,胃不行了,大部分被切除后,他又大笑著說,反正到這個年齡了,“無所謂(胃)”了,這樣一直活到92歲。
■我們都希望健康長壽,享盡天年,無疾而終。我印象中,能無疾而終的人多半健康長壽,之所以健康長壽,是因為器官內臟均衡地衰老,衰老到一定程度后,瓜熟蒂落,一了百了,這種走法是最好的。
人的一生,從出生到老去,從染病到死去,處處離不開醫學關懷。作為與疾病和藥物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貢獻卓著的藥理、毒理學家,83歲的秦伯益對人的生老病死與醫學的關系有著很深的感悟。
近日,在中國醫藥教育大會暨中泰慢病防治國際論壇上,秦伯益講述了自己對待生老病死的樂觀心態,啟人心智,令人深思。
生 愛心教育和理性教育
“病人是醫生的衣食父母,醫生是病人的救命恩人”,這兩句話沿用上千年,本義沒錯。然而,現在卻常常容易引起誤會,病人誤以為“我是你的父母,你該關照我”,醫生認為“我是你的恩人,你應該感恩”,如果大家彼此這樣要求,醫患關系就好不了了。
此時,醫學人文的性質就變了,變成“有付出,有報酬”的單一回饋形式,歸其根本,關鍵還是我們的基礎教育有問題。
人從呱呱落地,就開始面對教育,這貫穿了人的一生。教育的規律應是以人為中心,按人的生理、心理、心智發育過程來設計教育內容和教育方法,其中愛心教育和理性教育尤為重要。有了愛心,有了理性才能是完整的人;如果從基礎教育起,培養的是沒有愛心和理性的人,長大就會闖大禍。
那么,一生的教育應如何去做?出生前6年的學前階段,小孩從媽媽體內子宮剛出來,什么都不懂,充滿好奇,實際上他是在觀察和了解周圍環境,我們應放手讓他去探究、多問問題,給予簡單易懂的回答,啟發他去思考;
而到了小學,接觸外界范圍擴大,認識不同的人,關鍵應是培養愛心,愛父母、愛老師、愛同學、公共財物、個人衛生,以及對家鄉的愛;
多一些愛心教育,少一些仇恨教育;多一些道和理,少一些技和術。只有有了愛心,有了理性才能是完整的人。
上高中后,就應該培養理性,學會思考,學習哲學、邏輯學、公民學等。而到了大學,更重要的是培養人格,能不能說真話,能不能堅持真理,在各種壓力面前,能不能堅持獨立的人格,這將決定一個人能否成為堂堂正正、頂天立地的人。
現在學生的條件比起我們上世紀50年代上學的教科書多了三、四倍,但是細細看來,理的教育并不多,全都是技和術。英國哲學家弗蘭西斯·培根說過“知識就是力量”,然而,只有讀者用自己的思維和智慧去將知識實踐,付諸行動,才會產生力量,取得成功,從知識到力量是一個轉化和放大的過程。如果到了大學以后,還是滿堂灌課就大錯特錯了。
有一次,國家教委安排培訓全國優秀中學老師,一連三屆讓我去講課,培訓內容包括了文科和理科的關系,文學精神和科學精神的關系,卻獨獨沒有“公民課”的內容。
會后主持會議的司長對我說,現在“公民課”放在“政治課”里了。我說,政治課里講的公民是遵守紀律,遵紀守法,權利義務,做合格的螺絲釘;而公民課里講公民,第一句話就講公民是國家的主人翁,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要培養獨立人格的公民,有誠信和契約精神。這一點上,思想政治課顯然代替不了這些課程,而這正是我們現在教育最缺乏的一環。
老 老年健康貴在心態
不必刻意養生,一切順其自然。
從直立猿人到智人,再進化到現在已經300萬年,古代人平均壽命50多年,現代人的骨骼、肌肉、關節、內臟使用時間已遠遠超出古代,我現在83歲,已遠遠超過各器官的“保質期”,出問題也不奇怪,關鍵是要有好的心態,做到身心健康,預防保健,定期體檢,早診早治。
我目前的健康情況可以概括為八個字,清楚、通暢、不高、不大。清楚,頭腦眼睛耳朵感官清楚;通暢,呼吸道和兩便(大小便)通暢;不高,血壓血脂血糖不高;不大,前列腺和肝脾不大。各種化驗結果都還正常,這輩子沒有住過一天醫院。
老年健康,貴在心態,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活法。人生角色,總在不斷轉化,不要一條路走到底。我主張,在位時,全力以赴,廢寢忘食,義無反顧;退位時,欣然領命,戛然而止,飄然而去。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要活得瀟灑,懂得享受老年的快樂。如果在位時,磨磨蹭蹭,拖拖拉拉,不當回事,退位時,這也沒做,那也還想做,戀棧不去,那就沒意思。
回顧自己一生最快樂的時候,就是退休以后這十多年來的時光。因為責任已盡,負擔已除,經濟無虞,身體還好,感悟人生,懂得了生活,也知道已經到這個年齡,夕陽晚霞,稍縱即逝。要抓緊每一天,稍微一放松,就沒了;我會珍惜每一天,過好每一天的生活。
老年人有成熟之樂,天倫之樂,發揮個性之樂,孤獨之樂。一個人在時,有最大的思想空間,具有和書中的古人溝通,和世界上萬事萬物思想溝通的條件和智慧,不受各種打攪和干擾,獲得一些自己想享受的心靈愉悅。陳獨秀曾說過,做學問最好的是兩個地方,一個是實驗室,一個是在監獄,是否真正會生活的人,關鍵在是否有興趣和追求。
很多大藝術家、大思想家、大科學家,創造性高潮來臨的時候,往往是在靜中、夜中、雨中、枕中、獄中、病中。真正會生活的人是不會寂寞的,我就沒有寂寞的時候,一天到晚有干不完的事情,現在每天不到1點不熄燈,去年此時,我不到2點不睡覺。
老年最大的快樂就是,知足常樂,自得其樂,助人為樂。年輕的時候,賺錢是快活的,老年的時候,用的地方對,能雪中送炭是快樂;我們一生艱苦,晚年幸福愉快,觀念也可相應調整。無所求就無所失,大徹大悟后就沒有大悲大痛。
病 醫生安慰的不同解讀
人類未必能夠消滅疾病,而疾病也肯定消滅不了人類。醫學不斷在進步,但醫學也有它的局限性,例如結核菌產生了耐藥,它迫使我們研究,但仍有8%耐多藥結核不好治。
醫學歷史上,有位著名的特魯多醫生,1848年,他誕生在美國紐約撒拉納克湖旁,25歲醫學院畢業開始從醫,卻發現自己就是肺結核患者。肺結核,在當時以為是絕癥,他回到老家療養,通過營養加強,空氣環境改善,騎馬、散步、打獵,有所好轉,但回到紐約后又因勞累而病情反復;37歲時,他辭退工作,在老家建立世界上第一家結核病療養院。
100年前的1915年,特魯多67歲去世,患結核多年的他比當時美國平均壽命還長。他臨終時說了三句著名的話,刻在墓碑上,作為墓志銘,很多醫生去美國旅游,都會前去吊唁。
“To cure,sometimes;to relieve,often;to comfort,always”(有時去治療,常常去緩解,總是去安慰)。可是,現在這句話被宣傳過頭成了誤導,似乎要讓病人知道,我們的醫生只能總去安慰,來緩解醫患矛盾。
我很不同意這樣的說法,因為這不是事實。病人半夜三更去排隊,就診三五分鐘,只是去求個安慰?那還不如去佛堂拜菩薩。
我認為這句話可以作些修正,應該是“T o cure,in time;to relieve,anytime;to comfort,sometimes”(及時去治愈,隨時去幫助,有時去安慰)。安慰,是需要安慰時去安慰,不需要去安慰時沒意義。面對絕癥,能治就治,不能治就別治。不必過分強調醫生的安慰作用,醫生的安慰也不只是微笑、和藹、客氣。
如果我是病人,我對我的醫生只要求兩點,如果你能做到這兩點,我信你,把整個性命交給你。一是站在我面前,讓我感覺醫生是個有氣質和風度的人,一位嚴肅認真思考我的問題的人,仁愛,認真,知識博學,技術精湛,這樣的醫生我信任;二是講真情,說真話,哪怕只有三天可活也要如實告訴我,讓我做好這三天的事。
任仲夷,是一位我很敬重的長者,他對疾病樂觀的精神很讓我佩服。作為廣東省委老書記,他是建設深圳特區、為改革開放殺出一條血路的領導人。60多歲時,他的一只眼睛瞎了,但是他說我照樣“一目了然”;過了幾年,耳朵聾了,他說我“偏聽了”,但我“不偏信”。又再過幾年,膽囊切除了,卻照樣大膽改革,他說我現在“渾身是膽了”(膽汁往血液流);到了八九十歲時,胃不行了,大部分被切除后,又大笑著說,反正到這個年齡了,“無所謂(胃)”了,沒有也不要緊了,一直活到92歲,他對廣東和深圳的開發都起著決定性作用。
死走要走得安詳有尊嚴
人固有一死,或輕于鴻毛;或輝煌一生,或窩囊一世;或健康長壽,無疾而終,或久病纏身,生不如死;或走得舒坦、安詳、有尊嚴,或走得痛苦、凄涼。
東西方人有著不同的生死觀。孔夫子有言,“不知生焉知死”,孝子是不能在父母面前談“老”的。自古以來,中國人俗話說,好死不如賴活著,盡管賴活著遠不如好死。西方人有宗教信仰,靈魂和肉體是附著在一體的,死亡的狀態是歸宿、圓寂、涅槃、超度和凈土。
在我10歲那年,爺爺去世,棺材放在廳堂里祭天,客人們紛紛吊唁,家屬哭聲不斷。到了第三天,哭不動了,突然看到兩個老太婆大哭,后來知道是職業哭喪婆。原來,悲的氣氛也可以拿錢制造,讓我幼年的心靈就知道,婚喪喜慶全要花錢,不一定都是感情,有些禮儀都是靠錢換來的。
西方人死去,會當面談死亡的問題,親人圍著臨終的病人讀圣經、唱詩、聽悲樂,安靜地送家人走最后一段路。這或許就是文化的不同。有本書叫《死亡如此多情》,里面有句“我的死亡誰做主?”我明確地回答:“我的死亡我做主”。我會書面列出“生前預囑”,也希望“生前預囑”問題能得到全國人大的立法解決。
另外,臨終關懷,在中國也應該發展起來。1967年,英國女醫生西塞莉·桑德斯博士首先在英國倫敦圣·克里斯托弗建立臨終關懷醫院。我曾經到這家醫院訪問,在一間大活動室里,那些病人有的看畫報、打撲克,有的織毛衣、看書、看電視、聊天,他們的壽命都不會超過一個月。臨終的病人,前一個月還能享受正常的生活,讓我很受觸動。
圣·克里斯托弗臨終關懷醫院的院長告訴我,對于這些病人,一是對癥藥物用夠,過去我國嗎啡一般是10mg,用到100mg以上就很擔心,而英國一般會用到1g,多的時候到2~3g;二是安慰,我國照顧臨終病人的全部壓力都在醫護人員,但英國卻有五種人(心理學家、醫護人員、社工、志愿者、牧師)去疏導各種不同時期的心理障礙。
中國的志愿者很少,牧師更是基本沒有,中國志愿者都是學生有組織地去,回來寫一篇日記,按應試內容在做;而英國的醫院里,每天會公布病人情況,包括年齡、性別、職業,社會人員會很自然地利用休息時間主動預約,同一行業領域的人會很親切、無償的聊他們生活和了解的事情,形成一種愉快的文化氛圍。
死亡,是人生最后的歸宿,我們應該直面歸宿,走得安詳舒坦有尊嚴,至少不要制造新的痛苦。比如,呼吸心跳停止后,用機器搶救叫生命支持系統,我不同意這個名稱,用替代系統維持已經結束的生命,是自己騙自己。
最近,我為三聯書店的新書《死亡如此多情2》作序,我明確地寫著:迫于道義和輿論而過度搶救不是上策,出于感情而無意義地救治并不理性,為了救治絕癥患者而傾家蕩產沒有必要,家屬為了保持高干待遇而讓已經瀕臨死亡的親人長期住在ICU搶救徒受痛苦形同虐待,讓植物人長期住醫院很不人道。
我們都希望健康長壽,享盡天年,無疾而終。我的印象中,能無疾而終的人多半是健康長壽的,之所以健康長壽,是因為器官內臟均衡地衰老,如果衰老到一定程度,瓜熟蒂落,一了百了,這種走法是最好的。
我對自己臨終的態度:搶救啊,復蘇啊,切開啊,插管啊,除顫啊,統統不要,我的預囑準備這樣寫,我疼痛了鎮痛要用夠,我煩躁了鎮靜安眠藥用夠,臨走時請告訴大家,我曾經是一個長壽而快樂的老頭,我充分享受了人生,我知足了。就請放一曲舒曼的《夢幻曲》或者薩克斯管的《Going home》!我回家啦!
摘編自《健康時報》